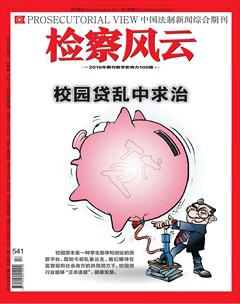遏制異形,人工智能需終極契約
宋穎
《異形:契約》是一部由美國20世紀福克斯拍攝的科幻電影片,屬于《異形》系列前傳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為《普羅米修斯》的續篇,該電影中不僅傳承了以往系列中的太空科幻、恐怖元素,在畫面、音效的處理方面更加細膩,在節奏、整體氛圍的控制能力也越加成熟。
區別于亞洲影視突發性的視覺、聽覺驚悚,美式影劇的恐懼更來源于內心,異形中的終極思辨更不免讓人細思恐極——我們相對自己所造的物種仿生人而言,短板太多:從生理上我們難免衰老、死亡,從效率上學習、成長速度慢,判斷上極易帶有感情色彩,生存、適應能力更無法與機器人相比……自封萬物之靈的自負不免被擊垮,我們的文明是否盡顯疲態,是否已經淪為寄生蟲一般以依附為生?又是否真可能徹底出局?
尋求答案,或許要從契約開始破題。契約,既是本部電影的影名,又是民事法律關系的基本元素,還是電影中太空船船名。“契約號”一行人所接受的殖民任務讓人們不禁想起人類歷史上的“五月花號”。“五月花號”上的自治契約,恰是美國建國的奠基石,也是現在美國信仰自由、法律精神的源頭。正是基于這種互助、自律以及公權的讓渡,人們漸漸尋找到一種良好的自治系統,讓人類最終能夠跨越種族、文化、宗教的隔閡,進而互相交流、共同成長。
即便在人與艦體“老媽”之間,影片中也透露出相應的規則:即要冒著船體損壞危險下降至離地80公里時,需要相應授權方可為之,而下降至離地38公里時,則需要兩名以上的共同授權方可為之;包括沃爾特對大衛提出的關于是否犧牲自己去救人類的問題,沃爾特也回之以“這是職責”,類似的規則在影片中多處出現,但也正是這種各司其職的契約,方能保證星際旅行的順利與安全。
相反的是,被視為“完美”的初始仿生人大衛心中并沒有平等、協商、契約的規則意識。他從誕生之初就被賦予了太多優越感,以至于在探尋生命起源過程中,逐漸視其他物種包括人類為附庸,他定義自己為“造物主”。在他眼中,他只是以上帝的視角,默默地看自己創造的物種之間相互廝殺,他心目中只有弱肉強食、只有創造或者毀滅,因此“有時創造,要先毀滅”成為他的口頭禪,其他的物種包括人類對他而言絲毫沒有訂立平等契約的可能。
影息人散,現實問題的思索隨之而來,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人類是否會創造出類似大衛一樣最終反噬人類的智能機器人?人工智能的學習能力、進化速度令人驚訝,出現更高級、會自主思考的人工智能也只是時間問題,相對來說人類無疑弱爆。也正因為此,霍金也提出“徹底的人工智能”或許會徹底摒棄人類的擔心。
破除這種憂慮的,不能僅指望于技術層面的限制,更重要的還在于通過立法確立一種規則思維,這恰似人類關于克隆人的普遍禁止一般,最終要回歸到立法層面。人工智能也是一樣。從科技立法層面來說,人工智能越是高速發展,就越需要給它制定多條不可逾越的底線——不能讓人工智能產生“自我”的自主感覺;不能擁有類似于人類的心理活動;不能產生侵害人類身心的任何動機等等。
沒有尖牙利爪,并非龐然大物,弱小的人類從野獸的包圍中逐漸走向食物鏈頂端,憑借的不僅僅是個人創造的意識與能力,更有著群體互幫互助、原始契約的社會結構支撐。不僅如此,人類跳出了叢林規則,跨越食物鏈的低級追求,致力于讓各種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不斷發展,萬物之靈方才實至名歸。
更為重要的,人類的自省、自律,讓他們懂得不能以貪婪的毀滅者形象接管地球,而應致力于保護這個星球的物種多樣性,致力于讓這個星球更加美好,無論是能力克制也好,權力讓渡也罷,或許可以說是人類與這個星球的最佳契約。同樣,這種契約規則,也應該可以成為破解人工智能憂慮的必要路徑。
編輯:成韻 chengyunpipi@126.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