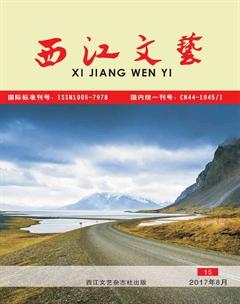自我觀念的比較:先秦儒家與近代西方
王曉瑩 王向陽
【摘要】:通過對先秦儒家和近代西方哲學中自我觀念的深入比較,揭示了中西方在自我觀念上的諸多差異及其原因,并探索了這種差異將中西方人引向何處及其對現代自我觀念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 自我觀念;自我;先秦儒家
一、先秦儒家的自我觀念與近代西方自我觀念的差異
(一)表達的差異
在西方語言中“我”基本上只能用一個代詞來表達(如:I ,Je, Ich, Ti, Te, Eu, Ik等),然而在中國尤其是古代語言中“我”卻能用一連串的代詞和名詞來表達(如:0g吾,予,余,已,身等)。從這些頻繁出現在先秦儒家經典中的“我”的同義詞,我們便可略窺先秦儒家哲學家們的自我觀念。作為一個生生不息的主體, “ 我” 本身具備完美的人格,它可以在交流、思考、自由選擇和與人的交往中展現出來,但又要通過后天教化來培養和發掘,最終每個“ 我”都可以成賢成圣。先秦儒家經典中有個詞叫做“反求諸己”,這是先秦儒家哲學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其中的“己”在先秦儒家對自我的探討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內涵。“子曰:‘為仁由己, 豈由人乎哉?”[1]“己”作為自我的體現,能夠在實踐行動中和交往中反映個體的道德修養,促使個體對自己的行為方式做出嚴格的審查,并激發個體的良知讓個體進行道德的反思和行動。這樣由“己”字所表達的自我觀念被賦予了一種道德涵義,成為個體自我修養和完善的核心。
在近代西方哲學的自我觀念中的自我多是“私”意義上的自我,它作為自我觀念的起點,基本上是一個不指涉任何他物的孤立存在。在以此為前提預設的近代西方哲學自我觀中,自我被塑造成了世界存在的前提及知識的來源,也成了區別他者的界限。從西方自我觀念發展的歷史來看:首先,在心理學視域下的自我(ego)既非主體, 又非客體, 而是各種各樣意識狀態和情感等內在狀態的匯集, 自我也并非單一的而是一束自我集:其次,傳統形而上學視域下,自我是一個不同于外界并與之相對的永恒的實體,它是每個個體獲得自我同一性的前提;最后,從認識論意義上來說,自我被視作與人的物理存在相對的靈魂,它是認識的主體,思維的核心。
(二)內涵的差異
1.作為道德的自我和意識的自我(ego)
不同于現代西方哲學的自我觀念總是與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分析密切聯系,先秦儒家在研究人的內在思想時,并未把自我視作是孤立的,在各種潛意識的欲望所支配下,持久不變的心理意識活動的主體。而總是把它與個體的社會角色和道德修養相結合,更加注重自我與他人的交往聯系和道德性自我的社會意義。從思孟學派的傳統來看,每個人生來就是善的,都可以成為圣人,但一個人最終成為什么樣的人仍需要自我進行正確的選擇。而荀子一脈則認為人性本惡,他區分了自我的動物性和人性兩個方面,旨在通過后天的道德教化和禮法規范來促使自我由前者向后者轉變。然而無論是這種自我的選擇還是轉化都不僅僅是簡單的在個人心理結構中便可以完成心理反省過程,而是需要在個體與他人的社會實踐交往溝通中才能建構和實現的。先秦儒家諸子遵從簡單的自然法則和整體觀念來實現自我,使自我與自我之間和諧相處,所以并未經歷過西方自我確認的心理陣痛。但這種自我實現途徑有時也要把握好尺度,不然就會讓自我湮滅于集體之中,從而成為他者實現的工具。
在近代西方,自我作為意識活動不變的主體是完全獨立的,既獨立于身體也獨立于外部世界。西方近代經驗主義者認為,自我不過是個體內在的知覺主體,除了能被它知覺到的東西,其他的東西都不是真實的。大衛·休謨走的更遠,他甚至不承認這種獨立的作為知覺主體的自我的存在。休謨認為自我所知覺到的僅僅是飛逝的感覺、知覺和思想。個體并沒有一個關于自我的實體的印象,自我的觀念不過是一個虛構,是一束知覺,休謨還證明它不過是源自于時空連續性和個體的相似性聯想。休謨的思想和方法對后來的哲學家啟發很大,使他們把原本與個體相關的所有的東西都歸于隨后成為意識客體的經驗。隨后的現代心靈哲學家更是提出了一個區別于普通主體自我的客觀的自我,最終又回歸到一個沒有外延的思維主體。
2.作為屬性的自我與作為實體的自我
在先秦如家諸子看來,自我并非西方傳統哲學中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種形而上學意義上人的實體性,反而恰恰是一種人的屬性,一種稟授于天地中蘊含的天道的一種人的本質屬性——仁。孔子曾說“仁者,人也”[2]。“仁”作為先秦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內涵是極其豐富的,但簡單地從構字來說,“仁”是在“人”字右邊加了一個“二”,這就是說,只有在至少“二人”的交往互動關系中,才能給個體下定義。這也就說明了作為自我象征的“仁”必須在個體的交往生活中體現出來。這種作為屬性的自我不是個體區別他者的本質存在,也非西方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實體。個體的同一性要在個體與天道,社會和他人的多重關系中尋找。
3.統一的自我與分裂的自我
早在柏拉圖那里,西方人就開始把自我就被看作是一個能夠進行思考和沉思的精神性的靈魂。與之左的是,先秦儒家的自我概念很少被賦予“我思”的涵義。
在先秦儒家那里,“心”雖常常被賦予西方哲學中靈魂自我的涵義,而作為個體認知思考的器官存在,稱作認知之心。先秦儒家的道德自我先驗地賦予個體以良知之心,因此較少提到個體的內在復雜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先秦儒家沒有劃分清楚內在自我與外在自我的界限,只是表明他們認為這個界限不是那么絕對,他們的自我即使個體要認真體悟的東西,也是要去追求實現出來的東西,內外本是一致的也是一體的。自我即可以借助外在行為舉止的中介實現出來,也可以通過外形在的行為舉止被觀察到并加以判定分析,它是一個統一的一元的自我。
與先秦儒家相反,近代西方的笛卡爾式的“我思”式的自我確實一個二元的分裂的自我,不僅僅是身體與心靈分裂,還是個體與他者的分裂。這種心靈自我是私人性的,沒有廣延的,因此它獨立于身體存在并無法被他者所知曉,即便是自己也要通過反省才能夠知覺到。這種分裂直到現代分析哲學家賴爾那里才得到了徹底的清算。
二、差異形成的根源
(一)時代背景的影響
每個時代的思想都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系。先秦儒家自我觀念與近代西方自我觀念之間的差異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所產生的時代背景不同。先秦儒家的哲學家們生活在禮崩樂壞,連年混戰的春秋戰國時期,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亂世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代,各派思想在一起激蕩,最終醞釀出最具活力的中國文化。相較于認知的自我他們更看重道德的自我,看重其所帶來的整體社會效應。由于他們所處的這些時代,在這些思想家的身上無不有著一種強烈的救民于水火的責任感,一個人不僅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周圍的人負責,自覺承擔起對他者的義務。這種強烈的責任感與義務感最終滲入到他們的思想之中,從而在建構自我的過程中賦予自我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與義務感,使自我的實現和確認與他人和社會之間緊密相連,個體的自我不會單獨獲得意義,而是通過他者來獲得或在由其所處社會中的倫理地為所決定的。
(二)思維方式的不同
先秦儒家思想家所代表的中國古代人民善于運用整體性的類比求同思維方式,先秦時期便已流行天人合一之說,不是從主客對立的角度看待天與人的關系,而是從整體的角度去看待。把個人與宇宙相類比,每個個人都是一個小的宇宙。
而近代西方哲學家所代表的近西方人則善于運用分析比較的辨析求異思維方式,這使他們不會關注個體與他者的關系,只是極力突出個體與他者的不同。而且在研究自我時選取了個體的維度,只注重孤立地分析個體自我的復雜性,喜歡將自我作二元的劃分,從而把肉體的形軀之我與思維的心靈自我區分開來。從而造成了西方自我觀念肉體的長期分離。
(三)道德自我的保障基礎不同
近代西方哲學家在面對倫理學問題時都要預設一個超驗的最高裁決者或保證者,即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來保證他們能夠最終完成對倫理學問題的探討和對先天觀念的追溯,同樣的,個體的自我存在與價值也要靠此來保障,但這種保障是來自自我之外,靠信念和邏輯來支撐,但他們在追求個體同一時卻又要把這個最高的東西也驅逐出去。而在先秦儒家思想家那里他們在人的良知之心里找到了自我與天道的同一性,這種同一性最終成為了約束自我最強有力的道德命令。通過體現天道自我獲得完善和發展。儒家對道德自我思考的起點是人性和天生具有的感知能力——四端。
三、差異所造成的影響
先秦儒家對個體同一性的考察,從其現在的狀態關涉到其過去與未來。他們的自我觀念認為天道是其起源也是個體存在的基礎,只有當自我呈現出人性中所蘊含的天理時,個體才具有了真正的自我特征,此時個體與世界成為一個整體,自我的任何欲望都不會超越天道的底線,個體從心所欲不逾矩便達到了儒家所追求的圣人的境界。
儒家的自我觀念以引人成圣為最終目標。個體先天地擁有天道所賦予的德性,這些德性之源是人的良知,它揭示了人人都可以成圣成賢的基礎和可能性。孟子所講的四端是人人都具有的善根,只要把它們培育好,個體就能實現自我。除此之外儒家也提供了通過學習來達到圣人境界的方法,但這種學習必須是能夠把所學運用在實踐行動之中,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從而彰顯出作為道德自我的個體良知。圣人是儒家所設想的一種理想人格,他的修養已達到了十分完美的境地。圣人在自己身上體現出天道,復活了深植在每個個體心中的圣人理想和天道,從而不僅實現了自我的同一性,也實現了與整個人類的同一性,彰顯了宇宙的規律和天地之大美,從而與天地同一。
而在近代西方的自我觀念中,自我不是被設想為一個原子式的獨立存在就是被定義為一個與肉體相互分離的思維實體。這也造就了西方人常以區別于他人的孤立的獨特的自我為核心來指稱自己,這樣便導致西方文化總是特別注重肯定和保護個人的獨立性,這或許就是西方文化一向非常推崇個人主義的哲學根源之一。西方人他們特別注意將自己與他者區分開,以突顯出自己的個性和獨特性,彰顯出同他人不同的一面。任何時候都要劃分清楚彼此的界線,以確保每一個個體自我都擁有自主性與獨立性。
結 語
在現代西方哲學中一些哲學家也看到了傳統自我觀念存在的問題,他們開始建構一種新的自我觀念。這種新的自我觀念自覺不自覺地融合了先秦儒家的道德自我。它開始關涉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和自我對他者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在社會交往中確立自我,構建一種開放的關系中的自我而非封閉孤立的自我。這種自我構建在后來儒家的心學之中和西方的現象學運動中均有體現,這正是中西方自我觀念的殊途同歸。
參考文獻: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0頁.
[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6頁
[3]汪鳳炎,鄭 紅. 論中西方自我的差異[J]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1月第33卷 第1期
[4]姚新中著,焦國成,劉余莉譯.自我建構與同一性儒家的自我與一些西方自我觀念之比較[J]哲學譯叢.1995年02期
[5](美)羅伯特·C·所羅門 著,陳高華譯.哲學導論:綜合原典閱讀教程[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
作者簡介:王曉瑩(1992—),女,漢,籍貫: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在讀碩士研究生,單位:中央民族大學,研究方向:教育學;
王向陽(1990—),男,漢,籍貫:河南鄭州,在讀碩士研究生,單位:中央民族大學,研究方向: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