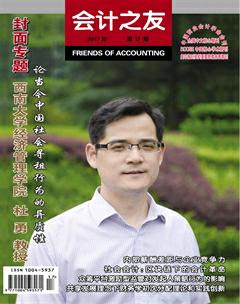論當今中國社會尋租行為的異質性
杜勇
【摘 要】 面對各類尋租行為日益增多的現實,“尋租”一詞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然而,無論是理論界的學者還是實務界的工作者都很少考慮到尋租行為之間的異質性。事實上,從我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和現實國情來看,目的不同的各種尋租行為之間存在本質差異。文章在對尋租行為產生的根源、尋租行為的內涵與特征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尋租行為劃分為公益性尋租和私利性尋租,并著重闡述了二者的區別和聯系,提出了要杜絕腐敗行為,現階段比較現實且可行的做法是走“識別尋租行為的異質性—嚴格規避私利性尋租行為—糾正公益性尋租行為—倡導社會責任、多方共贏理念”的過渡性路徑,并分別提出規避私利性尋租行為、糾正公益性尋租行為的有效措施。這對于拓展尋租行為異質性的理論研究和規范尋租主體的各種行為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 尋租行為; 政府干預; 公益性尋租; 私利性尋租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17-0002-06
一、尋租行為產生的根源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利益追逐呈現愈演愈烈之勢。謀取利益無外乎兩種方式:社會生產總量增加,其內部成員按原有的份額取得更多的產品;或者社會生產總量不變,部分內部成員爭取更大的份額以取得更多的產品。簡單舉例,前者通過把蛋糕做大,在蛋糕分配方法不變的情況下使全體成員獲利,稱之為“尋利”;后者保持蛋糕的大小不變,通過改變蛋糕的分配方法而使自己或部分成員或部分群體獲利,稱之為“尋租”。當然,處于轉型經濟時期的中國社會中,更多的是“尋利”和“尋租”兩種方式的結合,即尋租主體在做大蛋糕的同時改變蛋糕的分配方法,從更大蛋糕中為自己或部分成員或部分群體分享更多的利潤。
政府干預理論認為,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管制,妨礙了市場競爭的作用,從而創造了少數有特權者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安妮·克魯格(Anne Krueger)的論述,這種超額收入被稱為“租金”(Rent),謀求這種權力以獲得租金的活動,被稱作“尋租活動”,俗稱“尋租”。租金的根源來自對該種生產要素的需求提高而供給卻因種種因素難于增加而產生的差價。柯蘭得爾中給尋租下的定義是為了爭奪人為的財富轉移而浪費資源的活動,而克魯格則認為尋租是為了取得許可證和配額以獲得額外收益而進行的疏通活動[1]。尋租行為的產生和發展,與各類尋租主體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法律、文化等環境有關。結合我國的現實情境,本文分別從經濟資源的稀缺性、不成熟的市場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及監督制約機制的缺失等方面去分析中國現實社會中尋租行為產生的根源。
(一)經濟資源的稀缺性
相對于人的需求來說,資源都是稀缺的。稀缺的經濟資源主要有兩種配置方式,即分別由市場的供求關系這只“看不見的手”自行決定和由政府的行政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強制分配。市場調節通常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特征,政府能夠克服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功能和效率的不足。然而,政府在通過行政干預發揮“看得見的手”功能去彌補市場自由決定而導致的分配不均、分配低效以及分配滯后等缺陷的同時,也存在許多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如資源的浪費、低效率使用以及政治腐敗等。為了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人們普遍寄希望于“兩只手”的配合運用,以實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轉變。然而,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各類行為主體為了追逐各自或自己所在集體的利益,盡可能地利用各自所擁有的權力和掌握的信息優勢將本來就非常稀缺寶貴的資源自私地納入自身的腰包,從而滋生了“尋租”現象。從這層意義上來講,資源的稀缺性是引發各種尋租行為的導火索。
(二)現實市場的失靈性
現實中的市場往往是不完善的,它們或多或少都具有某些市場失靈的特征,如市場調節的滯后性、交易信息的非對策性、交易成本的高企性以及作用范圍的局限性等。首先,各類市場行為主體一般是根據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市場價格信號做出決策,然而,這種信號往往具有較長的滯后性,導致各類市場行為主體難以及時捕捉到市場信息的變化,從而做出非理性的決策。其次,對于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能夠進入市場流通的大多是盈利性的私人產品,極少涉及交通運輸、電力水利以及公共教育等社會公共產品,這便使得市場自我調節機制在這些涉及公共產品的領域難以發揮優化配置資源的功效,從而產生較大的信息不對稱和較高的交易成本。現實市場中表現出的各種形態的不完善必然引起市場的失靈,從而給各種非市場化因素乘虛而入的機會,此時,所謂的“潛規則”便得以大行其道。因此,現實市場自身的失靈為尋租行為的盛行提供了賴以生存的溫床。
(三)政府干預的過度性
市場失靈導致了政府介入,“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共同調節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人們企望使用政府力量來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2]。然而,政府自身也有缺陷,導致這只“看得見的手”也時常失效。政府官員的腐敗是政府失靈最典型的表現。在現有的行政任命和制度失效的環境中,難以避免一些政府官員在做出決策的過程中上會以為國家或社會服務的名義來為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團尋租,他們往往直接或間接地將公共資源轉移到與其利益相關的市場行為主體手中。此外,像勞動者就業、產品定價等問題的解決還只能依靠市場的供求關系自由決定,如果政府過度介入這些本該由市場自由決定的領域,只會使問題更加復雜化,而且會削弱市場機制自身的力量,最終可能導致權力過于集中、權力濫用,為尋租行為的滋生創造了機會。
(四)監督體系的缺陷性
雖然黨和國家大力推進深化改革,但是我國仍然存在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資源配置功能不甚成熟,法律法規相對滯后的現象,這使得資源配置功能不甚成熟,法律法規相對滯后,使得利益相關者鉆空子,打“擦邊球”,競相追逐尋租機會。特別是對權力掌控者的監督體系不完善,使得他們能夠通過設置進入門檻、限制供給等手段造成人為的資源稀缺,最終給一些組織或個人進行尋租活動創造了條件。此外,現行的法規對尋租行為的界定模糊,處罰力度不夠,難以起到震懾作用。由此,對權力掌控者監督體系的缺陷性為尋租行為的開展創造了外部環境條件。endprint
二、尋租行為的內涵與特征
(一)尋租行為的內涵
尋租理論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1967年塔洛克(Tullock)發表《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一文。塔洛克提出,當事人為達到目的會采取各種方法,包括游說、賄賂、欺詐、走私販私、偷稅漏稅等[3-5]。只是當時塔洛克并未使用“尋租”一詞,但他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就是后來發展起來的尋租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尋租作為一個理論概念,1974年由克魯格在《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正式提出。克魯格在分析發展中國家限制進口所引發的一系列經濟后果中,發現存在著大量的尋租活動,進而從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對經濟增長造成的影響角度出發,指出正是尋租活動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除了塔洛克和克魯格之外,另一位對尋租理論有著重要貢獻的學者是巴格瓦蒂,他提出的“直接非生產性尋利活動”概念,不僅涵蓋了政府干預條件下的尋租活動,還囊括了尋求政府干預的活動。自然,它也包括利用合法進口(繳納關稅)和非法進口(偷漏關稅)的差額取得額外收入的走私活動。尋租概念一經發現,其基本思想就在經濟學領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如微觀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國際貿易理論、政治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現代產業理論、發展經濟學等,而且它的主要思想和觀察方法也滲透到政治學、法學、社會學、行政學、管理學等眾多學科,為這些學科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
尋租,尤其是權力尋租,與“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有不少學者將“尋租”等同于“腐敗”,但尋租與腐敗終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首先,尋租屬于經濟學范疇,而腐敗是一個政治學、社會學的概念;其次,尋租,特別是權力尋租會滋生腐敗行為,然而腐敗行為并不僅僅包括尋租活動;此外,尋租活動未必會造成資源的浪費,但腐敗行為藐視法律,褻瀆公平,浪費社會資源,這是二者的最大差別所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尋租行為是發生在各方尋租主體之間的、為獲取某一方或幾方私有利益的故意行為。也就是說,尋租行為最終的獲益者可能是私人,也可能是某一團體或組織,而腐敗僅僅是尋租行為的一個極端表現。這里的利益所得,是指尋租活動參與者雙方均有利可圖。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尋租者不擇手段賄賂政府官員以獲取既得利益。在雙方博弈過程中,尋租者獲得的政策信息、稅收優惠即為尋租收益,而為此所付出的金錢、物質等形成了尋租成本,對于尋租活動的另一方參與者政府官員而言則相反。
(二)尋租行為的特征
1.尋租活動的排他性
由前面的討論不難得知,社會資源具有稀缺性,那么資源的合理配置(由誰分配、如何分配)顯得至關重要。經濟學理論中,一個“理性經濟人”受利益的驅使,有可能利用或創造條件使自己獲利,與此同時必然會損害消費者剩余,而這一行為并未創造任何實質性的社會財富。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尋租者個人分配到更多資源的同時,意味著剩余的其他利益主體受到影響,顧此便不能即彼,即所謂的“排他性”。
2.尋租活動的利己性
與上述“排他性”特征相輔相成的便是“利己性”,無論是何種手段何種形式的尋租行為,其目的都是為了個人或個人所在的利益集體服務。楊朱理學所宣揚的“為己”思想也正是尋租行為甚至更多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近年來,雖打造“陽光政府”“有限政府”的口號不絕于耳,但尋租行為卻呈現愈演愈烈之勢,歸根溯源還是“利己”二字。
3.尋租活動的腐蝕性
政府作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市場進行適當干預是為了彌補市場經濟中可能存在的“失靈”現象,進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公共利益和社會福利。然而,由于現實生活中尋租行為的存在,政府干預的后果往往與其初衷背道而馳。誠然,部分尋租行為也許并未對社會資源的分配、社會公平的實現造成嚴重后果和惡劣影響,但權力及權力掩蓋下的私欲所帶來的腐蝕性不能被忽視。
4.尋租活動的中介性
尋租主體競相追逐超額利潤,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經濟,帶來資源的不合理分配、機會的不均等、信息的不對等,影響了社會公平的實現。然而,正是由于存在諸如此般不公平、不公開、不公正現象,更加劇了尋租者對各類資源市場的爭奪,進一步刺激尋租活動的發生。以尋租活動為中介,尋租主體的趨利性要求和社會公平的實現目標陷入惡性循環。
5.尋租活動的多元性
各類尋租行為潛滋暗長,尋租手段更呈現多元化特征,由單一的權錢交易日益發展為權物交易、權色交易、權權交易。尋租行為發生的領域也由原先的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文化等相關領域。此外,除了尋租活動的大量存在,設租行為也日益猖獗。所謂設租是指權力擁有者利用權力獲得非生產性經濟利益的行為。例如,政府官員利用手中職權設置障礙,引得尋租者紛紛示好,以牟取私利。此時政府官員的角色由尋租者改變為設租者,但本質上都是尋租活動的一種方式。
三、公益性尋租和私利性尋租的區別
在現代尋租理論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將各種不同形式的尋租行為混合在一起進行分析,沒有考慮到這些尋租行為在尋租目的、尋租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異性。事實上,在中國現實社會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尋租行為,這些尋租行為可能是出于尋租主體的私利發生的,而有些可能是出于集體或所在組織的利益產生的,他們在尋租目的、尋租性質等方面存在本質區別,因此,有必要去區分和研究不同尋租行為的特征。從已有的研究文獻來看,僅有極少數學者對此進行了區分。在現代尋租理論研究中,有研究者將尋租區分為合法尋租與非法尋租[6],其中,合法尋租如企業向政府爭取優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維護自身的壟斷地位等;非法尋租如行賄受賄、偷稅漏稅、走私販私等。也有研究者將尋租劃分為正當性尋租與非正當性尋租[7],其中,正當性尋租是指利益集團通過游說政府獲得生產或經營的壟斷權,維護和擴大既得利益;領導者廠商憑借技術、資金等優勢穩步提高自己的市場占有率,排斥跟隨者進入市場、擠壓它們的利潤份額;水務等部門因為所謂公共品供給定價難題每年得到國家巨額財政補貼,得以供養日益增多的冗員、維持龐大體系的運轉;其他如對外貿易政策措施中的進口配額制、出口補貼,藝術家獲得的豐厚報酬等。以上諸種形式,雖未必有利于推動技術進步與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然均在法律約束范圍之內,故歸之于正當性尋租序列。非正當性尋租則更為普遍,其往往以下列方式表現出來。分利集團采取賄選方式操縱選舉,使得有利于本集團的競選人上臺,以維持既得利益;官僚權貴富豪階層阻礙改革的推進,維護既得利益;個體通過向官僚行賄獲得行政許可以謀求非法收益;廠商對主管部門虛報、瞞報經營數據,偷稅、漏稅獲取非法收益;此外,走私販毒、坑蒙拐騙、敲詐勒索等以非法途徑謀求對社會既得利益進行再分配的刑事犯罪均屬此列。然而,這些尋租行為的類型僅僅從單一維度進行了劃分,考慮得并不全面,對各種尋租行為的特征分析也并不深入。本文認為,在中國當前的現實社會中,尋租行為之間的差異是多方面的,因此,有必要從多個維度對不同尋租行為進行區分和比較。由此,本文提出按照尋租目的、尋租方式、尋租成本、尋租效益的不同可將尋租分為公益性尋租和私利性尋租。endprint
所謂公益性尋租行為是指個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企事業單位)出于維護某個部門或集體的利益,為該部門或集體爭取更多的資源而發生的尋租行為;私利性尋租是指個體(一般是個人)出于維護自己或親朋好友的利益,為自己或親朋好友爭取更多的資源而發生的尋租行為。具體而言,它們的區別在于:
(一)在尋租目的上的差異性
公益性尋租即尋租人或尋租人所在組織出于維護某部門或某集體的利益而進行的尋租行為,旨在為該部門或集體爭取更多的資源,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可視為集體行為;而私利性尋租則是尋租人個人為了維護自己或親朋好友的利益而進行的尋租行為,可視為個人行為。
(二)在尋租方式上的差異性
公益性尋租主體(如企業)多通過正當的手段(如進行社會捐贈、提供就業機會、履行社會責任、解決環境問題等)以期從政府那里獲得更多的財政補貼,爭取到更優惠的稅收政策,取得更便利的銀行貸款等。而私利性尋租是尋租主體(如個人)通過非法手段(如行賄等)牟取私利。
(三)在尋租成本上的差異性
關于尋租成本,塔洛克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為促進財富轉移所花費的成本;第二類是為阻止財富轉移所花費的成本;第三類是尋租形成的特權導致資源利用扭曲所造成的成本[8]。第三類成本因并非形成于尋租過程常常被忽略,事實上,它是尋租成功的結果在社會成本上的客觀反映。Soares et al.(2011)在研究政府進口管制引起的尋租活動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中發現,尋租導致進口保護,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刺激相關尋租者展開尋租活動,致使市場價格扭曲,資源配置不合理,經濟效率的低下,這些都是尋租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即使公益性尋租中尋租主體用于社會捐贈、環境保護等所花費的成本會高于私利性尋租中尋租者個人行賄政府官員所花費的成本,但從其社會影響來看,后者由于尋租特權導致資源利用扭曲所造成的成本(即第三類成本)卻是不容忽視的,其影響之大、范圍之廣、效果之顯著常常超過前兩類尋租成本之和。從這個角度分析,兩者在尋租成本上存在著較大差異。
(四)在尋租效益上的差異性
無論是公益性尋租行為還是私利性尋租行為都會產生一定程度上的負面效應。但公益性尋租在影響范圍、尋租方式及尋租成本上與私利性尋租有著顯著的區別,這就造成了尋租效應上的差異性。一般來說公益性尋租中,企業通過一系列措施在獲取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創造了相應的社會正效應。其提供的就業機會、履行的社會責任、進行的社會捐贈都會直接或間接地有利于社會公眾而不僅僅是政府機關或某領導個人。然而,私利性尋租在帶來極大的社會負效應的同時,幾乎很難創造正面效應,而且從精神層面來說,舍“大家”為“小家”的私利性尋租行為更具利己性特征。
四、公益性尋租和私利性尋租的聯系
(一)公益性尋租向私利性尋租轉化
通過前文分析可知,公益性尋租行為是指個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企事業單位)出于維護某個部門或集體的利益,為該部門或集體爭取更多的資源而發生的尋租行為,但是這種尋租行為要想真正起到為部門或集體謀利的效果就需具備以下前提條件:尋租主體高尚的品德、良好的社會誠信氛圍、合理的監督控制體系、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及權力的相對分散等。如果一個公益性尋租行為主體缺失這些要素前提,就可能發生尋租主體借助公共資源、打著為公共群體謀利的幌子來為自己或與自己有利益關系的親朋好友謀求私利的情形。政府采購中公職人員吃“回扣”現象,便是公益性尋租向私利性尋租行為轉化的典型代表。
公益性尋租向私利性尋租的轉化往往帶有自發性、利己性、可預見性的特征。受趨利性因素的影響,每一個“理性經濟人”在面對利益誘導時,總會呈現出兩種行為思想不斷博弈的過程。這時,尋租主體品德的高低、社會誠信氛圍的好壞及監督控制體系是否完善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此“經濟人”的行為導向。博弈的結果無外乎兩種,其中一種便是實現了公益性尋租向私利性尋租的轉化。而此種轉化過程是自發性的,效益是利己性的,結果是可預見性的或者說是有預謀性的。所以,防止公益性尋租向私利性尋租轉化的有效措施應該從尋租主體自身、社會誠信氛圍及監督控制等角度入手。
(二)私利性尋租向公益性尋租轉化
私利性尋租是尋租人個體為了維護自己或親朋好友的利益而進行的尋租行為。這種尋租行為本是個體運用個人資源或公共資源為自己謀求利益,倘若私利性尋租主體處于某個組織的核心位置或擔當要職,那么其通過私利性尋租建立的個人關系不經意間也會使得該尋租行為個體所在的組織獲益,即私利性尋租行為在為尋租行為個體帶來好處的同時,也為該個體所在部門或集體帶來豐富的信息資源、優先的獲利機會、優惠的稅收政策等。例如,某單位領導與政府某部門領導私交非常好,這種關系在為單位領導個人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可能給該領導所在單位帶來更多的政府資源。私利性尋租向公益性尋租的轉化便由此產生。
私利性尋租向公益性尋租的轉化往往是偶然性、利他性和不可預見性的。私利性尋租行為主體常常擁有著財力、物力或人力資源,他們借助手中資源為自己牟利的同時也會不經意間為自己所在組織帶來利益,而利益之間的相互性又會為他本人創造更多的財力、物力及人力資源。由私利性尋租向公益性尋租的轉化過程是偶然性的,效益是利他性的,結果是不可預見性的。同時,由于此種轉化會對組織內部多數人有益,所以轉化過程中阻力較小,呼聲較高,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在當前,尋租行為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很難而且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徹底鏟除各類尋租行為,可以在嚴格制止私利性尋租行為的同時,對公益性尋租行為的利己動機進行排查和糾正,然后再逐漸消除尋租行為。
五、有效規避兩種尋租行為的措施
(一)公益性尋租行為的有力糾正措施
公益性尋租行為更多出于集體組織利益的考慮,有力的糾正措施應更側重于提高尋租主體素質、健全完善社會誠信體系、遵守市場競爭規則、維護市場經濟穩定、創造良好企業文化等。endprint
1.提高尋租主體素質
無論是部門領導、企業高管,還是政府公職人員,均可視為尋租行為的參與者。提高尋租主體素質相當于源頭治水,培養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是有效規避尋租行為的基礎;當然,適當程度提高尋租行為參與者的福利待遇,建立更為有效的薪酬激勵機制,可起到“高薪養廉”的作用。二者雙管齊下,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官員尋租的機會成本以削弱其尋租動機,效果更佳。
2.健全社會誠信體系
運用各種宣傳、教育的手段,尤其是新聞媒介的輿論導向作用,深化社會誠信教育,讓民眾普遍意識到尋租行為所帶來的弊端。如果社會經濟生活的參與者人人講誠信,尋租行為自然就無處遁形。良好的社會誠信氛圍,可使尋租主體自覺抵制尋租活動,是一種極為有效的辦法。
3.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盡可能多地引入競爭機制,創造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環境,合理分配稀缺的社會資源,保障資源的優化配置。一旦市場經濟本身的“失靈”現象得到緩解或好轉,尋租行為便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
4.創造良好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長期生產實踐中,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經全體員工共同認可并遵從的理想目標、價值追求、意志品質和行為準則。隨著尋租活動的日益猖獗,當前在企業內部進行尋租行為的相關教育迫在眉睫。讓遵紀守法,抵制尋租腐敗行為的思想深深融入企業文化中,不僅是響應黨中央和政府的號召,更是出于對企業內部成員尤其是高管階層的保護,防患于未然好過于“亡羊而補牢”。
(二)私利性尋租行為的有效規避措施
私利性尋租行為更多出于個體利益的考慮,更側重于從限制高管個人權力、加強個體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尋租行為成本、加強監督控制力度等方面考慮規避措施。
1.限制高管個人權力
有限權力,對于政府職能部門亦或是企事業單位組織內部都是不容忽視的。權力的過分集中必然帶來欲望的膨脹和決策的獨斷性。合理分權才能從根本上抑制這一行為,減少利用公權牟取私利的機會,縮小權力異化的空間;從根本上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和政府越位、錯位的現象,防止權力的濫用和對社會公平的踐踏。
2.提高尋租行為成本
加大對尋租主體的處罰力度是提高尋租行為成本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使尋租行為帶來高收益的同時伴隨著高風險、高代價。作為一名理性經濟人,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其終極目標。一旦尋租成本大于尋租收益,“準尋租主體”必然要望而生畏,自律其身。此外,上文提到的“高薪養廉”措施,間接提高了尋租行為成本,使“準尋租主體”切實意識到進行尋租活動是非理性的從而自覺放棄這一行為。
3.加強監督控制力度
為了將可能存在的尋租行為降為最低,要求事前監督機制和事后懲罰機制相互配合。事前監督即要加強公共權力監督制約機制,建立新型監督管理體系,積極引導社會輿論監督,增強公民監督意識,真正實現人民監督。事后懲罰應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讓監督控制不僅僅是一紙空文,一句口號。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才能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只有做到從嚴從重懲治尋租行為,才能讓法律發揮其應有的震懾力。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資源的稀缺性、不成熟的市場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及監督制約機制的缺失著手,分析了尋租行為產生的根源;通過對尋租及尋租理論的內涵進行探討,指出了尋租行為的特征:尋租是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負和博弈,具有負的外部效應。尋租作為一種非生產性的謀取利益的活動,對于個人來說是有效的,其實質卻是將尋租的負外部性讓整個社會來承擔。它是對公共權力的濫用,造成了資源和財富的極大浪費,帶來了社會整體福利的凈損失,破壞了社會主義和諧建設。
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將尋租行為劃分為公益性尋租行為和私利性尋租行為,并著重闡述了二者的區別和聯系,分別提出有效規避兩種尋租行為的措施。對于公益性尋租行為,側重于從提高尋租主體素質、健全社會誠信體系,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創造良好企業文化等方面著手。而對于私利性尋租行為,則更多側重于限制高管個人權力,提高尋租行為成本,加強監督控制力度。
通過上述尋租行為異質性的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1)政府要正確發揮其宏觀調控職能,在調節市場經濟失靈現象和彌補市場經濟自身弊端的前提下,處理好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關系。凡是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和資源合理配置的行為要積極鼓勵,提供優惠政策和便利條件;凡是阻礙市場經濟發展和破壞資源合理配置的行為(如尋租行為)要有效避免,正確引導,及時遏制。
(2)企業要積極從事生產性活動,通過技術革新、產品設備的更新、引進高新技術人才來提高生產率,從而達到盈利性目的。切忌盲目跟風,企圖通過尋租行為等非生產性活動來獲得超額利潤,最終造成資源和財富的極大浪費。同時,應該深刻地意識到尋租行為所帶來的利益并不增加社會總價值,它只是價值分配方式和分配比率的相對改變,并無任何實際意義。
(3)社會要利用輿論的力量正確引導,逐步建立完善社會監督機制,加強相關立法工作,健全社會誠信體系。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氛圍,達成一致的口徑,使人們普遍了解尋租行為的負效應,讓尋租行為無處遁形。
(4)個人要在提高專業領域技術水平的同時切實完善自身道德建設。無數研究結果表明,有才無德比有德無才的危害性大很多。無論身處何種崗位何種職位,都不應該試圖通過投機取巧、行賄受賄等尋租行為來謀取利益。藐視法律、違背公平終究會受到嚴懲,而誠實守信、遵紀守法、敬業奉獻才是社會主義和諧建設的正能量,才是早日實現“中國夢”的積極元素。
【參考文獻】
[1] KRUEGER A 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3):291-303.
[2] 俞憲忠.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J].學術論壇,2004(6):94-98.
[3] TULLOCK G.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monopolies, and theft[J].Economic Inquiry,1967,5(3):224-232.
[4] TULLOCK G.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Rent Seeking in Dictatorships[J].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 Theoretical Economics,1986,142(1):4-15.
[5] TULLOCK G. Efficient rent seeking[M].Efficient RentSeeking. Springer US,2001:3-16.
[6] 蒲艷,王官誠.尋租成本問題研究述評[J].經濟學動態,2012(11):142-148.
[7] 楊宏力.尋租理論的發展流變及其方向瞻望——兼論隱匿權威尋租的源起與治理[J].經濟學家,2010(8):100-104.
[8] 戈登·塔洛克.尋租——對尋租活動的經濟學分析[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