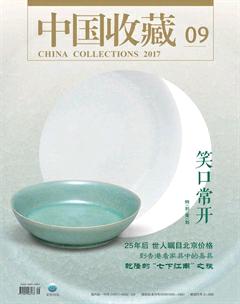寫一副好對子
賈理智
一般來說,文學和藝術是嚴肅的。但對于楹聯來說,情況就不同了。試想,還有哪一種文學形式像楹聯一樣,上為學者文人,下為婦人孺子所喜聞樂道呢?
這種現象歸根結底還是在于對聯的規則并不復雜,尤其是對語言的色彩、風格,對題材、內容都沒有什么要求。它廣泛應用于社會生活,易學、易懂、易記,也不難寫。只要對得好,無論語言之俗雅,題材之大小,思想之深淺,皆成對聯。
歷史長河中,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愿意在對聯中幽默一次。清陳云瞻在《替云樓雜說》中曾記載過一個故事:“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口須加春聯一幅,帝微行時出觀。”第二天,明太祖微服出巡,挨門觀賞取樂。當他走到一戶人家,見門上沒有貼春聯,便詢問緣故,原來主人是閹豬的,既不識字也不會寫,明太祖當即揮筆寫下“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的對聯送給了這戶人家。不僅幽默風趣,形象生動,還做了廣告宣傳,簡直堪稱一副特色絕對。
傳說蘇東坡與好友佛印一天傍晚泛舟江上。忽然,蘇軾用手往左岸一指,又指指佛印,笑而不語。佛印順勢望去,只見一條黃狗正在啃骨頭,頓有所悟,隨手將自己手中寫有蘇東坡詩句的蒲扇泡入水中。兩人四目相對,不禁大笑起來。原來這是一副啞聯,蘇軾: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水流東坡尸(詩)。
鄭板橋做官前后,都住在揚州賣畫。過花甲壽誕時,他自己給自己寫了一副壽聯:
常如作客,何問康寧;但使囊有余錢,甕有余釀,釜有余糧。取數葉賞心舊紙,放浪吟哦;興要闊,皮要頑,五官靈動勝千官,過到六旬猶少。
定欲成仙,空生煩惱;只令耳無俗聲,眼無俗物,胸無俗事。將幾枝隨意新花,縱橫穿插;睡得遲,起得早,一日清閑似兩日,算來百歲已多。
這副對聯,寫得輕松愉快,灑落自在,是極為有趣的,傳神地表達出鄭板橋的風度和胸懷,以及老年的興趣和性格。
諷刺與幽默常常像是一對孿生兄弟,諷刺中含幽默,幽默中又帶諷刺。對聯中運用了諷刺和幽默的手法,可以淋漓地嬉笑怒罵,可以善意地批評規勸,或令你解頤,或令你捧腹;或如骨鯁在喉,或如芒刺在背。
清代的阮元曾經模仿秦檜夫婦追悔的口氣寫了副對聯,貼在岳飛廟鐵鑄的秦檜與王氏的像上:(秦檜)咳!仆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王氏)啐!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幽默里含諷刺,風趣中有痛斥,據說連阮元本人后來謁岳飛廟時,見了這副對聯還不禁失笑。
抗日戰爭勝利后,畫家吳湖帆諷刺漢奸梁鴻志、吳用威的對聯是:孟光軋姘頭,梁鴻志短;宋江吃敗仗,吳用威消。此聯用了兩個歷史故事的四個人名:孟光是梁鴻妻子,封建時代有“舉案齊眉”的佳話;吳用是宋江的軍師,人稱智多星。此聯之巧,在于嵌字自然天成,還頗有點歇后語的味道,道出了那些丑惡靈魂和無恥面目。
由此可見,對聯的應用生動地展現出了中國人幽默、機智的民族性格。雅俗共賞,這絲毫不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