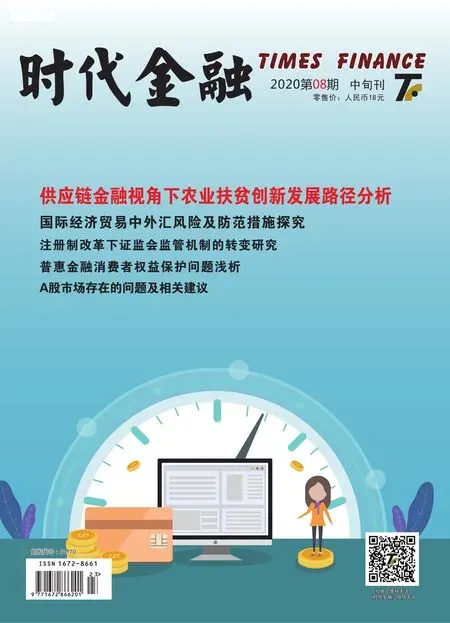暴力文化視域下的校園欺凌現象分析
【摘要】近年來,校園欺凌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如果把欺凌事件的原因簡單地歸咎于個別學生的自身問題或是校方的失責反而會遮蔽欺凌事件背后復雜的社會因素。而其中,暴力文化對青少年的暴力行為的出現影響尤為巨大。暴力文化渲染了一種暴力氛圍,損毀青少年的價值觀,為校園欺凌提供了暴力樣本。
【關鍵詞】暴力文化 校園欺凌
近年來,校園欺凌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毆打致傷、扒衣、拍裸照等惡性欺凌事件經過媒體放大后顯示出令人震驚的暴力特性。“校園欺凌網絡輿情分析稱,從2014年6月1日到2015年6月31日,涉及“校園暴力欺凌”的網絡新聞達36,761篇次,相關論壇貼文達39,189篇,微博達721,947條。”[1]大量的暴力事件的出現使得對此問題的思考迫在眉睫。如果把欺凌事件的原因簡單地歸咎于個別學生的自身問題或是校方的失責反而會遮蔽欺凌事件背后復雜的社會因素。在眾多的社會因素中,暴力文化的傳播對中小學生欺凌行為的產生影響尤為巨大。暴力文化盡管不是誘發校園欺凌的唯一原因,但不失為其中一種關鍵的誘因。
一、暴力文化渲染暴力氛圍
科技的進步,傳播平臺的日益多元使得文化的傳播更加迅捷。由此帶來了文化傳播的兩面性,一方面優秀的文化可以更加快速而廣泛的傳播;另一方面,這也為暴力文化的傳播帶來了便利。書本、電視、網絡、智能移動設備等媒介的全方位、立體化覆蓋,使得“暴力文化”無所不在。傳播內容的分級機制的缺失使得成人和兒童一起享受著暴力文化傳播所帶來的快感。
暴力文化的廣泛傳播,形成了一種效應場,“當人們置身或觀察這一效應場時,便會與它發生感應關系,從而自覺或不自覺的獲得某種特殊的體驗、熏染和感受,感悟暴力文化的精神、情調、氣質和狀態”,[2]這就是所謂的暴力文化氛圍。它實際上是一種誘發暴力發生的文化氛圍。在布迪厄眼中,這種氛圍足以引起“習性”的產生,而這種習性是一種的無意識的文化產物,它隱秘地塑造著人的認知結構,并最終是一種結構性的再生產。而由“暴力文化”營造起的暴力氛圍對人的影響是長久的,而且這種影響是拒斥變化的,它從孩童時期就建構起人的文化認知結構,后來的說教和強力扭轉并不足以引起認知結構的顛覆性改變,它只能在原來的基礎上修修補補。長期浸淫于暴力文化之中形成的“習性”,是一套相對持久的無意識內化結果,青少年的行為往往會以一種無意識的形態被“習性”影響著。青少年對社會觀念好壞的判斷來自習性,更準確的說是一種傾向,引導個體以一種特定的方式行動。而個體的行為往往是傾向性的,而不是有意識地、理性計算的。“浸淫于暴力文化的人,其涉獵‘現實暴力的可能性比正常人高出31%。而且,暴力對未成年人的影響明顯高于成年人。”[3]
二、暴力文化損毀價值觀
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對外界的符號信息缺乏理智的判斷,由此帶來了對暴力文化核心價值的盲目認同,并承認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暴力文化的客觀結構的內化過程不僅是心理的過程,而且是身體的過程。它從身心兩面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念,在缺乏正確引導的情況下,青少年很容易誤入歧途。
青少年的心智是根據認知結構構建的,而認知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于這個世界的結構。恰恰基于這樣的事實,青少年持有一套基本的、前反思性的假定。這種假定構筑起青少年的人生信念和價值觀念。無需喋喋不休的勸導和潛移默化的灌輸,就接受了它們。“在所有形式的‘潛移默化的勸服中,最難以變更的,就是簡單明了地通過‘事物的秩序發揮作用的那種勸服。”[4]這種勸服樹立的價值觀是隱秘的卻又是持久的難以變更的,是一套深刻內在化的、導致行為產生的主導傾向。暴力文化的這種不為人知的強制作用,通過“誤識”在社會實踐中悄然且持續地發揮作用。被支配者在自身的被支配中是同謀。這種屈服源于他們的慣習與他們身處其中的場域之間的無意識切合關系,它深深地寄居于他們社會化了的身體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施暴者和被欺凌者都是暴力文化的受害者。
三、暴力文化提供暴力樣本
青少年兒童具有可塑性和模仿性是教育行為之所以有意義的前提。正是這種可塑性為教育學的“教”制造了意義,這兩個特性為教育創造了基礎性條件,而這種可塑性也同樣為不良習性的養成制造了漏洞。暴力文化為青少年提供了大量暴力樣板,暴力動作和酷語、穢語、色語從動作和話語兩方面對校園欺凌進行著“指導”。在實施欺凌的過程中學生會把自己幻想成心中的暴力偶像,藉此來滿足自己的英雄美夢。
暴力影視文化是青少年兒童暴力樣板的母本。青少年兒童對影視中宣敘的暴力美學深深迷戀。暴力文化能誘發暴力犯罪是毫無疑義的。早在1988年,美國心理協會“電視與社會”稽查小組主席就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指出:“電視足以引起侵犯行為,這是有證據支持的。”[5]學生在欺凌過程中呈現出對影視中暴力美學的借用,試圖從動作方面極力向武打演員靠近。暴力文化指導著學生的心靈,成為學生的處事綱領。暴力可以解決的問題絕不會用溝通進行和解。金庸是武俠世界中的最大暴力領袖,他的暴力書寫曾經一度風靡校園。而名噪一時的網絡小說——《壞蛋是怎樣煉成的》,則是武俠體的現代續寫。這些充斥著暴力的書刊可以被中小學生輕易的從書店里購到,它們影響著中小學生的日常行為實踐,成為校園里培育暴力欺凌的溫床。
總之,如果把校園欺凌只是當作學校場域中的偶發事件,這就遮蔽了校園欺凌產生的更深層次的文化原因。無論是校長免職或是開除肇事學生都無法撼動校園欺凌的文化根源,這種表面化的處理方式只能平息事件,卻無法切斷校園欺凌的根基。一些研究者試圖運用嚴苛的律令來杜絕校園欺凌的發生,但是,律令卻無法撼動暴力產生的根源。嚴苛律令的無力性在于,一方面它可以強烈的震懾到校園欺凌的發生,給欺凌者的心理和身體加以束縛;而另一方面它卻不能從根本上切斷欺凌行為的發生,正如再怎么極端的刑罰都無法阻止犯罪的產生一樣。唯有對文化進行清洗才能直擊校園欺凌的內核。
參考文獻
[1]魏葉美,范國睿.社會學理論視域下的校園欺凌現象分析[J].教育科學研究.2016(2).
[2]潘登.暴力文化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4(2).
[3][5]李錫海.暴力文化與暴力犯罪[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
[4][法]布迪厄,[美]華康德.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昌成明(1990-),男,漢族,河南洛陽人,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批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