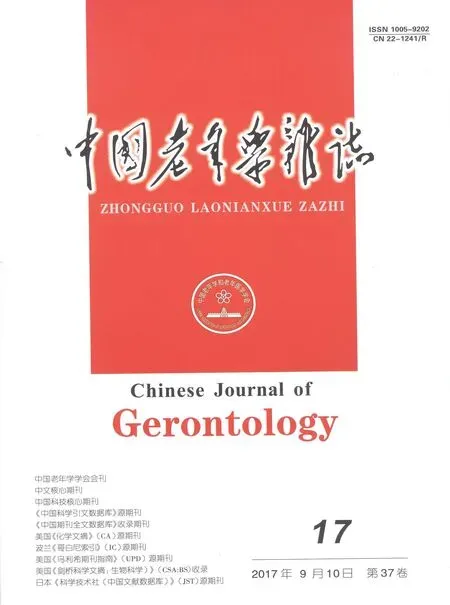老年癡呆患者家庭照護者應對資源的研究進展
英 杰 張歡歡 張美玲 石 穎 王守琦 劉鵬程 李 媛 刑莊婕 李煥煥 孫 皎
(吉林大學護理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1)
老年癡呆患者家庭照護者應對資源的研究進展
英 杰 張歡歡 張美玲 石 穎 王守琦 劉鵬程 李 媛 刑莊婕 李煥煥 孫 皎
(吉林大學護理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1)
癡呆;照護者;應對資源
癡呆是一種進行性發展的神經綜合征,會出現認知功能退化,記憶力減退及行為障礙等癥狀,無法完成日常活動〔1〕。在我國主要由配偶或子女承擔照護者的角色,照護過程中家庭照護者生理、心理及社會方面都發生了應激反應〔2〕。同時,研究發現對癡呆患者良好的照護可以減少行為問題出現的頻率、嚴重程度及住院次數〔3〕。及時掌握照護者的應對資源,給予個體化的支持,既能幫助照護者維持其自身健康的狀態,也有益于癡呆患者的健康。本文根據近5年關于癡呆照護者的研究,將家庭照護者應對資源總結為內在因素及外在因素兩個方面,對其相關測量工具進行綜述。
1 檢索策略
分別對Pubmed、Embase、中國知網(CNKI)及萬方數據庫進行檢索,納入標準:1.調查性文獻,2.主要研究對象為癡呆患者相應的家庭照護者,3.使用非自制相關量表,4.非會議文獻,有研究結果,5.可找到全文,6.中文文獻除以上要求外,需為2016年科技核心(統計源)期刊文章。最終納入49篇相關研究。篩選過程由兩名研究者獨立進行,有異議時由第三人給出意見。
2 癡呆患者家庭照護者的應對資源
本文依據家庭照護者在照護癡呆患者的過程中可利用的應對資源,歸納為內在因素(心理方面、自我效能、應對方式)和外在因素(社會方面、家庭方面)。這些因素或許無法直接消除照護者的壓力,但可以作為保護因素使照護者能更有效地應對所面臨的挑戰。對癡呆患者家庭照護者應對資源進行評估的常用測量工具見表1,根據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依次對測量工具的異同點進行闡述。
2.1外在因素 與癡呆患者家庭照護者外在因素相關的研究集中于照護者的家庭方面和社會方面。
2.1.1家庭方面 隨著癡呆患者病情不斷惡化,照護壓力不僅涉及主要照護者,還會影響到整個家庭,家庭功能與照護者負擔及抑郁相關〔17〕。家庭支持的研究涉及家庭中多個因素,如家庭功能,家庭成員間的溝通等方面。
研究者主要使用了FAD〔4〕和家庭關懷度指數問卷〔6〕進行研究。FAD是基于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而制定的量表,適用于12歲以上的家庭成員,條目豐富、全面,各個分量表之間的關聯度強,因此具有極大的內部一致性。國外研究者使用了FAD中的總體功能量表〔17,18〕,包含與其他6個分量表高度相關的12個條目,其Chronbachα=0.92〔5〕,從整體上評估家庭系統中的健康或異常狀態。國內研究者使用的中文版FAD包含60個條目〔9〕,完成整個FAD量表的評估需花費15~20 min的時間,在以往的研究中多用于少年兒童,腦外傷等患者的照護者群體。APGAR量表評價個體對家庭支持的滿意度,用于篩查有功能障礙的家庭,內容簡潔,涉及調查對象與其家人之間情感、交流和互動的關系,對其用來評價家庭功能存在爭議〔19〕,還未廣泛應用到各類照護者群體當中。
此外,國內外研究者還使用了家庭滿意度量表(FSS)、家庭溝通量表(FCS)、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量表(FACES-Ⅳ)等。一項使用FAD、FSS、FCS及FACES-IV對哥倫比亞90名照護者(其中88名為癡呆照護者)的研究結果顯示,以上這些家庭動力與照護者的抑郁、壓力及生活滿意度顯著相關,提示利用家庭支持作為切入點對照護者進行干預非常有意義〔17〕。
2.1.2社會方面 家庭照護者作為癡呆患者的主要照護資源,但因個人能力有限需要社會提供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家庭照護者的社會支持與其照護負擔,生活質量及心理健康都具有相關性〔20〕。
關于社會支持的研究,學者們多使用SSRS〔14〕、SPS〔15〕和LSNS等〔16〕,這3個量表都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支持進行了維度劃分。SSRS量表內容簡短,從主客觀的角度去測量照護者的社會支持情況,此外還包含了個體對可獲得支持資源態度的內容。SSRS已應用于癌癥、小兒腦癱、透析、癡呆等患者的照護者群體中,是國內關于社會支持研究中使用最廣泛的量表。SPS內容涉及范圍更廣,表達了個體與外界存在著多種形式的關系,適用于不同的人生階段,從6個維度深層次的分析個體的社會支持,已應用于癡呆及腦外傷等患者的照護者當中,但還未在國內普及。LSNS是Lubben根據Berkman-Syme社會網絡量表(BSNI)而修訂的適用于老年人群體的量表,通過評估調查對象與其家庭和朋友之間的關系親密度,從而了解個體與外界互動的狀態,完成該量表的測量只需5~10 min,因此非常適用于老年配偶照護者。研究者已使用該量表對癡呆、中風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的照護者進行研究。此外,國內外研究者還使用了MOS社會支持調查(MOS-SSS)和領悟社會支持問卷(MSPSS)等量表。

表1 癡呆患者家庭照護者應對資源測量工具的概述
頻次指相應量表在納入文獻中的使用頻次英指其中(包含的英文文獻數量;中指其中包含的中文文獻數量)
2.2內在因素 內在因素即家庭照護者自身所擁有的,較為穩定的特質。針對癡呆患者家庭照護者自身內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自我效能及應對方式3個方面。
2.2.1心理方面 心理方面主要包括心理彈性和心理一致感兩方面的研究,根據納入文獻的結果,家庭照護者的心理彈性與其抑郁程度〔21〕及生活質量〔22〕相關。關于心理彈性的研究中多使用RSA〔12〕(RSA),其從包含45個條目的初版修訂而來,對促進心理彈性提升的保護因素進行評估,在我國使用廣泛,但還未涉及照護者的研究。此外還有心理彈性量表(RS)和簡化心理彈性量表(BRS)等。
心理一致感同樣屬于一種心理保護因素。從納入的文獻可知,家庭照護者的心理一致感與其照護負擔〔23〕和生活質量〔24〕相關,其可以在照護負擔和抑郁焦慮之間起到中介作用〔25〕。對于心理一致感的研究通常使用SOC〔13〕。SOC評價個體對于來自內外部環境壓力的認識、控制能力及應對過程的意義,該量表有29個條目及13個條目兩個版本,兩種版本均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已應用于癌癥、癡呆、精神分裂癥等患者的照護者中,二者均表現出了良好的信效度。使用RSA、SOC及生活定向測驗修訂版(LOT-R)對130名拉丁美洲癡呆家庭照護者的研究顯示〔26〕,這三個量表都能夠很好地解釋其精神方面的生活質量。
2.2.2自我效能 中度及重度癡呆患者的家庭照護者自我效能可作為患者的神經精神癥狀作用于照護者負擔及抑郁的中介因素〔24,27〕,也可在家庭照護者的社會支持與生活質量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6〕。
關于自我效能的研究多使用RSCSE〔14〕GSES〔15〕。RSCSE專為照護者研發,國外使用較廣,可用于臨床及科研當中,評估照護者處理照護活動相關問題的自信程度。由于量表的復雜性及受調查者的理解能力不同,評估時需要調查者進行引導,不建議獨立完成。GSES是單維度量表,但在后續使用中發現該量表可被劃分為多個維度〔28〕,其目前已被譯成28種語言,應用于癡呆、透析、心力衰竭等患者及失能老人的照護者中。
此外還有自我效能感量表(SES)、癥狀管理自我效能量表中國版和中國家庭照護者自我效能問卷(SEQCFC)等。
2.2.3應對方式 逃避應對可在照護負擔與照護者抑郁焦慮之間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3〕。積極應對與照護負擔及抑郁情緒皆顯著相關,可在照護負擔與抑郁之間起到中介作用〔29〕。照護者應對方式又與其生活質量相關〔18,30〕。
關于家庭照護者應對方式的研究多使用Brief COPE〔16〕和RWCC〔31〕。兩者都是從多個維度評估個體面對壓力的應對方式,Brief COPE是對原有60個條目的COPE進行濃縮刪減后再添加了自責分量表所形成,減輕了被調查者的應答負擔。目前已應用于癌癥、腦外傷、癡呆及中風等患者的照護者當中。而RWCC將應對方式劃分成情緒(自責、幻想、逃避)或問題為關注點的兩大類,再加入尋求社會支持維度,三者的Chronbachα分別為0.82、0.70、0.61〔32〕。RWCC由包含68個條目的原版修訂而來,信效度也更優于原版。Brief COPE及RWCC都未出現于國內癡呆照護者的研究中。
此外,國內外研究者還使用了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CSQ)、應對方式問卷(WCQ)和宗教應對量表(RCOPE)等。
癡呆患者家庭照護者應對資源內在因素的研究還涉及到了照護者感激、智謀、虐待、照護態度、照護動力、樂觀傾向、神經質及外向性等方面。
3 小結與展望
目前,關于癡呆患者家庭照護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照護負擔和心理健康方面,而對照護者應對資源的研究尚缺乏,尤其是家庭支持及個人內在因素方面的研究較少見。在發展中國家,家庭仍是照護的重要提供場所,家庭支持及照護者個人因素的多樣化應作為制定及實施干預的考慮因素。為加強照護者的應對資源,除在國家層面上積極出臺有利政策,做好公共衛生資源的分配,加強社區醫療團隊建設之外,護理研究者應與社區護理人員進行合作,對照護者進行長期的全方位的評估,把握其反應及應對資源的個性和共性,對其提供更為高效的干預措施指導。
為更精確的測量研究對象的某種因素,在使用量表測量時應將研究對象的特點、量表的完成時間及難易程度等納入考慮范圍,例如研究對象是老年配偶照護者或子女照護者等,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針對不同人群使用不同的量表。國內研究者還應嘗試自主研發或引進國外評價較好的專門用于癡呆照護者的量表,根據我國國情進行文化調試,同時在大量癡呆照護者群體中進行信效度的檢驗。
1李 崢.老年癡呆相關概念辨析〔J〕.中華護理雜志,2011;(10):1045-5.
2楊 振,張冬梅,陳 任,等.我國五省(市)老年癡呆照料現狀調查分析〔J〕.安徽醫學,2013;34(6):847-50.
3García-Alberca JM,Cruz B,Lara JP,etal.Disengagement coping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giver burden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aregivers of people with Alzheimer′s disease.Results from the M?LAGA-AD study〔J〕.J Affect Disorders,2012;(136):848-56.
4Epstein NB,Baldwin LM,Bishop DS.The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J〕.J Marital Fam Ther,1985;11(4):345-56.
5Ridenour TA,Daley J,Reich W.Factor Analyses of the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J〕.Fam Proc,1999;38(4):497-510.
6Smilkstein G.The family APGAR:A proposal for a family function test and its uses by physicians〔J〕.J Fam Pract,1978;6(6):1231-9.
7Smilkstein G,Ashworth C,Montano D.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family APGAR as a test of family function〔J〕.J Fam Practice,1982;15(2):303-11.
8肖水源.《社會支持評定量表》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應用〔J〕.臨床精神醫學雜志,1994;(2):98-100.
9王 婧,Lily Dongxia Xiao,李小妹.社區癡呆癥病人家庭照顧者負擔及影響因素研究〔J〕.護理研究,2016;(7):786-90.
10Cutrona CE,Russell DW.The Provisio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Adaptation to Stress〔J〕.Adv Personal Relationships,1983:2678-82.
11Lubben JE.Assessing Social Networks Among Elderly Populations〔J〕.Fam Commun Health,1988;11(3):42-52.
12Friborg O,Hjemdal O,Rosenvinge JH,etal.A new rating scale for adult resilience:what are the central protective resources behind healthy adjustment〔J〕?Int J Meth Psych Res,2003;12(2):65-76.
13Steffen AM,Mckibbin C,Zeiss AM,etal.The Revised Scale for Caregiving Self-Efficacy: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ies〔J〕.J Gerontol,2002;57(1):74-86.
14Zotti AM,Balestroni G,Cerutti P,etal.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erceived Self-Efficacy Scale in cardiovascular rehabilitation〔J〕.Monaldi Arch Chest Dis,2007;68(3):178-83.
15Antonovsky A.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e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J〕.Soc Sci Med,1993;36(6):725-33.
16Carver CS.You want to measure coping but your protocol′s too long:Consider the brief cope〔J〕.Int J Behav Med,1997;4(1):92-100.
17Sutter M,Perrin PB,Chang YP,etal.Linking family dynamics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ombian dementia caregivers〔J〕.Am J Alzheimers Dis,2014;29(1):67-75.
18Panyavin I,Trujillo MA,Peralta SV,etal.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dynamics on quality of care by informal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ementia in Argentina〔J〕.Am J Alzheimers Dis,2015;30(6):1236-43.
19Gardner W,Nutting PA,Kelleher KJ,etal.Does the family APGAR effectively measure family functioning〔J〕?J Fam Practice,2001;50(1):19-25.
20蔣振虹,譚小林,趙 科,等.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照料者心理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醫藥導報,2015;(11):55-9.
21Sutter M,Perrin PB,Peralta SV,etal.Beyond Strain:Personal Strengths and Mental Health of Mexican and Argentinean Dementia Caregivers〔J〕.J Transcult Nurs,2016;27(4):376-84.
22Trapp SK,Perrin PB,Aggarwal R,etal.Personal strengths and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dementia caregivers from Latin America〔J〕.Behav Neurol,2015:1-8.
23Stensletten K,Bruvik F,Espehaug B,etal.Burden of care,social support,and sense of coherence in elderly caregivers living with individuals with symptoms of dementia〔J〕.Dement,2014;73(6):61-9.
24Gallagher D,Ni Mhaolain A,Crosby L,etal.Self-efficacy for managing dementia may protect against burden and depression in Alzheimer′s caregivers〔J〕.Aging Ment Health,2011;15(6):663-70.
25Orgeta V,Sterzo EL.Sense of coherence,burden,and affective symptoms in family carers of people with dementia〔J〕.Int Psychogeriatr,2013;25(6):1-8.
26Zhang S,Edwards H,Yates P,etal.Self-efficacy partially mediate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family caregivers for dementia patients in Shanghai〔J〕.Dement Geriatr Cog,2013;37(1-2):34-44.
27Zhang S,Edwards H,Yates P,etal.Partial mediation role of self-efficacy between positiv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family caregivers for dementia patients in Shanghai〔J〕.PLoS One,2013;8(12):1-7.
28周永安,趙靜波,張小遠,等.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在廣州高校大學生中應用情況研究〔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2;20(5):722-4.
29Papastavrou E,Tsangari H,Karayiannis G,etal.Caring and coping:the dementia caregiver〔J〕.Aging Ment Health,2011;15(6):702-11.
30Tay KC,Seow CC,Xiao C,etal.Structured interviews examining the burden,coping,self-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family caregivers of persons with dementia in Singapore〔J〕.Dement,2014;15(2):1-17.
31Vitaliano PP,Russo J,Carr JE,etal.The Ways of Coping Checklist:Revision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J〕.Multivar Behavres,1985;20(1):3-26.
32Hooker K,Frazier LD,Monahan DJ.Personality and coping among caregivers of spouses with dementia〔J〕.Gerontologist,1994;34(3):386-92.
〔2017-01-09修回〕
(編輯 郭 菁)
吉林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2016224)
孫 皎(1971-),女,博士后,副教授,主要從事社區與老年護理研究。
英 杰(1990-),女,碩士在讀,主要從事社區與老年護理研究。
R473.2
A
1005-9202(2017)17-4420-04;doi:10.3969/j.issn.1005-9202.2017.1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