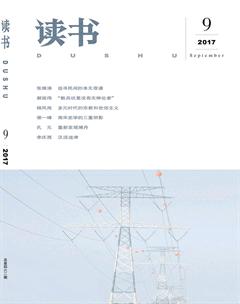創新的經濟學邏輯
汪毅霖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官方文件和各路媒體上對于創新的呼聲可謂一浪高過一浪,創新幾乎成了全民運動。之所以如此重視創新,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創新對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供給側改革甚為重要,二是當前創新的供給相對于需求來說嚴重不足。如何彌補這一供求缺口呢?或許我們該稍稍冷卻一下萬眾一心的激情,回歸經濟學的常識,對創新的邏輯做一番考察。需要申明的是,創新的邏輯不可能是形式邏輯,因為形式邏輯是靜態的,無法容納“創新”—未來的各種可能;創新的邏輯只能是動態性質的辯證邏輯,其可以刻畫創造性的活動—從無到有的過程。于是,雖然創新本身的形式邏輯不可知,但我們卻可以去考察諸影響因素共同作用于創新的辯證邏輯。
一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新
經濟學家如一九七二年諾獎得主阿羅、一九七四年折桂者哈耶克和二○○一年獲獎者斯蒂格利茨等,都將創新理解為信息 / 知識的生產,認為創新實質上是關于生產方式如何從一種形式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信息,或者說可以將創新活動視為一個獲取特定的新信息 / 知識的過程。
知識論視角下的創新是個經濟學而非自然科學概念,其并非僅指高新科技的進步,甚至主要不是指科技進步([美]埃德蒙·費爾普斯:《大繁榮》)。經濟學家所理解的創新囊括了生產手段在多元方向上的各類重新組合,且技術創新與非技術創新是互補的。熊彼特(經濟學創新理論的開拓者)的概括很全面,創新包括五種類型:新產品、新的生產方法、新的市場、新的原材料來源、新的生產組織形式。于是,新型抗瘧藥是創新,“雙十一”是創新,第一個吃螃蟹也是創新。
創新的式樣雖五花八門,卻都要遵循一個經濟學的基本定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故熊彼特稱創新的經濟結果為“創造性破壞”。企業的重要創新將淘汰舊一代的產品,使得先前的生產能力被廢棄—例如智能手機淘汰了傳統手機。并且,創新不僅會帶來所謂“破壞”(故傷人一千),且往往伴隨著高投入、高風險(故自損八百)及只是或許才會有的高回報。既然如此,為什么中國現在仍要將創新視為發展的核心和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呢?這還要從經濟學理論本身尋找答案。
二○○五年克拉克獎得主阿西莫格魯及其合作者曾提出一個有趣的框架,可用來解釋后發和先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差異(Acemoglu, Daron, et al., 2006,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4, No. 1)。對于遠離世界科技前沿的后發國家,自主創新的壓力很小,鼓勵模仿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經濟增長;相反,對于先發國家和正在快速追趕的后發國家,自主創新的壓力變得顯著,只有將制度安排調整為有利于創新的模式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這一框架可以視為若干年前林毅夫—楊小凱之爭的另一個版本,故非常適合解釋中國的現實情況。當一個國家距離科技前沿尚遠時,其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可以通過引進、模仿來實現。想當年,有經濟學家批評東亞模式有增長無效率時,一種反駁是說東亞國家的效率改善是通過引進高技術含量的機器設備實現的。但是,改革開放至今已近四十年,經濟增長奇跡的一個間接結果是中國距離世界科技前沿愈發接近,通過模仿他國創新而達成廉價技術轉移的潛力已所剩無幾。同時,勞動力成本和環境壓力也使得粗放型增長變得不可持續。
由于耽于后發優勢,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多年來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傳統的依靠要素驅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無法避免的困境,是要素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歷史上的馬爾薩斯陷阱以及近代的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皆源于此。部分西方經濟學家看衰中國前景,其理據就在于他們認為無自主創新的中國式增長不可能邁上中高等人均收入水平的臺階(宣曉偉:《我們離現代化有多遠?》,《讀書》二○一四年第四期)。為了實現這“驚險的一躍”,中國制造必須升級為中國創新。
于是,如果說自主創新不足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階段之前還只是疾在腠理的話,現在則已幾乎痛入骨髓了。未來中國經濟能否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確實命系于本國的制度安排能否調整為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模式。
二 人的因素與制度因素
號召萬眾創新的原因在于中國目前的創新供求失衡。隨著中國模式論的流行,當下很多國人抱持著一種迷思—只要某項事業進展不順,立即就寄望于政府的扶持,尤其是加大財政支持的力度。那么,中國創新的不足是由于外界的經費投入不夠嗎?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近年來我國的科技經費總量(包括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位,且仍呈逐年上漲趨勢。同時,近年來各地為了鼓勵商業模式的創新,各種孵化基地如雨后春筍一般地興起,政府的相關財政投入不可謂不大。既然不差錢,制約中國創新的更核心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雖然任何個人和企業都無法單獨完成創新,故仍可堅持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但辯證地說,我們也不該否認,某些先進者在創新中確實起了帶頭作用。按照熊彼特、哈耶克、米塞斯、諾斯等經濟學大師的觀點,這些創新的帶頭人就是所謂的企業家,“他(她)的工作是找到新思想并將它們付諸實施”([美]威廉·鮑莫爾:《企業家精神》,武漢大學出版社二○一○年版)。同時,除了魯濱孫,創新者與其他人一樣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工作的。于是,影響創新的不外乎是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
從人的因素來說,一個社會的創新水平關鍵在于該社會中是否有足夠比例的人具備創新能力(故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對于創新來說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以及該社會是否能夠為這些有創新能力的人予以有效的激勵—提供創新動力。前者和后者都取決于一個社會的制度環境,即影響創新的制度因素。人的努力有時會推動制度變遷,但更多時候,人只能在自身無法左右的既定制度下行動。例如,按照馬克思的邏輯,未覺醒的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異化,成為機器的附庸,不可能具備創新的能力和動力。endprint
經濟學的人力資本理論和能力方法都認為,能力的養成離不開教育。那么,當今中國的教育制度是有利于創新人才(潛在的企業家)的涌現抑或相反呢?其實,創新能力是教不出來的。君不見,喬布斯、蓋茨和扎克伯格哪一個不是中途輟學?馬云的畢業之所恐怕也難言名校。原因在于,創新屬于無中生有地創造新知識,是從○到一,故不可教;而課堂上傳授的都是公認的幾無爭議的知識,這種舊知識的積累是從一到二以至無窮,所以可教。
雖說創新不可教,但在當今社會,正規教育仍是創新的必要條件(因而第一次工業革命中沒受過正規教育的手工藝者成為創新主力的情況可能不會再重現),其原因有二:一是正規教育的功能在于教給學生基本的知識,從而為創新打下知識基礎,免得“思而不學則殆”,搞出些返古的假創新;二是當企業家有了創新的想法時,需要有足夠多受過正規教育的高素質勞動者將這種新想法具體化。不過話說回來,正規教育也可能抑制人的創新能力的成長。例如在八股化的教育模式下,學生們的理性行為是放棄廣泛閱讀和獨立思考,但少聞寡思會導致學生們的創新潛能全面下降(缺乏多元知識和批判精神),是為“學而不思則罔”。
會影響創新的制度遠不止于教育一葉,只不過更多維度的制度安排是通過左右激勵機制而影響人的創新動力。制度及其演化存在面向歷史的路徑依賴,我們的現有制度是對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加以揚棄的產物,而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不利于創新的。除了少數可以用非常明確的技術標準衡量的領域(如核工業和太空探索),完全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創新相對較少。對此,經濟學所能給出的解釋是:這是因為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為創新提供能充分反映貢獻的激勵。這種激勵遠不止于對企業家的直接物質獎勵,更包括資源的大規模重新配置,從而可使創新的成果代替舊的技術、商業模式和市場。不止如此,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于政治正確的強調難免會演變出“日丹諾夫主義” “李森科學說”之類的假創新,徒增一個社會的制度成本。
按照經濟學家的說法,“企業家是對可觀察的機會抱有警覺,從而會主動采取經濟行動以強化自身財富、權力和聲譽的人”(Baumol, William, and Robert Strom, 2010, “‘Useful Knowledge of Entrepreneurship: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History”, in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照此定義,中國歷史上并不罕見企業家的傳統(如胡雪巖),當代中國也不缺乏企業家的基層土壤(如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和城市待業青年自發的自謀職業),可為什么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了,我們卻仍然感到整個社會的創新不足,甚至草根的自發創新水平還不及改革之初?經濟學家從制度的角度所給出的回答是:一方面,改革初期遍地黃金式的簡單創新機會已經被拾光了,更高投入和更具風險的創新需要建立在更為激勵有效的制度環境下;另一方面,由于仍處于經濟改革的進行時,中國當前的制度安排中遺留甚或新生了大量的阻礙創新的因素。所以,雖然我們有了馬云,卻少了些張云、王云。換句話說,一個社會的企業家群體并不會突然地出現或消失(假設教育等影響創新能力的制度不變,則一個社會中企業家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應大體穩定),只不過在各類制度安排下企業家會將自己的資源投向不同領域(基于創新的尋利或依附于舊體制的尋租)。于是,制度改革應致力于為生產性創新提供激勵,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仍脫不開那句老生常談—如何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三 創新過程中的市場與政府
多數國人乃至很多經濟學家的一種思維慣性是,一旦發現市場失靈(現實對于理想的偏離),就立即寄望于政府的有形之手能糾正看不見的手。殊不知政府并非全知全能全善(否則豈非與上帝無異),故也會有政府失靈。我們不應該在現實的市場運作與理想化的政府干預之間進行比較,而是應該對比兩種機制的實際情況。例如,對于當前的創新不足,我們要先確診其病因到底是市場失靈還是政府失靈,然后才好對癥下藥。
公道地說,中國的各級政府在促進創新方面不可謂不積極,甚至將創新驅動提升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但是,看得見的手在創新領域發揮作用的邊界何在?政府在角色定位上樂于將自身視為把握創新方向和監控創新過程的主體。但“按照定義,創新是不可預測的,如果可預測,則其就算不上是創新”(Arrow, Kenneth, 2017, “Information as an Economic Commoodity”, in On Ethics and Ecom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Kenneth J. Arrow, Routledge),故政府對創新的微觀干預會以極大的概率使創新偏離最優路徑,從而將誤導而非引導創新。其邏輯在于:政府干預創新的第一步是自身(而非市場中的企業)要對創新的方向和路線進行預判,然后再在土地、信貸、稅收等政策上向政府樂見的創新領域傾斜。受這種激勵機制的影響,很多企業不是根據市場需求和價格信號去做出創新判斷,而是把精力放在了揣度和追蹤政府的意圖之上。企業的這種投機行為也需要創新(如想出新辦法來打通關系),只不過展現的是尋租型的企業家精神。這種非生產性的企業家活動不會提升社會的總體財富和生產效率,反而會因為資源誤配而起到阻礙作用。所以才會有經濟學家斷言,中國當前在產業鏈高端的高水平創新不足,“根子在于創新和企業家精神被日益強化的行政官僚體制所束縛和扼殺”(田國強、陳旭東:《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第二版)》,中信出版集團二○一六年版)。
暫且放下政府扶持在基礎科技領域的作用不表,諸多商業模式的創新其實是規避了政府干預的產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違法的,是農民們的自發努力讓違法行為最終被合法化。支付寶不是政府扶持的結果,而是私有企業與國有銀行博弈的產物。順豐快遞也沒有受過產業政策的加持,而是在郵政部門的層層阻撓之下謀得了生機。相反,某些政府成功實施了干預的領域反倒在績效上乏善可陳,如中國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扶持光伏產業的結果是產能過剩和行業虧損。就連以產業政策的成功而聞名的日本也不例外,要不是本田宗一郎等企業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堅決抵制住了通產省規模優先的產業政策,就不會有日本汽車產業后來的輝煌。馬云和本田的企業是靠自身的創新而非政府的扶持做大做強的,故企業家才是創新的最大推手。endprint
上述中國改革中成功的創新實踐說明:企業家的任務是在市場中發現和創造知識(及其所帶來的盈利機會)。按照哈耶克的洞見,知識并非靜態給定的,而是分散的、默會的、不斷更新的,先有知識的新組合才會有生產手段的新組合暨創新,而知識的運用、存續和生產所依賴的是從無序到協調的自發、動態市場過程。就是說,創新是自發秩序而非理性建構的結果,政府的過度作為只不過是“假裝有知識”—就算在信息時代、互聯網時代乃至于大數據時代也照舊無法做到。所以,激勵創新的辦法無他,唯有讓“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市場在創新過程中同樣應該起決定性作用。
當然,辯證地看,我們也不可否認政府在創新領域確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故而應該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在信息 / 知識生產中應該起到的作用是為創新培育良好的制度環境,并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按照創新所涉及的信息 / 知識的分類屬性來說,政府應該提供和生產具有正外溢性即公共良品性質的信息(如基礎科技),限制具有負外溢性即公共劣品性質的信息(如不良廠商為獲得租金而制造信息混淆),同時通過完善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來鼓勵私人性質的分散知識能夠有效投入生產領域。
政府尤其應該扶持可成為企業創新跳板的基礎性科技創新—因為“創新者通常只能獲得創新所帶來的利益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存在與創新活動相關的正外部性)。對于基礎研究和大多數應用研究來說,這是正確的。這里存在一個連續統(continuum):研究越實用,溢出的程度就越是減少。因此社會回報通常超過私人回報—證據顯示這種回報的確非常之高。在基礎研究和存在大量溢出的應用研究方面,如果沒有政府支持,就會有投資不足”([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六卷)下》,中國金融出版社二○○七年版)。但即使是在基礎科技領域,企業家在創新中的作用仍不可輕視,因為創新不同于發明或者說不能止步于發明,而是“把發明付諸實施的過程,把一個無形的創意轉變成可操作的、經濟上可行的經濟活動”([美]威廉·鮑莫爾:《企業家精神》,武漢大學出版社二○一○年版)。如果說發明是科學家的主要工作,那么將發明市場化則是企業家的專職營生,雖然兩種活動有時存在交叉(如喬布斯就兼具發明家和企業家的雙重身份)。
四 余論
“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在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國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根本解決之道就是實現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在新的生產手段的組合中提高要素的邊際回報率和國民經濟的潛在生產能力。又由于企業家的自發創新會自動避開低利潤的夕陽產業或產能過剩的領域,而選擇高利潤的朝陽產業或產能不足的領域,甚至干脆創造出新的產業從而破壞落后產能,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完成將會成為創新驅動的一個自然結果。然而,實現創新驅動實則是一個制度問題,需要全面改革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才能推進。
古往今來,阻礙改革的原因向來只有兩類:一是我們對周圍的世界沒有正確的認識,謂之認知困難;二是改革動了某些人的奶酪,即所謂的利益沖突。拙論的目的旨在為緩解第一類困難做些努力。至于如何排除第二類阻礙,則不是我輩這種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力所能及的了。幸而,按照螺旋式上升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正確觀念總是可以戰勝既得利益的阻礙。思之,足可自慰矣。
(補記:本文初稿完成之際,驚聞當代創新經濟學大師鮑莫爾教授不幸離世。同悲之余,謹以此文悼之。)
《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
劉莉、陳星燦 著 定價:75.00元
本書展現了中國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對此時段內的考古發現、研究成果,以及文明誕生和發展的現象和動因進行了系統梳理和解釋。對狩獵采集者的生存適應模式、文明誕生、農業起源、早期國家的誕生等焦點問題進行了詳述。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