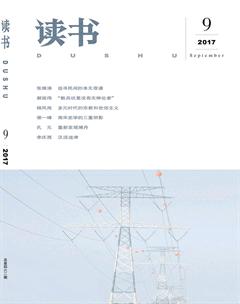吃貨與鄉情
孫歌
對于全世界的吃貨來說,不了解中國的飲食就談不上有文化。這倒不是因為中國菜好吃,而是因為,中國飲食譜系繁多,以至于無法用有限的幾樣來代表它。因此,打算籠統地討論中國菜,基本上是癡心妄想;而作為吃貨,了解飲食的復雜性才能彰顯有別于口腹之欲的文化品格。
很多社會的菜系,都是有代表性品類的。比如提到日本菜,人們會立刻想到生魚片、壽司、天婦羅;說到韓國菜,烤肉、泡菜、冷面當仁不讓;說到意大利菜,首推意大利面、比薩、海鮮飯;說到印度菜首推各種咖喱;說到英國菜是魚和薯條;說到德國菜是酸菜豬肘;說到法國菜,那就讓人想起蝸牛、鵝肝了……不是說這些社會里沒有別的菜式,也不是說這些被視為代表的菜式最好吃,但是,一個社會的飲食里面有代表的品種,這似乎成為吃貨們的常識。
這個常識對于中國的飲食文化而言,似乎不太有效。有位日本朋友對我說,中國菜很難像日本菜那樣找到代表性的菜系,所以,說到中國菜,他們只能說“中華料理”了。所以他問我,能不能舉出一個菜系來代表中華料理呢?
我一時間語塞。作為一個東北人,我不打算說東北菜是中國菜系的代表。而我喜歡的菜系實在很多,厚此薄彼也不公道。最后,我只能回答說:對中國人提這樣的問題,不,對中國菜提這樣的要求,并不是個明智的做法。
很多年以前,我和幾個北京的朋友一起造訪杭州,當地的朋友設宴招待我們。盛情與美味,使得在場的幾個北京人都異口同聲地說,相比之下,北京菜實在不值一提。時至今日,我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當時究竟吃了什么菜,但是這有趣的自我否定姿態,卻一直留在記憶里沒有褪色。
另外的一次,我在上海受到了友人的招待。上海菜和杭州菜相近,都有咸甜適中的特點,很合我的口味,所以,盡管具體吃了什么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是吃到的東西很美味,這個模糊的感覺卻和那次吃杭州菜一樣,都留在我的感覺記憶中。但是,更為鮮明的記憶,卻是在酒足飯飽之后友人與我的一段對話:
“接下來你要去哪里呢?”
“從這里直接去廣州。”
“那還是再多吃點吧!去了廣州,怕是也吃不到什么好東西。”
廣東菜一直是我喜愛的菜系,雖然有很多笑話調侃廣東人什么都拿來煲湯,可是我還是很喜歡廣東的湯。聽到上海朋友漫不經心的話,我不由得大吃一驚。
于是我到了廣州。當地的朋友熱情地招待了我,我喝到了美味的湯,也吃到了講究的廣東菜。席間,廣州的朋友問我從哪里來,我回答說從上海來。于是,廣州的朋友也同樣不經意地說:“那你餓壞了吧,上海也沒有什么好吃的啊!”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在香港吃廣東點心。我問同桌的香港人:香港的點心跟廣東的點心,是不是同樣的味道?
那位香港朋友毫不猶豫地說:當然不一樣。廣東的點心和廣東菜都太油膩,而且也很粗糙,香港的更為精致……
中國人對于家鄉菜的那份執著,絕對不是可以小覷的事情。舌尖上的中國,準確地說應該是舌尖上的鄉情。人總是對自己的家鄉情有獨鐘,哪怕表現得有些偏執,也是可以原諒的。倒是我們那次在杭州對北京菜的自我否定,顯得有些離譜,不過,那或許并不能代表北京胡同里的感覺,因為我們中只有一位是貨真價實的北京人—雖然對北京菜的自我否定,他叫得最響。
家鄉菜是文化認同的重要媒介。曾幾何時,《我的中國心》唱響大江南北時,有位從美國歸來的友人對我說了句半開玩笑的話:我倒是沒有什么中國心,可是我有個地地道道的中國胃。
我不能算是個合格的吃貨,不過,不知不覺間,我懂得了一個重要的道理:菜品所擁有的文化性質,絕對不可以隨意輕慢。要了解一地的文化,從吃開始也許是個捷徑。
在日本,我最不喜歡吃的,就是當地的中華料理。無論是高級的還是普通的,日本的中華料理總讓我覺得不倫不類。因為,雖然大師傅可能是中國人,但是食客卻是日本人為主,所以,無論如何,總要配合食客的偏好。實話實說,日本的中國菜雖然也很美味,它卻已經成為日本料理的一個分支,而且總不免讓我跟國內的原版做比較,這有些像我不太喜歡在國內吃日本料理一樣。
飲食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因為它需要配合各種環境元素。從前,我不喜歡吃四川菜,因為它的麻辣讓我很不舒服。后來有一次我到重慶小住,在漫天霧氣中突然愛上了重慶小面,從而理解了重慶火鍋為什么需要那么強烈的感官刺激。雖然我回到北京之后又不太吃川菜了,但是,對于川菜卻多了一種理解,甚至是認同。記得有一次在南京,酒店里的早餐提供了豆腐腦。鄰桌一位顯然來自四川的年輕女老師吃了一口,大聲用川味普通話說道:“這東西不加辣子,怎么能吃呢!”我聽了之后,不知道為什么竟然覺得有道理,雖然那碗豆腐腦不加辣子依然味道不錯。
四川人這種一絲不茍的飲食品格,有時讓我覺得羨慕。聽說去四川的時候,如果你向大師傅要求一碗不加辣椒的擔擔面,他也許會配合,但是卻會在做好那碗不辣的面條之后,在上面加上幾個紅紅的辣椒塊,并且囑咐你吃的時候先拿掉它們。沒有辣椒的川菜,宛如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是任何一個川菜廚師都無法容忍的。我倒是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廚師,不過也有過類似的經驗:有次在一家面店里點了一碗牛肉面,傳菜員很認真地問我要不要加辣椒,我說不要加辣椒;結果端出來的卻是一碗大號的加了大塊牛肉的“擔擔面”—原來這種程度的辣,在川菜里只不過是基礎調料而已,不能算是“加辣椒”。我一邊用手絹擦著辣出來的汗,一邊不免想象:要是我回答說加辣椒,那會吃到什么呢?重慶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地道的重慶家庭里肯定有一位調小料的高手,往往還是不外傳的獨家秘方;用十幾二十種材料做出的麻辣小料,那是只有自家才能獨享的奢侈品。
因為講學而在重慶小住,讓我有機會了解了重慶火鍋的秘密。北京人對火鍋的想象不會超越東來順涮羊肉的范圍,然而用同樣的邏輯去對待重慶火鍋,那可是原則性錯誤。重慶火鍋不僅麻辣,而且重油,然而重慶街頭似乎并沒有因此而充斥著胖子;個中的秘密,原來在吃火鍋的蘸料里。我們在北京吃涮羊肉,往往用芝麻醬和醬油做基礎調料,而且吃貨們往往一頓火鍋要消耗不止一碗調料;但是重慶火鍋卻以香油或菜油加上蒜末作為基礎調料,它的功能在于化解食物的辣味。在很多火鍋店里,碗碟邊上都會加一個小易拉罐,里面是一罐香油,這就是基礎蘸料。原來,無論多么麻辣,都可以用油脂瓦解它的強度,難怪川菜喜歡大量用油。既然如此,就需要改變一下我們對蘸料的態度:重慶火鍋的蘸料不是用來吃的,所以地道的重慶人吃火鍋的時候,這一小碗蘸料會越吃越多—不僅原有的油脂不會被吃掉,而且從鍋里撈出來的各種食物,也會在蘸料里減輕麻辣強度的同時,把從鍋里帶出來的油脂湯水也一并留下。當重慶朋友津津樂道地給我啟蒙的時候,我終于明白了,原來北京的川菜火鍋真的只是贗品。endprint
作為東北人,我對家鄉菜并沒有應有的那份執著,這讓我在其他省份的朋友面前一直感到有些心虛。實話實說,小雞燉蘑菇,豬肉燉粉條,這些菜當年曾經讓我期盼著早些過年,但是時至今日,卻并未轉化成思鄉的味道。想到這些代表性的菜肴時,我印象深刻的倒是一些跟味道不那么相關的細節:當年插隊去,鄉親們請客的時候,一大鍋燉出酸菜白肉粉條,盛到大碗里卻變成了兩道菜—一碗是酸菜粉條,另一碗是肉片粉條。那年頭,吃點肉不容易,沾了肉味的酸菜粉條,也可以作為一道菜肴獨立。鄉親們的這種苦心與智慧,讓我一直難以忘懷。當然,那時的酸菜白肉之美味,也是后來我吃到的各地美味所無法取代的。
現在,東北菜也算是一個菜系了,不過很多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比如松仁玉米,我從前并沒有見過。當然,我絕對不敢說這不是東北菜,因為我畢竟見識有限,而東北其實很遼闊。
雖然不那么拘泥于家鄉菜,家鄉的味道對我來說依然是一種難以忘懷的奇特感覺。想起來有些奇怪,我感覺記憶中的家鄉菜,竟然集中于我兩次插隊那些日子的飲食印象。那是我生命中最清苦的時期,特別是第一次,隨父母下鄉的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家里很少能夠吃肉,還未成年的我又正是在意吃食的年紀;然而留在我記憶里的,并不是年節時的肉食,卻是散發著淡淡清香的黏豆包。
黏豆包是東北農村特有的一種主食,由紅小豆做餡,黏米做皮。這種黏米當地稱為黃米,外形有些類似小米,但是具有糯米一樣的黏性。黃米又分大黃米和小黃米兩種,我家插隊的吉林省農村,以大黃米為上乘。每年冬季,天寒地凍之時,各家的主婦會把黃米磨成粉,發酵后包成豆包,蒸熟,冷凍。臘月的東北是天然冰箱,各家院子里的小庫房就是冷凍室,黏豆包蒸熟后送入這天然冰箱,冰冷如鐵,一排排帶著細碎的冰碴兒,整齊地裝進袋子里收藏起來。在村莊的臘月里,勤勞的主婦會蒸出整個正月里的黏豆包,供全家人和前來串門的客人享用。來客時,端上一盤子黏豆包,是家庭小康的象征,要是再配上一碟白糖,那簡直就是貴族了。
我還記得當年跟著母親學做黏豆包時的情景。黃色的面皮,紅色的豆餡兒,在我眼里是世上最好看的顏色。豆包蒸熟,皮兒是酸的,餡兒是鮮的,沒有白糖,卻是無上的美味。這種美味很珍貴,因為東北人并非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它,黃米和紅小豆在當時都屬于奢侈品,只有打著過年的旗號才能合理合法地吃到。是啊,那個時代樸素的“正月”,黏豆包是不可缺少的主角。正因為如此,粗糙卻新鮮的味道,才會幻化出生命中的一抹亮色。不過,還有另外一層理由同樣不可忽視:即使在物質不再匱乏之后,黏豆包仍然是季節性食物——它只有配合了東北地區特有的嚴寒,才能激發出人們味覺的滿足感。沒有徹底冷凍過的黏豆包,那就像是摳像的明星一樣,再漂亮也不地道。
二十多歲移居北京,我一直沒有機會與黏豆包邂逅。偶爾一時興起,我會移情別戀于冰糖葫蘆。這也是對嚴寒有要求的食物,盡管商店里的冰糖葫蘆攤檔每年秋末就早早開張,春風刮起也不肯收攤,我卻只在寒冷的日子里才肯出手。食物與氣候環境的關系,通過味覺來定格,這或許就是美食的奧秘所在吧。
隨著北京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飲食店充斥了大街小巷。我家對面開了一家東北赫哲族餐館,里面開始賣黏豆包了。第一次請客去這家餐館,也是在寒冷的冬天,我立刻點了一籠。店員端上竹制的籠屜,同時送上一碟白糖。同桌的友人十分奇怪,問我其中的關系,我示范了黏豆包蘸白糖的吃法,友人紛紛效仿,反應卻并不熱烈。對他們來說,這大概是很奇怪的食物,實在說不上好吃;不過說老實話,我自己也沒有找到期待的感覺。這籠黏豆包沒有缺點,卻缺少個性。它沒有我當年在鄉下吃到的那種因發酵而來的獨特酸味,當然也因此更容易被食客接受,只是,如同今天統一考試的標準答案一樣,標準固然標準,卻很難給人留下特別的印象。
可見,飲食的執著,并不能僅僅歸結于味覺與氣候環境給人的感覺,還需要一些其他的要素。飯店的黏豆包無法喚起我少年時代的記憶,顯然因為我已經不再擁有當年的心情。回想起來,我對于黏豆包的不舍之情,似乎與窘迫生活中意外出現的快樂有關。當年隨著父母插隊,雖然物質生活并不寬裕,但是卻躲開了城市中造反派的迫害,淳樸的鄉親們讓我們全家在動蕩的年代里獲得了安全感,黏豆包這種在城市里未曾見過的食物,就在那份來之不易的安全感中給我帶來了獨特的慰藉。至今我依然還清楚地記得,在冰天雪地里拉開簡陋的儲物間木門,從布袋子里拿出冰凍的黏豆包時的那份快樂—在我,那真是個奢侈的瞬間。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認為,地方菜肴永遠只與那個地方有關。直到不久前我造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時候,這種感覺才開始松動。
在這兩個擁有大量華人移民的國家,我反復地聽到同一句話:“這里的海南雞飯最正宗。”我沒有吃過不正宗的海南雞飯,沒有什么比較的資本,但是啟蒙從經典開始,總是不會錯的。于是新加坡的朋友帶我去了當地一家據說是最正宗的海南雞飯店鋪,讓我吃到了一頓簡單的美味:原來就是白切雞加上米飯。不過,據說那看似簡單的雞肉和米飯各有講究,并不是普通的做法。我努力地品味著,希望以后吃到冒牌的海南雞飯可以辨認出來,但是有個疑問卻依然讓我無法釋然:正宗的海南雞飯不在海南,卻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新馬的朋友對我說,倒不是說海南島上已經沒有雞飯可吃了,問題在于,新馬的海南雞飯仍然恪守著一兩百年前的樣子,而海南島的雞飯卻不斷花樣翻新,丟掉了本色。
“再說了,現在海南島上到處都是東北人嘛!”
我想到今天大陸的東北菜肴,包括我并不熟悉的松仁玉米,認可了這種說法。移居到新馬的華人后代,還忠實地傳承著地道的海南菜、福建菜和廣東菜,這讓我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我想起了日本那些并不恪守原教旨的中華料理,依稀覺得其間有些不同的性質,卻又難以判斷。
不久之后,我又去了海南。招待我的朋友們里似乎沒有正宗的海南人,不過他們也盡心盡力地帶我去了海口著名的小吃城。我在里面品嘗了海南人過年必吃的素菜煲,一邊想象新加坡和馬六甲的海南餐館里是否也有同樣的東西,覺得當一個吃貨實在需要過硬的本事,而我似乎不太具備。不過,在海口砍開的椰子,確實比馬六甲餐館里拿出來的冷凍椰子鮮爽可口,個頭也比較碩大,我總算比較了一回。
然而印象最深的,卻是我在海口吃到的東北菜。那是地道的東北人做出的東北菜,喚起我兒時的模糊記憶。其實這些年偶爾回東北,我已經無法吃到曾經的東北菜了,倒不是它們不存在,而是我跟它們再也無從接頭。東北的朋友們,一定會帶我去當地人覺得好吃的飯店,吃那些絕對不便宜的大魚大肉,那些司空見慣的家常菜,不會被實在的朋友拿來招待我。倒是在海口,東北菜的家常和淳樸變成了賣點,身價激增,我才和它們得以謀面。當然,非要挑剔不可的話,我還是要說一句,這個餐館里的花皮豆角缺少東北豆角特有的厚實口感。問起緣由,海南朋友笑答:海南氣候炎熱,豆角成熟太快,只好就這么水嫩著燉啦。
海口東北菜館里端菜沖茶的姑娘們,齊刷刷地在盤起來的頭髻上插著不止一個煙袋鍋,大概是對東北三大怪之一的“大姑娘抽煙袋”的形體詮釋?這個十分拙劣的設計似乎走的是趙本山紅火的那些日子里以土為美的成功路線,不知道為什么,我在離開海南之后,印象里最鮮明的竟然是它。在人口高度移動的今天,地域文化逐漸地變成了符號。人和地域、氣候、環境的關系,在這樣的移動中并沒有被消滅,但是卻再也無法直觀地想象。在海南吃東北菜,在新馬吃海南菜,在北京吃廣東菜、淮揚菜和天南地北的各種菜肴,看上去已經破壞了人與環境的固定關系,實際上,破壞的只是外在的關聯,內里的連接,卻在我們的心里。吃貨用味覺記憶鄉情,而鄉情并不存在于舌尖之上,它只有在吃貨的心里,才能激發出真正的味道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