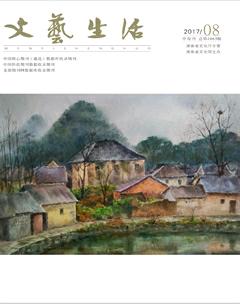談美術(shù)作品的民族風(fēng)格
程偉
摘 要:民族風(fēng)格是一個(gè)民族在長(zhǎng)時(shí)期發(fā)展中形成的反映本民族特色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是由一個(gè)民族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生活、自然環(huán)境、風(fēng)俗習(xí)慣、藝術(shù)傳統(tǒng),以及共同的心理狀態(tài)、審美觀(guān)點(diǎn)等多種因素構(gòu)成的。由于一個(gè)民族具有相對(duì)固定的居住范圍,因此美術(shù)的民族風(fēng)格與地方風(fēng)格具有一定的聯(lián)系,但二者不能等同,畢竟影響民族風(fēng)格最主要的因素是有共同審美心理的人群,而影響地方風(fēng)格最主要的因素是地域環(huán)境。
關(guān)鍵詞:美術(shù)作品;民族風(fēng)格;創(chuàng)作
中圖分類(lèi)號(hào):J206.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5-5312(2017)23-0019-01
富有民族特色的美術(shù)品,不但為本民族的廣大讀者所喜聞樂(lè)見(jiàn),也可以為其他民族的讀者所理解和喜愛(ài),從而使獨(dú)具民族風(fēng)格的美術(shù)品進(jìn)入世界藝術(shù)寶庫(kù),成為人類(lèi)共同的財(cái)富。這正契合了當(dāng)下流行的一句話(huà):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藝術(shù)貴在多元并存、百花齊放,獨(dú)具特色的民族美術(shù),拿到別的美術(shù)風(fēng)格中去,容易顯得新奇,引人注目與驚嘆;而且美術(shù)的民族風(fēng)格往往是一個(gè)民族長(zhǎng)期積累沉淀下來(lái)的精華,本身就很有魅力。所以美術(shù)品越有民族風(fēng)格,越獨(dú)特,越鮮明,越容易被其他地區(qū)、其他民族所喜愛(ài),就越能走向世界。
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瓷器藝術(shù),含蓄而淡雅,高貴且溫潤(rùn),以獨(dú)特的民族風(fēng)格,讓世界對(duì)中國(guó)有了認(rèn)識(shí)和了解。China——瓷器——中國(guó),這三個(gè)詞語(yǔ)是一個(gè)整體,在西方人的眼中,瓷器就是中國(guó),瓷器就是中華民族的特色。傳統(tǒng)卷軸畫(huà),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中華民族風(fēng)格,當(dāng)北京奧運(yùn)會(huì)開(kāi)幕式上巨大卷軸徐徐展開(kāi)的時(shí)候,宏偉壯麗的中國(guó)詩(shī)篇開(kāi)始上演。書(shū)法藝術(shù),也具有獨(dú)特的中國(guó)特色,唯有中國(guó)的書(shū)法,把文字與書(shū)寫(xiě)發(fā)展成了意味雋永的藝術(shù)形式。紙、筆、墨、硯,再加上書(shū)齋、園林小景,便可組成一個(gè)典型的中國(guó)場(chǎng)景。可以說(shuō)中華民族歷史悠久,自文明初創(chuàng)的5000年以來(lái),形成了太多具有民族風(fēng)格的美術(shù)元素,這些元素,又反過(guò)來(lái)彰顯中國(guó)獨(dú)特的民族風(fēng)格。
有趣的是,當(dāng)西方的美術(shù)形式根植于中國(guó)本土之后,很快就會(huì)被中國(guó)化,形成中國(guó)風(fēng)格,這是由于中國(guó)文化具有強(qiáng)大的結(jié)構(gòu)力特點(diǎn),善于吸收和消化外來(lái)藝術(shù)樣式,并迅速轉(zhuǎn)化成本民族特色。油畫(huà)這種西方主要繪畫(huà)方式被中國(guó)藝術(shù)家接納和運(yùn)用也有一個(gè)民族風(fēng)格的形成過(guò)程。油畫(huà)引入中國(guó)是在明清時(shí)期,當(dāng)時(shí)油畫(huà)以寫(xiě)實(shí)性為主體,依照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美術(shù)理論,不能人藝術(shù)之流。清代畫(huà)家鄒一桂在其《小山畫(huà)譜》中有一段評(píng)說(shuō):“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繪畫(huà)于陰陽(yáng)遠(yuǎn)近,不差錙黍,所畫(huà)人物、屋樹(shù),皆有日影。其所用顏色與筆,與中華絕異。布影由闊而狹,以三角量之。畫(huà)宮室于墻壁,令人幾欲走進(jìn)。學(xué)者能參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筆法全無(wú),雖工亦匠,故不人畫(huà)品。”鄒一桂說(shuō)得比較極端,但也確實(shí)是油畫(huà)初入中國(guó)時(shí)的尷尬。中國(guó)畫(huà)家真正使用油畫(huà)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油畫(huà)的風(fēng)格民族化還是從20世紀(jì)初開(kāi)始的。當(dāng)時(shí)一批接受了西方審美教育的留學(xué)生試圖以西洋畫(huà)創(chuàng)作來(lái)挽救中國(guó)繪畫(huà)的頹勢(shì),但是他們學(xué)成歸國(guó)后,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shí)還是不能容忍那種透露西方文明的明暗、色彩和表現(xiàn)方式,僅是對(duì)西洋畫(huà)嚴(yán)謹(jǐn)?shù)脑煨捅憩F(xiàn)出一些興趣而已,這些藝術(shù)家自覺(jué)地開(kāi)始了融合的工作,這也是油畫(huà)民族化的開(kāi)始。
油畫(huà)已經(jīng)被正式納入中國(guó)繪畫(huà)教育體系,如何讓這種外來(lái)的藝術(shù)形式真正成為中國(guó)人自己的東西?人們?yōu)榇苏归_(kāi)持續(xù)討論,有人認(rèn)為油畫(huà)既然是外來(lái)畫(huà)種,就應(yīng)該保持外來(lái)視覺(jué)語(yǔ)言特色,不能同中國(guó)藝術(shù)混為一談;也有人認(rèn)為中國(guó)人畫(huà)油畫(huà),或多或少都會(huì)有中國(guó)味道,無(wú)意強(qiáng)求民族風(fēng)格;也有人指出自覺(jué)追求油畫(huà)的民族氣派是必要的。在這不到100年的時(shí)間里,在對(duì)油畫(huà)民族化問(wèn)題的討論中,油畫(huà)藝術(shù)實(shí)踐從來(lái)沒(méi)有停止過(guò),而且在把油畫(huà)這種西方成熟的繪畫(huà)語(yǔ)言結(jié)合中國(guó)實(shí)際情況的過(guò)程中,風(fēng)格面貌確實(shí)發(fā)生了變化。
董希文的油畫(huà)《開(kāi)國(guó)大典》以濃厚的中華民族風(fēng)格和宏大的中國(guó)氣魄展示了一種油畫(huà)的新面貌,為建國(guó)初期油畫(huà)的中國(guó)風(fēng)格樹(shù)立了時(shí)代楷模。從構(gòu)圖到設(shè)色,從人物到場(chǎng)面,都滿(mǎn)溢中國(guó)風(fēng)度。畫(huà)家借用了民間年畫(huà)、敦煌壁畫(huà)、工筆重彩的傳統(tǒng)繪畫(huà)方式,不強(qiáng)調(diào)光影變化的視覺(jué)效果,而著重加強(qiáng)高純度色彩的運(yùn)用與對(duì)比,加之出色的油畫(huà)技藝,使畫(huà)面取得了既富麗堂皇、莊嚴(yán)熱烈,又通俗親切的效果,在探索油畫(huà)民族風(fēng)格上獲得了巨大成功。董希文指出“我們的各種藝術(shù)都應(yīng)該具有自己的民族風(fēng)格…… 關(guān)于油畫(huà),由于我們努力學(xué)習(xí)蘇聯(lián)及其他國(guó)家的油畫(huà)經(jīng)驗(yàn),已經(jīng)有了顯著的進(jìn)步,產(chǎn)生出許多能真實(shí)地表現(xiàn)生活的作品,但為了使它不永遠(yuǎn)是一種外來(lái)的東西,為了使它更豐富起來(lái),獲得更多的群眾更深的喜愛(ài),今后,我們不僅要繼續(xù)掌握西洋的多種多樣的油畫(huà)技巧,發(fā)揮油畫(huà)的多方面的性能,而且要把它吸收過(guò)來(lái),經(jīng)過(guò)消化變成自己的血液,并使其有自己的民族風(fēng)格。……油畫(huà)中國(guó)風(fēng),從繪畫(huà)的風(fēng)格方面講,應(yīng)該是我們油畫(huà)家的最高目標(biāo)。……油畫(huà)上是否能發(fā)揚(yáng)我們民族的特色,實(shí)質(zhì)是首先要問(wèn)一個(gè)畫(huà)家他的血液里是否具有自己民族的藝術(shù)因素在內(nèi),提得更高來(lái)說(shuō),是否是更多地去考慮中國(guó)人民對(duì)于藝術(shù)的欣賞習(xí)慣和喜愛(ài)的深度的問(wèn)題。”至此,繪畫(huà)界掀起了董希文一直倡導(dǎo)的“油畫(huà)中國(guó)風(fēng)”,而這種思潮一直影響至今。
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中國(guó)的油畫(huà)創(chuàng)作進(jìn)入自由而生動(dòng)的時(shí)期,油畫(huà)的形式問(wèn)題談得相對(duì)少了,油畫(huà)的內(nèi)涵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中心,說(shuō)明這種外來(lái)畫(huà)種基本適應(yīng)了中國(guó)的國(guó)情,“他者”的身份逐漸消失,開(kāi)始成為中國(guó)畫(huà)壇不可或缺的藝術(shù)形式。羅中立的《父親》、陳丹青的《西藏組畫(huà)》、陳逸飛的《潯陽(yáng)遺韻》、靳尚誼的諸多肖像畫(huà),以及方力均、劉小東、李曉剛等當(dāng)代油畫(huà)家的作品,以各自獨(dú)特的方式參與時(shí)代的記憶與書(shū)寫(xiě),成為不可或缺的中國(guó)印象。
參考文獻(xiàn):
[1]李艷萍,廉睿強(qiáng).美術(shù)作品:形象、寓意與風(fēng)格[J].芒種,2012(2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