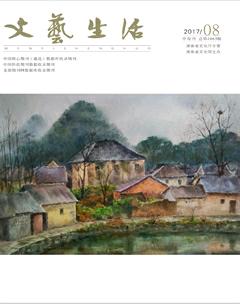淺談《源氏物語》的美學思想
樊情
摘 要:當前對于《源氏物語》美學思想的研究主要總結了“物哀”、“幽玄”、“風雅”這三大觀點。本文通過介紹《源氏物語》以及其作者紫式部,敘述并分析在大的社會背景條件下對《源氏物語》美學思想的影響。
關鍵詞:源氏物語;物哀;美學思想
中圖分類號:I313.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23-0066-02
一、日本美學思想的發展及源氏物語美學思想的研究現狀
日本傳統文學美學的基調——真實(まこと),提倡寫實主義、充分體現現實與文學的統一。隨著社會的發展,日本的文學美學趨向演變為“哀”(あわれ),但是隨著文學思想、文學理念的豐富“哀”已經不能夠體現日本文學的審美內涵,于是在“哀”的基礎上升華歸納總結出現了“物哀”(物の哀れ)這一經典的日本美學思想。紫式部的《源氏物語》的文學理論就是以“物哀”為中心的。居宣長曾提出《源氏物語》的本旨是“物哀”。而紫式部在日本文學史上對于“物哀”的完成有著極大的作用。日本古代文學思潮由“哀”到“物哀”是經紫式部之手完成的。
《源氏物語》中的主導審美思想是“物哀”同時它也體現了“風雅”與“幽玄”。日本人一直生活在過于超政治性的土壤之中。于是,日本的文學無可避免的帶有超政治性的色彩——“風雅”。幽玄是以歷史社會為背景,展示著多姿多樣的形態,可以說它不僅僅是日本中世、也是整個日本文學的重要的中心文學理念。古代日本人在接受外來文化的過程中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加以取舍,把中國古典文學富于社會政治批判精神的文學作品排除在外。而吸收他們喜歡的符合他們的審美情趣的東西。紫式部的知識體系和思想淵源都受到了中國古典思想與佛教的影響這些因素就成就了《源式物語》中的“物哀”、“風雅”和“玄幽”這三大美學思想。但在整個的《源氏物語》中還是以哀為美的“物哀”為主要美學基調的。
二、《源氏物語》及紫式部
(一)《源氏物語》
《源氏物語》是日本文學史上的杰作,被廣大學者為“日本的《紅樓夢》”。 它以奢靡的宮廷生活為背景,通過對主人公源氏政治上沉浮的描述和奢靡感情生活的刻畫來展現當時宮廷貴族們圍繞著“權勢”二字所發生的聚散離合、及錯綜復雜的權勢之爭。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整個宮廷貴族、尤其是大貴族奢華糜爛的生活以及紊亂的男女關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上層貴族腐朽的精神面貌。也預示著物極必反盛極而衰——這一帶有宗教色彩的悲劇觀。這部作品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從首卷的“桐壺”到三十三卷的“藤花末葉”主要描寫的是源氏的前半生,述說了他與十悲情女子之間的情感糾葛。第二部分從三十四卷的“新菜(上)”到四十一卷的“云隱”著重分析源氏的心理活動,描寫了源氏對年輕時期生活的后悔和對人世的徹悟。第三部分以宇治為舞臺、熏為主人公,鋪陳了紛繁復雜的男女糾葛事件。“作者紫式部在《源氏物語》全書貫穿了濃厚的無常觀和宿命思想。”
(二)紫式部其人
紫式部(約973~1014年),平安時期的女作家、歌人,出身于書香門第。熟讀中國典籍、擅樂器和繪畫,信仰佛教。約22歲時,嫁給比自己年長20多歲已有妻室子的地方官藤原宣孝,體驗了一夫多妻制家庭生活的辛酸。她、作為一個中等貴族的婦人在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年代“她在生活中所感受的哀痛,使她具有了進行創作的一個最主要基礎:悲劇感,也使她的作品呈現出哀艷凄婉的悲劇美。”加之多年的宮庭生活,讓她親眼目睹了宮庭婦女的不幸遭遇,對她們悲慘的命運有深切的感受。“從舊壘中來”,對其中“情形看得較分明”(魯迅語),使她對封建貴族階級的驕奢淫逸的生活了解透徹,對貴族家庭由盛及衰的過程看得真切。遭家道中衰之變,嘗個人喪偶之苦,晚景悲涼。在她的身上有一種“世事無常嘆飄零”的感傷。作為一名女性作家她反映了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女性的命運、《源氏物語》真正動人的力量也是來自于那眾多的栩栩如生的貴族婦女以及的她們的愛情婚姻悲劇。紫式部的筆下處處透著一股哀傷:不僅僅是作者對自己命運的哀傷更是整個日本社會的哀愁與悲傷。那是一種“日本式的多愁善感的文學精神,西洋人稱之為日本式的哀愁。”
三、《源氏物語》美學思想的產生
(一)中國古典思想的影響
在讀《源氏物語》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里面有大量的“詩歌”。那些詩歌有的平實易懂如“生前誠可恨,死后皆可愛”、有的像五言詩如“冷露凄風夜,深宮淚滿襟。遙憐荒渚上,小草太孤零”、有的像七言詩如“面臨大限悲長別,留戀殘生嘆命窮”。這些詩歌或抒情、或詠物、或嘆情事。雖然《源氏物語》中詩詞比較中國的詩歌來說在遣詞、意義的表達、意境等方面都遜色了許多。但我們可以看出漢學對《源氏物語》的影響。紫式部在《源氏物語》中的精彩表現的確離不開她本人在中國漢學方面的造詣,她的父親是漢學家,耳濡目染使她對漢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她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漢學教育,她深厚的漢學修養在《源氏物語》中有充分的體現。《源氏物語》中引用中國古典文學典籍185處,其中白詩(白居易的詩)達106處之多。但是,日本人對于我們中國古典文化的吸收并非照搬,他們只是吸收自己喜歡的,屏棄不符合自己審美趨向的東西。如唐代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等“閑適詩”和“感傷詩”大受他們的歡迎。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詩詞分為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但紫式部卻只是對“閑適詩”和“感傷詩”情有獨鐘。 這些就影響了源的行文基調——“閑適”而“傷感”,在風雅的同時又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傷感、“物哀”之美—“日本式的哀愁。”
(二)佛教思想的影響
《源氏物語》處處透著一股命中注定的哀傷、源氏對自己的悔恨對自己年輕是放縱的悔恨,對人生、人世的徹悟,這些都是注定的宿命的輪回,佛教的無常思想、日本的“物哀”。紫式部“物哀”文學觀和審美觀中儒佛道思想的印記是平安以后日本民族對中國儒佛道思想的批判式地接受在文學上的具體體現,這又進一步說明了“物哀”與佛教的關系。她還信仰佛教,由于信仰佛教使她在自己的作品(《源氏物語》和《紫氏部日記》)中有意識無意識地回流露出佛教方面的思想。這就是佛教思想對《源氏物語》美學思想以及作者本人基本審美趣向的影響。
“《源氏物語》中的悲劇建立在佛教悲觀、虛無主義基礎之上,努力表現“前身自業”、“因果報應”和“陰陽輪回”等佛教觀念,缺乏對命運的抗爭力,但表現了這種使人興嘆、使人感動、使人悲哀的‘物哀”。
四、結語
《源氏物語》是一首憂傷的詩、透著悲劇美,它是封建社會的警鐘,警示著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端。它是哀歌、封建末世的哀歌,它是悲歌、眾多女性的悲歌。它是一面鏡子折射了那個時期日本社會的哀傷和那個時代特有的悲劇美。那種與佛教虛無憂傷一樣淵源流長的“物哀”之美,一種櫻花凋零般的傷感情懷。它的作者正是用她細膩的筆在體驗宮廷生活之后,又從吸收佛教思想之后完成日本文學史上由“哀”到“物哀”的轉變的。
參考文獻:
[1]謝志宇.20世紀日本文學史——以小說為中[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2]劉潤德,張文宏,王磊日.本古典文學賞析[J].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12).
[3]王詠梅.“哀”與“物哀”—— 論日本古典文學的感傷悲美[J] .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03).
[4]曾真.哀艷與清麗——《源氏物語》與《枕草子》美的意識比較[J].湘潭大學學報,2000(12).
[5]張銅學,龍菊英.《紅樓夢》與《源氏物語》比較研究[J].懷化學院學報,2006(12).
[6]尤忠民.日本文學中的傳統美學理念——物哀[J].天津外國語學院院報,2004(06).
[7]葉琳.“風雅”與“超政治性”的日本文學[J].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2005(04).
[8]邵永華.源氏物語及物語文化考辯[J].湛江海洋大學學報,2006(10).
[9]李瑩.日本平安時代的女性文學[J].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1).
[10]李青.淺談日本文學理念——幽玄[J].湖北教育學院學報,2004(0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