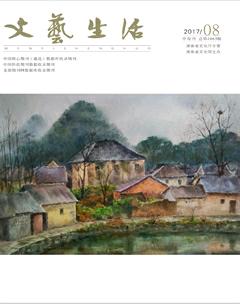明中葉散文發展因素淺論
趙西芝
摘 要:明代文學的中期,一般是指從弘治到隆慶(1488—1572)的近百年時間。這是明代文學從前期的衰落狀態中恢復生機、逐漸走向高潮的時期。這一時期文學復古思潮日趨活躍,整個文壇幾乎籠罩在濃厚的復古思潮之中,試圖重新審視文學現狀,尋求文學出路。受此影響,明中葉散文得到了長足發展,流派眾多、名家輩出。究其原因,程朱理學、臺閣體、八股文、陽明心學,甚至民歌都對明中葉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或推動或制約的影響,本文力求在影響明中葉散文發展因素這一方面做一些簡單研究,讓大家能對明中葉散文有一個更為清晰的了解。
關鍵詞:明中葉散文;程朱理學;陽明心學;民歌
中圖分類號:I20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23-0114-02
一、程朱理學、臺閣體對明中葉散文的制約
程朱理學在明初被指定為官學,是有明一代的正統思想。以致整個社會崇經窮理的風氣十分盛行,影響到文學領域,致使“尚理不尚詞,入宋人窠臼”①的創作理氣化現象趨向活躍。再加上明初的幾代君王都對程朱理學特別垂青,甚至一度上升為崇拜,拜在程朱理學門下不肯挪步,所創作的詩文也都賡和升平,雍容典雅,以至形成臺閣體,統治文壇幾十年。明初程朱理學的流行和臺閣體的興盛,再加上森嚴的文化專制、宦官的專權使得明代文學毫無生機、死氣沉沉,幾乎窒息了整個文壇,同時也使散文的發展陷入了一個死胡同,內容上大多為頌圣德、歌太平,藝術上講究雍容典麗,缺乏生氣。因此,袁行霈認為“這些潛伏在社會安定興盛背后的壓力,多少對文人起著震懾的作用,使他們不敢去正視和表現廣闊的社會生活,抒發個人思想感情”②。直到明中葉,程朱理學受到懷疑,臺閣體衰弱,復古之風漸興。明中葉散文才擺脫束縛,在復古中艱難發展。程朱理學和臺閣體對于明中葉散文的影響,學者們大多持否定態度。
二、八股文對明中葉散文的扼殺和反推
八股文是由明太祖朱元璋與劉基所定,是官方所規定的科舉應試文體。在思想禁錮的明代,一般文士如果想通過科舉躋身仕宦的行列,勢必要對這種應試程文苦苦研習,這就造成了有明一代八股文的流行。尤其是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間,八股文逐漸趨于成熟,這就不可避免地對明中葉散文作家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以至于明中葉唐宋派的代表人物歸有光、唐順之、茅坤等散文大家都是寫八股文的好手,讓八股文興盛一時。按理說,八股文作為官方禁錮文人思想的一種文體,它的出現是無可厚非的,但它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深遠的,尤其是它的一些表現手法及理論對明清兩代的散文、詩歌、小說以及戲曲創作上的影響。“從總體來說,它內容上要求貫穿代圣人立說的宗旨,刻板的闡述所謂圣賢的僵化學教,形式上又有嚴格的限制,加之它以官方規范文體的面目出現,嚴重束縛了作者的創作自由,給文學的的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③。同是也極大扼殺了文學的創造性,使當時的文壇形成了千篇一律呆板生硬、毫無新意的創作風氣。這種內容和形式上的極端程式化,不僅造成思想的禁錮和僵化,也必然造成散文發展的障礙。因此,前七子“倡言復古,主張文必秦漢”,不只是反對臺閣體的庸弱,更是對八股文的否定和挑戰。
八股文在對明中葉散文的發展起到負面作用的同時,也刺激了散文朝著前進的方向發展。正是對臺閣體詩文和八股文的厭惡情緒或本能的反桎梏意識,刺激了詩文風尚的改革。明中葉的古文運動,原是為了時文的不能盡情發揮。然而它雖不具有八股文的形式,卻無往而不是八股的精神,雖無形式上的束縛,卻無處不是自己在束縛自。明清兩代,真可謂是八股文一統天下的時代。此時期的古文,深受八股文的影響,“蓋無人不浸淫漸漬于八股之中,自不能不深受其陶化也”(陳柱 《中國散文史》)。
三、陽明心學對明中葉散文的推動
研究明代文學,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注重對陽明心學的研究,陽明心學同樣對明中葉散文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許多明中葉散文家的散文也或多或少有著陽明心學的影子。眾多版本的中國文學史和散文史以及大量學術論文均對其進行了探究。
王守仁,世稱陽明先生,哲學家。他倡言良知之學,后世謂之心學,唯心主義。他提倡的以改良和知行合一為宗旨的心學在明代影響很大。雖說在當時他是從思想上標新立異,但卻是對作為統治思想的程朱理學的公然對抗。他在《答聶文蔚》中解說致良知,目的在于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如此則天下可得而治。這是和程朱理學著重維護封建秩序是不同的。“由于思想上有了這樣的突破,發而為文,也就有所標新,有深度,也有特色”(郭預衡《中國散文簡史》)。王守仁的散文雅健雄沉,能獨抒胸臆,被世人盛贊為“上承宋濂、方孝孺之余緒,下開唐宋派之先”(吳志達 《明清文學史》)。
明中葉的唐宋派繼承唐宋古文精神,能在散文理論和創作兩方面提供同時代人未能提供的東西,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對明中葉新人文精神的受容。明中葉的新人文精神,主要體現在陽明心學和市民意識中。所以說,唐宋派是明代最早接受陽明心學影響,并將其新人文精神注入文學理論和創作中的第一個散文流派。陽明心學使思想空前解放,膽大識高,是非標準不茍同于古人今人,于是便敢對復古派的主張提出異議,另辟蹊徑,開創新的散文流派。比如王慎中,唐順之、起初本是沉溺于擬古文風的人物,而接受陽明之學后后,不但看出了復古派的癥結所在,還大膽揭露其弊,提出自居特色的散文主張,歸有光更把后七子的領袖王世貞稱為妄庸巨子,一再加以申斥,也與他對心學人文精神領悟有關。
陽明心學對唐宋派影響甚巨,唐宋派作家的散文也都體現了陽明心學所影響的痕跡,尤其是歸有光的散文質樸自然,抒情真切感人。唐順之也曾受陽明心學的熏陶,為文強調心地超然具有千只眼,主張直抒胸臆,信手寫來,如寫家書。他認為,如此行文,雖或疏鹵,卻是宇宙一樣絕好文字。
四、民歌對明中葉散文的革新
明代民歌對散文的發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明一代,民歌數量劇增,反映生活的內容十分豐富,藝術感染力很強。袁行霈十分注重民歌對明中葉散文作家和散文創作影響的研究。他認為對民歌的重視,對加強文人創作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改變擬古之風,推動文學發展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在有明一代,散文的發展是曲折的,是在擬古與反擬古的反復斗爭中蹣跚前行的。盡管明代的一些散文家圍繞著創作方法、發展方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探索和論辯,但仍然苦尋無果,始終無法找到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在困惑、迷茫之時,觀點不同的各派卻在民歌這個新的天地里形成了共識,這就是,他們一反士大夫鄙視民間文學的傳統陋習,充分肯定民歌的地位和價值,并且明確地提出,文人作詩應當向民歌學習。這是明代中、后期文學批評家向我國文學批評史提供的最新鮮、也是最重要的經驗之一”④。這種觀點不僅有利于文人作詩,它自然也會促使散文家以民歌的新鮮內容與藝術技巧補充與改善散文的創作。李夢陽提出“真詩果在民間”,主張文人從民歌中吸取有益營養以助己創作。試圖建立民歌與文人詩文創作之間的聯系,主張文人需學習街市俗曲。
民歌對明代文人的創作思想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創作實踐。“唐宋派”愛好民歌的樸實無華、通俗易懂的語言風格,并從語言風格入手學習民歌,為寫作詩文提供不同于擬古的新方法。王慎中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豐文粹》),茅坤強調文章家要體察物情,心物相印,莫逆于心,才能寫出好文章。歸有光諷刺擬古主義者“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他引生活瑣事入文,抒發內心的真實思想感情。其代表作《項脊軒志》就寫得親切樸質,平易淺近,頗得民歌真味。優美的民歌小調、清新自然的“里巷謳謠”,使明代文人體驗到了四書五經、秦漢散文、唐詩宋詞里所少有的獨特的愉悅感與美感。于是文人們不僅搜集、賞愛這些率真可愛的作品,還從理論上對明代民歌進行評說,并以民歌為參照來探討明代散文的革新發展之路。
注釋:
①徐熥.《幔亭集》卷十六.《黃斗塘先生詩集序》.
②③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1,65.
[3]馬啟俊.民歌對明代散文創作的影響[J].六安師專學報(綜合版),1998(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