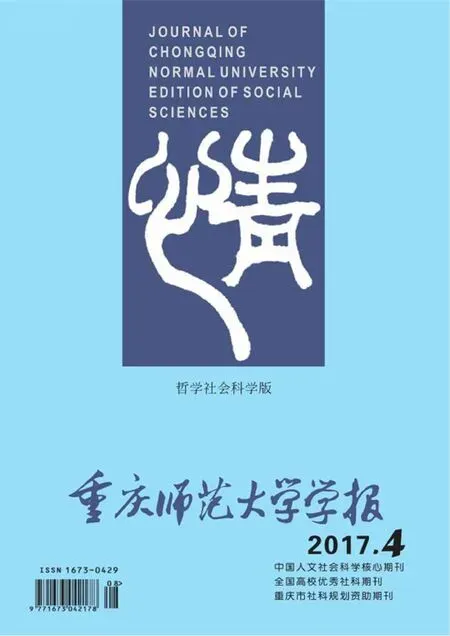里耶秦簡“徒簿”類文書的分類解析
李 勉 俞 方 潔
(1.重慶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學院,三峽文化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重慶 401331;2.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重慶 402260;3.南京師范大學 文博系,江蘇 南京 210097)
里耶秦簡“徒簿”類文書的分類解析
李 勉1俞 方 潔2,3
(1.重慶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學院,三峽文化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重慶 401331;2.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重慶 402260;3.南京師范大學 文博系,江蘇 南京 210097)
里耶秦簡中的“徒簿”類簿籍文書記錄了秦代遷陵縣“徒隸”勞作的相關信息。根據簡文中的名稱,可將這批文書分為“作徒簿”“徒作簿”“徒簿冣”等三類。其中“作徒簿”為司空、倉當日作徒工作安排統計,為“作徒日簿”的簡稱;“徒作簿”由徒隸的接收方制作,為“司空/倉徒作日簿”的簡稱;“徒簿冣”在 “日作簿”的基礎上制作,或稱“月作簿”,一般是對當月徒隸勞作情況的累積統計。從“徒簿”看,秦政府從管理方、接收方、勞作內容等方面對徒隸勞作的管理十分細致。
里耶秦簡;徒簿;徒隸管理
秦漢簡牘涉及政府運作和社會控制的多個方面,對這些出土文獻的研究也逐漸成為秦漢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本文論及的里耶簡“徒簿”等簿籍簡出土數量較大,格式較為一致,內容較為詳細,記錄了秦代洞庭郡遷陵縣“徒隸”勞作的相關信息。[1]對這批“徒簿”簡進行分類解析有利于我們了解秦代縣官府如何管理官徒,如何利用徒隸進行勞作,如何對勞作徒隸和監管官府進行統計和監督。根據已整理、公布的里耶秦簡,共有一百多枚名為“作徒簿”“徒簿”或“徒作簿”的“單獨簡”,[2]數量頗為龐大,其中不乏記錄清晰、結構完整者,這就為我們對這批簿籍進行分類解析提供了便利。
里耶秦簡中有“作徒簿”“徒簿”“徒作簿”“作徒日簿”和“徒簿冣”。其中“作徒日簿”是“作徒簿”的一種格式,兩者可歸為一類。“徒簿”與“作徒簿”格式相同,故“徒簿”即“作徒簿”,[3]或為其省稱,兩者可歸為一類。“徒作簿”內容、格式與“作徒簿”不同,二者不可歸為一類。“徒簿冣”的格式與“徒作簿”相似,但對徒隸的統計方法不同,二者不可歸為一類。綜上,根據名稱,里耶簡中的“徒簿”簡可分為“作徒簿”“徒作簿”“徒簿冣”等三類。
一、作徒簿
首先來看“作徒簿”,簡8-686+8-973“廿九年八月乙酉庫守悍作徒薄(簿)”較為完整,筆者以該簡為例,分析其格式及特點:
廿九年八月乙酉,庫守悍作徒薄(簿):受司空城旦四人、丈城旦一人、舂五人、受倉隸臣一人。·凡十一人。AⅠ 城旦二人繕甲□□。AⅡ 城旦一人治輸□□。AⅢ 城旦一人約車:登。AⅣ 丈城旦一人約車:缶。BⅠ 隸臣一人門:負劇。BⅡ 舂三人級:姱、□、娃。BⅢ 廿廿年上之C(正)
八月乙酉,庫守悍敢言之:疏書作徒薄(簿)牒北(背)上,敢言之。逐手。Ⅰ
乙酉旦,隸臣負解行廷。Ⅱ(背)(8-686+8-973)[4]203
正面第一行為該類文書的標題,一般格式為“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某人作徒簿”,上簡是“庫”的作徒簿,遷陵縣諸官中的三鄉、田官、畜官、田、少內均有作徒簿。從該簡背面文字看,所謂“庫守悍作徒簿”當指“守庫嗇夫悍所負責作徒簿”[3]132-143。該簡中的“庫守悍”當為庫嗇夫的“守官”。作徒簿一般由遷陵諸官署的長官負責,如簡8-1069+8-1434+8-1520之“庫武作徒簿”,簡9-564之“貳春鄉徹作徒簿”等。里耶秦簡中“某官+某人”的格式一般是“某官嗇夫某人”的省稱,嗇夫不在署,由“守官”代理具體事務。由里耶簡7-67+9-631看,遷陵吏員未滿編,其中官嗇夫滿編為十人,缺二人,另有三人“徭使”,故僅有五人在署。[5]所以我們也多見“某官守某人作徒簿”,而少見“某官某人作徒簿”。
沈剛先生將文書主體部分分為三部分,即:接受刑徒的明細與數量,對接受刑徒所作工作的具體分工,部門長官針對上級的匯報文字。[6]鄉部、田官、畜官、田、少內等縣諸官是徒隸的接收方,因此作徒簿中均書“受”徒隸多少人。徒隸的派出方為倉和司空兩官署。其中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債及犯罪的隸臣妾(如隸臣(妾)系舂、隸臣(妾)居貲等)均由司空監管,隸臣妾由倉監管。接收方均寫明徒隸的派出官署,如司空城旦、司寇丈城旦、司空居貲、倉隸臣、倉隸妾等。
正文最后一行一般為“部門長官針對上級的匯報文字”,通過“敢言之”來看,該類文書遞送的官署應為遷陵縣廷。
該簡背面所書為縣廷的收文記錄。高震寰先生根據簡8-1069+8-1434+8-1520指出:“作徒簿的書寫與上交都在庚子日,日中時文書到達縣廷,可以知道作徒簿不是事后記錄,而是在晨間安排好今日工作后,就要上繳。”[3]由此,我們認為“作徒簿”應為司空、倉當日作徒工作安排統計,縣屬各官署要把每日作徒勞作的詳細分工情況上報縣廷。筆者懷疑“作徒簿”的全稱應該是“作徒日簿”,因此簡8-1069+8-1434+8-1520才會書寫:“疏書作徒日薄(簿)一牒。”縣廷要監督各官署“作徒日簿”的上交情況,如某官署未上報某日“作徒薄”,縣廷要予以責問,如簡8-1436“六月都鄉不上乙丑作徒薄(簿)”和10-688“丗四年十二月癸丑司空不上作徒薄(簿)”。都鄉未上交六月乙丑日的作徒簿,司空未上交丗四年十二月癸丑日的作徒簿,因此這兩個官署都受到了縣廷的責問。
以上就是第一類“徒簿”——“作徒簿”,或稱其全稱為“作徒日簿”。
二、徒作簿
再看第二類“徒簿”——“徒作簿”,陳偉和魯家亮先生已經注意到“徒作簿”與“作徒簿”的區別。他們指出“徒作簿”是司空、倉等管理機構派出作徒及自己使用作徒數量和勞作的記錄,“作徒簿”是接受方接受作徒數量和勞作的記錄。[7]根據現有資料,“徒作簿”只有8-145+9-2294“丗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圂徒作薄(簿)”和11—249“丗一年九月庚戌朔癸亥司空色徒作薄(簿)”。筆者發現有倉上交“作徒簿”的例子,即簡8-1559:
五月辛巳旦,佐居以來。氣發。居手。(8-1559)[4]358
所謂“冣”即“倉徒簿冣”,見于簡10-1170“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而此處倉稱“上五月作徒薄(簿)”,似乎倉之“徒簿”稱“作徒簿”而不稱“徒作簿”。但此“倉作徒簿”與“倉徒作簿”并非一物。簡8-1559與簡8-207或有關系密切,書之于下:




里耶秦簡(壹)整理小組認為“佐”前一字疑為“茲”字。根據簡8-1559,“佐”前闕文疑為“叚倉茲”,簡207可能是假倉嗇夫茲與倉佐居率領徒隸捕捉猿猴的相關記錄,包括所捕猿猴的種類、數量,所使用徒隸的人數及食物。從簡207“百五十人”前一字似為“一”,我們難以想象捕捉猿猴需要150人,因此這里的150人應為累積人數,這與簡10-1170“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對倉徒的統計方式頗為相似,因此簡207或與“冣”類徒簿有關,也就暗合了8-1559簡的內容,因此我們認為簡8-207和簡8-1559關系密切。由之,里耶秦簡(壹)整理小組認為“將捕爰”是“假倉茲說明上簿牒的原因”[4]258有其合理性,茲所上交的“作徒薄(簿)及冣(最)”是為“捕爰”作徒的簿籍,而非倉五月份所有徒隸的勞作簿。所以,我們認為雖然簡8-1559記載有所謂“倉作徒簿”,但并不能否認“倉徒作簿”的存在。
下面我們以簡8-145+9-2294“丗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圂徒作薄(簿)”為例,解析“徒作簿”類簡的格式和內容,為便于論述,將其錄于下:
丗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圂徒作簿。AⅠ
城旦司寇一人。AⅡ 鬼薪廿人。AⅢ 城旦八十七人。AⅣ 仗(丈)城旦九人。AⅤ 隸臣毄(系)城旦三人。AⅥ 隸臣居貲五人。AⅦ ·凡百廿五人。AⅧ 其五人付貳春。AⅨ 一人付少內。AⅩ 四人有逮。AⅪ 二人付庫。AⅫ 二人作園:平、□。AⅩⅢ 二人付畜官。AⅩⅣ 二人徒養:臣、益。AⅩⅤ 二人作務:雚、亥。BⅠ 四人與吏上事守府。BⅡ 五人除道沅陵。BⅢ 三人作廟。BⅣ 廿三人付田官。BⅤ 三人削廷:央、閑、赫。BⅥ 一人學車酉陽。BⅦ 五人繕官:宵、金、應、椑、觸。BⅧ 三人付叚(假)倉信。BⅨ 二人付倉。BⅩ 六人治邸。BⅪ 一人取簫:廄。BⅫ 二人伐槧:始、童。BⅩⅢ 二人伐材:□、聚。CⅠ 二人付都鄉。CⅡ 三人付尉。CⅢ 一人治觀。CⅣ 一人付啟陵。CⅤ 二人為笥:移、昭。CⅥ 八人捕羽:操、寬、□、□、丁、圂、叚、卻。CⅦ 七人市工用。CⅧ 八人與吏上計。CⅨ 一人為舄:劇。CⅩ 九人上省。CⅪ 二人病:復、卯。CⅫ 一人【傳】徙酉陽。CⅩⅢ

?小城旦九人:GⅠ 其一人付少內。GⅡ 六人付田官。GⅢ 一人捕羽:強。GⅣ 一人與吏上計。GⅤ
?小舂五人。GⅥ 其三人付田官。GⅦ 一人徒養:姊。GⅧ 一人病:□。GⅨ8-145+9-2294
【丗】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圂敢言之:寫上,敢言之。/痤手。Ⅰ
十月乙亥水十一刻刻下二,佐痤以來。Ⅱ8-145背+9-2294背[8]
與“作徒簿”類簡一樣,“徒作簿”第一行為標題。從標題看,“徒作簿”由“司空”制作,倉很有可能也是制作“徒作簿”的機構之一。“徒作簿”負責者是司空和倉兩個機構的長官。
“徒作簿”與“作徒簿”最大之不同在于前者由徒隸的監管方——司空、倉制作,后者由徒隸的接收方制作。因此,我們在“徒作簿”中既可以見到為司空、倉勞作者,又可以見到司空、倉派遣到其他官署勞作的徒隸,這部分徒隸前書“付”字。從簡8-145+9-2294看,接受司空刑徒的官署有遷陵三鄉、少內、庫、畜官、尉等。簡10-1170“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雖非“徒作簿”,但與“徒作簿”關系密切(我們將在下文予以論述)。由該簡看,倉監管的隸臣妾派遣給了庫、牢、鐵官、它縣、田官、司空、貳春、少內、啟陵等官署。可見,遷陵各縣級官署都接受了司空和倉監管的徒隸,部分徒隸還派遣給了其他縣和都官(如鐵官)。
一般來說,“徒作簿”的正文部分根據徒隸性別和年齡記錄了徒隸的分工。第一類是成年男性徒隸,包括城旦司寇、城旦、鬼薪、丈城旦、隸臣系城旦、隸臣居貲、大隸臣等;第二類是成年女性徒隸,包括舂、白粲、隸妾系舂、隸妾居貲、大隸妾等;第三類是未成年徒隸,包括小城旦、小舂、小隸臣、小隸妾等。詳見表一。

表一 《徒作簿》徒隸身份統計表
“徒作簿”的背面為司空、倉上報縣廷的文字。從簡8-145+9-2294看,該“徒作簿”制作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十月乙亥日,發出的時間是“十月乙亥水十一刻刻下二”。那么“水十一刻刻下二”是該日幾時呢?關于里耶秦簡中的“水十一刻刻下若干”的計時格式,李學勤、張春龍、胡平生、孫慶典等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我們認為孫慶典先生的觀點較為合理,他指出白晝漏刻為十一刻,夜晚漏刻為五刻,全天總計十六刻,恰與十六時制對應。根據孫先生的研究,“水十一刻刻下二”就是十六時制中的“平旦”,即早上4:30至6:00。由此可見,“徒作簿”實際上也應該叫做“徒作日簿”,司空或倉在安排、統計完該日徒隸的分工之后要立即將“徒作簿”上交縣廷,這與縣廷對其他官署的要求是一致的。
以上就是第二類“徒簿”——“徒作簿”,其全稱或為“司空/倉徒作日簿”。
三、徒簿冣
下面我們來看第三類“徒簿”—— “徒簿冣”。
“徒簿冣”見于簡10-1170“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為便于論述將其錄于下:
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AⅠ
大隸臣積九百九十人,AⅡ 小隸臣積五百一十人,AⅢ 大隸妾積二千八百七十六,AⅣ 凡積四千三百七十六。AⅤ
其男四百廿人吏養,AⅥ 男廿六人與庫武上省, AⅦ 男七十二人牢司寇,BⅠ 男丗人輸戜(鐵)官未報,BⅡ 男十六人與吏上計,BⅢ 男四人守囚,BⅣ 男十人養牛,BⅤ 男丗人廷守府,BⅥ 男丗人會逮它縣,BⅦ 男丗人與吏□具獄, BⅧ 男百五十人居貲司空,CⅠ 男九十人毄(系)城旦, CⅡ 男丗人為除道通食,CⅢ 男十八人行書守府,CⅣ 男丗四人庫工。CⅤ
?小男三百丗人吏走, CⅥ 男丗人廷走,CⅦ 男九十人亡,CⅧ 男丗人付司空,DⅠ 男丗人與史謝具獄,DⅡ

首先來看標題,關于“冣”,張春龍先生在《里耶秦簡》(壹)的序言中將其寫作“最”[10]3,賈麗英先生因之認為“最”是考課中成績最好者,因此她認為“倉徒最簿”是倉屬徒隸管理考核優秀者[11]。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將該字釋為“冣”。按:《說文》曰“冣,積也”,其注曰:“冣與聚音義皆同,與冃部之最音義皆別。《公羊傳》曰:‘會猶冣也,何云,冣之為言聚。’《周禮》太宰注曰:‘凡簿書之冣目。’劉歆與楊雄書《方言》曰:‘欲得其冣目。’又曰:‘頗愿與其冣目,得使入錄。’按:凡言冣目者,猶今言摠目也。”[12]上引“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隸臣妾的數量非常大,其中大隸臣有990人,小隸臣為510人,大隸妾為2876人,總數為4376人。考察里耶秦簡中的“徒簿”簡,除了簡8-1143+8-1631和8-1095外,各官署接受的司空、倉的徒隸數量多為個位數,最多者僅見簡8-1566“田官日食牘”中的“舂廿二”人。即使以此作為每個官署獲得隸臣的平均人數,根據簡7-67+9-631中官嗇夫的數量為十,派往遷陵各官署的隸臣總數也僅有220人,即使再加上行徭它縣、鐵官、郡府的隸臣數量也很難達到990人。況且簡7-304“廿八年遷陵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責作官府課”記載了二十八年遷陵縣隸臣妾的數量,僅有189人。因此“丗四年十二月倉徒薄(簿)冣”所統計的隸臣妾人數絕非倉監管的實際隸臣妾人數。從“積”字看,該簡記錄的是十二月參加勞作的隸臣妾的累積人數,是倉根據“徒作日簿”而作的月度統計,因此這種文書才取名作“冣”,即《周禮·太宰注》所言“簿書之冣目”。“冣”也可寫作“最”,居延漢簡中多見“最凡”和“冣凡”,有總共、合計之意,表示對事物數量的統計[13],如“最凡吏百石以下七十四人(214·76A)”[14]340、“最凡卒閣三十一人,帛百亖十六匹(EPF22·263)”[15]494等。簡8-1143+8-1631和8-1095與該簡相似,以簡8-1143+8-1631為例,將其錄于下:
該簡是貳春鄉八月使用作徒的統計,學界一般稱作“月作簿”。該簡也采用“徒隸身份+積人”的格式,因此是貳春鄉對該月作徒累積數量的統計。這類“作徒簿”與“徒簿冣”十分相似,似可歸于一類。
前引簡8-1559載假倉茲上交五月捕爰的“作徒薄”,提到“上五月作徒薄(簿)及冣(最)丗牒”,為何會有30牒呢?丗一年五月辛巳日即五月三十日,倉茲率領徒隸捕爰很可能耗時29天,每日書寫一牒“作徒簿”,外加本次捕爰活動的“徒簿冣”,共計30牒。前文提到“作徒日簿”要在每日的旦時上報縣廷,為何倉茲要把29日的“作徒日簿”一并上交呢?我們認為因為捕捉猿猴要深入森林中,無法按時上報“作徒日簿”,只能待該任務完成后一并提交“作徒日簿”和“作徒冣”。
除了以上幾類明確定名為“徒簿”的簡外,還有幾種簡與徒簿簡相似。例如簡8-284:“丗一年司空十二月以來,居貲、贖、責(債)薄(簿),盡三月城旦舂 廷。”[4]128居貲、贖、責(債)薄(簿)是對特定身份徒隸勞作情況的記錄,可將其歸入徒簿類簡中。再如簡8-1665:“廿七年十一月乙卯,司空昌【薄(簿)】黔首□大男子四人。其□人載粟。”[4]375相似的簡還有8-1586。 “載粟”見于張家山漢竹簡《二年律令·徭律》“節(即)載粟,乃發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16]64,“載粟”是百姓在地方官府服役的項目之一,因此這枚簡很可能是司空對黔首徭役的安排。
以上就是筆者根據現有資料對徒簿類簡所做的分類和解析,從“徒簿”看,秦代對徒隸勞作的管理十分詳細。倉和司空是監管官徒的官署,負責派遣徒隸到各個官署,根據徒隸的年齡、性別、身份安排勞作。司空和倉在安排完徒隸的勞作后要及時上報縣廷,接受徒隸的官署也要把徒隸的分工情況及時上報官署。各個官署在“日作簿”的基礎上要制作“作簿冣”,或稱“月作簿”,一般是對當月徒隸勞作情況的累積統計。
[1] 李力.論徒隸的身份——從新出里耶秦簡入手[C]//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C]//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1;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C]//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1;曹書林.里耶秦簡“作徒簿”勞作者身份問題研究[D].鄭州大學.2014;賈麗英.里耶秦簡所見徒隸身份及監管官署[C]//卜憲群,楊振紅.簡帛研究(二O一三),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J].史學月刊,2015,(2).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C]//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1; [日]角谷常子.論里耶秦簡的單獨簡[C]//簡帛(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3.
[3] 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C].//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1.
[4]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5]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EB/OL].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68.
[6] 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J].史學月刊,2015,(2).
[7] 魯家亮.里耶秦簡所見遷陵三鄉補論[J].國學研究,2015,(4).
[8]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EB/OL].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69.
[9] 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J].文物,2003,(1);張春龍.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J].中國歷史文物,2003,(1);胡平生.讀里耶秦簡札記[N].中國文物報.2003-09-07;孔慶典.10世紀前中國紀歷文化源流——以簡帛為中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11] 賈麗英.里耶秦簡所見徒隸身份及監管官署[C]//卜憲群,楊振紅.簡帛研究(二O一三),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12] 許慎撰,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 [日]永田英正.居延漢簡集成之一——破城子出土的定期文書(一)[C]//簡牘研究譯叢(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國艷.居延漢簡“最凡”使用情況及其用法演變考察[J].蘭州學刊,2006,(11).
[14]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5]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6]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劉力]
OntheClassificationofTubuintheLiyeBambooSlips
Li Mian Yu Fangjie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2. Chongqi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 Chongqing 402260; 3. Colleg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China)
The document of Tubu in the Liye bamboo slips recorded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Qianling Tuli in the Qin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name of Liye bamboo slips, these files can be divided into 3 classes of initials, such as Zuotubu, Tuzuobu and Tubuzui. Zuotubu was the abbreviation of Zuo tu ri bu, which was the work arrangement from Sikong and Cang. Tuzuobu was written by Tuli’s receivers, which was the abbreviation of Sikong/Cang tu zuo ri bu. Tubuzui was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Rizuobu, which was also called Yuezuobu. Tubuzui was cumulative statistics about Tuli’s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at month. Considered from Tubu, government of the Qin Dynasty detailed provisions on the management party, receiver and job description.
Liye bamboo slips; Tubu; Tuli management
2017-04-26
李 勉(1987— ),男,山東濱州人,歷史學博士,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三峽文化與社會發展研究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秦漢史。 俞方潔(1986—),女,重慶人,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講師,南京師范大學文博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秦漢考古。
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秦代縣政研究——以簡牘資料為中心”(2016BS021)。
K232
A
1673—0429(2017)04—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