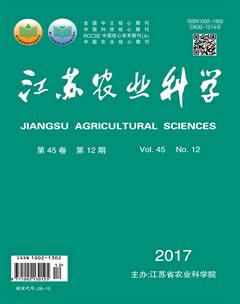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西部欠發達地區城鎮化的空間格局
劉超+黃克紅+丁鐳+盧麗雯+曾克峰



摘要:欠發達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及空間格局的研究,直接關系到新型城鎮化在西部省份的實施策略。以貴州省為例,選取人口、經濟、空間、社會4個子系統17個指標,運用熵值法對貴州省9個市州2000—2014年城鎮化水平進行綜合評價,并運用ArcGIS10.0軟件對貴州省各市州城鎮化綜合水平進行地理空間的可視化表達,結果表明:(1)貴州省城鎮化綜合水平整體上呈穩步上升狀態,貴陽市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其他市州;(2)2008年后人口城鎮化對城鎮化綜合水平的貢獻率明顯變弱,而且增速明顯低于經濟、空間和社會城鎮化水平;(3)貴州省城鎮化總體呈現“一核兩翼多區域發展”的空間格局;(4)城鎮化綜合水平空間格局變動主要在相對第二、第三與第四等級之間,2008年之前格局變化的驅動因子為經濟子系統,2008年之后格局變化的驅動因子則為社會子系統。未來城鎮化過程的關鍵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因此,今后西部地區城鎮化水平的建設要更加注重人口、經濟、空間和社會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城鎮化;空間格局;演變分析;貴州省
中圖分類號: F291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002-1302(2017)12-0299-05
城市化是伴隨工業化和經濟發展而出現的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1]。2013年12月11日召開的中央關于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推進城鎮化的主要任務,強調了中國城鎮化發展的“穩中求進”、努力實現“人的城鎮化”等方針[2]。之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出臺,這標志著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大轉型。新型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演變過程,它涉及人口、經濟、環境、資源、空間和社會等各個方面[3]。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強調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這就要求城鎮化應以城鎮空間承載力為基礎,以提高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為目標,因此,這就要對城鎮化水平建設進行綜合評價。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社會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至2014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已達 54.77%,按照美國地理學家諾瑟姆提出,城鎮化“S”形過程曲線[4],目前,我國城鎮化進程處于30%~70%的中期加速發展階段[5]。相關學者認為,中國城鎮化發展速度和規模是人類前所未有[6],因此,中國城鎮化發展水平成為當前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城鎮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中國雙重城鎮化[7]、城鎮化水平的綜合評價[8-11]、城鎮化區域類型劃分[12]、城鎮化空間格局[13-15]、城鎮化的提升對策或質量與速度的協調性[10,16]等方面。評價指標方法普遍采用均方差決策法[17]、熵值法[15,18]、阿特金森模型[19]、APH[20]。研究區域尺度主要以省域為單位或在省層面以市域為單位,地域集中在三大經濟帶、東部沿海和經濟較發達的省份,例如長三角、珠三角、長江經濟帶等區域,而針對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城鎮化發展研究較少[21]。對于這些西部欠發達地區,城鎮化更是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推動社會進步、實現西部地區跨越式發展的關鍵所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西部地區城鎮化率由2000年的24.1%提高到2014年的46.89%,14年間提高了22.79百分點,但仍低于東部沿海地區60%以上的城鎮化率[22]。2014年11月27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博參觀人居科學研究展時,強調要打破“胡煥庸線”,中西部如東部一樣也需要推進城鎮化建設[23]。2014年,貴州省進入長江經濟帶規劃,與長江經濟帶各地海關(貴陽綜合保稅區正式封關運行)實現通關一體化,打破了貴州三不靠(不靠海、不靠江、不靠邊)的瓶頸,與粵桂共建貴廣高鐵經濟帶,為貴州省城鎮進程提供更為優厚的外部環境。因而,筆者選擇貴州省為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分析的研究區域,以此為其他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研究提供參考。
1研究區概況和數據來源
1.1研究區域概況
西部欠發達地區是指我國西部地區內部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24],包括12個省市及自治區,即西南5省市區(四川省、云南省、貴州省、西藏自治區、重慶市)、西北5省區(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新疆自治區、寧夏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廣西自治區。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實施,部分中心城市及其腹地率先加速發展,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趕上或者接近了東部發達地區水平。同時,西部部分地區仍難擺脫老少邊窮的發展狀況,城鎮化進程受阻。貴州省(24°37′~29°13′N,103°36′10~9°35′E)地處中國的西南部,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典型代表。全省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地貌可概括分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4種基本類型,其中山地和丘陵的面積達到 92.5%。2014年,貴州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9 251.01億元,比上年增長了10.8%,是2000年的8.9倍,三次產業構成由2000年的27.2 ∶39.0 ∶33.7調整為2014年的 13.8 ∶41.6 ∶44.6。2014年貴州省城鎮化率達到40.02%,低于西部平均值的46.89%,城鎮化水平嚴重滯后。因此,研究貴州省城鎮化發展的綜合水平評價及空間格局演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1.2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源于《貴州統計年鑒2001—2014》《貴州六十年統計匯編(1949—2009)》和貴州省各個市州2000—2014年國民經濟統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研究對象為貴州省的9個地級市州,包括貴陽市、六盤水市、遵義市、安順市、畢節地區、銅仁地區、黔西南州、黔東南州、黔南州。其中,畢節地區和銅仁地區2012年后改為畢節市和銅仁市,為了保持行政范圍和數據不變,本研究只稱畢節市和銅仁市。
2指標選取及評價方法
2.1評價指標的選取endprint
城鎮化是一個包括人口、經濟、社會、生態、土地、文化及基礎設施等多個子系統的復雜變化過程。因而,對于城鎮化綜合水平的測度方法開始傾向于綜合指標代替原來的單一指標。不同學者對城鎮化評價指標的選取和評價方法有不同的觀點,本研究根據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特點,并參考以往的指標選取原則[14-20,23],將產業城鎮化作為經濟城鎮化,將居民生活城鎮化和景觀環境城鎮化合并為社會城鎮化,將土地城鎮化和基礎設施城鎮化合并為空間城鎮化。選擇人口、經濟、空間和社會城鎮化4個子系統,18個評價指標(表1)來評價城鎮化的綜合水平。
2.2評價方法——熵值法
在綜合指標體系的評價中,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主要有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主觀賦權法是主要根據評價者或專家主觀上對各評價指標的重視程度來決定權重的方法,客觀賦權法則是根據各原始指標所提供的信息量來決定指標的權重[25]。本研究使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以克服人為確定權重的主觀性以及多指標變量間信息的重疊,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經濟等研究領域[18,25]。在信息論中,熵是系統無序程度的度量。某項指標的指標值變異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該指標的權重也越大;反之該指標的權重越小。熵值法主要計算步驟如下。
原始數據標準化處理:為了消除指標的數量級、量綱不同造成的影響,便于匯總比較,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評價公式為:
Y′ij=(Yij-Yjmin)/(Yjmax-Yjmin)。
(1)計算第i年份第j項指標的比重:Xij=Y′ij/∑mi=1Y′ij;
(2)計算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Ej=-K∑mi=1(XijlnXij),其中K=1/lnm;
(3)計算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冗余度:Gj=1-Ej;
(4)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Wj=Gj/∑mi=1Gj;
(5)計算第i年份評價城鎮化綜合水平得分:UDQi=∑nj=1WjY′ij。
式中:Y′ij是樣本城鎮第i年第j項指標的標準化處理后的值,Y′ij∈[0,1];Yij是第i年第j項指標的原始數據;Yjmax和Yjmin分別代表不同年份研究區域指標屬性值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中,m代表評價年數,n代表指標個數。
3城鎮化水平的綜合評價
3.1貴州省城鎮化發展特征
根據表1城鎮化綜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均方差決策法對2000—2014年貴州省9個市州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計算,得出綜合城鎮化水平(圖1)和4個子系統城鎮化水平演化過程(圖2),以及貴州省9個市州的城鎮化水平綜合得分(圖3)。
從圖1可以看出,2000—2014年貴州省城鎮化綜合水平不斷提升, 由2000年的0.063提升到2014年的0.148,特別表1城鎮化綜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指標類型代表意義評價指標權重X1人口城鎮化(0.191 4)反映城鎮人口的集聚程度,表現較直觀,是城X11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0.063 3鎮化水平的基礎指標X12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0.064 7X13人口密度(人)0.063 4X2經濟城鎮化(0.297 3)反映各種非農產業發展的經濟要素向城鎮集聚X21人均GDP(元)0.055 6的過程,產業結構的轉換,表現相對間接,卻是X22非農產業比重(%)0.065 6城鎮化水平發展的根本動力X23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億元)0.049 2X24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0.065 3X2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0.061 6X3空間城鎮化(0.239 6)反映居民聚落和經濟布局在空間區位再分布,X31建成區面積(km2)0.054 8并呈現日益集中化的過程X32人均道路面積(m2/人)0.062 0X33人均城鎮住房面積(m2)0.065 1X34人均公園綠地面積(m2)0.057 7X4社會城鎮化(0.271 7)城鎮化水平的最終升華,反映城鎮化對城鎮居X4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0.062 5民生活水平的影響,表現最間接,是衡量城鎮化X42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元/人)0.053 7水平的根本標準X43每千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人)0.038 3X44每萬人大學生數(人)0.061 8X45城鎮公共汽車和出租車總量(萬輛)0.055 4
是2009—2014年城鎮化水平提升速度較快;而城鎮化率(城鎮人口比重)由23.87%增加到40.01%,發展總體趨勢較平穩。二者雖然都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但城鎮化水平的增長速度大于城鎮化率的增長速度。
從圖2可以看出,人口、經濟、空間和社會城鎮化水平都表現出明顯的遞增趨勢。其中,經濟城鎮化帶動著人口城鎮化、空間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發展,并且城鎮化子系統表現出2個明顯的特征:一是2008年前經濟城鎮化>人口城鎮化>空間城鎮化>社會城鎮化,二是2008年后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空間城鎮化>人口城鎮化。一方面表明經濟城鎮化是提升貴州省城鎮化綜合水平的主要驅動力;另一方面表明貴州省經濟、空間和社會城鎮化相對比較低,處于城鎮化的加速提升階段,需要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城鎮化的核心驅動力,人口城鎮化還處于低速發展階段,需要加快產業轉型和戶籍制度改革,以促進非農產業就業,留住技術人才,加速城鎮化進程。
從圖3可以看出,(1)貴州省各市州城鎮化水平整體均呈遞增勢態,其中貴陽市變化最為明顯,由2000年的0.107遞增到2013年的0.234;(2)除了省會貴陽市外的其他各市州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處于0.05到0.15之間,而貴陽市城鎮化水平遠遠高于其他8個市州;(3)除了貴陽市外其他8個市州的城鎮化水平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該結果與王禮剛利用主成分和聚類分析方法研究的2008年貴州省城市化綜合水平[26]基本一致。endprint
從圖4可以看出,貴陽市的城鎮化各子系統得分上升明顯,尤其是社會城鎮化,由2000的0.025上升到2014年的 0.073,增幅0.048,是全省平均水平0.024的2倍;經濟城鎮化水平始終高于其他3個子系統城鎮化水平,且人口、經濟和空間城鎮化表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核心是人,人民群眾生活得更美好,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內涵是推動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從而實現城鎮空間承載力的提升及城鎮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再是單純地追求人口的城鎮化,而更加注重城鎮化進程中對城鎮空間承載力以及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時印證了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真正含義。
3.2貴州省城鎮化綜合水平空間格局演變
以貴州省地州界行政地理底圖為圖形數據,把各市州城鎮化水平綜合得分輸入到數據庫中作為屬性數據,利用ArcGIS10.0軟件對貴州省城鎮化水平得分數據進行自然斷裂法的可視化表達,對貴州省9個市州的城鎮化水平進行劃分。其中,時間斷面分別是2000、2008、2014年(圖5)。具體空間結構及其演變特征如下。
貴州省城市化綜合水平發展的空間結構呈現出“一核兩翼多區域發展”的空間格局,即以省會貴陽為核心,以遵義和其他市州為兩翼的空間格局。這種格局與2010年貴州省提出的“以貴陽市為中心,遵義、安順、都勻、凱里等為支撐”的黔中城市群的空間開發格局相一致。
首位度城市的等級結構,貴州省綜合城鎮化水平的空間等級結構整體呈現出一種以貴陽市為核心城市的單中心圈層結構模式,但其中遵義、畢節、銅仁和黔西南受核心城市(貴陽市)的影響相對較少,該結果與單曉婭等研究的城市數量、等級規模結構[27]較為一致。表明這4個市州與貴陽市的人口、經濟、空間和社會聯系不強,為了增強整個區域的綜合實力,有待加強區域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方針等方面的分工與合作。
城鎮化演變特征。從圖5可以看出,在時間斷面內,處于相對第一等級(1個市)、第二等級(2個市州)、第三等級(3個市州)、第四等級(3個市州)市州的數量沒有發生變化;處于相對第一等級的始終是貴陽市,沒有任何變化,而處于其他
等級的市州卻在不斷發生變化。2000年處于相對第二等級的有遵義市、黔南州,處于相對第三等級的有六盤水市、安順市、黔西南州3個市州,相對第四等級的城市有畢節市、銅仁市和黔東南州3個市州。2008年的城鎮化水平空間格局變化較為明顯,其中,六盤水市相對等級由2000年的第三等級上升到第二等級,安順市的相對等級由2000年的第三等級下降到第四等級,黔南州的相對等級由2000年的第二等級下降到第三等級,其他6個市州沒有變化。與2008年相比較,2014年9個市州的城鎮化水平的空間格局變化不大,處于相對第二等級的有遵義市和黔東南州,處于相對第三等級的有六盤水市、黔西南州和黔南市3個市州,相對第四等級的有安順市、畢節市和銅仁市3個市。其中處于相對第一等級的貴陽市、第二等級的遵義市、第三等級的黔西南州和第四等級的銅仁市4個市州的等級沒有變化,處于相對穩定狀態;而處于變化之中的是六盤水市、安順市、畢節市、黔東南州、黔南州5個市州。
4城鎮化空間演變原因分析
為更深入認識貴州省城鎮化水平空間格局演變的原因及其綜合發展情況,根據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4個方面的分維度測評,對貴州省城鎮化水平空間格局演變的根本原因進行分析和描述。
從圖6可以看出,2000年初期格局中,經濟城鎮化對城鎮化綜合水平的貢獻率最大。該結果與馬子量等用空間杜賓模型檢驗西部地區省域城市化動力機制[28]較為一致。貴陽市在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4個子系統都遠遠高于其他8個市州,其城鎮化水平處于相對第一等級。處于相對第二等級的遵義市和黔南州,除了人口城鎮化處于相對第四等級外,其他3個子系統都處于相對第一、第二等級,但其人口城鎮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相對第三等級的市州中,人口城鎮化水平都處于相對第二等級,六盤水市的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水平處于相對第二等級,安順市的經濟城鎮化水平處于相對第二等級,黔西南州的社會城鎮化水平處于相對第二等級,但這3個市州的空間城鎮化水平都有待提升。相對第四等級中,畢節市和銅仁市的經濟城鎮化水平較低,導致空間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水平較低,同時,人口城鎮化水平較高,但其城鎮化綜合水平較低。黔東南州除了經濟城鎮化外,其他3個子系統都處于相對第四等級,導致其城鎮化綜合水平處于相對第四等級。
2000—2008年,貴州省城鎮化水平的空間格局的變動主要發生在初期格局中的城鎮化水平相對第二、第三和第四等級的市州中。貴陽市、遵義市、銅仁市、黔西南州和黔東南州5個市州在城鎮化4個子系統均處于穩步遞增勢態,城鎮化水平的相對等級沒有發生變化。六盤水市和畢節市城鎮化水平的相對等級上升主要是因為經濟城鎮化的提升速度較快,同時,伴隨著空間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的提升速度較快。安順市和黔南州城鎮化水平的相對等級下降主要是因為城鎮化進程中經濟快速的增長,而城鎮空間承載力及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同步的增長。總體來看,貴州省城鎮化水平空間格局的主要因為部分市州經濟增長導致空間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增長的速度不均,人口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上升的速度較為一致,但上升速度較為緩慢(圖7)。
2008—2014年,貴陽市、遵義市、安順市、銅仁市、黔西南州和黔南州6個市州的城鎮化水平都是穩步上升的狀態,但相對等級沒有發生變化。城鎮化水平的相對等級發生變化主要發生在第二、第三、第四等級的市州中(圖8)。黔東南州城鎮化水平的相對等級上升主要由于城鎮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及城鎮空間承載力提升,引起空間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快速上升而人口城鎮化增長幅度相對緩慢。六盤水市和畢節市2個市城鎮化水平的相對等級下降了一級,主要是由于社會城鎮化水平與全省的平均水平進一步拉大,而人口城鎮化和空間城鎮化也沒有得到大幅的提升,致其城鎮化水平的相對等級下降。endprint
5結論與建議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增長,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但城鎮化進程的區域差異也越發明顯。西部地區作為經濟最為落后的區域,其城鎮化率為46.8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54.77%,對于西部地區各省市區來說,提高自身城鎮化水平對于提高經濟效率和促進其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所以對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研究西部欠發達地區城鎮化空間格局的演變特征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本研究通過構建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值法對貴州省各市州2000—2014年的人口、經濟、空間和社會城鎮化進行定量化和可視化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結果。
貴州省城鎮化綜合水平整體上呈現逐年穩定上升的趨勢,經濟城鎮化帶動著空間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的發展;各市州城鎮化綜合水平總體呈現遞增的趨勢,除了省會貴陽市外,其他8個市州城鎮化上升速度相對緩慢。在新型城鎮化發展中,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不再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最終目標,但在城鎮化進程中應加強戶籍制度改革,推進鄉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移,讓當地農民就近就地城鎮化。在加強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城鎮化進程中對城鎮空間承載力以及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城鎮化發展的空間結構為“一核兩翼多區域發展”的空間格局。這種格局與2010年貴州省提出的:“以貴陽市為中心,遵義、安順、都勻、凱里等為支撐”的黔中城市群的空間開發格局相一致。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今后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的首要任務是發展區域中心城市。不僅提高城市數量,更要提升城市規模層次和質量,以增強中心城市集聚輻射和帶動作用。同時,加強中小城市建設,以城市群為依托,大力發展中小城市,著力培育潛在大城市,適度促進小城鎮發展。
城鎮化水平的空間格局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市州之間城鎮化4個子系統發展速度參差不齊,其中城鎮空間承載力的提升及城鎮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對城鎮化空間格局的變化影響相對較大;人口、經濟、空間和社會城鎮化等對城鎮化綜合水平的貢獻作用大小各不相同,人口城鎮化提升的速度相對穩定,社會城鎮化的提升速度較快。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強調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因此,今后西部地區城鎮化水平的建設要更加注重人口、經濟、空間和社會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牛曉春,杜忠潮,李同昇. 基于新型城鎮化視角的區域城鎮化水平評價——以陜西省10個省轄市為例[J]. 干旱區地理,2013,36(2):354-363.
[2]陸大道,陳明星. 關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編制大背景的幾點認識[J]. 地理學報,2015,70(2):179-185.
[3]姚士謀,張平宇,余成,等. 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與實踐問題[J]. 地理科學,2014,34(6):641-647.
[4]Northam R M. Urban geography[M]. New York:Johm Wiely & Sons,1975:65-67.
[5]何孝沛,梁閣,丁志偉,等. 河南省城鎮化質量空間格局演變[J]. 地理科學進展,2015,34(2):257-264.
[6]孫平軍,丁四保,修春亮,等. 東北地區“人口-經濟-空間”城市化協調性研究[J]. 地理科學,2012,32(4):450-457.
[7]Shen J F. Understanding dual-track urbanization in post reform China: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analysis[J]. 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2006,12(6):497-516.
[8]Shen J F. Estimating urbanization levels in Chinese provinces in 1982—2000[J].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Review,2006,74(1):89-107.
[9]方創琳,王德利. 中國城市化發展質量的綜合測度與提升路徑[J]. 地理研究,2011,30(11):1931-1946.
[10]Chen A.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case of Fujian province[J]. Modern China,2006,32(1):99-130.
[11]Gu C L,Chan R K,Liu J Y,et al. Bejings socio-spatial restructuring:Immigr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poch of national economic reformation[J]. Progress in Planning,2006,66(4):242-310.
[12]王洋,方創琳,王振波. 中國縣域城鎮化水平的綜合評價及類型區劃分[J]. 地理研究,2012,31(7):1305-1316.
[13]陳忠暖,高權,王帥. 中國省際城鎮化綜合水平及其空間分異[J]. 經濟地理,2014,34(6):54-59.
[14]劉彥隨,楊忍. 中國縣域城鎮化的空間特征與形成機理[J]. 地理學報,2012,67(8):1011-1020.
[15]楊璐璐. 中部六省城鎮化質量空間格局演變及驅動因素——基于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分析[J]. 經濟地理,2015,35(1):68-75.
[16]楊剩富,胡守庚,葉菁,等. 中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協調度時空變化及形成機制[J]. 經濟地理,2014,34(11):23-29.endprint
[17]梁振民,陳才,劉繼生,等. 東北地區城市化發展質量的綜合測定與層級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學,2013,33(8):926-934.
[18]王富喜,毛愛華,李赫龍,等. 基于熵值法的山東省城鎮化質量測度及空間差異分析[J]. 地理科學,2013,33(11):1323-1329.
[19]陳文峰,孟德友,賀振. 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綜合評價及區域格局分析[J]. 地理科學進展,2011,30(8):978-985.
[20]王富喜,孫海燕. 山東省城鎮化發展水平測度及其空間差異[J]. 經濟地理,2009,29(6):921-924.
[21]鄧祥征,鐘海玥,白雪梅,等. 中國西部城鎮化可持續發展路徑的探討[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10):24-30.
[22]李曉曼. 中國西部新型城鎮化動力若干問題研究[J]. 改革與戰略,2014,30(3):97-100.
[23]陸媛媛,丁鐳,黃克紅,等. 寧夏城市化綜合水平測度及提升路徑[J]. 寧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37(3):378-384.
[24]王灃,張京祥,羅震東. 西部欠發達地區城鎮化困局的特征與機制——基于寧夏南部山區調研的探討[J]. 經濟地理,2014,34(9):40-47.
[25]陳明星,陸大道,張華. 中國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測度及其動力因子分析[J]. 地理學報,2009,64(4):387-398.
[26]王禮剛. 貴州省各地市州城市化水平綜合評價——基于主成分、聚類和GIS分析方法[J].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96-103.
[27]單曉婭,王婷. 貴州城市化與產業集聚的相關性實證分析[J].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3(2):103-108.
[28]馬子量,郭志儀,馬丁丑. 西部地區省域城市化動力機制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4(6):9-15.紀素蘭,張木蓮,馬曉杰. 農業科研單位辦公自動化系統高效運行的障礙分析和對策建議——以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為例[J]. 江蘇農業科學,2017,45(12):304-30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