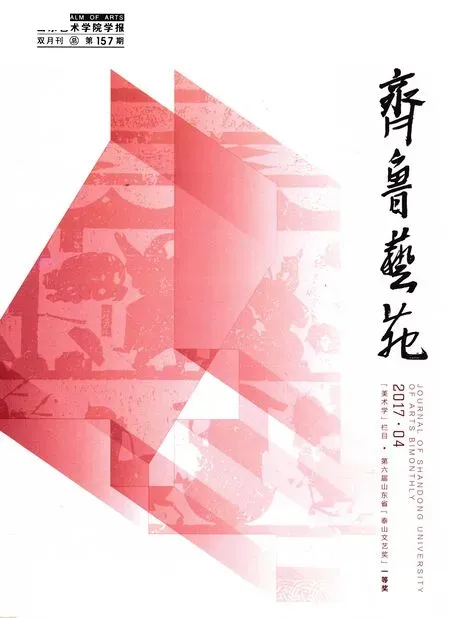現代抽象藝術對“機器”的信奉與超越
——簡述包豪斯內的兩種藝術潮流
蘇夢熙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上海 200433)
現代抽象藝術對“機器”的信奉與超越
——簡述包豪斯內的兩種藝術潮流
蘇夢熙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上海 200433)
為國內研究者較少提及的是,德國包豪斯工藝美術學院內所存有兩種不同的創作潮流:一是以莫霍利-納吉和奧斯卡·施萊默等人為代表的信奉機器的創作,一是以保羅·克利、約翰·伊頓等人所代表的疏離機器的創作。本文通過揭示與探討這兩種不同的創作潮流來反觀藝術對現代社會的弊端進行超越的可能性,從而對藝術家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刻反思。
包豪斯;抽象藝術;保羅·克利
18世紀所發生的西歐產業革命將機器納入人類文明發展軌道,同時也深刻地改變了藝術的面貌,德國包豪斯工藝美術學院一方面順應現代抽象藝術的發展潮流,一方面則成功地將藝術同現代工業生產緊密相聯。包豪斯研究在國內已有不少成果并呈增長趨勢,而為研究者較少提及的是學院內部所存有的兩種不同創作潮流,本文正是要通過揭示與探討這兩種不同的創作潮流,以此反觀大時代背景下藝術家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在其中,保羅·克利和約翰·伊頓等人以藝術形式對自我身體的構建展現了對機器進行超越的可能性,這對于信奉機器并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先鋒派來說無疑是一條重要的反思之路。
一
機器的高速運作對視覺器官帶來的初次震撼不言而喻,福樓拜1865年開始寫作的小說《情感教育》以描繪一艘正起航的蒸汽客輪上的景象作為開頭,參照這部現代小說的先聲,拉開了現代生活序幕的正是機器。藝術批評家羅伯特·休斯在《新藝術的震撼》中提到,機器意味著對地平線空間的征服,它意味著過去很少有人體驗過的一種對空間的感受——景色的連續和重迭,象是倏忽閃現的浮光掠影,這是只有依靠高速運動的機器才能擁有的視覺感受。休斯指出,火車上的景象迥然不同于馬背上的景象,它在同一時間內壓縮了更多的母題,它沒有留下什么時間去詳述任何一件事物。[1](P5)乘坐火車帶來了不一樣的空間體驗,19世紀末印象主義那緩慢的坐船的觀賞方式與駐足停留的觀看被顛覆了,20世紀是先鋒派的視野。

圖1 《空間里連續運動的物體的一個形態》,1913年,現藏于二十世紀博物館。
包括未來主義、達達主義和構成藝術等在內的先鋒派以高速運作的物體作為描繪對象,作品中彰顯著對于速度的熱愛。意大利未來主義藝術家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的雕塑《空間里連續運動的物體的一個形態》(圖1)就是典型例子,那個大跨步的行走者因為運動而無法被固定為一個單一姿勢的形象,他的形象不斷被擴張、拉長,直至運動結束。這種對運動的熱愛模糊了繪畫空間的形象,巴拉《被拴住的狗的動態》中,小狗與裸女的形象不再是立體主義繪畫中那被打碎的實體,而只是一個個擴散開來的色塊,一團團墨跡。形象消散了,畫布前景上存留下來的是對運動物體的感受。先鋒派的繪畫形象傾向于成為運動原理的具象展示,在杜尚《下樓梯的裸女,2號》中,運動的機械傾向體現得更加明顯,在藝術生涯中,他也曾多次放棄對“物體”的描繪,只著重于“運動原理”,如《咖啡研磨機》(1911)中那高度凝練的色情隱喻:人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為“展現”(含有杜尚式諷刺)性愛的運動原理而造出的簡單裝置。先鋒派對于機器的認同態度深刻地影響了現代藝術的發展,德國包豪斯工藝美術學校建立時,許多現代藝術家加入這一現代抽象藝術的大本營,正是在這里,現代抽象藝術形成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一是對機器的認可,另一則是背離機器的創作,前者以莫霍利-納吉、奧斯卡·施萊默、阿爾伯斯為代表,后者以克利、約翰·伊頓為代表,抽象大師康定斯基雖然因為學院內部矛盾的緣故傾向后者,但他的藝術形式卻同前者更為接近。

圖2 T1,1926年,現藏于古根海姆博物館。
作為構成主義的主要人物,莫霍利-納吉(Laszlo Moholy Nagy)于1923年被聘為包豪斯的教師并擔任金屬工作坊的主任,納吉為包豪斯引進了國際先鋒主義關于藝術創造的主張,他所有的努力體現為關于作品結構性和功能性的理性規劃。如果說,在杜尚那里找到的機器原理具象化還包含了一絲主觀性的諷刺色彩,在納吉這里,機器的原理不過是一種普通事實,這種事實成為了構建新藝術的方法論,他的繪畫是最早用以探索物的結構與特性的藝術作品之一:玻璃、水晶、各類金屬代替了古典靜物畫中的水果、花朵與食品。這些物在納吉的畫中不是以“用具”的身份出現的,它們是作為被打磨成幾何形狀的玻璃片和水晶球、按照規則彎曲得一絲不茍的鐵絲、被整齊切割好的鋁片進入畫中,納吉的繪畫不是再現被機器創造出來的事物,而是作為機器來構成新的標準物。在金屬工作坊中,納吉與他的學生致力于把各種實物進行組合拼貼,使物的表面與繪畫表面融為一體,物的空間結構就成了繪畫的空間結構(圖2),“光線落在這些構造中的真實物體上,使色彩比任何繪畫組合都顯得更為生動。”[2](P313)以真實的物質為原料,把繪畫與機器相等同,最終生產出純粹又真實的標準物,這就是構成藝術之所以能夠投身于現代機器工業生產的原因。
與納吉相反,另外兩位包豪斯教師——表現主義畫家約翰·伊頓(Johannes Itten)與保羅·克利(Paul Klee)對機器保持疏離的態度,堅持身體感知與個體經驗的主導性。納吉進入包豪斯前幾個月,伊頓正好離職,這位藝術家在包豪斯中以對東方哲學和宗教的推崇而聞名,克利雖然對他的教學手段“有些諷刺”,但兩人的創作主張本質上是相通的。伊頓常常在上課前帶領學生做呼吸和凝神的練習,使學生放松身體,認為“一個手指痙攣的人,他的手怎么能用線條來表現特殊的情感?”[3](P7)伊頓表示,人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和理解節奏的本質,但從根本上來說,它只能意會。具有節奏的書寫形式有其自身的內在能動性,正因為這一點,它才成為諸形式中具有生命的一支。[4](P90)如何獲得有生命的形式是伊頓和克利共同追求的目標,克利在包豪斯的課堂上告訴學生什么是線條、什么是點:“有的線條給人的感覺是命不久矣,應該馬上送去醫院……如果一個點變得太厚顏無恥、太傲慢或太自鳴得意、仿佛吞噬了它附近許多其他的點時,人們會很遺憾地把它從得體的點中剔除掉……”[5](P52)。再現事物的運動狀態是印象派的做法,去探索這一運動的原理是先鋒藝術的目標,而克利與伊頓的要求是從個體的情感直覺出發去體驗形式的運動,這當然是十分困難的,“每個人都知道怎么樣畫圓,但并非每個人都有能力來體驗圓。”[6](P46)如何體驗運動的“圓”與如何制造出一個運動的“圓”之間是有所區別的,這正是伊頓與納吉的區別,也是克利與先鋒派之間的區別。
二
如何體驗藝術形式的內部運動?在1920年發表的《創造信條》中,克利把線條的運動描述為一場旅行:“回頭看看我們到底走了多遠(反向運動),思考一下已走過的距離(一束線條)。有條河擋在了我們的前面,我們借用一條船(彎曲的線),稍遠處有一座橋(曲線系列)。”[7](P585)。從克利的描述中可以了解,體驗形式運動的要求促使藝術家必須塑造一個開放而不是封閉的空間。在封閉的繪畫空間里,往往是“有”占據了主導地位,從架上繪畫的起源開始,人們就力圖描摹周圍充斥著實物的空間,而在開放的繪畫空間中,“無”則成為重要的手段,伊頓引用老子《道德經》中的一段話中用以描述自己的藝術精神:“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輪中空的地方用來放輪軸,因此車才能用;器皿中間要空,才能裝食物;房屋要鑿開窗子,才能住人。伊頓所引老子這一“有無相生”的觀點正是中國哲學為空間觀念所作出最偉大貢獻之一,而“有”與“無”的博弈正是兩種不同繪畫空間觀念的碰撞。
奧斯卡·施萊默(Oskar Schlemmer)自稱“包豪斯舞臺”是開放的舞臺,堅持以人的變形來適應抽象空間[8](P8),追求人體有機法則和機械法則的一致性。表面上看,這一新型的包豪斯舞臺是無限變化的,實際上它仍是“有”所主導的空間,取決于表演者運動的形式建構,與機械法則相一致的要求證明人體的變形仍需遵守一定的法則,因此,以機械為基底的舞臺絕不會是無限的。克利的繪畫拋棄了古典繪畫的中心透視體系,空間不再以古典式的三維劇場出現,而是被拆除了坐標隱退在背景中,對縮小深度畫法的摒棄將形象置于一個無位所、無方向的抽象界域里,與施萊默不同的是,克利將個體的身體經驗和運動體驗融入作品中,在他那些描繪活動的線條畫中(如《圖3,喜劇》(1921),《洪水沖走了城鎮》(1927),人們能切身感受到生成的微妙和不可預測,克利的繪畫展開的是一個真正無限的世界,它使我們了解到為何“無”對于構建開放式空間來說如此重要。

圖3 《喜劇》,1921年,現藏于泰特現代藝術館。
“無”中蘊含著流動性,“有”是被規定的、固有的,只有“無”不受限制地變化,正是這種看不見的力量才促使想象力發生,使得物體的可能性得以實現。按照施萊默所構想的那樣以機械型人體來代替真正的演員*“機械化的人型,這種新類型的令人震驚的形象由最為精確的材料構成,它將最高尚的觀念與理想人格化,去象征一種新的信仰。”見包豪斯舞臺[M].周詩巖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15.,無限的機械運動模式就會仍然指向封閉的空間,而克利的繪畫旨在用變化的“無”來建立一個開放的“中間世界”。這一中間世界的形式介于平面與線條之間,被克利稱為“線性媒介”。線性媒介打破了視覺空間和觸覺空間的界限,構成了觀者一種混合的感覺體驗,不斷發展的視覺功能會賦予克利沒有背景、平面或輪廓的繪畫以想象的普遍價值和規模,最終恢復一種觸覺空間,構成了平面相交的無限制場所*關于這一點的具體分析可見筆者文章《從德勒茲生成哲學看克利“畫出不可見之物”》[J].美育學刊,2017:2.。
從精神認識層面上來說,這一開放的世界介于現實與想象之間,在探討藝術家同時代的關系時,這個屬于死者和未生者的世界是不可預知的,同時又是屏蔽機器而因此寄寓著人性的希望的最后場所*“一切浮士德式的事物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居于一個遼邈的創造起點,于此我為人類、動植物、巖石,為地、水、火、風,為所有的續生力量作更重要的告白。”[瑞士]克利.克利的日記:1898-1918[M].雨云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238-239.。當代藝術中繼承了這一開放式空間觀念的作品日漸增多,法國當代雕塑家貝爾納·維內(Bernar Venet)就試圖在現實中構建有著不定型的外輪廓的空間,他把這種外輪廓線稱為“不確定的線”,作于巴黎拉德方斯區的《兩根不確定的線》(1988)坐落在高樓林立的商業區,外部光照使雕塑投影在大樓玻璃壁面上,雕塑整體所構建出的世界是非靜止的,不確定的線勾勒出非限定的、形式不定的空間,這個空間打亂了周圍以直線封閉、以完結的線條成形的恒常空間。維內希望通過這些不確定的線條,將成形的、封閉的空間轉變為開放的空間,為機器占據主導地位的城市生活作出反思。
三
現代藝術曾有過反抗機器的例子,唯美主義及相關的新藝術運動就十分堅決地反對將藝術納入包括機器生產在內的現代社會體制。與這些藝術主張不同,先鋒藝術走上的是一條藝術與生活重新結合的道路,不是藝術服從于生活,而是生活服從于藝術的指揮。彼得·比格爾提到,當先鋒主義者們要求再次與實踐聯系在一起時,它們不再指藝術作品的內容應具有社會意義。對藝術的要求不是在單個作品的層次提出來的,而是指藝術在社會中起作用的方式。先鋒主義者無一不對社會的改革投入自己的心血,包豪斯正是這樣一個通過藝術教育來調和藝術家與工業化世界的例子,這里的實驗室直接與現代建筑的工地相連,與工業化設備、家居、服裝的流水線相連,一旦模型被制作出來,商品就會被生產出來、上架。包豪斯用這樣的方式把自己與機器時代緊緊關聯,按照比格爾所說,一旦藝術與生活合流,不管是藝術服從于生活還是藝術指揮生活,藝術彌補生活不足的功能都會消失,藝術對生活的反思也不復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先鋒藝術的這一問題便已經在納粹統治下的社會中凸顯出來:未來主義藝術家在意大利為墨索里尼高唱頌歌,包豪斯則以接受工作委托的方式為德國納粹政權服務,讓·克萊爾關于“世俗化并沒有宣告藝術的獨立,而是給它簽了一份賣身契,讓它為更邪惡的勢力服務。”[9](P121)的這一說法因此而令人震動。
克利的朋友之一,同為“青騎士”一員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弗朗茨·馬爾克對戰爭持十分積極的態度,他主動服兵役,并在寫給親朋好友的信中說,“流血犧牲要比永恒的欺騙好,這場戰爭正是歐洲為了‘凈化’自身而甘愿承擔的贖罪與犧牲。”[10](P221),這種對戰爭的神秘體驗代表了當時很大一部分先鋒藝術家的態度,證明藝術家將戰爭與藝術一樣當作改變生活的特殊手段,背后是對日耳曼民族主義的渴求,德國先鋒藝術對生活革命性的態度和納粹的崛起有著無法撇清的關系。馬爾克戰死后,克利思考了他和自己的不同,“他并不為了把自己置于與植物、巖石及動物相同的層次上而變成只是全體的一部分。在馬爾克身上,與大地的聯系凌駕了他與宇宙的關聯。”而“我(指克利)不喜愛動物和帶有世俗溫情的一切生物。我不屈就它們,也不提升它們來遷就我。我偏向與生物全體融混為一,而后與鄰人與地球所有的東西處于兄弟立場上。我擁有。地球觀念屈服于宇宙觀念。”[11](P237-238)這樣看來,克利借在多維空間中散步的線條所組成的“中間世界”來脫離大地的做法代表了另一種自我反思的傾向,抗拒浮士德式尋求人類進步的方式,克利認為唯有逃離地球、保持無限的運動(創造)立場,才能夠獲得源源不絕的生機,同時因為遠離人類本有的內在矛盾,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寧靜。
承認機器的效用并依靠機器的功用來重塑生活,先鋒藝術對機器的推崇很快轉向為國家社會主義政權服務,不管是因為擔憂前途還是與納粹情投意合,在作出這樣的選擇時,先鋒藝術家們變成了固步自封的守舊派,藝術家以為自己是在建造一種新現實,沒想到反過來為現實所奴役。藝術作為人類文明中最燦爛的花朵竟然與滅絕人性的大屠殺相關,這讓人想起《啟蒙辯證法》中對于人類控制于物而又被物所控制的循環過程的展現,阿多諾與霍克海默這兩位睿智的思想家指出,主體在面對自然的多樣性時遭受到了磨難,這些磨難所帶來的痛苦正是主體個人意識覺醒的體現,反思使得主體慢慢學會了理性地去面對自然與他人,并因此壓抑了主體性中非理性的一面,而非理性帶來的恐懼又轉化為個人意識的痛苦,繼續生成主體性中的理性。啟蒙理性的生成過程正是先鋒派和機器之間的辯證關系的本質,先鋒派正是過于信服機器的作用而無法真正釋放內心的恐懼,這種恐懼一旦被利用,藝術將從個人的審美變為大眾的野蠻狂歡。這提醒我們,藝術脫離于現實就無法生存,而當藝術與現實融為一體之后又消磨了審美的真正意義。藝術與絕對的惡之間僅一步之遙,這不得不讓我們像克利一樣去思考如何依靠有限的形式去構建藝術與現實的“中間世界”。在德國包豪斯的內部,克利、伊頓與納吉、施萊默所代表的兩股藝術潮流對機器的不同態度所引發的對立正應了《啟蒙辯證法》中的那句話:理性如果不同不可預知的命運相結合的話,它就只能作為一種有限形式的理性起作用[12](P48),與希望在物質世界中找到一種符合要求的境域的先鋒藝術相比,那些將藝術創作的來源置身于自我的主張,把感受融入對人類理性的思考中,成就對人類獨立性的思考。
[1][澳]羅伯特·休斯.新藝術的震撼[M].歐陽昱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
[2][匈牙]拉茲洛·莫霍利-納吉.新視覺:包豪斯設計、繪畫、雕塑與建筑基礎[M].劉小路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
[3][瑞士]約翰·伊頓.造型與形式構成:包豪斯的基礎課程及其發展[M].曾雪梅,周至禹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4][5][德]弗蘭克·惠特福德.包豪斯:大師和學生們[M].藝術與設計雜志社編譯.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9.
[6][瑞士]約翰·伊頓.造型與形式構成:包豪斯的基礎課程及其發展[M].曾雪梅,周至禹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7]遲軻.西方美術理論文選(下冊)[M].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5.
[8][德]奧斯卡·施萊默.人與藝術形象,見包豪斯舞臺[M].周詩巖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9][法]讓·克萊爾.藝術家的責任:恐怖與理性之間的先鋒派[M].趙岑岑,曹丹紅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10][德]瓊·威斯坦恩.戰爭與革命中的表現主義,見曹衛東主編.審美政治化:德國表現主義問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1][瑞士]克利.克利的日記:1898-1918[M].雨云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
[12][德]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劉德卿)
10.3969/j.issn.1002-2236.2017.04.011
2017-05-09
蘇夢熙,女,復旦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理論。
J110.99
:A
:1002-2236(2017)04-004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