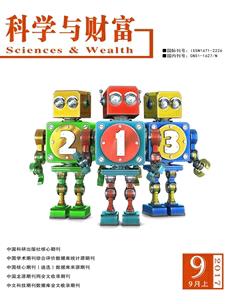《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讀書報告
摘要: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一書中總結了19世紀以來世界民主化浪潮的進程及產生的原因,重點分析了70年代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過程和特征,預測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走向。亨廷頓在書中以“西方文化論”為理論基礎,帶有文化偏見,我們應該結合時代背景,重新審視民主轉型理論。
關鍵詞: 民主;民主化;民主轉型;民主鞏固
1寫作背景
本書重點分析了20世紀后期大約30個國家從非民主政治體制向民主政治體制發生的轉型,由于當時作者所關心的那些問題還在發生,因此這本書更多的是初步的評估和解釋,只有等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告一段落的時候才可以對這一現象做一個更全面深入的解釋。就像文中亨廷頓所說“本書橫跨理論和歷史兩個領域,不是一本理論著作,也不是一部史書,而是介于兩者之間,基本上是一部解釋性的專著。”
2民主和民主化
民主和民主化的定義是這本書的邏輯起點,古希臘開始至今,對民主定義的探索從未停止。作為一種政治體制,“‘民主已經有2500年的歷史,而在頭2300多年,他一直被看作是個‘壞東西;直到最近100來年,它才時來運轉,被當作‘好東西”。在《第三波》這本書可以看出作者是宣傳民主的偉大旗手,亨廷頓預言道“時間屬于民主一邊”欲談民主化,必先談何為民主,亨廷頓首先引用了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對民主的定義, 即選舉是民主的本質,競爭和參與是評判民主兩個標準。選舉是民主的全部嗎?學者們各抒己見,亨廷頓認為民主的方法是為作出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個人通過競爭人民手中的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就是選舉。
選舉等于民主嗎?亨廷頓在《第三波》中談到20世紀80年代的危地馬拉,是由選舉產生政府,實際上軍人執政政權,政府成為軍隊的代言人和傀儡。亨廷頓對選舉和民主的關系產生了質疑,所以亨廷頓在書中介紹了拉里·戴蒙德對民主的看法,戴蒙德在其刊登在《民主雜志》中的一篇觀點鮮明的文章中詳細說明了自由民主與選舉民主的分野。自由民主國家不僅僅舉行選舉,而且還要將政府對社會的控制降到最低,如限制行政權、保證司法獨立、保護個人權利。
民主化是國家從非民主狀態走向民主狀態,強調過程大于結果,民主化過程就是強調在自由、公開、公平的選舉中產生政府取代不是通過這種方式產生的政府。
作者認為自由民主是一個西方的產物,非西方國家的自由都是在受西方國家自由民主的影響下產生的,亨廷頓強調東亞社會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自由民主觀念極其薄弱。
3三波民主化浪潮
亨廷頓對民主化浪潮這一概念定義:“一次民主化浪潮是在一個特定的事件內發生的由非民主政體向民主政體的成批的轉變”在民主化進程中,有的國家轉向民主化,有的國家朝著非民主化方向發展。三波民主化情況大致如下:
第一波民主化浪潮:1828—1926年,起源于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約33個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一波回潮:1922—1942年,約有22個國家被顛覆。民主化回潮反映出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黷武主義意識形態的崛起,如1933年希特勒奪權,終止了德國的民主。
第二波民主化短波:1943—1962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約40個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二次民主化回潮:1958—1975年,約22個國家的民主制度被顛覆。
第三波民主化產生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中下級軍官發動政變推翻了反對非殖民化的薩拉查政府,建立民主制度為標志。首先南歐開始民主化,希臘由選舉產生的文官政府取代了軍政權。
4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思考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響至今,與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化相比,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更為復雜。亨廷頓提出兩個問題:為什么大約只有30個威權體制國家,而不是約100個其他的威權主義國家轉向民主政治體制?為什么這些國家政權變遷發生在70、80年代,而不是其他某一段時間?亨廷度從五個方面回答了這兩個問題,同時把這五個原因歸結為相互聯系推動民主化進程的原因。
4.1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產生的原因
4.1.1威權政體因政績困局面臨合法性危機
亨廷頓認為威權政權幾乎毫無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績當作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威權統治者往往把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政績基礎之上,威權統治者為了換取民眾的支持,被迫作出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諾,但是經濟發展有自身規律,當威權政體無法解決本國的經濟危機、權力體制缺乏自我更新機制、對外軍事行動失敗等各種因素,合法性受到挑戰而瀕臨瓦解。
4.1.2經濟發展和經濟危機對民主的影響
在書中,亨廷頓認為經濟與民主發展有全面的相關性,無論是經濟高速發展還是經濟危機的出現,都會對民主化轉型產生重要的作用。經濟的發展帶來教育水平的提高、中產階級的壯大、市民社會的成長,這些都是有助于民主化轉型的因素。但是經濟的發展不一定帶來民主化轉型,他指出人均GDP在1000到3000美元之間的國家最容易產生民主化,比3000美元再高也不會增加民主的概率,由此可見,經濟的發展只是影響民主化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不是決定因素。
4.1.3天主教改革有利于民主化發展
天主教由過去與地方政權和威權政府關系密切的角色轉變為獨裁政權的反對派,使威權政權失去了他們在宗教中的合法性,在60年代中期后,教會幾乎一致反對威權政權。在巴西,在軍政府執政不久,教會也與政府決裂,當時,巴西全國主教會議發表了一篇聲明,斥責政府國家安全主張是“法西斯式的”主張,并且為積極的教會反對活動鋪平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智利、墨西哥、烏拉圭等國家,天主教紛紛動員人們和平抗議威權政府。
4.1.4外部勢力對民主的支持
“民主規范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那些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規范的認同”歐盟和美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民主,80年代末東歐出現的民主化是蘇聯政策的出現變革產物,蘇聯新政策為廢黜現有的共產黨領導人,非共產黨參與權力并通過競爭性選舉產生政府打開大門,這是東歐相繼發生民主化外部原因之一。endprint
4.1.5民主國家示范作用和滾雪球效應
一個國家民主化的成功會鼓勵其他國家開始民主化,一國的民主行動本身就有可能成為另外一個國家民主化的契機,會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產生連鎖反應,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類似的國家中示范效應最為強烈。1989年8月東歐,蘇聯默認或鼓勵非共產黨人士在波蘭執政,11月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12月羅馬尼亞都發生了類似的事件。
根據亨廷頓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原因的分析,這次浪潮是內部民主化條件的具備和外部力量的推動下合力以及全球化發展合力下發生的,同時亨廷頓認為政治精英的對民主的認可和共識也是民主化發生的必要條件,“在第三波中,創造民主的條件必須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領袖愿意冒民主的風險時,民主才有可能出現。”
4.2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過程
亨廷頓將第三波中轉向民主化威權政權分為三種:一黨體制、軍人政權和個人獨裁。民主化過程包括:威權政權的垮臺;民主政權的建立以及民主政權的鞏固。根據第三波民主化政權中執政集團和在野或反對集團的互動關系,亨廷頓概括出三類變遷過程:一是變革,二是置換;三是移轉。
變革是由政府中的改革派主導下的民主化,政府中的改革派比保守派力量強大,變革過程中反對派要從外部向政府施壓,且反對派中溫和派居多,與有較強改革意愿的改革派合作,走向民主。
置換是反對派的力量主導下推翻威權政權或威權政權自行垮臺的民主化,反對派比政府力量強大,置換通常要經歷三個階段:1)為推翻政權而斗爭;2)政權的垮臺;3)垮臺后的斗爭。置換過程中,政府中反對派的力量及其薄弱,保守派把握政權,拒絕任何變革。
移轉是政府中的改革派和政府反對派通過談判達成一致的民主化,至少政府的和反對派同意臨時分享權力。政府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就改變政權進行談判,移轉過程中需要政府和反對派進行溝通談判,雙方也需要平衡和壓制內部的各種反對力量,保證談判過程順利進行。談判結果是雙方都有機會分享權力,競爭權力。
4.3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特征
亨廷頓認為三次民主化浪潮絕是簡單的重復,第三波民主化與前兩次有所不同,是以“妥協、選舉和非暴力”為特征,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政治精英進行談判和妥協是第三波民主化進程的核心,這需要政府內和反對派各個團體之間做出妥協讓步,亨廷頓認為妥協或許就是“民主交易”,即民主參與范圍的擴大和參加和反對派領袖和團體在戰略和策略上的節制,比如反對派同意放棄暴力和革命。
選舉是民主運作的方式,威權統治者察覺到在國內恢復其合法性的必要性,試圖通過選舉恢復其日益衰落的合法性,因為威權統治者對國內環境反饋較少,所以盲目地相信他們能夠贏得選舉,政府用盡各種欺騙、共和手段左右民主選舉,但是這些威權統治者幾乎毫不例外的在選舉中失敗,選舉結果既是預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
前兩次民主化都是以暴力為杠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低度暴力,亨廷頓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證實,在絕大多數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暴力的總體水平是相當低的,“除1974年到1990年的尼加拉瓜外,總體的政治死亡人數大約在2萬人左右,主要集中在南非和亞洲大陸”亨廷頓還認為“考慮到政治變遷方面所取得的積極結果,在第三波中以人的生命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低的”,低度暴力受諸多因素影響:一些國家在民主化之間有過暴力體驗,在第三波民主化,不論是政府還是反對派都會避免重蹈覆轍;政府和反對派協商談判降低了暴力發生的可能性;保守派政府中使用暴力鎮壓反對派的意見不一致;社會階層的同質性一般會通過協商談判達成一致;政府中改革派力量強大到足以控制保守派和反對派的力量,也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降低暴力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因素造就了民主化的成功。
5民主鞏固
一國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如何鞏固新生的民主政權,如何避免民主政權回潮?是政府的改革派或者反對派面臨治理國家的挑戰。
亨廷頓認為處在發展和鞏固其新生民主政治體制中的國家,可能會碰到三種類型的問題:轉型問題、情景問題和體制問題。如何處理這三類問題,決定了該國民主政權的穩固程度。
5.1新型民主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兩個主要問題
民主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兩個問題主要是指新政權建立后需要處理和清算舊政權的遺留事宜,主要包括如何對待前政權官員的“虐待者難題”以及如何減少軍隊對政權的介入并保證文官體制的“執政官難題”,對前政權侵犯人權的官員進行清算和處置,是法辦懲治還是遺忘與寬恕,各國對這些人的處理方法各不相同。對于舊政權中軍人統治的國家,如何安撫軍隊中的既得利益者,平息軍人對民主政權的敵對情緒,是新生的民主政權面臨的問題。
5.2檢驗民主鞏固的標準
亨廷頓認為“兩次政權輪替”的標準是民主鞏固的標志。具體從兩方面校驗民主是否鞏固,一是民主價值是否得到政治精英和公眾的認可,“政治精英和公眾堅定的相信統治者應該按這種方式加以選擇的程度,即對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態度上的校驗”。第二個標準是從民主行為上檢驗,“政治精英和公眾的確通過選舉選擇領導人的程度,擠兌這個國家政治中的民主事件的制度化進行行為檢驗”。如果新興的民主國家出現了政權的兩次易手,說明已經達到了民主鞏固,那么如何才能促進民主鞏固呢?作者分析得出了影響民主鞏固的條件。
5.2有助于民主鞏固的條件
第一,具備民主的經驗,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化的經驗為第三波民主化提供了借鑒,亨廷頓認為,過去有民主經驗比沒有這種經驗的國家更有助于第三波民主國家的鞏固;第二,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政權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高度發達的經濟、更為復雜的社會和受過教育的人口的增多都有助于民主政權的建立;第三,國際環境和外國對民主的贊揚影響民主國家的穩固,民主的觀念在世界大國間得到普遍的認可;第四,第三波國家中民主轉型的時機也會影響一國的民主鞏固;第五,轉型過程中低度暴力也是是民主鞏固必不可少的;第六,政治精英和公眾如何對新政府無力解決的問題作出反應。endprint
筆者認為培養民主文化是有助于民主鞏固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樹立民眾對民主的正確認識,使政治精英和公眾相信民主體制的價值,即“民主并不意味著問題必將解決,但它是卻意味著統治者可以被更換”。當人們了解到,民主只是為專制提供一種解決辦法,而未必為所有其他問題提出解決辦法,對威權政權產生的幻滅和降低是民主得以鞏固的基礎。
6民主的展望
“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現實”亨廷頓認為經濟發展為民主體制取代威權體制創造了條件,每一波浪潮都會比前一波浪潮進步,時間屬于民主一邊。
7現代社會與民主轉型預測
亨廷頓在《第三波》中的民主轉型理論,是以“西方文化論”為理論基石,他指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為民主制度的發展提供適宜的基礎”。鼓吹“西方文化論”者,就是突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以西方民主為標尺,評判其他國家的發展,文中表現出了偏見與歧視。
總之,亨廷頓的民主轉型理論在探索世界民主化進程的規律方面,做出了一定貢獻,影響深遠,但是他的《第三波》與民主轉型理論以“西方文化論”為理論基礎,具有明顯的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特征,面對21世紀民主化發展的新特點,亨廷頓的理論難以做出有力解釋,因此我們需要全面的思考亨廷頓的民主轉型理論。
參考文獻
[1] [美] 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M],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2] 王紹光:民主四講 [M]上海:三聯書店,2008.
[3] [美]戴蒙德:第三波過去了嗎?[A]民主雜志[C]1996.7.7.
[4] 周敏凱,趙盈:轉型民主問題與現代民主形態多種屬性研究—兼析亨廷頓的轉型民主觀[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版),2014(3):92—97.
[5] 周淑娟:對民主及其與經濟發展之關系的思考—讀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J],學理論,2013(25):60—61.
[6] 羅湘衡:對第三波民主化的若干思考[J]教師教育論壇,2008,21(6):25—27.
[7] 周敏凱:世界民主化實踐新動向與對亨廷頓轉型民主理論的反思[J],上海市社會科學界學術年會,2014.
[8] 常偉娜:民主鞏固[D].吉林大學,2014.
[9] 劉啟云:亨廷頓的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理論評析[J].理論視野,2008,105(11):53—54.
作者簡介:
梁書慧(1992.12--) 女,山西省長治市市人,學歷:碩士研究生,專業:中外政治制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