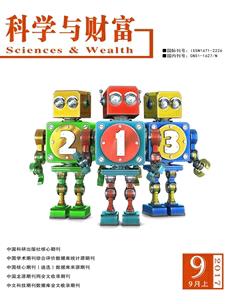對"股份公司治理和杠桿收購問題"的研究
近兩年內最受人關注的資本大戲之一的“寶萬之爭”在資本市場中掀起了一波波風浪,各行各業互表其態。“寶萬之爭”的高潮到現在已經告一段落,其后遺效應在市場上也是一直或大或小,將近持續兩年的“寶萬之爭”反應了資本市場多個層面的深層次問題,已然坐實了其必定成為資本市場的一大經典案例,我覺得這一案例值得我們做出探討、研究和剖析。“寶萬之爭”這場戰役看似正面交鋒實則太過錯綜復雜,這場金融資本與實業的博弈所折射出的東西值得人深思,我們很有必要撩開籠罩在股權之爭上的面紗,對其進行剖析。從“寶萬之爭”中我想從兩個方面談談我的思考,即上市公司治理問題和杠桿收購問題。
一、上市公司治理問題
萬科,職業經理人控制著公司的經營權,管理層持股少,股權結構分散,創始人的股權極易被稀釋。我們縱觀中國市場,無不發現,地產行業幾乎是模式化的。雖然在以中央政府調控為主的房地產市場相對穩定,但是如若管理層缺少危機感和長遠意識而保守于保守和理想化的股份制改革,企業遭受“野蠻人”入侵也是遲早的事情。
“寶萬之爭”亦可以說是“股權之爭”,即便萬科作為全球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甚至進入了世界500強行列,但是公司治理這塊凸顯的問題依然無法掩蓋,“股權之爭”的存在顯示著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由此“寶萬之爭”上演了一幕并購的“攻-防”戲。王石放棄了股權,可想而知,作為企業家的他這一舉止使得內部治理機制不夠完善的萬科在內部治理方面更加帶有障礙性。目前來看,中國公司治理應用中的主要矛盾是企業創始人和投資者之間的沖突。我們都知道的阿里巴巴采用了“合伙人制”,這樣保證創始人的權力和控制力,即便創始人持股較低,但是AB股架構使得可以提名董事會半數董事。萬科理應及時推動股權制度改革。
我們可以留意到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并沒有明確董事的提名權,這使得控制股東有更大的操作空間來修改公司章程進而控制董事提名,即便這是一套可靠的防衛機制,但是防衛過當會嚴重損害了其他股東的利益。如果我們不能提高董事會的自主性,那必須要采取手段使得董事會的結構和流程更加明文規范和透明化。
任何一個公司都會牽涉許多的利益相關者,而公司治理必須要協調好這些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警惕治理手段成為利益爭奪武器,公司價值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還依托于董事會的自主性和主動承擔責任的意識。
二、杠桿收購問題
“寶萬之爭”所產生的另一問題就是上市公司收購問題。有相當大部分業內人士質疑寶能收購萬科的信息披露的合規性,我們知道當初寶能取得萬科A股股票5%,后又繼續增持股票,但是,并未履行書面報告義務。九個資管計劃被寶能作為杠桿資金,如此似乎在打擦邊球而有意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此九項很容易被劃分為上市公司收購的一致行動人。
寶能的杠桿收購,已完全突破了僅通過銀行借貸融資收購的傳統模式來獲得資金來源。寶能收購萬科,不僅僅利用了括銀行,還利用了券商、信托、基金等各類金融機構在內的各類杠桿資金,這也讓人質疑其收購資金來源的合法性。相關監管部門理應加強對杠桿收購資金項目流通的監管。
再次采用美國80年代超級市場行業杠桿收購的數據,Chevalier(1995a)研究了杠桿收購是如何影響產品市場的競爭以及對于消費者的效用。研究表明杠桿收購明顯從一定層面上可以影響產品市場的定價決策。我們知道,被收購公司債券持有人具有顯著的負收益,而杠桿收購對于被收購企業的利益持有人而言具有整體的正向收益,這是一種相當大的不平等。"寶萬之爭"中一個引人熱議的點就是利用資產管理計劃配資實施杠桿收購,我們不免質疑這一模式的合理性和透明性,側面反映出目前我國收購融資工具的缺乏和杠桿市場融資制度的不完善。
“寶萬之爭”為許多上市公司敲響警鐘,大小型上市企業應保持對環境的敏感性并有必要地進行股權改革,從而完善公司制度。對于上市公司的治理,管理層應該具備自主性、責任意識以及長遠的發展視野。在杠桿收購領域,我國應盡快引入有效的、標準化的融資工具。同時我國仍然缺乏針對創始股東的保護,體現公權力的公司立法也始終缺少保護創始股東權益的條款。希望我國的《公司法》、《證券法》等能進一步完善,政府及監管部門能加大對資本市場運作的監管,攜手“無形的手”讓資本市場更加健康繁榮。
參考文獻:
[1]溫秀英. 透過“寶萬之爭”解讀公司治理[J]. 統計與管理,2016,(11):121-122.
[2]劉蕾.淺析萬科股權之爭[J].當代經濟,2016(5)
[3]《中國杠桿收購存在的主要問題——“寶萬之爭”研究報告節選之七八》
[4]周志軼. 創始股東保護問題研究——國美股權與控制權之爭對中國公司治理的啟示[J]. 戰略決策研究, 2014(5):83-94.
[5]黃偉程. 創業板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績效研究[D]. 浙江大學, 2014.
作者簡介:
徐丹,本文第一作者,(1996.11~)女,漢族,祖籍江西省九江市,本科生在讀,現就讀于江西師范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 會計學(ACCA)專業。
劉汕,本文第二作者,(1997.03~)男,漢族,祖籍江西省贛州市,本科生在讀,現就讀于江西師范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 會計學(ACCA)專業。
黃厚林,本文第二作者,(1996.08~)男,漢族,祖籍江西省贛州市,本科生在讀,現就讀于江西師范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 會計學(ACCA)專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