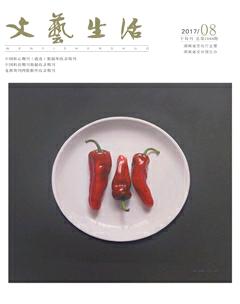從向郭之“學”談到山水畫之“師”
朱文婉
摘 要:從向郭在《莊子注》中對“絕學任性”的觀點出發,加之馮友蘭對其之注解,聯系回顧中國山水畫的沿學路徑。采擷跨多時代的古代畫論,論證中國山水畫由古至今的學習方法——師古、師造化的思路。同時,反觀向郭的觀點,從而推導出向郭“絕學”之說并非通達中國山水畫的學習方法,提出進入中國山水畫學習的正軌必須--先潛學后任性。
關鍵詞:中國山水畫;師古;師造化;向郭;莊子注
中圖分類號:J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24-0072-02
一、前言
南朝劉義慶在《世說新語·文學》第十七篇提到,“向秀于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競,而秀卒。...郭象者...見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己注。”而又由于“其義一也”,加之劉孝標注釋表明,當時解釋《莊子》主要有兩派,其一為向郭義。因此,把“合述”《莊子注》的向秀和郭象稱為“向郭”。
向郭在《莊子》的“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而君之所讀者,古人之魄已夫!”中注:“當古之事,已滅于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后至焉。”(《莊子注·外篇·天道第十三》)。其中,“絕學任性”即是棄師古而任性情,“與時變化”是其觀點的支撐條件。即相同的已知條件在不同的時間節點發生,得到的結果也并非唯一,因此“學”便沒有其必要性。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把“學”解釋為“模仿”,同時歸結出向郭的觀點--“模仿是錯誤的”,其中理由之一為“模仿是無用的”,也就是向郭提出之“學”無用,投射在藝術領域即是“師”無用。
若以傳統中國山水畫的學習系統反觀向郭的“絕學任性”,向郭其意似乎并不通達。山水畫自魏晉時期漸脫離人物畫獨立成科,在迄今已1300年的歷史中,山水畫的傳統教學一直依托如向郭所言之“學”,即“師古”、“師造化”。
二、對“古”之師與學
師古就是師名家、師名畫,縱觀歷代畫家無不在此基礎上潛心浸淫,最終形成自我風格和面貌,陳傳席所撰《中國山水畫史》就詳細交代了歷代山水畫家各師其誰。若以時代論,北宋宮廷組織對前晉唐名跡的摹本,宋畫,尤其是北宋,血脈上直接從唐演進過來,味道氣息,幾無二致,只在精粗上區分。而在師古風氣最盛的元,以趙孟頫的“作畫貴有古意”為始,元以后師父臨摹以教其徒子的風氣蔓延。
明清多以師古為能事,師古已成文人的審美旨趣。
明董其昌宗法五代、宋、元。其畫如惠山之泉水,平淡之中意韻無窮,既有黃公望的灑脫華滋,倪云林的簡淡蕭疏,王蒙的蔥郁秀潤,吳鎮的堅實凝重,趙孟頫的高古典雅,董源、巨然的平淡天真,又有五代、宋代荊浩的渾厚嚴實,米氏的爛漫天真。
清代四王更是長于師古,追求筆筆有來歷。如王時敏強調“一樹一石,皆有原本”;王鑒之坡石取法黃公望,點苔取吳鎮,用墨取倪瓚;王翚取黃公望、王蒙的書法用筆,取巨然、范寬的章法布置。王原祈以得黃子久之“腳汗氣”為榮等。
郎紹君在一次訪談中,也以20世紀為分界線提到“師古”的前世今生及學畫者對其態度的轉變,最后得出結論:其實,對于學習中國畫而言只存在如何臨摹的問題......臨摹是必須的。
對古之師與學還需回溯另一蹊徑方成圓融,即書法。真草篆隸行,不同的書體,不同的法帖,幾乎任何筆法都能直接變作國畫技法,相對的,勾勒皴擦點染,無不源自書法......是故唐代書法的大成,實則從某種角度為后世的山水畫作了筆法上的鞏固,五代的高峰也就在情在理。
最后,如董其昌云:“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元章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個不相似。使俗人為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二·畫源),亦即,“學”易,但學其神氣難,師古前須區別簡單的“學”與有目的的“學”。同時,其在剖析倪瓚畫作時提到,倪瓚畫樹、山石、皴等各有其似,但“各有變局”,從而提出“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亦即,技法層面上雖可師法古人,但可貴之處在于,能融會貫通的同時,需學會“變”。這也是中國畫技法不斷完善和完備的支點。
三、對“造化”之師與學
明人董其昌與莫是龍對中國山水畫的學習路徑有著相似的思路。董在《畫禪室隨筆》中提出:“畫家初以古人為師,后以造物為師”。莫在《畫說》中云:“畫家以古人為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為師”。
針對董和莫的言論,清代董棨在《畫學鉤深》中道:“前賢云‘師古人而后師造化。古人之法是用,而造化之象是體”。另外,從范寬畫山水始師李成、荊浩,后居據在華山、終南山,又可見,中國山水畫的取材最終需落實于造化,即自然是畫之粉本。
此表明,從師古人到師造化,這不止是強調“師”,同時也強調了師的次序。
而師古人兼師造化的另一方持的觀點卻是,先領悟造化,再用古法去印證在造化中的領悟。如清代戴熙言:“古人不自立法專意摹繪造化耳。會得此旨,我與古人,同為造化弟子”(《習苦齋題畫》)。又如清代金漢言:“畫家宜先知造化之精微、參合古人之粉本”。(《讀畫叢談·規矩》)
但排除這種次序的影響,學習中國山水畫跳脫不了的是“古”和“造化”兩個因素。除了以上陳述的師古的重要性,古人對師造化有著大體量的記載。
明人沈顥在《畫麈》中寫道:“董源以江南真山水為稿本;黃公望隱虞山即寫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筆硯,遇云姿樹態,臨勒不舍;郭河陽至取真云驚涌作山勢,尤稱巧絕”。強調了古人師造化的事實及延伸出師造化的重要性。包括唐志契在《繪事微言》中言:“凡畫山水者,看真山真水,極長學問,便脫時人筆下套子,便無作家俗氣。……故畫山水而不親臨極高極深,徒模仿舊人棧道瀑布,是模糊邱壑,未可便得佳境”。即強調山水畫家必須存師造化的觀念,在目遇自然后的“得佳境”,“模仿舊人”非能至。
凡此種種論述甚多,都在秉持師造化的信念。而造化也許可分第一造化(云川草木)和第二造化(屋廟舟橋),但目之所涉,皆需“中得心源”,這是山水畫家在實踐中長此以往的理解和深化中國人的山水。以主觀意緒對造化客體進行回爐再造,先師造化再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中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山水師自然,山水和道似乎如出一轍,這種外延的相關性,似乎予山水畫以真理的“學”。
四、結語
回顧向郭在《莊子注》之“學”說:“若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己。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 羨鳥耳。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在學畫的層面,若“止乎本性”,則如王學浩在《山南論畫》中言之,“如夜行無火”,若“不求之”,則如董棨在《畫學鉤深》中言之,不知“規矩方圓之至也”。
向郭提出的“絕學”,在藝術的各個領域并非觸類旁通,至少從中國山水畫的學習方法上反觀,國畫后來者的必經之路也許并非是“絕學”,而是“潛學”,先潛心學習古人古畫、再到自然造化中領悟寫生。最后,“任性”,任心性而作。因此山水畫不僅只是一種視覺符號,山水畫是中國人心性的再現。
參考文獻:
[1]郁俊.流轉的繁華:盛期中國山水畫的審美演變[J].知中-山水,2016.
[2]姜麗娜.解析董其昌的臨摹觀[J].中華兒女(海外版)·書畫名家,2012(06).
[3]張桐瑀.臨摹·臨摹——龍瑞、郎紹君談臨摹[J].美術觀察,2004(03).
[4]鹿迅.山水演義[J].知中-山水,20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