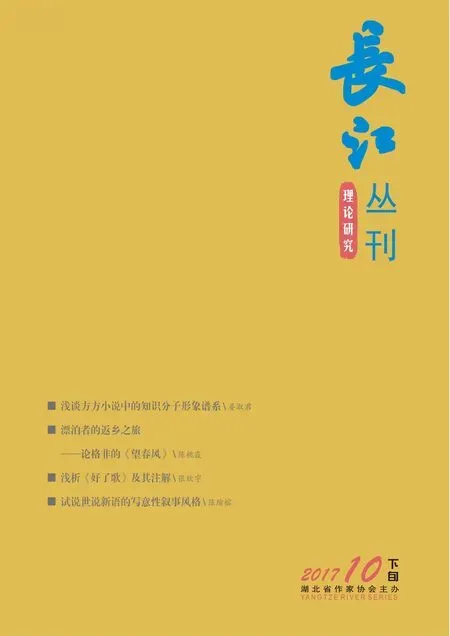沉重的精神困擾
——評歐曼中篇小說《胭脂路》
王新民
沉重的精神困擾
——評歐曼中篇小說《胭脂路》
王新民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隨著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的迅速推進,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個體的生存感受,也在時代浪潮的裹挾之下,被不斷地顛覆和重整。中篇小說《胭脂路》采用女性視點,細膩地描寫了女主人郝秋梅,在劇烈的社會顛覆和重整之中,個人愛情、婚姻、家庭的困境和情感的履歷。郝秋梅在城市底層生涯的種種遭遇,真實而深刻地展示了當代大多數城市底層女性,所面臨的生存與婚姻家庭的雙重困境。歐曼在這部小說中,不僅為我們淋漓盡致地揭示了時代和社會生活的喧嘩表象,并且努力探究了浮華生活背后沉重的精神困擾。在中篇小說《胭脂路》中,一個生活側面是喧囂雜亂欲望橫陳,另一側面則是現實與內心波濤暗涌,寂靜中潛藏躁動的危機,讓女主人公的內心掙扎紛亂不堪。時代憂患與女性生存、婚姻家庭窘境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作品凝重的底色和略顯焦灼的情感基調。

《小說月報》2016年第4期中篇小說專號轉載《胭脂路》
作家的作品與自己所生存的時代往往是息息相關的,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這么劇烈,當下社會的現實這么豐富,作為一個作家,不可能完全拒絕這樣的現實,不可能完全回避現實層面的晦暗。歐曼的小說直面現實,堅持平民記事取向,實際上是一次“平民寫作”的真誠實踐。她以平視的姿態,拒絕煽情的虛構,對轉型社會期個體迷茫的真實記錄,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實的書寫,是這個時代城市底層生活原汁原味的再現。沉重的市民情結,深切的世俗關懷,親和的民間立場,是歐曼小說的人文精神能夠勇敢突破政治中心意識形態話語框架,消解政治烏托邦文學宏大敘事文學構架,觸及民生要義,直抵遮蔽下的晦暗,在人間悲情中發現美與善,真實展現下層市民生態與心態的寫作驅動力。歐曼的小說遠離了“東方詩意”的裝潢,擯棄了“化蝶”的喜劇性終結,沒有以一種人為的亮點,消解生命個體的深切痛苦、切除人與苦難的基本聯系。因此,她的小說機智地躲避了善與惡,靈與肉涇渭分明的那種革命化的人道主義對立。在中篇小說《胭脂路》中,作者并沒有將主人公精神的困境推向極端,善與惡,美與丑總是同體共存,迷失的個體總是能夠在困惑中尋找到自我解嘲的理由,從而在麻目的狀態下獲得心靈的自慰。
歐曼的小說世界,不是一個虛擬的世界,而是那些艱辛地生活在大城市縱橫交錯、臟亂無序的街巷之間的市井小民,痛快淋漓、毫無遮蔽地表現自我、認識自我、張揚自我的“生活場”。歐曼將自己的筆觸伸向生活的現場,還原生活,書寫現實生活中瑣碎與卑微的世俗人生。歐曼對生活在城市下層社會的市井百姓生命跋涉的艱辛,個體生命被歲月無情吞噬的痛楚與無奈,有著一種深切的了解和同情;在日復一日的平庸中,這些生活在底層社會的小市民,以城市人特有的小智慧,精明的計算著,辛苦的忙碌著。郝秋梅們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讓每一天能夠活得不那么煎蹙,怎么能夠多賺點錢讓兒子在學校的生活不那么艱澀,至于活著的宏旨大意,他們幾乎從來不去探究,也沒有閑情逸致去問個究竟。事實上,在一個強大得可以吞噬一切的“秩序”中,大多數個體的人都無力與命運對抗,他們的命運就是每天生活在沉重,疲憊的柴米油鹽、凡人瑣事之中。除了對于自己身邊的利害,不得不保持一種本能的敏感之外,對于什么高雅,什么情致,的確有著一種知識分子精英想象不到的麻木。他們的理想就是活著,活著的力量來自于忍受,忍受生活賦予他們的幸福與痛苦、沉重與無奈、平庸與卑微。對于自己生命的意義、價值,他們不可能有一種自覺、清醒的提升意識。他們不可能像那些天降大任于一身的士大夫知識精英們一樣躊躇滿志,一樣偉大高尚。歐曼的小說講述的就是這些普通市民怎么活著的故事,記錄的是她們千瘡百孔的情感經歷。
郝秋梅一直在尋找自己生存的陽光,她希望站在陽光下去感受生命的能量。但是,她的潛意識里,仍然不能擺脫傳統女性意識支配下的隱忍生存模式。所謂傳統女性意識,指的是女性在自我認知的過程之中自覺地將善良、淳樸、堅韌、寬容視為一種美德,并以此為標準來要求自己。面對底層生活的艱辛,隱忍生存是郝秋梅的選擇,本本分分做女人是她們的人生信條。在遭受了重大的打擊之后,她在隱忍的同時沒有放棄生活的信念,在她身上呈現的是一種生命的力量,一種情感的力量。在經歷磨難之后,她往往更能明確生活的方向,堅強活著。這就是傳統女性意識支撐之下的一種自我拯救。這種自我拯救也是中篇小說《胭脂路》對于底層女性隱忍生存的一種呈現。
與善良、守已安分的女主人公郝秋梅相對應,在中篇小說《胭脂路》中,作家塑造了一個庸俗卑瑣的、高度欲望化的男性形象。她的丈夫易貴華是生存資源與話語權力的壟斷者和擁有者,也是構成郝秋梅艱辛生存環境的直接根源。在一個按照男權文化內在邏輯運行的社會,女性作為男性的本能對象和欲望符號,在一定意義上成為男性肉體的承歡者。女性的命運其實只能是:要么主動與男性“合作”,屈從甚至完全迎合男性的意志;要么被這個社會所擠壓,在女性自身的生存困境中左沖右突,在傳統女性意識的支配下隱忍生存。這不是郝秋梅一個人的命運,而是許多社會底層女性的宿命。歐曼以其獨到的見地、細膩的筆觸,塑造了郝秋梅這個在傳統與現代、現實與理想、愛情與苦難的夾縫中生存的當代底層女性形象,藝術化地表現了她在情感世界中的痛苦與歡樂,作者持守一種沉靜而清醒的寫作立場,揭示出處于“時代裂縫”底層女性遭遇的重重困境。歐曼摒棄了廉價的樂觀,嚴肅地審視并探討著底層女性在情愛抉擇和精神追求上的出路問題,她關注社會熱點問題、更關注底層女性的命運,這樣就為她的作品灌注了一種知識分子的視野和人文情懷。
歐曼構造故事的原則是順其自然,不是編故事,是故事本身就那樣,她只是復述出來。人物也是,小說中的人物不那么掙扎糾結,好像生活隨便怎樣,他們照樣那樣,沒有憤怒,也沒有驚喜。郝秋梅的命運,有許多無可奈何之處,但也不過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是要直面的。作者只是以先天的觀察力和悟性,直接或間接地汲取著日常生活中可抓取的寫作素材,然后藝術裁剪、秉筆直書而矣。歐曼筆下的故事也許有點傳奇,但傳奇里還是普通男女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原生態的、當下性的底層圖景以不易為人察覺的方式,悄悄蛻變成作家想象的“市井拼圖”。歐曼的小說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樸實、老道的文字刀刀見傷,傷及見血,凸現出一個個在時代與境遇里百般掙扎而惶惑與無力的女性的人生際遇。
愛默生說,我們在天才的作品中,會認出被自己告誡的思想,它們陌生而回來。寫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仿佛早已遠離塵囂。但沐浴在千年不變的月色里,只要翻開“人性”這部讀不盡的書,就會看到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的傳奇。其實在歐曼小說中,底層的艱澀和平庸書寫得并不張揚,寫作風格也并不華麗,甚至還有點蒼
涼。歐曼用通俗的語言,來訴說這個時代的故事,說故事本身便成為一個沉淀生命的很重要的使命。歐曼以她綿綿無盡、峰回路轉的故事來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是一個充滿人間煙火的社會,這個社會充滿了莫名其妙的文學想象。歐曼在小說中虛構了生活中脆弱的部分,虛構了事物悲傷的完美,她的小說切中了很多在特定情況下或者是敏感、或者是讓人感動的、或者是讓人心有所屬、戚戚焉的情節。另外,城市生活的語境和經驗,也讓她得以成就了一種更開闊、細膩深入生命的視野觀察。從文學角度來回應人生無言以對的迷惑,歐曼一下子就直統統地面對我們嚴峻的現實,以及人的生存、婚姻、家庭困境,但這是寫底層必然會面對的問題,它讓你無法轉彎抹角,因為歐曼不可能以隱晦恍惚、吞吞吐吐、語焉不詳書寫來取悅于習慣了擁抱陽光的讀者。

王新民,筆名斯民。湖北武昌人。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二級編劇。著有抒情詩集《走向黎明》、《美麗的陣痛》,散文詩集《顫抖的靈肉》,少兒詩集《溫柔的小溪》,評論集《與繆斯女神握手》,散文集《悠悠歲月》、《王新民文集》(四卷)等。作品曾獲武漢地區首屆中青年作家優秀文學作品一等獎、廣西《漓江》優秀文學作品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