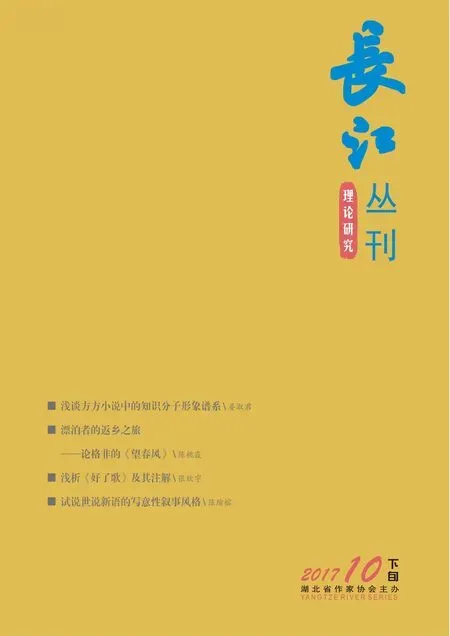《叔叔的沙漠》的敘事策略
李春光
《叔叔的沙漠》的敘事策略
李春光
荊門作家金成海的小說創作,大都是以“小江湖”這個地名為背景展開,故而他的中篇小說集干脆命名為《小江湖軼事》(2016年武漢崇文書局出版發行)。金成海以“精神還鄉”為思想旨歸,在“小江湖系列”故事中,探討了城鄉二元結構下的農村生活的深刻變革,以及農民遭遇的時代牽絆。而個中顯者當屬《叔叔的沙漠》一文,曾在《長江文藝》頭條推出,被認為是作者“在精神還鄉的道路上完成的飛躍”的標志。此文不狃于常規的鄉土敘事,又不囿于赤裸的身體敘事,更不拘泥于俗套的傳奇敘事,在借鑒先前的寫作傳統的基礎之上獨出機杼,可謂力透紙背。
鄉土敘事
曾大興先生認為,“鄉愁”就是流動或遷徙在異地的人們,對于家鄉的一種回憶式的情緒體驗,包括對親情、友誼、愛情的回憶,對家鄉的自然山水與人文景觀的回憶,對個人成長經歷的回憶。正如金成海在是書“自序”中所說的那樣,他癡迷于一個“此鄉非彼鄉”的虛構的文學地理空間——“小江湖”,由于時空的異質性,即“我的精神在四處游移”,導致了他的“精神還鄉”,和他一起精神還鄉的還有“我爺爺”、“我叔”以及“登九”等,他想通過他熟悉的“漢江沙灘”表現一種“原生態的東西”。而這種“原生態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隔簾花影般的“鄉愁”,一種對故鄉土地的隔空親吻。
有學者將鄉土文學概括為三大品格,即“鄉土病”、“農家苦”和“鄉土趣”。而這其中,“農家苦”敘事策略的終極指向,是為了論證農民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在新世紀的小說創作中,雖偶有提及,但已去主流甚遠。“鄉土病”和“鄉土趣”仍然是新世紀以來鄉土小說聚焦的熱點。《叔叔的沙漠》也不例外。
首說“鄉土病”。這種鄉土敘事,在開掘農業社會中農民精神層面的某些痼疾方面最是用力。男尊女卑的褫奪、家族宗法的威權、落伍時代的感傷等等,無不戳弄著作家充斥胸肋的鄉愁。作家一方面在再現這些痼疾的癥狀與產生原因,另一方面也在搜求著療救這種痼疾的良方。差不多每四年克死一個男人的“白虎星”白寡婦,在克死“我”本族叔輩、沔陽縣的賣小雞者、鄰村的“半瞎子”以及她的小叔子之后,沒人敢應她的“招”,最終成為絕佳的“臨時茍合”的“草狗子”。族人們擺布著白寡婦的人生,“白虎克夫”的過時思維扼殺了她尋求真愛的權利。在聽到“安徽省有人分田的消息”后,叔能夠進入王家灣的那片河灘,便是族人們在宗法制的鄉村中相互妥協的結果。叔與許書記在建養牛場上的分歧,正體現了小農思想在現代化浪潮下的不合時宜與底氣不足,而“漢江集團”的最終倒閉,與其說是經營不善,倒不如說是與時俱進的“誤打誤撞”與“鋌而走險”的農民思維作亂的結果。
再說“鄉土趣”。這種鄉土敘事,最有鄉土的模樣。描繪如詩如畫的故土風物,展現憨厚質樸的故土人情。依托田園牧歌式的恬淡書寫,把作家淡淡的“鄉愁”建構出了具體的輪廓,如此可感,又令人神往。“文學空間并不是一種外在的景觀或場景,也不是見證時間在場的固化場所,而是一種生存體驗的深度空間,它的生成源自作家對于生存的內在體驗。”作家虛構出的王家灣,正是這種“對于生存的內在體驗”的最好注腳。王家灣的文學空間建構,頗有作家故鄉的影子,流經村口的“襄河”以及上游的“丹江水庫”,均為叔的沙漠提供了更好的憑依。進入沙漠之后,叔侄二人在草地上打滾、在瓜地里吃瓜、在襄河里游泳捕魚、吃糍粑刁子魚、喝汽酒,又是多少文人魂牽夢繞又難以折返的景象,正如“我”所說:“我羨慕他那田園式的生活”。總是喝得爛醉如泥卻十分討老婆歡心的“林不滅”,豪爽潑辣不拘小節的林芝,以及“背大時”卻免除了鄉親們牛草錢的叔,借用鏡子反光擾亂日軍轟炸機的爺爺等等,均是“民風很淳樸的”的最好佐證。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最大的突破之處就在于,將“鄉土病”的畸變與“鄉土趣”的褪色淬煉在一起,而調和二者的佐料便是城鄉二元結構沖擊下的思維意識的漸變。“我”歆羨叔田園式的生活,可“我”更希望通過考大學來“走出這偏僻的鄉村,吃商品糧”,過“星期天逛公園,看老虎獅子大象孔雀鷹子鳳凰”的城里生活。陳春娘“臭罵”叔,“鄉巴佬想啥美事?見過商品糧戶口嗎?”這些話讓叔意識到,“原來這世上都是有等級的”。致使后來,叔把孩子全都轉為“中價糧”,以提高孩子們的“社會地位”。“鄉土病”畸變成了逃離故土、唾棄家鄉的無力掙扎,與躋身“商品糧戶口”的百般試煉,“鄉土趣”則褪色成工業化時代下的不那么講究“生態平衡”的開發,與世風日下中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糾葛與情感羈絆。在時代的洪流中,叔的心就像他的沙漠中已經堰塞后的那汪死水,無甚可戀。
最終,叔叔的歸宿,仍然是他的故土。每當叔叔思想發生重大轉變之時,他都會去沙漠邊的襄河中游泳,這是一種逃避的表征,更是一種自由的解體。“返回自然出于人們逃避的需要,人們要逃避對不滿社會的無能為力,逃避沒有男人氣概的矯揉造作。”其實,“自由”具有兩種面相,“一方面,人擺脫外在權威,日益獨立;另一方面,個人日益覺得孤獨,覺得自己微不足道、無能為力”。在襄河中,在沙漠里,這些漸遠的鄉土,起初是叔擺脫宗法權威、日益獲取自由的“飛地”;后來成了叔大展拳腳、改天換地的“試驗田”;最終成了叔逃避被時代碾壓的落寞、舔舐千瘡百孔的靈魂的“收容所”。
身體敘事
新世紀的小說創作中,對身體的格外重視已然成為一道不可忽視的風景。“對肉體的重要性的重新發現已經成為新近的激進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寶貴的成就之一。”對身體的欣賞,尤其是對女體的欣賞,成了作家用身體言說故事的一種妙門。通俗者,容易把“身體”引入肉欲縱流的漩渦里而失之穢褻;高雅者,喜歡將“身體”并入色空觀念的奧旨中而失于玄想。身體是敘事的媒介,并非敘事的歸宿,文學作品中身體更是如此。“我們的活動總是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的統一。雖然諸如吃、喝等行為通常僅僅被歸結為身體性的,然而,它們卻滲透著社會的、認知的和審美的意義。”這些文學性的身體,附著作家的價值取向、哲學思考與審美塑造,而對于穢褻與玄想之間的“過渡帶”的把握,則取決于作家對身體意義的詮釋與申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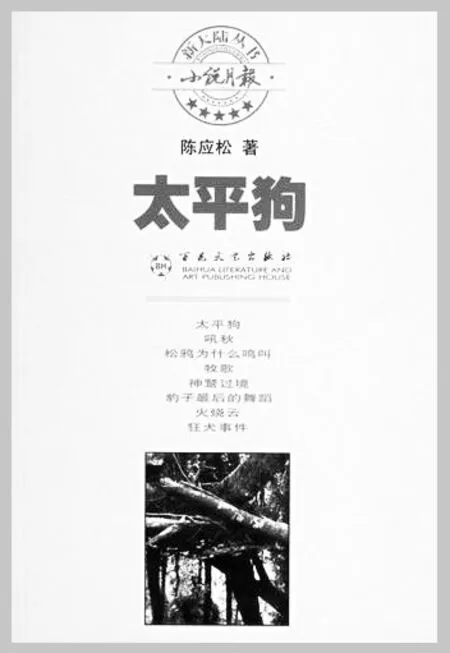
《太平狗》
與以往偏重于女體敘事不同的是,新世紀以來,出現了很多以男體敘事為構架的小說作品和文學形象,陳應松《太平狗》中的程大種,熊育群《無巢》中的郭運盼,鬼子《被雨淋濕的河》中的曉雷,無不袒露著男體敘事的覺醒與決心。《叔叔的沙漠》也是男體敘事中的一員,而金成海身體敘事的焦點則是叔的“體毛”。
叔的體毛,遺傳了爺爺的優良基因:“爺爺從臉上的硬扎扎的連腮胡到胸口那嚇煞巴人的胸毛,直竄到肚臍。”爺爺的體毛,成了“我”對雄壯男人的第一印象。白寡婦“油脂般潔白圓滑的身子趴在我爺爺那健壯的軀體上”時,最愛撥弄的就是爺爺的“胸毛”,而爺爺這條“青龍”沒有被“白虎”克死,也從側面十分滑稽地證明了爺爺生命力的旺盛。進而,這幅以身體(特別是胸毛)構成的春宮圖,被迫地促成了爺爺與叔之間微妙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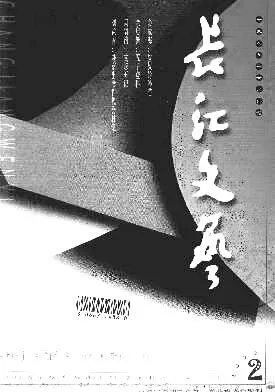
《叔叔的沙漠》原載《長江文藝》2002年第2期
叔想上河灘時,嘴巴上的絨毛是“漸黑漸粗”的。當叔上了河灘之時,“我”發現叔“從臍下往上直通胸膛已經有了淡稀的胸毛”(雪白的屁股,發育完全超過我的下體),這些都標志著叔已經成為一個“準男子漢”。而叔叉腰眺望遠方的情景,和這青春萌動的身體一起構成了叔對美好將來的憧憬。這是一個發育良好的身體,是一個不諳世事的身體,是一個敢想敢錯的身體。“身體并不滿足于肉體所給予的空間體積范圍,它通過想象、欲望、情感和意志,將自己延伸到物質性空間之外,試圖占有一切象征性的空間。”在接下來的時光里,叔用他略顯稚嫩的“準男子漢”的身軀,去構想、去設計、去搭建他的理想空間。
叔擁有了河灘的所有權后,他可以在他的河灘上大顯身手。這時的叔,“胡子硬了長了,與鬢角連在一起”,還有“不算太濃的胸毛”,“腿上的汗毛密密的”(尖尖的喉結,硬硬的、有繭的、粗糙的手,滿是抬頭紋的額頭,充滿血絲的眼睛,赤裸的上身,碩大的男性器官),這是旺盛的生命在瘋狂地生長,這是理想的版圖在肆意地擴張。在接下來的時光里,叔用他男子漢的身軀,去刨取豐收的喜悅,去哀嘆上蒼的無常,去詛咒時代的吊詭。在曲折而螺旋上升的路軌上,叔的身軀除了流血、流汗,更多地是付出了樸素而又異于常人的智慧,而這聰慧的神經元就像叔身上愈發濃密的體毛一樣,在翻滾的時代浪潮中,時而被風吹倒,匍匐于地;時而迎風微漾,高歌于空。
叔擁有了“江漢集團”之后,尤其是集團陷入經營窘境之后,叔“那淡淡的胸毛已變得濃密密的”,“可惜有些已白了”。這是一具看遍人世繁華、閱盡浮世滄桑的身軀,多少有了一些波瀾不驚、寵辱偕忘的狡黠。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又似乎不在他的掌握之下。“江漢集團”“虧損二十多萬”的現實,并沒能扭轉叔的舊式思維,反而變本加厲地將錯就錯。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當現代化的困境汩汩而來之時,除了放任自流,叔別無他法。當一個“土夫子”“渴望得到社會的承認”的夢想,居然是在誤打誤撞、鋌而走險之中實現時,“我”才大夢方醒,叔“只不過是一個小人物啊”!一個被時代洪流裹挾得左沖右撞的“小人物”。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巨大潮汐中,這些小人物,在漲潮之時,解離故土,魚躍成龍;在退潮之時,惜別城市,打回原形。而那蒼白的不只是叔的胸毛,更多的則是無所適從的落寞與世道蒼黃的無奈。
這漸變的體毛描繪了叔大半生的奮斗軌跡,它見證了叔身體的萌動、強壯與衰微。這個身體不僅為家族血脈而生,更多地則是為了發動時代的巨輪而生。“人們被其所處環境的不同要素吸引或排斥,這往往是一種頗具感官性和體認性的事情。但正是這些反應,而不僅僅是看似‘非具身性’的智識評估,為社會系統的維護、發展和轉化提供了基本的動力。”正如叔為了保護每況愈下的S-2號肉鴨——致富鴨亦或是政績鴨——而“用肩膀把即將傾斜的棚頂扛住”,身體也“一軟躺在雨地里”,最終卻賠了八百多塊一樣,無數個身體,無數個類似叔的身體,匍匐摔倒在歷史的河岸邊,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追趕時代的巨輪。少數人上了船,意氣風發,從此一帆風順;多數人則被甩回岸邊,精神委頓,從此銷聲匿跡。
傳奇敘事
鄉土空間之中,總會有一些奇聞異事流淌到作家的血液中,而中國敘事文學傳統中,尚“奇”的理念,先天就存在于作家的文學基因里。傳奇敘事就在這樣的循流中應運而生。金成海先生的傳奇敘事,既有明清傳奇小說的精神滋養,又有現當代創業史詩的珠玉盈澤。在傳統的語境中生發人生如夢的亙古長嘆,在現代的語境中揣度精神還鄉的終極旨歸。正如英國學者所言:“所有優秀的小說都必須帶有傳奇的一些特質。小說創造一個首尾連貫的幻影:它創造一個引人入勝的想象的世界,這個世界由詳細的情節組成,以暗示理想的強烈程度為人們領悟;它靠作家的主觀想象支撐。就最普遍和持久的層次而言,也許這樣理解現實小說更為準確,它是傳奇的變種而不是取代了傳奇。”
第一,叔的奮斗史。
叔的奮斗史,亦可稱為“叔的傳奇”。沈從文先生在《水云》一文中說:“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動人的傳奇……再無什么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樂得失經驗更加離奇動人。”此話用在叔身上再合適不過。70年代初,叔靠在河灘上打牛草賣給生產隊而賺了300塊錢;70年代后期,叔擁有河灘后,靠賣西瓜賺了600多塊錢,而秋天的一場大水沖走了叔的所有收成;于是,叔開始販牛,冒著投機倒把的風險,成了縣里最年輕的萬元戶,由于超生和坐吃山空,最終存款降至三位數;隨著市場經濟的開始,叔經營起了“致富鴨”,由于摸不清市場經濟規律,不但血本無歸,還倒賠了800塊錢;于是叔操起了自己的本行,以比市場價低15%的價格購進一批ST-1號肉牛,此時還是還不起欠鄉農技站的30000塊錢的S-2肉鴨飼料錢;后來,叔“以他的沙漠和現有的牛、資產占了60%的股份”成了“王家灣養殖總公司”的總經理,成了農民企業家和縣人大代表;隨著“組建企業的‘航空母艦’”的風行,“王家灣養殖總公司”更名為“漢江集團”,叔依舊是老總,是一手遮天、專權獨斷的老總,后來集團虧損20多萬并最終倒閉,叔不但失去了全部財產,還倒貼了幾萬,最終只剩下100頭牛陪著精神異常的叔,回到他夢想開始的地方。這是平凡人的創業傳奇,更是當代農民的創業史詩。這個形象具有普適性,這個故事也有代表性。
第二,駝子點化叔。
駝子本身就是個傳奇,他也曾經“受過高人指點,滿腹牛經馬道”。生平最重信義,為朋友的官司豪擲重金。他知道叔胸毛的走向,更知道叔前天夜里“跑過馬”。“他能叫你一夜成名,也能叫你片刻功夫名聲掃地”。這是傳奇敘事的第一步,點化者頗有來歷。
駝子和叔約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我講的事兒要咽到肚子里,不許傳給別人”。在駝子“傾盡了自己的平生所學之后”,他便在這個星球上消失了,“就像仙人一樣只有其名沒有其人”,只留下一個八角銅錢作為信物。叔也認為這個駝子“是上天在冥冥之中派來點化自己的”。而正是這駝子的點化,幫助了叔平安的度過了兩次重要的人生轉折。這是傳奇敘事的第二步,被點化者不許泄露天機。
駝子還傳授給叔“一個樸素的人生哲學道理”。他認為,一個成功的人,首先自己要做好人,其次要會認人,“知足就是個好人,不知足就是個小人”。他重義,信奉“錢是用的,水是流的”,切記一個貪字,“更不可坑蒙拐騙”,總之要知足常樂。這是傳奇敘事的第三步,點化者給被點化者一些必要的啟示,大多是業報輪回之苦、棄惡從善之念、貪戀知足之嗔以及修身養性之法等。
當叔歷經半生繾綣最終跌入人生谷底之時,卻在縣城的街上遇見了一個賣老鼠藥駝背老人,而這時的駝子已經不認得叔了。叔在被精神失常的駝子冷落之后,自己的精神也陷入了凌亂中,“時而狂笑,時而傻笑”。最終集團倒閉了,留給叔的只有一百頭牛,叔又回到了沙漠,脖子上仍然掛著那個八角銅錢,“一切都恢復了原樣”。這是傳奇敘事的第四步,被點化者歷經人間磨難,最終參透點化者當初的話語玄機,抒發人生如夢之慨嘆。
這個故事剛好印證了那句“身后有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的古話。“似夢?似鬧劇?反正一切都恢復了原樣”,這是作者的嘆息,與其說是在嘆息叔叔的人乖命舛,倒不如說是在嘆息生命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滄海一粟之感。這是人生的無常與歷史的無常相互齟齬的產物,“無常感體現在面對歷史的恢弘與循環,人們的渺小之感也應運而生”。叔叔從沙漠發家,并最終回到沙漠,這是一種循環,是一種天理人欲糾纏其中的循環。駝子的“天理”是知足常樂,叔叔的“人欲”是步步高升。當世間的一切早已如過眼煙云之時,誰還會記得自己當初那卑微的初心。為時已晚后,才發現那個被我們棄之如敝履的初心是多么的難能可貴,但畢竟為時已晚。這正是: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劉小楓先生在《敘事與倫理》一文中認為,現代的敘事倫理可分為兩種,即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在人民倫理的大敘事中,歷史的沉重腳步夾帶個人生命,敘事呢喃看起來圍繞個人命運,實際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只是個體生命的嘆息或想象,某一個人活過的生命痕跡或經歷的人生變故。自由倫理不是某些歷史圣哲設立的戒律或某個國家化的道德憲法設定的生存規范構成的,而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偶在個體的生活事件構成的。
雖然叔這具“沉重的肉身”以“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出現在作品當中,但是這“具體的偶在個體”卻承載了作家“人民倫理的大敘事”的某些意圖。文本中行文的暗線便是刻意模糊的歷史敘事,正是作家的這種障眼法導致了“鄉土敘事”與“身體敘事”的某些乖離。身體所追求的,鄉土不能給予;鄉土所承載的,身體偏要突破。當二者不能圓融之時,作家找到了破解此類迷關的屢試不爽的萬能解藥——傳奇敘事,讓人生如夢、萬境歸空的佛理道境出面調和,輪回與無常之感讓文本的宿命論色彩漸次激升。而這種所謂的“宿命”,與其說是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的最終告饒,倒不如說是人民倫理的大敘事的漣漪猶在。
作家不是歷史學家,更不是攝影師,他不能把有限的時空記憶轉化成直觀可感的觀瞻之物。作家能做到的只能是在有限的文本空間內,去訴說自己的關切與耳語。我們從來不是真正的歷史學家,我們總是一部分的詩人,我們的情感或許只能用逝去的詩歌來翻譯。”而這“逝去的詩歌”便是作家在“精神還鄉”的路上淺吟低唱的禮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