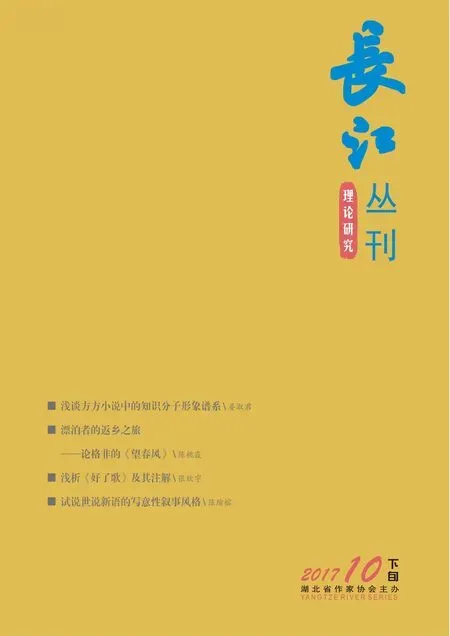淺論新世紀中國文學生產的影視化轉型
李幸雪 張 丹 王澤伊
淺論新世紀中國文學生產的影視化轉型
李幸雪 張 丹 王澤伊
“文學生產”這一概念由馬克思提出,“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只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到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這一概念是工業革命之后復雜的社會環境催生的,本文所論及的“文學生產”是指以新世紀市場語境為基礎的文學文本創作過程。在市場語境下,文學生產的影視化轉型主要表現為生產的圖像化、集體化、類型化。
一、文學生產的圖像化
文學生產的圖像化指文學主動向影視文學靠攏,越來越貼近影視的制作模式,文學創作者在創作文本時往往有意無意地運用影視化的因素,考慮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劇的可能性。影視化因素滲入文學致使文學文本開始呈現圖像化的特點,主要包括圖像化場景、圖像化結構和圖像化人物三個方面。
1、圖像化場景
影視劇由連續的場景變換構成,受到影視劇的影響,文學文本也會不自覺地呈現出一種“銀屏意識”, 讓文字呈現出強烈的視覺沖擊感,將文本中的場景寫得“可拍”。著名作家嚴歌苓就曾提到影視元素對創作的影響力:“電影只會讓你的文字更具色彩,更出畫面,更有動感,這也是我這么多年的寫作生涯中一直所努力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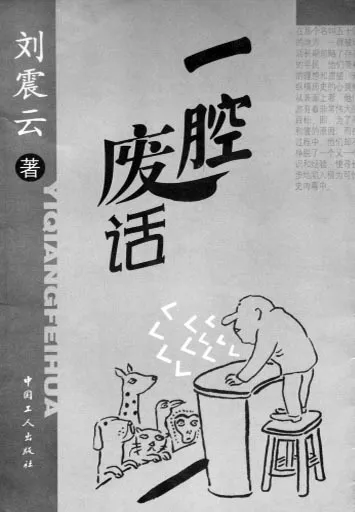
《一腔廢話》
以當下熱門的《人民的名義》為例,作者周梅森此前擔任過多部政治劇的編劇,熟知影視改編的過程和重點,因此在創作該文本時也有意無意地放入了很多利于影視改編的圖像化場景,例如在貪官趙德漢被查出豪宅中私藏巨額贓款的場景中,描寫趙德漢貪污的贓款時,沒有用數字一筆帶過,而是將巨大數額轉換成可見的具體實物進行描寫:“一捆捆新舊程度不一的鈔票……構成一道密不透風的鈔票墻壁。”這樣的圖像化描寫給讀者帶來的是視覺上的震撼。而描寫趙德漢即將被帶走的情景時,“求”、“轉悠”、“撲”、“痛哭”“顫抖”等一連串的動作描寫生動形象地刻畫出了趙德漢的形象和被揭穿的心理。類似的圖像化場景描寫也大量出現在各類網絡小說中,如《法醫秦明》、《余罪》等懸疑推理類小說著重描寫疑點重重的案發現場,蛛絲馬跡都在作者筆下;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幻城》、《花千骨》、《武動乾坤》、《誅仙》等仙俠玄幻小說,一方面致力于塑造虛擬奇特的幻境,在讀者腦海中營造出一個新的具象的可觀的世界,另一方面描寫大量一氣呵成的打斗場面,使用大量動詞將人物的每一個動作都描述得清晰可辨,從而增加文本的視覺沖突和閱讀快感。
2、圖像化結構
小說和影視兩種藝術手法在敘事結構上存在明顯差異,米蘭·昆德拉曾指出“小說的結構原則是時間,電影的結構原則是空間,”兩者的結構存在著抽象感知和具象感知的區別,隨著影視影響力的擴大,很多小說選擇使用畫面性的空間結構,其中,蒙太奇的手法追求結構組織上的跳躍性和多變性,成為影響大部分文學作品,尤其是網絡文學作品敘事策略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作家選擇獨立的圖像化場景進行拼接,營造出不同的觀看效果。
例如劉震云的小說《一腔廢話》,整個故事由用畫面感強烈的空間結構構建而成。小說目錄一改傳統小說所采用的章節分段方法,而改為“第一場”、“第二場”,具有明顯的影視文學特征,同時以“五十街西里”、“模仿秀”、“辯論賽”等畫面感強烈又相對獨立的空間場景命名章節。畢飛宇的小說《推拿》則是以 “王大夫”、“沙復明”、“小孔”等主要人物來劃分章節,不同的人物有各自的出場場景,主要人物的轉換必定伴隨著空間場景的轉換,不同的相關故事也在變換的場景中發展。人物的圖像化的場景單元,又都與盲人推拿的生活相對應,小說便圖像化地展示了“盲人”這一群體的生活世界,若干個相對獨立的單元交織成圖像化的空間網絡結構。但網絡小說呈現的圖像化結構則多為時空轉換,《爵跡》中“黑暗洞穴”“黃金湖泊”“霧隱綠島”等章節的命名顯然是以空間場景轉換劃分,體現出典型的影視文學分場設計,《匆匆那年》《致青春》《左耳》等青春類小說則插入回憶單元,用青春時期畫面與現實生活畫面的切換增加視覺上和情感上的強烈對比。正如張邦衛在《大眾傳媒與審美嬗變:傳媒語境中新世紀文學的轉型研究》一書中所說:“新世紀的小說與劇本寫作總是首先設定一系列的具有故事性、視覺性的單元、片段和場景。”。
3、圖像化人物
傳統文學作品中,不同讀者對人物的想象具有差異性,正所謂“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隨著文學生產的影視化轉型,部分文學作品開始出現大量畫面化人物形象,注重人物外貌描寫,用泛濫的人物對話、連續的動作描寫、華麗的環境渲染取代細膩的心理刻畫,用細致入微的細節描寫將文本人物形象具象化,使讀者看文本就能預見具體的畫面。
劉震云的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于2016年被搬上熒屏,其小說原作,具有明顯的影視化創作傾向。例如,小說通過大量的人物對話塑造了多個人物形象,從高級官員到底層民眾,對話占據了主要篇幅,并使用較多表現力較強的方言土語,很大程度上貼近了影視文學的對話體。不得不說,小說有刻意使用對話塑造影視所需圖像化人物的嫌疑,與電影改編的成功和小說的影視化寫作不無關系。畫面化的人物形象在網絡小說中則更為常見,集過度的外貌描寫、動作描寫、環境描寫于一身。例如郭敬明的《爵跡》、《幻城》,不僅寫到人物的面色、發色、著裝、手中道具、聲音等多個細節,并用大量具象比喻來修飾,“像冰雪”、“像云一般”、“像水晶”等隨處可見。在類似作品中,作者往往塑造出一個個預置影像化的人物形象,甚至提前考慮到了影視劇中從遠景到中景再到特寫的拍攝順序。
文學的圖像化生產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小說文本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圖像化場景、圖像化結構和圖像化人物為文學與影視的聯姻提供了便利,迎合了消費者的口味。同時,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又反作用于文學生產,促使文學生產在圖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二、文學生產的集體化
集體化生產是文學生產轉型的主要特征之一。所謂集體化生產,指的是文學作品的生產由作家的獨立創作轉變為由作家和出版社編輯、影視劇導演和編劇等人的集體創作,文學作品成為根據受眾需求而集體打造的文化商品。簡言之,文學的生產傳播過程由傳統的“作家→文本→讀者”轉變為“導演/編劇/編輯+作家→文本→媒介→讀者”的新模式。
在大眾傳媒時代的政治經濟學語境下,社會關注度和個人關注度都被轉換成了能夠利用來創造財富的稀缺性資源。這種“注意力經濟”使文學生產者不得不以讀者的興趣需求為首要生產動機,以此創造生產出合乎大眾需求的文學作品。報社、出版社編輯、影視集團制作人、導演、編劇等文化產業從業者深諳潛在讀者群的閱讀需求,因此作為“原始生產者”,憑借對市場需求的敏銳捕捉能力,為作家提供大致的創作主題,甚至是搭建大致的文本結構框架。作家作為“主要生產者”,運用自己的寫作能力往框架中填充內容,當作品大致成型后,再交由專業的編輯或編劇進行二度包裝加工,將文學作品打造成最符合大眾審美潮流的最終產品,由此形成了一條清晰的“原始生產者→主要生產者→產品加工者”的“文學生產流水線”。這一集體化生產模式已成為較普遍的文學新現象。
文學生產集體化的例子不勝枚舉。新世紀初,王朔在《我看王朔》一文中承認:“《無人喝彩》應該說是王朔和李少紅、英達共同創作的,那是一次有關電影劇本的合作,后來李少紅覺得不理想,放棄了,王朔就腆著臉把劇本連綴成小說,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了,轉手又賣給夏剛一道。”2010年以來,隨著青春文學、網絡文學等通俗文學的發展,文學的集體化創作更為明顯。應湖南衛視相親欄目《我們約會吧》制片方之邀,郭敬明與自己公司的其他五位作家一同進行了小說《丘比特來電》的創作,并作為小說進行網絡連載,最后由湖南衛視改編為電影《我們約會吧》上映;網絡作家八月長安應《被偷走的那五年》電影導演之邀,按照電影劇本創作同名小說,與電影同時出版發行。這些為影視作品量身定制的文學作品不再是傳統的作家出于個人靈感的創作,而是按照市場規律和受眾需求而生產的文化商品,是文學與影視聯姻后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一類文學創作中,作家不是唯一的創作者,而是置身于文化產業生產鏈其中的一環,僅需要完成自己的文學創作部分,文學作品的剩余價值則由其他生產者進一步加工挖掘。
這種集體參與的文學生產模式是對傳統文學創作的重大沖擊與改變。“原始生產者命題→主要生產者創作→后期生產者包裝”的近似流水線作業的文學生產模式,一方面能夠為作家省去命題立意與組織架構的過程,但同時也會使作家根據影視需要重塑小說語言,進行文字的取舍、改編和再創造。由此來看,這種生產模式雖具有較廣的受眾群體,在文學市場上倍受歡迎,但其是否真正具有恒久流傳的文學價值,仍有待商榷。
三、文學生產的類型化
在市場語境下,文學與影視聯姻意味著文學被納入“文學-影視-出版”這一多向互動的文化產品生產線,為了便于批量生產和復制,也為了以特定文化標簽吸引消費者,這類文化商品往往具有類型化的生產模式。例如,電影市場有喜劇、冒險、戰爭、幻想、恐怖、驚悚、懸疑、科幻、劇情、愛情、犯罪等分類,與電影的程式相對應,為了適應影視改編的需要,文學的生產也存在類型化傾向,在通俗文學寫作中尤為明顯。
白樺主編的《中國文情報告(2009-2010)》認為“類型在崛起”是2009年文壇的四大焦點之一,并將類型小說歸為“架空/穿越(歷史)、武俠/仙俠、……青春成長”等十類,這十種文學類型涵蓋了近十年被搬上熒屏的絕大多數作品。同一類型文學和影視作品扎堆的現象不僅是為了迎合受眾的喜好,更是類型化生產模式下“流水線定制文學”的結果。路金波曾公開承認,他公司旗下的寫手郭妮署名的青春小說是專門針對12-16歲“戀愛前期女生”市場流水線定制的產物,這一流水線“將一本書設定為可拆卸的三大情節、十二個小故事,任何一個故事都可以替換。”這些類型化的文學作品針對目標受眾而量身打造,遵循商業規律而非文學自身規律,內容趨于模式化而缺乏作家個人思想,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市場語境下文學話語權的出讓。
文學本是作家表達觀點、施展才華的空間,作家的創造力使文學生生不息,是文學保持獨立性的根本,但是在影視類型化生產模式的影響下,文學為了適應文化市場規律而陷入程式化寫作,這勢必造成文學的危機。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一文中認為,電影的“機械復制”丟失了藝術作品的“靈韻”,文學為迎合“機械復制”而進行的類型化生產同樣是導致“靈韻”喪失的關鍵。類型化的小說大大降低了文學創作的難度,同時也迎合了影視改編市場的需要,但就文學本身而言,類型化的批量生產也扼殺了作品的“靈韻”,使之徹底成為文化生產流水線的商品而喪失“文學性”。
表面上,文學生產的類型化是順應影視改編需要的結果,但究其根本,更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大眾文化的繁榮,也興起了“快餐式”文化消費,正是這一“麥當勞化”的社會文化環境催生了類型化的文學生產。正如葛紅兵所說:“新世紀以后經濟市場化的深入發展帶來了社會的階層化,社會的階層化導致了文學審美趣味的階層化,審美趣味的階層分化便使得小說創作類型化了。”一方面,文學生產的類型化適應于大眾文化趣味的分層,是服務文學受眾的需要,另一方面,類型化的批量生產也損害了文學自身的原創性與生命力,成為“快餐式”文化生產流水線上商品。如何找到市場化與文學性之間的平衡點,是市場語境下文學生產轉型過程中的當務之急。
新世紀,中國文學正處于文學市場化的時代,在市場語境下,文學的存在方式不再是純文學的單一維度,而是處于傳播學、社會文化學、經濟學等眾多學科的交叉視閾下。媒介的融合一方面為文學插上了通向千家萬戶的“翅膀”,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文學自身界限的日益模糊。雖然文學生產的影視化轉型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文學的危機,但是在市場語境下,這一趨勢也是文學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求生存,謀發展”的表現,體現出新的文化消費趨勢對文學生產的反作用和文學自身的積極調整與應對。通過這一影視化轉型,文學能更好地適應影視改編的需要,從而以大眾媒介為載體,擴大文學的受眾面,增強文學的影響力;也能更好地在文化市場中尋求立足之地,從而以切實利益支持作家的文學創作,為文學的前進提供物質動力。但是,如何在向影視靠攏的同時保持文學自身的獨立性,是關系到文學發展的重大命題。文學的獨立性作為存在的根基必須予以保護,保持作家創作的獨立性和作品的文學性,才能使文學之樹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