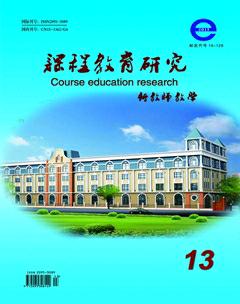關于高中語文閱讀教學的幾點思考
余春林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指出:“閱讀教學是學生、教師、教科書編者、文本之間的多重對話,是思想碰撞和心靈交流的動態過程。”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陳暉也曾說:“應將閱讀教學適當轉化為在閱讀中不斷探索和發現的過程。”因此,在閱讀教學中,我們應倡導“自主探究”的學習模式,推動學生在閱讀中不斷探索和發現,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閱讀體會和經驗,并與同學、老師交流溝通,實現“思想碰撞”和“心靈交流”。
一 調動學生的閱讀期待,使閱讀成為一個主動探究的過程
走近學生,你會發現不少學生普遍對語文教材甚至語文讀本有排斥心理。學生不愿意閱讀或難以靜下心來閱讀教材中的文本,這往往會使閱讀教學成為無效教學。因此必須調動學生的閱讀期待,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如何調動學生的閱讀期待呢?如何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呢?首先,教師在選擇閱讀篇目時要有針對性,充分了解學生的閱讀水平以及喜好,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們的閱讀趣味。例如在教授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3》第一單元時,幾乎所有學生在魯迅的《祝福》與海明威《老人與海》之間選擇了海明威的文章,要求在課堂上學習《老人與海》,在課外自學《祝福》。 我尊重了學生的選擇。(雖然自己對《祝福》體會更深,也更容易把握。)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如果我們有機會有能力尊重學生的興趣,可以盡力而為。其次,在學生閱讀未知作品之前,我們對其興趣的調動也很重要。例如在教授新課時,要重視“課堂導入”這一工作。恰當的“課堂導入”,可以把文本與學生的生命體驗或者以往的知識經驗相聯系,讓他們產生解決自己苦痛的愿望,或者產生共鳴,從而使其產生強烈的閱讀期望。例如,我在教授人教版高中語文教材五冊《人是什么》這一課文時,就做了如此的導入工作:“雨果曾說,我們都是罪人,我們都被判了死刑,只是都有一個不確定的緩刑期而已。我們是否也有過這樣的感覺?是否也曾懷疑否定自己的人生?人生的意義何在?生命的價值何在?我想,這樣的問題困擾過雨果困擾過哥德,也一定困擾過你我。或許,學過趙鑫珊的《人是什么》這篇課文,她會給我們一些幫助與啟示。”這樣導入,使文本與學生的個體生命體驗相聯系,或許能夠很好地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二 給學生自主閱讀的機會,使學生完成原始閱讀
傳統的閱讀教學喜歡在學生閱讀文本之前介紹文本作者,寫作背景以及作者寫作風格等。這種做法往往使得學生失去了原始閱讀、自主閱讀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的閱讀一開始變帶上了教師的閱讀痕跡、思想痕跡,難有自我真實干凈的閱讀,所以這些做法違背了閱讀的基本規律。遵循閱讀的基本規律,學生在沒有外來干擾因素下的對文本的第一次閱讀——原始閱讀(也就是現在廣泛受到關注的“裸讀”),學生對文本的原始理解,才應是我們閱讀教學的最初點。教師應提供給學生沒有干擾的外在與內在的環境,保障學生能擁有獨立的自我閱讀過程與感受。一千個讀者便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更何況“老師這個讀者”與“學生這個讀者”,大都有著不少的年齡差,閱讀體會自然會有很大差異。所以我們不能先入為主,一定要清楚學生的閱讀體驗。記得我曾經要求學生在課堂自主閱讀魯迅的《傷逝》,在采訪同學的閱讀感受時,有同學就說:“我同意魯迅的視角和觀點,愛情、生活、現實確實都很殘酷,需要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和責任心。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對愛情和生活還是應該抱著希望啊……。”聽到他勇敢地說出最后一句,我猛然發現了十五歲的高一學生的閱讀能力,以及他們對生活的美好訴求。所以,后邊我對本文的教學與引導都是在尊重他的觀點基礎上進行的。了解,才會促成理解。
三 了解學生的閱讀體驗,尊重學生的閱讀體驗,還要豐富升華學生對文本的原始理解
“新課標”強調教師要“珍視學生的獨特的感受、體驗和理解”。只有尊重學生的個性化的閱讀感受,才能保護學生探究的積極性,才能使語文教學充滿生命的活力。但是,閱讀教學不能停留于原始理解,還應幫助學生有后續理解。首先,在學生有了初步的感知與理解的基礎上,老師此時可介紹作者的寫作風格以及寫作背景等,適當地知人論世,可以幫助學生更深刻更準確地把握到作者的本意,增加學生理解的深度。其次,老師還可介紹自己獨到的理解或者專家學者的理解,最終使學生增加自己的閱讀廣度。
閱讀最需要的是體驗、理解,更需要思維能力的培養。在平日的閱讀教學中,我們可能更容易給學生灌輸一些閱讀技巧。比如如何讀懂文章的技巧,如何篩選信息的技巧,卻沒有關注應該有怎樣的思維過程。曾經有一位老師用兩個課時上完《紫藤蘿瀑布》。期間用大量的精力來討論探究作者表現了怎樣的思想情感,花很多時間讓學生在文章中篩選出能夠表現贊頌生命力的文字。下課后卻又有好幾個學生向教師發問“紫藤蘿瀑布到底是什么?”我想這就涉及到思維過程的問題。感知,應是思維的第一過程。學生應該仔細閱讀了描寫紫藤蘿瀑布的文字之后,有了對紫藤蘿的生動準確的感知之后,才能循序漸進地去感受文字的情感和思想之美。所以,在閱讀教學中,想要升華學生的原始閱讀,就要尊重思維規律,訓練學生思維方式,提升學生思維水平。
有人曾提出語文有八種思維模式:分解,突顯,聯系聯想,想象,立象,抽象(立意),對比,類比。這幾種思維模式我們可以運用于我們的寫作中。相反,我們在深切掌握了這幾種思維模式之后,也能幫助我們更加有力、更加清晰地閱讀別人的作品;借助這幾種思維模式,也能升華學生的閱讀。
對比這種思維模式,我們就常常需要在閱讀中使用。例如我們在解讀汪曾祺的《受戒》的 時候,可以與沈從文的《邊城》相比較,你就會很清晰地發現他們似乎在訴說著同樣的東西:夢是對現實的逃避,更是對未來的期盼。夢,意味著心靈未死,希望猶存。又例如你若將蘇軾的《赤壁賦》中的生命意識、哲學觀與蘇軾所受濡染的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相對比,或許你就能更多的理解“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這些句子的內涵。如若你能將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與清教徒文化相對比,或許你就會明白作者他不只是在訴說夢想而已。因此,掌握并靈活運用幾種思維模式,有助于我們更深層次地解讀文本。
如果說作家寫作是在“立象”的話,那么我們的閱讀就是在“抽象”。在立象與抽象的閱讀過程中,我們需要給學生的是:時間、尊重、獨立的閱讀、平等的交流、思維的碰撞、思維模式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