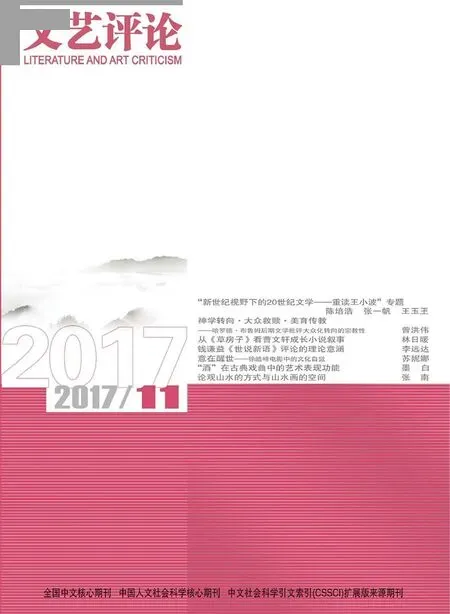隱喻、民族情懷與小說改編
——以日韓中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為例
○沈嘉達 沈思涵
隱喻、民族情懷與小說改編
——以日韓中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為例
○沈嘉達 沈思涵
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韓國,與中國文化具有天然的共通性。就影視界來說,中韓合拍、韓日翻拍、中日影視改編等文化融通,已經是不爭的事實。2005年,日本著名推理小說作家東野圭吾創作的長篇推理小說(也是其“神探伽利略系列”的第三部)《嫌疑人X的獻身》正式出版,隨即摘得“這本小說了不起”“本格推理小說Top 10“”周刊文藝推理小說Top 10”三大推理小說排行榜年度總冠軍。其后,由西谷弘導演,福田靖編劇,福山雅治、柴崎幸、堤真一、松雪泰子、北村一輝等主演的同名懸疑劇情片于2008年10月4日在日本上映,并獲得第32屆日本電影學院獎之話題獎、最具話題影片獎和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之最佳亞洲電影提名獎。2012年10月18日,由方恩珍執導,柳承范、李瑤媛、趙鎮雄主演的《嫌疑人X》正式在韓國上映,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影片獲得了“第49屆百想藝術大賞”,趙鎮雄、李瑤媛分獲“電影類最佳人氣男演員”和“電影類最佳人氣女演員”榮譽。好的東西總會讓人分享,同樣根據東野圭吾小說改編,由蘇有朋執導,王凱、張魯一、林心如、葉祖新等主演的《嫌疑人X的獻身》于2017年3月31日在中國大陸上映。該片是東野圭吾推理小說首度在中國影像化的成果,一時間見仁見智,眾說紛紜。
一
電影是光影藝術,同時也是文學藝術。就一般意義上說,一部成功的電影,一定要講好民族故事,表現好主題和人物。那些有意營造氛圍、淡化主題和人物的實驗類作品另當別論。
東野圭吾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中的人物其實非常有限:中學數學老師石神哲哉,鄰居花岡靖子及其女兒花岡美里,靖子前夫富堅慎二,再就是警察草薙、岸谷和大學物理副教授湯川學。小說敘寫花岡靖子用電線勒死了好賭輕薄的前夫富堅,暗戀花岡的石神老師幫她設下各種計策,應對警察草薙的盤問。然而,湯川學經過層層推理,最終揭開石神殺死流浪漢救助花岡的“案中謎案”。
本文將通過分析比較日韓中三國電影的人物設置,揭開其背后的深層意味。
日版電影可以說非常忠實于原著。改變之處就在于草薙的助手由男伙伴岸谷變成了女同事內海。表面上看,不經人事的內海警察的出現,一是可以因其不斷向湯川請教而連接起推理線索鏈,進一步陪襯湯川的“神探伽利略”本色;二是年輕漂亮的內海本身也成了吸引青年受眾的亮點。實際上,觀眾對日版電影的人物改編給予了充分肯定。
韓版電影別具特色。東野圭吾在回答韓國媒體的采訪時就明確地講:“電影里沒有物理學家,本來原作里面有犯人和警官,原作中與罪犯屬于朋友關系的物理學家(湯川)作為偵探介入(時)十分煩惱,而這部電影里沒有這種感覺。但是,警察有按照自己的思路來抓住犯人,人物表現非常果敢,電影沒有不流暢的地方。”①具體地說,就是將原小說中警察草薙和大學物理副教授湯川的角色統一到“趙警官”身上。其結果正如東野圭吾所言:一是“沒有”了“屬于朋友關系”的“十分煩惱”的“感覺”;二是,警察變得“非常果敢”,能夠“按照自己的思路來抓住犯人”。整部影片故事顯得更加緊湊,線索更加集中,情節推進更快更流暢。
中版電影重回老路又略作改變。原小說中可以置身事外的大學物理副教授湯川,變成了江城警察學院的副教授(也是省公安廳高級顧問)唐川;日版電影中的女警察內海變成了男警官羅淼。這樣做的好處便是:唐川置身案件之中并主導破案,是一種匡扶正義的“職業行為”,更加符合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
既然是根據原小說改編,且沒有要違背原作的意愿,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原作者東野圭吾的創作“意圖”。眾所周知,《嫌疑人X的獻身》發生的背景,正值20世紀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②。其時,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社會矛盾尖銳,政權更迭頻繁,民眾冷漠不堪,社會情緒處于焦慮糾結之中。正因為如此,東野圭吾才一而再再而三強調其小說“意圖”:“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帶給讀者更多的東西,比如人性的獨白,比如社會的炎涼。我想,這些東西是人類永遠需要關注的命題,因此不存在‘過氣’的危險。創作者應該通過作品,表達自己的思想,努力去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好,而不是僅僅局限于語言的游戲或其它一些東西。這是一個作家的責任,不僅僅是推理作家應該這樣做。如果一部作品和社會沒有發生任何關系,我實在不敢想象這是一部怎樣的作品。”③平心而論,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如此受到日本社會的推崇,除了小說本身的精細推理,更重要的無疑是作者很好地表達了這個“失去的十年”的時代情懷,引發了廣大受眾的普遍共鳴。我們甚至可以將東野圭吾的小說主題歸納為一點,就是“慰藉卑微者飽受死亡威脅的心靈”。“卑微者”何以產生如此感受?曰:現代化所帶來的工具理性至上、精神焦慮和生存的無意義感。正因為如此,在東野圭吾的多部小說尤其是“神探伽利略”系列小說中,其反對工具理性的現代價值觀非常突出。這與重視敘寫“官商勾結、民族矛盾”的社會推理派小說家松本清張絕然不同。
就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講,石神為何要上吊自殺?因為處于“失去的十年”的他,是一個除了對數學感興趣對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感冒的“數學怪物”。而剛搬到隔壁居住的花岡靖子,以其“笑顏如花”和“總是能為他帶來新鮮氣氛的聲音”,點燃了石神幾近枯竭的生命之火。正因為如此,石神才會殺死無辜的流浪漢制造假象,也為自己死心塌地為花岡頂罪心安理得。請注意,這個“數學怪物”石神,對湯川頑強揭開殺人案謎底也不以為然:“就算揭露了案件真相,也沒有人會感到幸福。”在一個工具理性社會里,用冷酷的理性揭開僅有的溫情面紗,雖然破解了案件之謎,但卻喪失了一段人間最美的真情。這到底是簡單的“得”還是徹底的“失”?
基于以上原理,東野圭吾在原長篇小說中(實際上也是多部小說中),并不是讓專司其責的警察本身來破獲案件,而是將其職能轉移到并無直接關系的大學物理副教授湯川學身上。這里似乎有一個問題:難道作者肯定湯川學嗎?否!其深層含義或者說作為一個“隱喻”,在日本同名電影中得到了真實的體現——如前所述,內海警探作為女性能夠吸引年輕觀眾,能夠起到讓案件推理登堂入室的作用,但別忘記還有一個其實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利用內海對高大英俊、精明冷血的湯川學的一廂情愿愛戀,來實現作者的“反諷”意味:盡管湯川學通過理性推斷,破譯了石神“密碼”,但是湯川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內海的溫情,隱喻的是整個日本社會的工具理性屬性。湯川這樣的工具理性主義者,就是下一個石神。他與石神的區別,只不過一個教數學,一個搞物理;一個殺人,一個找出殺人者而已。
現在,我們再回到韓版電影,會發現故事流暢、線索單純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應有的深層意味。湯川對石神復雜感情的表現(這與日本民族性格是相吻合的)和內海擔負的“反諷”職能無法得以落實。人物的簡化,帶來的是意味的淡化。而中版電影也沒有在人物設置上達到日版高度,不客氣地說,蘇有朋根本就沒有理解東野圭吾對“失去的十年”所抱有的悲憫情懷,更談不上有所提升了。
二
《嫌疑人X的獻身》是東野圭吾本格推理小說的巔峰之作,這里,我們自然要論及“本格推理”。所謂“本格推理”,是與“變格推理”相對而言的。1926年,甲賀三郎提出“本格”和“變格”概念,將推理小說區分為“以推理解謎為主”和“以變態心理、離奇事件為主來展現意外性”兩大類。前者強調的就是推理的邏輯性、公平性。而就敘事本身來說,本格派推理小說往往一開始就明確顯示案件兇手,然后,再由湯川學一類人物通過細枝末節和精密思維,推斷出事件原委。譬如東野圭吾的《紅手指》,一開始就寫到前原昭夫被妻子八重子急電告知,兒子直巳殺害了一名女童。接著便是前原昭夫苦思冥想、絞盡腦汁設計騙局企圖讓兒子逃脫懲罰。東野圭吾的《信》也是剛開篇就敘述哥哥剛志為了籌足弟弟學費,入室盜竊,失手殺死曾對自己有恩的老太太。《彷徨之刃》中,女兒繪摩被伴崎和菅野加害,一開篇就和盤托出,并不向讀者隱瞞。《嫌疑人X的獻身》同樣走的是本格推理之路。在第二章就寫到,花岡靖子前夫富堅慎二暗夜向花岡索要錢財并侮辱母女,花岡母女無奈殺死了這個無賴。可以見出,本格推理小說完全不是中國偵探小說“曲終奏雅”套路,諸如先發現一具尸體,然后按圖索驥,逐步深入,最終撥云見霧找到真兇。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東野圭吾及其日本同名電影中,一開始警察草薙就死死認定花岡母女有重大殺人嫌疑,而置其他可能的嫌疑人于不顧。其后,故事也緊緊圍繞花岡母女展開。假若在中國,這只能是一出煙幕戲——貌似真兇只能說明最終不是元兇。這里,我們需要明白的是,本格推理的倫理是:富有邏輯性和公平性的推理本身才是重點,而不是其他。就是說,小說或電影只需要將“本格推理”的“邏輯性”和“公平性”表現精當就行,而不需要考慮這種對花岡母女殺人的“論斷”是不是簡單和武斷。當然,明白這個道理,并不等于在電影觀賞時就能夠完全接受這樣的敘事過程。畢竟,電影藝術不等于小說藝術,電影的直觀性欣賞特征需要導演做出更多的鋪墊。正是基于此,日版電影中,導演有意增加了富堅慎二賭場借錢600萬被人追殺,因此變身無賴向已經成為便當店店長的花岡靖子勒索這一橋段。(小說只是簡單提及一句:“富堅長年挪用公款東窗事發,遭到公司開除。”)這樣設置好處有二:一是讓觀眾更加同情花岡母女,更加憎惡富堅;二是更能夠理解花岡靖子殺死富堅的行為,因為從前的陪酒女花岡好不容易做了店長,有了穩定的生活,因此備加珍惜,而不愿失去,從而才會鋌而走險,沖動殺人。電影對小說的改編,已被日本民眾完全接受。
韓版電影雖然也注意尊崇本格推理原則,但整部電影充滿韓式風格:煽情、暖色調、偶像派人物等等。譬如日本和中國電影都將殺人者設置為“母女關系”,而韓國則安排為小姨和外甥女。筆者臆測,如果是母女關系,母親必然因年齡和經濟限制,顯得蒼老和窘迫,不如置換為小姨和外甥女,則都可以鮮活靚麗形象示人。再如男主角,原小說是這樣描寫石神的:“他是個高中老師。他體型矮壯,臉也很圓、很大,可是眼睛卻細得像條縫。頭發短而稀薄,因此看起來將近五十歲,不過實際上可能比較年輕。似乎不太在意穿著打扮,總是穿著同樣的衣服。”請注意,這就是一個未老先衰、機械無趣的中學數學老師形象。可是,韓版電影男主角飾演者柳承范本質上仍是一位英俊小生。東野圭吾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講到:“原作的主人公‘石神’其貌不揚,這也許是他拒絕戀愛的原因。但是電影里面的‘石固’的外貌是比‘石神’更帥,所以不用解釋他心里的微妙的復雜情緒。”④由此可見,偏離了作者既定原型。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曾對白花善(即花岡靖子)有過幫助、白花善對之抱有好感的風度翩翩的南泰宇的出現,卻贏得了觀眾稱道。一方面是韓式電影偶像人物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也很好地詮釋了白花善的愛戀心理,畢竟,南泰宇有錢有地位能保護母女,又英俊瀟灑吸引女性。這個橋段的設計,便很自然地導向石固(即石神)的妒忌,繼而寫匿名信威脅母女,讓白花善錯誤認為石固是“變態”從而苦悶不已,甚至主動獻身以求解脫。當然,最根本的還在于,所有這一切都反襯了石固對白花善深沉的愛:即便受到誤解,即便明知愛情無望,即便曾經給予自己新生的白花善現在要“殘酷”地剝奪掉自己的生之意志,石固仍然堅定地為白花善殺死路人,以求自己定下心來為白花善頂罪。正如金石固自述:“這不是我的腦子,是我的心(在做)。”顯而易見,韓版電影的情節改編,既沿襲了原作本格推理模式,又體現了大韓民族的固有屬性和審美趣味。
蘇有朋是如何改編的呢?據報道,制片方在電影公映前夕公布了東野圭吾的來信:“今天的中國已是世界電影的堂堂大國,我的作品《嫌疑人X的獻身》能在中國拍成電影上映,真是不勝榮幸。感謝各位的努力。看到才華橫溢的你們沒有拘泥于原著,而是富于創造性的改編,我感到欣慰而有趣,非常期待能早日看到你們的作品。”⑤誠如所言,中版電影進行了“富于創造性的改編”。譬如,沒有一開始就交代陳靖母女(即花岡母女)被迫殺人一事,而是采用倒敘視角,雖然出現了受害人傅堅,但并沒有馬上轉入殺人場景。只是在完成倒敘之后,才與原小說同步,進行推理破案。何以做出如此改變?道理很簡單。中國觀眾不太習慣東野圭吾模式,而日本觀眾卻習以為常。早在20世紀20年代,江戶川亂步發表《兩分錢銅幣》之后,推理小說便開始在日本文壇大行其道。本格派、社會派、新本格派逐次上演,已經在日本有著深厚的受眾基礎和很高的閱讀期待。“韓國雖然沒有成熟的推理小說的文化體系,但推理懸疑類電影已是韓國電影一種重要的類型,觀眾在各種推理形式的接受上有豐富的經驗。”⑥因此,韓版電影沿襲了日版路徑。
具體地說,蘇有朋版電影將日本社會特有的“矛盾心理”(也就是東野圭吾所言的“心里的微妙的復雜情緒”)予以淡化,將原小說中本格推理(其實是“人情和人性之理”)簡化為中國式傳統影視中習以為常的“正義與邪惡之爭”。尤其是最終王凱飾演的警察唐川猛地推開緊閉的大門走向充滿陽光的外面世界,象征著唐川走向新的生活(光明的尾巴)。筆者以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蘇有朋之所以獲得贊譽,就在于作為正義化身的江城警察學院副教授唐川運用細節推演出最終兇犯,滿足了中國觀眾“正義戰勝邪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傳統情懷。那么,“敗”在何方?蘇有朋為投合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和民族情懷,一味強化唐川作為正義方之“精明”(讓唐川對石泓的手表進行水分檢測等),肆意敘寫石泓之“惡”(讓石泓買兇打人,偷走江城警察學院實驗室定向聲波發射器,干擾唐川破案等)。觀影的感受就是:狐貍再狡猾,也逃不過獵人的眼睛。然而,這已經偏離了原小說固有的意圖:關注小人物情感,關注“失去的十年”日本民族特有的優柔心理。我們不免發問:這還是東野圭吾的作品意味嗎?
三
小說成為影視資源現在已經成為常識。然而,成功地將小說改編為經典影視卻是難以企求的夢想。張藝謀當年去粗取精,準確把握莫言“紅高粱系列”小說中的“自由”精神,將土匪余占鰲、不守婦道的農村婦女戴鳳蓮演化為高揚生命活力的民族精靈,將“種的退化”經由“我是我自己的,我對我自己的行為負責”推舉到抗日救亡高度,從而拯救了原小說,也建構起自身的電影高地。其后,蘇童的很容易被看作是彌漫著江南頹廢氣息的“舊式鴛鴦蝴蝶小說”《妻妾成群》,被張藝謀點石成金為“民族劣根性”批判主題,化蛹成蝶。我們可以說,將小說改編成影視絕對不是對原作的簡單影像化再現,而是對原著精髓的提純升華。這里,有態度問題,也有能力、方法問題,更有認知、思維問題。
現在,我們平心靜氣地看待中版電影,我們可不可以講,蘇有朋的電影其實就是“借他人之酒杯裝自己之塊壘”?為什么人們會批評蘇有朋版電影林心如情感演繹缺乏沖擊力?為什么批評王凱是現代小生?為什么認為中版電影沒有東野圭吾小說的原味?不是演員不努力,而是因為導演主旨改變了。蘇有朋的“沒有拘泥于原著”,其實就是脫離了原著。至于韓版,電影原名就叫《完美的愛情》,演繹的重點自然是“愛情”本身,延續的還是一貫的情感路線。
這讓筆者想起曾經做過的跨文化比較研究。為什么河正宇根據余華《許三觀賣血記》煞費苦心拍攝的情感大片《許三觀》,并不能在中國獲得廣大受眾的認可?走情感路線就能成功嗎?未必。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進一步說,電影似乎是為表現親情而專門設置許家的災禍與不幸,沒有上升到張藝謀《活著》那樣的形而上高度。退而求其次,我們也可以拋開原小說中的一些‘束縛’而專注于韓國現實,譬如以親情來對抗已經高度市場經濟化了的韓國社會,或者在電影中設置親情與理性之間的難以調解的矛盾從而引發人們的主動思考,再或者引入外來文化以顯示親情的民族根性等。但是,電影《許三觀》走的是一條最簡潔的路徑,使用的是最單純的招數,尤其是影片結尾的大團圓結局和許三觀的‘這簡直是完美’(最后吃魚場景)的感嘆,完全消解了電影中本就稀薄的悲憫感,而顯示出比較陳舊的套路來。”⑦這就是問題的根本。
還有一個不成功的案例,就是馮小剛根據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改編成電影《1942》。就筆者看來,走煽情路線的馮小剛,盡管電影中也點綴著劉氏冷幽默,但“從小說到電影,從小說作者劉震云到電影導演馮小剛,不僅僅是載體和主導者的轉換,更多的是內蘊的流變和思想的衰減”,“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沒有貫穿始終的人物,也沒有作為主線的敘事線索,有的,是作者對人物命運的沉思和中華民族歷史的反省,是對統治者的反諷和對時代的警惕。然而,電影《1942》讓我們重新回到傳統電影的‘苦大仇深’時代,回到正統路線上去。那就是范東家的由富人到災民的淪落,由花枝、栓柱、瞎鹿等人的命運引發觀者對蔣介石統治的同仇敵愾,故事催人淚下,情節層層逼進,而電影離小說是漸行漸遠了”⑧。放棄思想,摒棄深度,也不能成功。
筆者想說的是,在一個碎片化、表象化的時代,如何拍出有深度的電影?確實值得認真思量。當王全安將陳忠實的《白鹿原》拍攝成“一個女人和幾個男人的風花雪月故事”的時候,難道我們不應該反省?劉醒龍花費6年時間、寫垮3臺電腦、光廢棄文字就達20萬言的百萬字長篇小說《圣天門口》,是以理念的深邃而特立獨行的。“在處理歷史事實時一個值得充分肯定之處,則正在于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一種外在的意識形態的規限與控制。相對于‘革命歷史小說’而言,在更大程度上盡可能地逼近了歷史的本相。”⑨卻被張黎拍攝成了完全不顧現實主義尊嚴、漏洞百出的“革命歷史傳奇”!迎合世俗,討好大眾,讓人欲哭無淚。
那么,到底該如何進行影視改編呢?這顯然是一個令許多人“頭疼”不已的問題。筆者也無法提供一個“規范”的答案。只能說——原則上講,它應該處理好以下幾對關系:一是意識形態訴求與影視本身的藝術規律之間的關系,二是小說與影視作為獨立門類本身各自的藝術屬性之間的關系,三是國別受眾的欣賞習慣與原作旨趣的關系。尤其是跨國改編,更應該慎之又慎。也許,好萊塢電影《花木蘭》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電影《花木蘭》取材于中國民間樂府《木蘭辭》,很好地保留了詩歌中的精髓——木蘭代父從軍故事,將對父之“孝”與對國之“忠”有機結合,由中華民族的家庭倫理延展為世界性的普世價值,能夠引發國際認同;同時,作為兒童動畫片,導演又增加了心地善良、樂觀豁達的“木須龍(Mushu)”形象(“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電影音樂也使用了多種東方樂器,采用了許多中國旋律。一句話,電影既弘揚了中華民族精神,又開掘出新的受眾“興趣點”;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這樣的改編方能稱得上是成功嘗試。
我們期待發現更多的成功轉換路徑。
①④懸疑巨匠東野圭吾稱被韓版《嫌疑人X》吸引[DB/OL],http://ent.sina.com.cn/m/f/k/2012-10-15/15153763942.shtml新浪娛樂,2012年10月15日。
②日本在上個世紀“二戰”之后曾以超快的經濟增長獨領世界經濟風騷。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平均增長速度僅為1.2%,淪落為發達國家之最低水準。是以被稱作“失去的十年”。
③李黎《東野圭吾:人性的暗夜》[N],《經濟觀察報》,2011年6月10日。
⑤蘇有朋獲東野圭吾認可觀眾盛贊《嫌疑人X的獻身》[DB/OL],http://movie.67.com/hyzx/2017/03/24/871804_2.html中國娛樂網,2017年3月24日。
⑥羅琳《〈嫌疑人X的獻身〉:推理的消解》[J],《電影藝術》,2017年第3期。
⑦沈嘉達,沈思涵《小說與電影:“許三觀賣血記”比較研究》[J],《武漢廣播影視》,2015年第12期。
⑧沈嘉達《模式、意義與當代小說之影視改編》[J],《新文學評論》,2016年第4期。
⑨王春林《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消解與重構——評劉醒龍長篇小說〈圣天門口〉[J],《小說評論》,2005年第6期。
(作者單位:黃岡師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 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