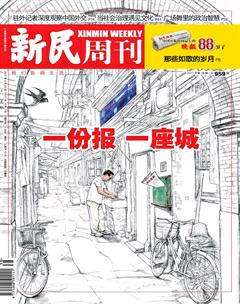當社會治理遇見文化
金姬+王仲昀
文化介入治理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過程,高舉高打的強力進入,收效也許適得其反。用心觀察、冷靜分析、且行且思、順勢而為,這是閔行案例留給我們的思考。
唱唱跳跳有地方;
唱唱跳跳有平臺;
唱唱跳跳有提升;
唱唱跳跳聚人心。
從呼應市民基本文化需求切入,政府職能部門拓展陣地、搭建平臺、創設機制,到今天普通的市民文化團隊文化素養獲得提升,溢出參與社會治理,這是近5年來,上海市閔行區公共文化建設留下的四個堅實腳印。
歷史選擇了閔行
自2014年上海市委啟動一號課題“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調研以來,滬上基層社會治理進入改革高潮。對于上海這樣的特大型城市而言,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社會治理的好抓手——從2013年起,上海連續舉辦覆蓋全市、貫穿全年的市民文化節。每年舉辦的5萬項多形式、廣覆蓋、高質量的各類文化活動和賽事,吸引了2400萬人次積極參與,文化的力量潤物無聲。4年來,公共文化活動吸引著眾多的市民參與。他們參與到社區自治中來,對社區和城市產生更多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新行者”的上海究竟如何用文化方式助推社會治理創新?位于上海地域腹部的閔行可能最有發言權。
一方面,閔行具有歷史悠久、內涵豐厚的文化資源,生動演繹著“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上海城市精神。
閔行作為行政區只有25年的時間,但它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馬橋文化。有專家認為,閔行馬橋文化與青浦崧澤文化和松江廣富林文化如同“滬”字的三點水,共同創造了上海古文化的輝煌。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高蒙河指出:“馬橋文化既是遠古上海走出歷史低谷的起點,也是遠古上海開始向近現代國際大城市攀援上升的原點。馬橋文化開放、多元文化的融合特征,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代上海城市精神‘海納百川的源頭。”
1000年的江南文化,在閔行積淀了豐富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七寶老街、召稼樓老街、朱行老街、曹行老街、顓橋老街、荷巷橋老街、杜行老街等江南古鎮老街文化資源,為現代城市發展預留了彌足珍貴的人文空間;而馬橋手獅舞、顓橋剪紙、七寶皮影戲、莘莊鉤針編結、民族樂器制作等,則傳承著閔行人的心靈手巧和精湛技藝。
近代社會以來,西方文化登陸,為處于上海近郊的閔行帶來開放的情懷,時尚的生活,更豐富了閔行歷史文化資源。新中國成立后,在黃浦江邊的老閔行地區,先后建立了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電機廠、上海鍋爐廠和上海重型機器廠,被稱為新中國現代重工業領域的“四大金剛”。現如今,在原先“四大金剛”的附近就有上海交通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等多所高校新校區,通過打破高校與社區、產業園區之間的隔閡,謀求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文化新局面。
另一方面,閔行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的發展不僅有歷史文化的先天條件,更有“天時地利”的后來優勢——2015年,上海市政府為了推進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社會化、專業化管理,開始在全市4個區試點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閔行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擁有253萬常住人口的行政區,在“十二五”期間就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方面不斷創新。據統計,“十二五”期間,閔行區累計新增公共文化設施5.51萬平方米;每年開展“百千萬”文化資源配送服務,包括100場“高雅藝術進社區”、500期文化培訓講座、2000場公益流動電影、4000份報紙雜志進社區、20000場數字電影進社區等。
文化活動平臺不斷豐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在區級層面,“十二五”期間的成果包括2014年的閔行區藝術節、兩年一屆的“金秋閔行”上海合唱節(2011、2013、2015),每年開展的上海浦江滬劇節、市民廣場舞大賽、四大民俗節慶活動、“金秋閔行”市民文化節、全區創作節目匯演、“激情閔行”社區文藝大聯演等。
而在鎮級層面,則突出活動全民性和本地區特點,開展了諸如“流動的魅力”系列活動、“我要上村晚”“文化天天樂”“炫梅隴”市民才藝秀等特色活動。全區現有群眾文化團隊1200多支,年均組織各類活動20000余場次,年均參與文化活動人數達400多萬人次。
文化這棵參天大樹,在閔行的土地上枝繁葉茂。
螺螄殼里做道場
在這一組組漂亮數字的背后,是閔行區對于文化服務體系的思考及探索。閔行區始終將“文化惠民”作為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更多的市民享受到看得見、摸得著、用得上的文化服務。對此,閔行區文廣局局長楊繼楨給《新民周刊》打了一個比方:“我們提供的文化服務不能像一個盆景,老百姓只能遠觀;而是如同一個公園,每個人都能走進去并成為景觀的一部分。”
為了讓更多的閔行人享受到“文化大餐”,閔行的文化干部們可謂煞費苦心。
一方面,要讓有限的文化產品送給最需要的人。區社會文化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專門跑了閔行區14個街鎮摸底,發現以往的文化產品供需并不匹配。“敬老院里的老人要看電影,但沒人去放;而我們在文化活動中心放的電影卻沒人看,因為年輕人都去電影院看大片了。”楊繼楨舉例。
另一方面,閔行區摸索出來一套“空間換服務”的成功經驗。“有些文化設施,如果政府來管理,可能每天只能利用8小時。如果這一帶老百姓的需求是16小時,但是我們不可能找到更多的場所了,怎么辦?”區群眾藝術館的一名干部介紹了他們的做法,“我們可以引入第三方管理,讓這個場所至少可以每天利用12小時,這樣也能解決一部分老百姓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把效能提高到最大,彌補公共服務不足。”endprint
“空間換服務”的想法,被最終的實踐效果證明是一個很好的構想。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終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對此,楊繼楨感觸很深:“政府不能應景、作秀、做概念,心里要裝著老百姓。搞文化服務,考慮的是領導喜歡嗎?會給我加分嗎?其實,我們要想明白到底為誰服務?我們現在搞的項目,如文化客堂間和城市書房,老百姓實實在在感受到了,他們會為你叫好。我想我的同事們會感到欣慰,因為我們為老百姓做了點實事。”
對于閔行區而言,“文化客堂間”和“城市書房”也是一種“無中生有”的公共文化服務。“文化需求不像醫療、教育那樣剛性、顯性,就目前的能力看,政府提供的設施和產品只能是一個基本的保障。因此,我們做了一些激活社會存量的工作。”楊繼楨以“客堂間”為例,這一空間本來就存在,是村里面的集體資產,原來是農民舉辦紅白喜事和聚會的場所。“但是這一空間不可能天天喝喜酒或者吃豆腐飯,閑暇時間就可以騰出來給我們作為文化場地來用,這就是‘無中生有。”
再以“城市書房”為例,現在很多實體書店生存艱難,但是也有一些商圈希望開設圖書館來提升文化品位,集聚人氣。“我們有幾家城市書房,都是人家商圈拿最好的門面房出來裝修,而政府稍微補貼一點就行。”楊繼楨表示。
“城市書房”采用政府、圖書館與企事業單位等第三方社會力量合作共建模式,引入24小時無人值守、讀者自我管理與志愿者自治管理相結合的運營模式,效應頗佳。
讓廣大市民唱主角
多年與群眾文化工作打交道的楊繼楨發現,以前的文藝演出都是政府請專業團隊過來演出,雖然節目質量高,但是礙于經費有限,每年能讓老百姓看得到的“高雅藝術”很有限。那么,如果“政府搭臺、群眾唱戲”行不行?不曾想,這個簡單的想法,一下子就點燃了閔行區全體群眾的文藝熱情。
楊繼楨以連續舉辦四年的浦江滬劇節為例。“閔行有很多人喜歡聽滬劇,但是這些滬劇迷可能沒地方去聽,有些人想唱兩句都沒有合適的活動平臺可以參與。5年前,我們先考慮把那些喜歡唱滬劇的人搬上電視節目,PK一下,拿出來大家比比看,看能否吸引人進來。結果一比火爆得不得了,場場爆滿。有一次晚上11點,我去比賽現場的時候發現整個場子里面座無虛席。第二年,我們就專心打造一個滬劇活動的平臺。我們跟街鎮聯手,把市里面相應的大賽資源引進來,活動品牌引進來,這就形成了浦江滬劇節。一屆一屆辦下來越做越好,現在其他區縣的人慕名而來,這也成為閔行區的一個文化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閔行區打造的這些文化品牌活動不是一次性,而是貫穿全年,讓老百姓時時刻刻都能參與進來。楊繼楨指出,“以往請來專業團隊演出,看完就結束了。而我們的這些文化節有一個過程,叫‘訓、賽、秀,群眾先參與培訓,水平提升了,就想表現一下,參加一下比賽。這樣既解決了一個文化素養提升的問題,又盡可能讓群眾更多地參與到文化活動中來。”
品牌的形成很多時候就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楊繼楨認為,“文化大餐不是說一年只吃三餐就結束了,而是天天要吃的。”閔行區文廣局更多是在營造良性的群眾文化生態圈。
可喜的是,經過努力,群眾參與的文化產品,水平也愈來愈高,甚至可以走出國門參與國際文化交流。
2017年2月,閔行區組織區內優秀鼓樂團隊、表演團隊、非遺展示團隊、書畫展示團隊、特色小吃團隊等41人赴日本參加“2017日本新潟春節祭”, 受到了新潟民眾的熱烈追捧。在閔行美食面前,日本民眾大排長龍,不論男女老幼直呼好吃,同樣,在春節祭開幕式上閔行演出的節目也令人耳目一新,鼓樂、變臉、魔術等表演令臺下日本民眾嘖嘖稱奇。專程趕來參加開幕儀式的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致辭表示,兩年前他曾來到新潟出席首屆春節祭活動,這次來到新潟發現春節祭規模又有所擴大,場面更加紅火,新潟春節祭越辦越好,成為促進中日兩國的民間友好的重要平臺。
2017年8月,閔行區組織區內優秀鼓樂團隊、舞蹈團隊、民族器樂團隊、非遺展示團隊與書畫展示團隊等23人赴捷克順佩爾克市進行文化交流,在幾日內通過多場演出交流,在當地大獲好評。順佩爾克市市長茲德內克·布羅茲表示,一個2.7萬人口的小城市,差不多是閔行人口的百分之一 ,能邀請到閔行的藝術家們,非常榮幸。并稱贊閔行的藝術家們為他們帶來了“一場震撼人心的演出”。在行游表演時,順佩爾克市街道兩側的市民高呼著“China、China!”在每一個表演點,市民都用熱烈的掌聲歡呼著閔行藝術家們的到來,并要求與他們合影。
潤物細無聲
當閔行區愈來愈多的老百姓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優質公共文化服務時,政府也看到了這一“民心工程”的溢出效應——社會治理。
閔行區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工委于7月召開閔行區文體團隊參與社會治理情況調研座談會,與會的閔行區文體團隊紛紛認為能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對團隊本身的地位與發展有四方面的幫助——積極參與社區街鎮文藝演出、文藝指導活動,豐富社區文藝生活;積極參與社區公益活動,如拆違建教育、創全活動、安全警示教育、愛國衛生、助殘養老活動等;在內部管理方面不斷提高對團隊隊員的要求,如發揮團隊中黨員模范帶頭作用、鼓勵每個隊員配合街鎮社區治理工作(如創全、拆違建工作);根據身邊發生的故事,創作一些反映當前社區治理中難點問題的原創作品在社區演出,發揮群眾文藝對社區治理的正能量作用。
閔行區文廣局群文科負責人江莉莉給《新民周刊》舉了這樣一個例子:“馬橋鎮有個村,村里的一座橋上有違建,是當地兩戶人家造的。政府讓他們拆,對方很抵觸,就是不拆。由于當地居民很少,所以基本上都知道這件事情。馬橋鎮有一個文化沙龍小隊,就以這件事排了一出戲。我就問這個沙龍小隊,這是村委會下的任務嗎?他們說不是,只是自發的覺得好玩。村里有周周演,月月演,演出之后大家都看到了,那兩戶人家也慢慢改變了想法,違章最終順利拆除。文化團隊參與社會治理,很多時候是一個順勢而為的過程,因為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榮譽感。”
閔行區的群眾文化工作和社會治理結合得最好的例子是廣場舞,這也讓楊繼楨有了“大媽局長”的外號。“2013年,我們用一個政府實事工程的形式來改造了100個市民跳廣場舞的地方,這也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我們先從提供服務開始,你這個廣場燈不亮,我給你弄弄亮,地不平我給你整整平。我們提供一些活動的平臺,你跳好了我還有一些小獎勵、小刺激,市民覺得政府很想著我們,自我約束了,自己管自己了,這不是一個進步嗎?我們在推進的過程當中也碰到阻力的,大家不理解,你政府憑什么去做這個事情?你想想看,那么多人在跳廣場舞,弄得不好就會成為一個社會治理的難點和痛點。”
江莉莉也表示:“我們搞活動的時候接觸到很多阿姨。她們可能平時被貼上了‘廣場舞大媽這樣的標簽。但是她們很多人并不把自己定義為‘大媽。我們在工作中和她們接觸時,一方面肯定她們的專業素養,另一方面也盡可能提供社會的認同感。在設計一些活動的時候,因為資金有限,我們會去拉企業贊助,比如最開始會讓企業贊助某個比賽的部分獎金,后來經過協商,一些企業也會和我們合作,設置一些公益基金。這樣一個廣場舞團隊獲獎以后,不僅可以自己得到獎金,還能以團隊的名義給孤寡老人或者家庭困難者獻愛心。”
閔行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國榮了解到閔行區文廣局的做法后頗為贊賞,他表示,文化團隊參與社會治理,不能夠硬性要求他們去治理交通、搞衛生、掃馬路,文化團隊在參加各類活動當中的自治管理就是一種社會治理。“以前我們說日本市民素質很高,整個大草坪上參加活動后周圍干干凈凈,現在我們文化團隊參與活動后干干凈凈、井然有序,這個本身就是參與社會治理。”
文化應該滋養人的心靈。如果一個人西裝革履去劇場,跑出去卻隨地吐痰,這就是失敗。以浦江滬劇節為例,閔行觀眾愈來愈守秩序、懂規矩。以前很多人大聲喧嘩,臺上唱得好也不會鼓掌、喝彩。現在他們都懂得看戲不要影響別人,這就是進步。
事實上,文化介入治理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過程,高舉高打的強力進入,收效也許適得其反。用心觀察、冷靜分析、且行且思、順勢而為,這是閔行案例留給我們的思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