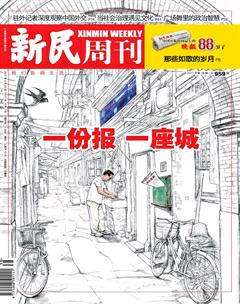致我們似是而非的生活
俞耕耘
這是一部感知之書,它復現再擬了生活的原本樣態:似是而非、夢醒交加,支離破碎。你能留下的唯有那點兒直感體驗。
從《空隙》《撫順故事集》再到《積木書》,作家趙松始終在追問一個問題:如何寫出異乎尋常的生活感知,形成一種私人的文字表達。《積木書》在某種程度上完成了這種內向性的自我書寫,作家甚至不太考慮他的理想讀者。因為作品本身會找到它的讀者。在故事中你會發現那些百感交集的生活因子:情緒、場境、氣味、光線和質感。這些直覺恰好拼合了凡俗人生的記憶紋路。你難以歸類它的文體,是像小說的散文詩,還是像短篇故事集的小長篇?
顯然,趙松有意游弋在各種文體邊緣,能確定的只有一點:它是敘事作品,是關于生活的印象寫生。《積木書》讓“非虛構”的標簽顯得無力,結集故事如雜糅的“閑譚”:有源于朋友的逸聞,新聞素材的加工,聽來的見聞,夢境的演繹,自身的心境。正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他延續了筆記體小說的傳統,一方面是化實為虛,以實寫虛的“寫實”,超出了現實主義慣常感知的陳詞濫調;另一面,那種簡淡卻沛然,洗練又豐饒的語言,亦是明清小品的氣味。
《天黑》再現了魏晉的名士范兒,是一次興之所至,興退而返的“訪友未遂”。《柔軟》就像槳聲燈影里的宴游,看似庸俗的老李反而能看清表象和本質的顛倒,顯出得魚忘筌的灑脫。手的柔軟比色相更為永恒。我很佩服作家淡遠文字中的醇厚理趣,像書法的枯筆,勾勒瑣事的干澀。《變化》和《舅舅》有生活的蒼老變易,《山》是向死而生的“煩”與焦慮,《狀態》是生活對自由的傾軋,精神的侵蝕。不同的是,故事又不失現代派的荒誕冷硬,幽默處生猛凌厲。《消息》是對世情的冷眼戲謔,《地平線》里誤解產生的滑稽段子,《交換》是對“觀念藝術”的冷嘲熱諷。
作家實踐了另一種“寫情境的”小說美學。人物面孔幻滅不清,成了無名符碼。時間成了封閉的虛空,空間則是沒有背景的淡入淡出,它們不再舉足輕重。你想捕捉的情節,可憐線索全都成了斷點,欲念浮動的光斑。能貫穿的,只是作品的氣味和調性:無以名狀的冷眼靜觀,疏離落寞(如《恐慌》)。正是這種感受蘊含了全書的隱喻所在。我們所謂的完整、富于意義的生活不過是拼湊起來的瞬間瑣屑:“積木”。它既可以搭建生活價值的幻覺,亦可推倒散落,一片瓦礫。生活與這作品一樣,讀法也暗合了活法,并沒什么“非此不可”。你可以任意拼接、易位、彌合生活的素材。然而,每個體驗瞬間、人物和故事又是拒絕敞開的唯一,如同被封存的“琥珀”,被賦予某種不可復現的永恒。
《積木書》利用了形式上的結構創造了敘事空間的無限可能。有點像中國古建營造中的“構件”和“模數”。每個故事就像一個建筑單元(構件),開篇用富于意味的省略號實現自由的榫接。有趣的是,趙松利用了“模數”,任意微縮、擴大著現實與藝術的“倍數關系”。
趙松也是這么“玩”小說的,他既有極微的視知覺,又有將瞬間延展放緩的擴張性。他能想象置身太空的宇宙感(《晚餐》),也會把巨大無比的城市比作“自然彎曲的綴了一些小燈泡的濕漉漉的粗繩子”,將生命周期視為禮花一樣“自然脫落”(《禮花》)。他對物性分析的迷戀往往化為抽象的感官,哲學的冥想,水珠凝結、雪花靜落皆可映現宇宙整體(《凝固》)。體驗的可能就在“空隙”里滋生蔓延,緩慢、出神、閃回,現實在他筆下就像被想象浸泡過的老報紙,充滿夢幻的褶皺印痕。
這是一部感知之書,它復現再擬了生活的原本樣態:似是而非、夢醒交加,支離破碎。你能留下的唯有那點兒直感體驗。趙松想做的就是實現“源初的捕獲”,用他深諳的生活技藝:幽微、簡淡、隔世蒼老的觀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