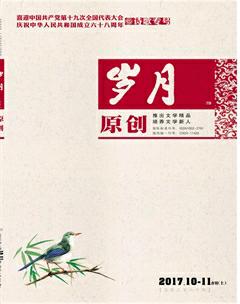《左傳·鄭伯克段于鄢》 杜注孔疏考異
劉娜++林賢
摘 要: 《鄭伯克段于鄢》為《左傳》中典型一文,杜預和孔穎達對該文都做出了較多的闡釋。通過對《鄭伯克段于鄢》杜注和孔疏的逐條對比和分析,可以發現孔穎達的正義有只申解傳文、只申解杜注和既申解傳文又闡述杜注三種類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疏不破注”的原則。在時代及自身的原因下,杜預注呈現簡約精當、敢于創見的特點。孔疏在堅持“疏不駁注”原則的基礎上,間接委婉地闡述自己的理解,論證資料詳備,但也有迂曲之嫌。
關鍵詞: 《左傳》 杜注 孔疏
《左傳》作為十三經中的巨著,因其出色的文筆和重大的學術價值,為歷代學者們所重視。早在漢代時,經學家如馬融、鄭玄、服虔等學者先后為《左傳》作注;魏晉時杜預“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簡稱“杜注”),對后世影響極大;唐時,孔穎達奉敕編修《五經正義》,作《春秋左傳正義》(簡稱“孔疏”),集合杜注及前人疏解自成一體,統一有唐一代解經方法;至清阮元主編《十三經注疏》,為《左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然考近代學者的研究著作,仍能發掘《左傳》杜注與孔疏的對讀研究尚有不足之處。
《鄭伯克段于鄢》是諸多文學作品選本中常見的一篇,其注疏數量及涵蓋范圍較為典型。本文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標點本)為底本,原文共分為35段注解,皆有杜注,16處有孔疏。杜注最多不超過60字,而孔疏字數最高為915字。無疏之注共有19處,共有三種類型。
一、《左傳·鄭伯克段于鄢》注疏
(一)孔疏只申解傳文。
以“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1]50為例,杜注為“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1]50。孔疏中只對傳文進行疏解:“謂武姜寐時生荘公,至寤始覺其生,故杜云‘寐寤而荘公已生。”[1]50遵從了杜預的觀點。《說文解字》釋“寤寐”:“寤,寐覺而有信曰寤,從 省,吾聲。一曰晝見而夜● 也。寐,臥也。從● 省,未聲。”[2]150“寤寐”的意思分別為睡覺和睡醒。孔穎達的說法與杜注一致,印證了孔穎達疏解傳文“疏不駁注”的原則。關于此條傳文的解讀,當今學界已經做出明確判斷,二人的說法皆誤。洪亮吉在解釋此條的時候說“是寤生始生即開目者”[3]184,亦誤。楊伯峻說:“寤生,杜《注》以為寤寐而生,誤。寤字當屬莊公言,乃‘牾之借字,寤生猶言逆生,現代謂之足先出。明焦竑《筆乘》早已言之,即《史記·鄭世家》所謂‘生之難。應劭謂生而開目能視曰寤生,則讀寤為悟,亦誤。其他異說尚多,皆不足信。”[4]10
此外,“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1]53應值得注意,杜預注為“公子呂,鄭大夫”[1]53。孔穎達解為“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1]53。杜預一從前文注解“祭仲”時的做法,只訓“公子呂”為何人。孔穎達在申解傳文時看到了“貳”字的重要性,“貳”與數字“二”不同,義為“兩屬”,即同時附屬于兩個統治者。這樣,對傳文的解讀就變得更加清晰。一方面,孔穎達對此條傳文的疏解可以理解為對杜注的補充。另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對杜注的反駁。杜注沒有達到清楚注解傳文的目的,孔穎達利用正義補充。
(二)孔疏只申解杜注。
這類注疏所占比重最大,共有九條,其中六條秉承“疏不駁注”的原則,對杜注進行了充分的闡釋。余下三條則有“疏駁杜注”之疑。有關“疏不駁注”,前人已有大量論述,此不再贅余。
雖說古代學者對于孔疏嚴格遵守“疏不駁注”原則已達成一致意見,但孔穎達作為一代大儒,對《左傳》有著深入見解。他在編修《春秋左傳正義》時完全采用杜預的注,并為之作疏,當杜注與自己的見解出現偏差時,他一方面盡力為之論證,另一方面采用曲折婉轉的辦法表達自己的看法,這就做到了“疏駁杜注”。試舉一例說明:
傳文“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1]56杜預注“賦”為“賦詩”,“融融”為“和樂”。孔穎達在疏解杜注的時候一方面竭力補充“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泄各自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泄泄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1]56。另一方面,他采用服虔的觀點“‘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1]56。指出莊公和姜氏兩人的賦詩應為互見之語,而杜注沒有說明,應為不足。這里還有一處值得注意的地方,即杜預注“賦”為“賦詩”中的“詩”的概念。根據當代學者研究成果,可以確信《左傳》中凡是提及“詩”的地方皆專指《詩經》。孔穎達在疏解杜注的時候將其理解為“自作詩也”,同時以唐人眼光分析詩歌的押韻情況,足見其受時代環境的影響。
(三)孔疏既解經傳,又申杜注。
這一部分在三種類型中所占比重最小,且孔穎達對經傳和杜注的說解都堅持“疏不駁注”的原則。例如傳文“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1]50。杜預注:“申國,今南陽宛縣。”[1]50杜預只對地理作了自己的判斷,孔穎達在正義中采用賈逵的觀點申解了“初”的含義,對杜注進行了一次補充。接下來便沿襲“疏不駁注”的做法,疏解“申國”的由來、“宛縣”的出處,與上文中“疏不駁注”原則下所舉例子的疏解方式完全相同。此外,“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與“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兩句的注疏亦與此同,不再贅述。
二、《左傳·鄭伯克段于鄢》注疏特點及成因
(一)杜注特點及成因。
魏晉南北朝時,南北經學分化。對于《左傳》的研究,北方大部分地區采用服虔的注解,而南方則多用杜注。有人曾說是因為杜預在晉朝地位顯赫,其學術影響力得益于他的政治勢力。這有一定的道理,但尚不完善。趙伯雄《春秋經傳講義》中說:“杜氏的《集解》成于他的晚年,書成后不久,杜預就死去了。要說《集解》的風行全靠作者的官勢,恐怕難以服人。”[6]186概括起來,杜注呈現出行文簡約而平實的優點,與魏晉南北朝史學繁榮的大趨勢不謀而合。endprint
批評者也看到了杜注的不足之處。杜預自稱有“《左傳》癖”,在注解《左傳》時,當經文與傳文不相符時,杜注常“疑經誤”。清人對杜注的批評達到頂峰。此外,關于杜預吸取前人成果而不標明姓氏出處的做法,后之學者頗有微詞,尤其到了清代,便評之為“攘善之病”。
杜注呈此特點的原因是,一方面,杜氏作《春秋經傳集解》時年歲已高,他自稱有“《左傳》癖”,無論《左傳》中的觀點是否對君主有損傷,他都如實注解。另一方面,他身處晉朝這樣一個剛剛經歷過三國分裂后的統一時代,儒家思想尚未占據統治地位。且此時佛教已經在國內廣為傳播,杜預能夠在注解中吸取佛教義疏的做法,以最簡約精當的文字完成注釋。
《春秋經傳集解》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盡管清人對其多有批評,但大量批評的同時也證明了杜注的重要地位。誠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所說:“《春秋》以《左傳》為根本,《左傳》以杜解為門徑。”[7]1-532
(二)孔疏的特點及成因。
從《春秋左傳正義》的內容來看,孔穎達尊杜說,主要堅持“疏不駁注”原則,將杜注的優點盡相承傳,不足之處也被放大了。正因其“疏不駁注”,招致后人諸多詬病。所謂“疏不駁注”,即是疏解前人傳注,完全遵從傳注觀點,即便有誤,也不加規正,反為之尋找證據證明。皮錫瑞說:“議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8]141他認為:“案著書之例,注不駁經,疏不駁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為病。讖緯多存古義,原本今文;雜引釋經,亦非巨謬。”[8]141按照皮錫瑞的觀點,“疏不駁注”只是當時的一種著書體例,“未足病”。皮氏為晚清著名今文經學家,能夠客觀評價孔疏,十分可貴。
事實上,孔疏中除了“疏不駁注”的部分外,還有一部分是破“杜注”的。究其原因,孔穎達是唐代大儒,對儒家經典著作有獨到的見解。此外,他能接觸到許多新材料和觀點,知識接觸面遠遠超越杜預,作疏時礙于要獨尊一家注解的疏解體例而將自己的觀點婉轉地打入到正義中,形成了如今的《春秋左傳正義》。客觀來說,孔穎達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杜預有著極大的不同。晉朝時,天下剛剛結束戰亂,中原與少數民族還處于對立狀態,君主專制統治尚未鞏固。唐朝時,孔穎達已身處盛世,國家統一,國力強盛,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成熟。統治者要統一思想,借編修《五經正義》汰除對自己不利的觀點,進而維護封建統治。所以孔穎達作正義時,特別警惕那些對統治者有危害的思想。觀之《春秋左傳正義》內容,雖已刪減大量繁雜的內容,但征引各家觀點,反復論證,顯得頗為迂曲。
綜上所述,本文在概述《左傳》及其注疏基本知識的基礎上,以《鄭伯克段于鄢》一文為例,逐條對比分析兩家注疏。得出杜注的特點是約簡精當,根源于杜預對《左傳》強烈的偏愛,漢儒豐碩的研究成果及當時外部學術環境的寬松和佛教的盛行;孔疏最大的特點是遵循“疏不駁注”的原則,獨尊杜預的注解。原因是孔穎達奉命編修《五經正義》,屬于官修經書的類型,言語必須符合統治者的意愿。但是作為一代大儒,孔穎達曲折地保持了一個學者的本分,在疏解杜注時遇到有疑問的部分將自己的觀點巧妙地表達了出來,做到了“疏駁杜注”。
參考文獻:
[1]李學勤.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漢]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3.
[3][清]洪亮吉.春秋左傳詁·隱公元年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7.
[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隱公元年[M].北京:中華書局,2009.
[5]李學勤.春秋左傳詁·隱公元年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7.
[6]趙伯雄.春秋經傳講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清]紀昀,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一[M].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8][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經學歷史·經學統一時代[M].北京:中華書局,20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