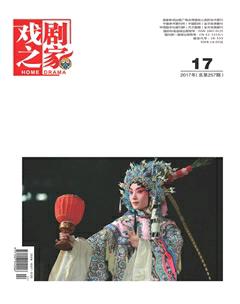鏡像中的自我追尋
趙彥彪
【摘 要】電影《茉莉花開》根據蘇童的中篇小說《婦女生活》改編,講述了一家三代單身女人的故事。電影中兩名演員飾演一家三代女人,一人分飾幾角所帶來的巧合、誤認的恍惚,無疑具有了鏡像隱喻的效果。除了三人相同的容貌,還有某種冥冥之中相似和輪回的命運——不幸的家庭、生育帶來的悲劇、被男人遺棄、獨自撫養女兒、欲望對象的缺失,這些都讓女性在這部電影里獲得了同一個符號屬性,某種意義上,成為一個人與一面鏡或一個夢的故事。三種不同的人生道路選擇,恰好對應拉康主體“三界”說,從而使影片中人物命運與哲學意義上的人類主體形成互動關系,構成了奇妙的映照。
【關鍵詞】《茉莉花開》;鏡像;拉康主體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17-0080-02
一、《茉》——鏡像中的主體想象
第一代主人公茉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影片序幕部分是一組俯拍,從她家經營的“匯隆照相館”的大牌子向下,經由掛滿相片的玻璃櫥窗,轉向主人公青春明麗的身影。可以說,茉成長的環境不是簡單的小市民家庭,而是一個由固態“影像”構成的世界。影片中出現的第一個場景即茉在電影院中全神貫注看著一部老上海電影,銀幕上是男女主角的調情場面。這個場景設置無疑具有深刻隱喻。電影院的銀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一面“鏡”,雖然不能映照出人們的物理真實,卻能成功制造一種混淆自我與他人、夢和現實的心理機制。這里的“鏡”借自拉康的“鏡像理論”,而由此衍生出的精神分析電影理論,正是建立在兩組類比之上的,即電影與夢、銀幕與鏡子。
克里斯蒂安·麥茨指出,電影的魅力極大得益于電影院的魅力。影院空間最大程度再現了鏡像階段:觀眾進入電影院,便意味著接受電影院的慣例,放棄自己的行動能力,只留下視覺觀看的動作。于是,觀眾返歸鏡像階段,聯系觀眾與銀幕世界的唯一途徑是目光。而銀幕上的故事與奇觀通過眼睛喚起凝視,我們由此成功避開象征秩序,進入幻想之中。觀影的快感在于,銀幕充當自我之鏡,隨時滿足自戀的觀看。我們看到,滿臉沉醉的茉雙目炯炯凝視著銀幕,即將擔起家庭責任、接受象征秩序法則的她,正沉溺于最后一場自戀的想象中。
茉失身于孟老板源于一個契機——孟老板將茉的照片登在了《良友》畫報的封面。與其說茉獻身于孟老板,不如說她獻身的是孟老板所代表的造夢機制,獻身的是對“自我”的理想化確認。她發現了畫報上的自己,一個光彩奪目、青春貌美的自己,一個完美的主體,也因此失去了對現實自我的掌控。接下來,茉改由中年演員陳沖扮演,有一個情節意味深長——女兒莉莉將男友鄒杰帶回家,茉夸他長得像電影演員高占非,后來就一直喊他“小高”,改不過口來。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意味的行為,高占非,作為20世紀40年代紅極一時的電影小生,代表著茉被埋藏的記憶和青春年華。對他的追憶,就是茉對曾經自己的緬懷。
而這種主體建構和“凝視”是分不開的,“凝視”不僅僅是主體他者的看,也是作為欲望對象他者對主體的回看,是二者的相互作用。因此,與其說凝視是主體對自身的一種認知和確認,不如說是主體向他者的欲望之網的一種淪陷。在電影里,貫穿茉一生的行動就是“凝視”。在她的眼睛深處,涂抹出了那幅畫面,而她自己也被那幅畫面捕獲。
茉沉浸在自己年少時代的幻想之中,在銀幕和畫報封面上獲得了預期的自我,而沉溺其中無法自拔。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年輕的茉不是遇到電影公司老板,不是選擇從事電影行業,而是遇到了比如說火柴大王之類的商人,她的命運也許會由此改變。即使她被拋棄,也能夠迅速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開始新的生活。她一生的悲劇,就在于沒有走出電影銀幕所構造的幻覺,沒有走出自我幻想。這種對鏡中形象的理想化確認終究不過是一種誤認,只能將她的自我引入欲望的不歸路。
二、《莉》——被異化的欲望
第二代女主人公是茉與孟老板的女兒——莉莉。她同樣成長于一個沒有父親的單親家庭。然而,與母親“攬鏡自照”的一生不同,自幼缺失愛與呵護的莉莉,一直徘徊于想象界與象征界之間,努力尋找自身的理想鏡像。
在拉康的理論中,通過想象界自戀式的幻想,主體產生了自我意識,并無可回避地被誘導到象征界,主體的認同對象也從鏡像階段的視覺實體(即小他者)轉為象征界抽象的文化結構和社會法則(大他者),因此,已被想象界虛幻影像誤導的人之主體,在象征界又一次遭受了符號秩序的異化。
如果說鏡像階段的第一代主人公茉停留在一種想象性認同,即“理想自我”,那么第二代主人公莉莉在象征界所追求的則是一種象征性認同,即“自我理想”。家庭讓她失望,她對母親的歷史深惡痛絕,試圖掙脫這種家族血脈的陰影,于是她向外尋找一個理想的自我。她愛上鄒杰,不是巧合,而恰恰是時代和她個人意志的必然。在籃球場上,鄒杰不是選手,而是裁判員,是秩序的裁定者。他準確優美的給分手勢讓場下的莉莉迷戀,甚至忘記了翻分數牌。在大會上,他的發言更是具有一種極大的感召力,“庭院不養千里馬,花盆難栽萬年松!同學們,讓我們把學到的本領用于實踐,到基層去,到車間去,到超英趕美的第一線去!出一身大汗,磨一手老繭,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貢獻我們壯麗的青春!”
可以說,從一開始,鄒杰就操著意識形態的話語出現在莉莉面前,而這種話語本質,就是一種符號化的象征結構。莉莉的主體就在這種符號秩序的詢喚中被建構了起來,她的愛,也不過是對這種先行的象征性概念的回應。她試圖擺脫母親沉溺一生的想象界,離開家庭,卻受到了外在象征界不動聲色的異化。
這種異化的極致就是莉莉對孩子的渴望,對自己患有不孕癥的絕望體驗。在原著中,莉莉對鄒杰說:“你總不能一輩子跟一個不會生育的女人在一起。”還有原來劇本中演員沒有說的臺詞——“沒有小孩,就留不住男人。”在莉莉的潛意識中,女人的本質被簡化為一個容器。而具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實則是一個男性欲望的承擔者。
拉康曾以菲勒斯(男根)為例,認為它是最具象征性和優先地位的欲望標志,“如果說男根是個能指,這意味著主體只能在他人的位置上才能達到這個能指。但是因為這個能指在那兒總是被遮掩著,并且是作為他人的欲望的理由,主體要辨認的就是這樣一個他人的欲望。”所以,“象征首先是表現為物件的被扼殺,而這物件的死亡構成了主體中欲望的永久化。”
在這部電影里,這個“物件”就是莉莉的生育能力,生孩子,對她來說,并不是一種“需要”,而是一種被“欲望”。“所以欲望既不是對滿足的渴望,也不是愛的要求,而是從后者中減去前者所得到的結果,是它們的開裂的現象本身。”我們會發現,莉莉所有的欲望,不過是“他者的欲望”,是被象征秩序所規訓的欲望。第二代主人公的一生,反映的就是主體進入象征界后遭受符號秩序異化并最終消失的悲慘境遇。
三、《花》——無法抵達的“實在”
影片前兩代女性不是在想象界中沉溺于鏡像中的主體無法自拔,就是陷入象征界符號秩序的規訓體系迷失了主體。原著中,第三代主人公和前兩代沒有本質區別。小說中三代女性的命運是輪回的,時間雖然在流轉,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對人生不變的態度,女人們只是在“自己的房間”繞圈罷了。
導演侯詠的改編耐人尋味。影片中的阿花接近一個“完美”的女人:對愛情的忠貞、對愛人的默默堅守、對外婆的孝順體貼,以及沒日沒夜織毛衣賺外快補貼家用,甚至在得知丈夫出軌、自己懷孕的情況下,仍然要保留肚子里的孩子。外婆去世后,家里只剩下她自己,她想去醫院卻叫不到車,在大雨滂沱的深夜,于路邊產下了自己的孩子。這個場景是影片的高潮,也是令觀眾印象深刻的一幕,阿花痛苦而執著的表情配上神圣莊嚴的音樂,加上大雨代表的洗禮隱喻,讓這場戲幾乎有了宗教的意味。生下孩子的阿花仿佛經歷了一場涅槃,放棄了怨恨,獲得了重生。影片最后,在淡淡的背景音樂《茉莉花》中,阿花帶著自己的女兒搬進了新居,她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侯詠指出了改編的理由,“我們不能像原著那樣僅僅是重復,表現三代女性像一個女人一樣具有同樣的凄涼人生,這樣會讓影片的基調沉淪下去,使觀眾感到心如死灰,這是我們要扭轉的格局,我們要避免或消除小說中這種消極的東西。”換言之,聯系我們梳理的脈絡,經歷了前兩代有局限的主體意識,導演似乎希望第三代阿花可以尋找到主體真正的、實在的“自我”。
不同于弗洛伊德學派的“現實觀”,在拉康看來,人永遠無法回歸實在界,因為人無法逃避象征界語言符號的巨網,除非他走向瘋癲。而這就是主體的悖論,“‘我作為主體是以不在的存在而到來的。這個主體與一個雙重疑難相協調;一個真正的存在卻會因自知而破滅;一個話語卻是由死亡來維持。”因此,并沒有什么確定無疑的人之主體性,因為凡是可以求證的真實都是用某種語言來敘述,用某種方式來記錄,最終都可以納入象征符號秩序中的現象,不過是某種打著科學和理性的幌子,最終讓人遭到異化的象征界而已。而實在界,只能是人在遭遇象征界語言符號之網異化之后,所呈現的一種創傷性和不可能在場的存在。
拉康對重返實在界的深刻懷疑,對人尋回主體的悲觀認識,某種程度上也是這部影片的注腳。小說作者蘇童和影片導演侯詠設計的故事,看似不過是結局的不同,實則反映了對“人能否進入實在界”的兩種哲學分野。蘇童秉持對人性一貫的懷疑態度和性惡論哲學,自然而然放棄了這種尋找。而導演則“堅定地追求自己的夢想,同時經歷著一種斗爭的過程”。在拉康主體理論的觀照下,這種“過程”很有可能只是一次徒勞無功的掙扎,然而,這種幻想的存在,也有效填補了符號性虛構留下的空白或裂縫,維持象征界穩定的運行,為我們的主體帶來些許虛妄的“幸福感”。
參考文獻:
[1]拉康.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鏡子階段——精神分析經驗所揭示的一個階段[A].拉康選集[C].褚孝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2]麥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
[3]曾勝.視覺隱喻——拉康主體理論與電影凝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88.
[4](法)拉康.拉康選集[M].褚孝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598.
[5]侯詠.導演手記《茉莉花開時》[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