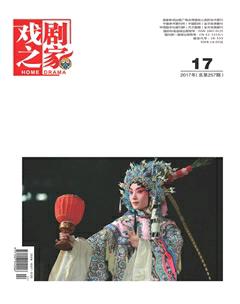論后工業社會語境下中國新生代導演的去符碼化影像實踐
劉琦
【摘 要】本文結合“現象學寫實主義”理論,從作者表達欲望的角度出發,聯系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特征,分析探討了中國新生代導演的影像創作中去符碼化的影像實踐及產生的社會根源。
【關鍵詞】符碼化;寫實主義
中圖分類號:J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17-0086-02
一
電影與寫實具有天然的近親性,巴贊對于保留現實多義性的熱衷在某些方面也體現為對無節制的個人表達的抵制,而對于現代主義者來說,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媒介的存在又將其逼退到柏拉圖的理想國之外重新面對現實與藝術摹寫二元關系的拷問,借用德魯茲用于闡述人類社會階段性特征的術語——符碼化,影像的符碼化無疑是取消藝術類同于現實的可能性確立其存在的唯一出路。弗·杰姆遜認為,對現實主義者而言寫實作為一種表達的風格系統具有天然的缺陷性。而可以明確的是,寫實的缺陷性相對應地作用于表達的欲望,或表達的需要,二者成正比相關。由此,可以推導得出:
其一,表達的欲望作為內在的促動力促使了藝術媒介的符碼化。中國30年代的左翼電影可以從反面例證這一推論。左翼電影中的抗戰題材影片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片投射出兩類表達的欲望體——愛國主義與紅色意識形態,同時,二者訴諸對象的大眾性又決定了影片的寫實風格及隱喻象征的符碼結構,典型地表現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一藝術實踐口號下社會縮影式的沖突結構,和具有濃烈身份政治象征意味的人物形象造成的影像所指與能指的割裂。
其二,以個人經驗結構和生命體驗為中心的藝術媒介的符碼化產生了具有絕對權威的個人闡釋模式,并由此形成個人話語霸權。很多研究者將中國新生代導演的寫作方式定性為風格化的個人寫作,本人并不同意這個看法,如果說這里所謂的個人寫作僅限于界定個人成長經歷的差別。賈樟柯在《賈想1996-2008賈樟柯電影手記》中說:“在我們的文化中,總有人喜歡將自己的生活經歷詩化,為自己創造傳奇……這種自我詩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西方現代主義電影作為排解“孤立、孤獨、反常、個人反抗、梵高式瘋狂”等個人情緒與描摹個人生命體驗的弗洛伊德式“白日夢”,影像時空被個體經驗結構成一連串被“無意識”夢境加密的符號系統,在這種私有化的影像空間中,無論是欣賞性或研究性地接受,觀者都被要求與作者的個人生命體驗同一,并面臨作者權威性的個人話語的審判。
二
如果不追究西方現代主義和中國第五代電影導演在表達傾向上的起源問題,即忽略資本主義異化及信仰危機與文革后一代對傳統及民族性的反思之間的差異性,那么二者相同的精英立場與表達主題的崇高性以及作品中共同流露出的強烈的改造世界的愿望就顯而易見了。賈樟柯在《賈想1996-2008賈樟柯電影手記》中描述了這樣一段經歷:“有一次在三聯書店樓上的咖啡館等人,突然來了幾個穿‘制服的藝術家。年齡四十上下,個個長發須,動靜極大,如入無人之境,頗有氣概。為首的老兄坐定之后,開始大談電影。他說話極像牧師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人名時他不帶姓,經常把陳凱歌叫‘凱歌,張藝謀叫‘老謀子,讓周圍四座肅然起敬。他說,那幫年輕人不行,一點苦沒吃過,一點事都沒經過,能拍出好電影?接下來他便開始談‘凱歌插隊、‘老謀子賣血,好像只有這樣的經歷才叫經歷,他們吃過的苦才叫苦”。以“凱歌插隊”、“老謀子賣血”、“吳子牛拉糞”等傳奇化經歷命名的第五代導演的個人苦難,在與“文革”這一集體受難儀式的相互關聯中,個人苦難與集體之殤以一種高度抽象化的訴諸于民族文化的精英式讀解與內省的方式同構起來,在這種以個體經驗同化集體經驗的對歷史真相的個人懷舊式改造中,苦難,作為被認同的集體的,更準確地說是一部分精英知識分子共享的記憶,在發散性的文化反思的創作命題中就轉化為以跨越現實的藝術定位重塑歷史的話語資本。在這種個人苦難=藝術創造的創作乃至接受模式中,在市場經濟的改革浪潮中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導演就陷入了藝術創造力被閹割的影響的焦慮之中。“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惱”,這些出生于六七十年代文革之后的中國新生代導演重新從寫實主義的角度出發,由此產生的對“父輩”作品的“誤讀”——抽象的民族寓言架空了當代社會中人存在的真實狀態,直接促動了新生代電影社會切片式的寫實風格的產生。賈樟柯電影中頻繁出現的客觀橫搖和靜止鏡頭,在某種類似拉康鏡像結構的心理語境中旁證了影響焦慮下其創作承繼性與逆反性的同在。下面以《站臺》和《三峽好人》中的兩個鏡頭為例:
橫搖鏡頭(《三峽好人》):起幅畫面(近景):韓三明站在拆遷樓頂,背對鏡頭,景深處是三峽連綿的山巒。鏡頭向右橫搖,人物從左出畫,起伏的山巒占據畫面。
靜止鏡頭(《站臺》):全景,畫右處,韓三明站在山坡上,背對鏡頭,景深處是連綿的山巒。
在上述兩個鏡頭中如果排除畫面前景處或起幅中作為畫面結構主體的“韓三明”的存在,我們更容易看到新生代導演在對寫意鏡頭的構圖處理上與第五代導演極簡主義構圖風格的親緣關系。然而,正是圍繞“人”的存在結構起的畫面調度避免了在第五代導演的作品中“人”淪為一種文化或民族品性的象征物。例如在《黃土地》中,人與景始終被壓縮在一個平面上,二者同生同構,在外部影像上,人只是作為畫面造型的結構性需求而淪為一種形式化的裝飾物,如山脊的邊緣輪廓線上向上攀緣的人的逆光剪影處理。在這種極簡化的畫面造型中,“人”被高度地抽象成為一種自在之物,被編碼在創作者個人風格化的表達系統之中。而新生代導演所要還原的,正是在這種個人化的自我表達中被遮蔽的個體真實存在的狀態,而這種還原,或者說某種程度上的表達,更多的是止步于“現象”的冷靜的注視,而非“現象”之后導演個人思想整合的結果。
三
“有些人一拍電影便要尋找傳奇,便要搞那么多悲歡離合,大喜大悲。好像只有這些東西才是電影應該去表現的,面對復雜的現實社會時,又慌了手腳,迷迷糊糊拍了那么多幼稚的童話。”賈樟柯在這里提出了一個如何去表現現實的問題。如果說第五代的文化反思是其作為曾經的一個歷史時期的見證者所完成的對一段歷史的追溯性整合,那么對于正在經歷的現實時空是否也能容納下那些已經結構在“歷史真相”之中的傳奇化個人臆想?對于不斷流變的現實時空,我們顯然已經失去從整體去把握其本質的能力,對于新生代導演來說同樣如此。尤其在國內的經濟改革中,市場經濟體制部分取代了計劃經濟體制,集體化的勞動、生產方式被自由競爭的單體化生產方式打破,城市工業化浪潮所帶來的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也使傳統的家庭結構瀕臨解體,個體在分散性的社會職能的編制中各司其職,計劃經濟時代的集體經驗被互不相關的個人生命體驗取代。拍攝于1996年的影片《巫山云雨》從某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市場經濟時代中,以相對松弛的國家監控管制力度、弱化的傳統道德約束力,以及分散與細化的勞動生產方式為特征的后工業時代背景下人的孤獨境遇,以下我將主要分析分散與細化的勞動生產方式造成的社會個體的彼此孤立。
麥強是三峽邊上一個信號臺上的信號員,一天下午,好友馬兵帶著妓女麗麗來看望他,馬兵想讓麥強與麗麗發生關系,麥強卻不感興趣。陳青是三峽邊上一個小縣城的旅館接待員,早年喪偶,和一個半大的孩子相依為命,與旅館經理老莫的關系糾葛不清。
小吳是鎮上的民警,正忙著操辦自己的婚禮。一天老莫上公安局向小吳報案,說麥強強奸了陳青,麥強被帶進了鎮上的派出所。后來經陳青本人澄清,雙方都屬自愿,麥強又被放了出來,釋放前,在派出所里民警小吳給麥強剃了個平頭。
章明在記錄影片的拍攝過程時回憶道,“我小時侯就住在江邊上,每天看著船從上游開往下游,或者從下游到上游去;船上的人、事都和我毫無關系,卻又真切地從我眼前開來開去,這情景給我的印象很深。”如果說賈樟柯的“小鎮影像”完全背離了蓬勃的市場經濟改革所衍射出的大都會蜃景,從反面書寫了正在經歷工業化改造的大多數中小城鎮的經濟、文化、家庭及個人的尷尬錯位,那么章明的“巫山”,因其獨特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意蘊,一方面其具有所有的那個時代中的中小城鎮所具有的“被改造”與“正經歷”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巫山”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盤踞著自然與社會雙重屬性的被“部分隔絕”的地域景觀。在被后工業文明所改變的時空結構中,更大規模與更快頻率的“外來物”作為一種想象的導體在與這塊被遺棄的土地的“遭遇”中,誘生出一種期待,如同影片的英文譯名《In Expectation》,“在期待中”,影片所要表現的正是在這種期待中背離現實的幻想與不可逆的現實的沖突,以及“期待”這一行為本身所蘊藏的根深蒂固的個體的孤獨。影片中,“船只”與“游客”作為一種他者化的外來物即成為片中人物擺脫這種“孤獨”的一種理想化的解決方式,然而在這個層面的期待中,人反而會陷入一種更為本質的不可逆轉的孤獨的境地中,這種宿命式孤獨的本質即后工業時代中分散與細化的勞動生產方式以及“異化”的勞動主體與勞動對象的分離造成的社會個體之間的相互孤立,然而勞動主體與勞動對象在物質上的分離卻又以信息化的方式在一種固定的時空結構之中被聯系起來,從而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紐帶將人綁縛在固定的時空關系之中,表現為在相同的時間內進行重復的生產勞動。關于這一點,在麥強的職業(揪石子信號臺信號員)特點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結語
在極度分散與極度細化的個人職能分工中,“人”逐漸被一種職業身份所取代,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生命經驗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多元化的差異性,而構成不同職業分類標準的知識結構的私有化、隱秘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屏蔽了“人”被他人“體驗”的可能性。正是現有的社會體系下這種加重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可知性使新生代導演對于“真實”的概念產生了一種相對化的理解,如賈樟柯所言,“他們(指張元、何建軍、王小帥等)不再試圖為一個時代代言。其實誰也沒有權利代表大多數人,你只能代表你自己。”相應的,冷漠的寫實主義風格,就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創作者個人表達欲望的“去符碼化”的影像實驗中,以大寫的孤立的“人”的影像,保留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真實。
參考文獻:
[1]弗·杰姆遜著.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唐小兵譯.陜西: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2]賈樟柯.賈想1996-2008賈樟柯電影手記[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