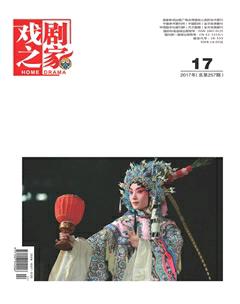苦難中的人性光輝
蔣甜
【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癡》中描繪了深刻的苦難,而梅什金是受難的原型,他的身上綻放著基督式的人性美。小說的悲劇結局,一如耶穌之死,實為救贖的開始,而梅什金就是犧牲于當下的一顆未來的種子。
【關鍵詞】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難;人性美;救贖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17-0245-01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紀俄國文壇上一顆璀璨的明星,他的作品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性。陀氏的小說中充斥著苦難、虛偽、錯亂、仇恨、抑郁、罪孽、嫉妒等等,就像是人類罪行和苦難的百科全書。《白癡》是陀氏深入刻畫苦難的又一杰作。這部小說壓抑怪誕,讓人難以卒讀。
一、對苦難的深度描述
陀氏的作品中對苦難的深度描述向來在作家和評論家中有很大的爭議。那么,陀氏為什么如此專注于描寫苦難呢?究其原因,與陀氏苦難的一生不無關系。陀氏的父親是個六親不認的酒鬼,暴躁不堪。年幼時母親因病去世,父親死于農奴之手。他自己28歲時曾被判死刑,但是臨刑前又獲釋,經歷了瀕臨死亡的殘酷煎熬。更殘酷的是,他在西伯利亞流放近十年,生活苦不堪言。陀氏從9歲起患上癲癇病后,就經常發作,病痛折磨了他一生。終其一生,陀氏的一生充滿了苦難。
除此之外,陀氏之所以如此關注苦難與其現實主義的寫作態度密不可分。面對各種激烈的抨擊,陀氏直言道:現實本就如此!他說:“我對現實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而且被大多數人稱之為幾乎是荒誕的和特殊的事物,對于我來說,有時構成了現實的本質。事物的平凡性和對它的陳腐看法,依我看來,還不能算現實主義,甚至恰好相反……難道我的荒誕的《白癡》不是現實,而且是最平凡的現實!”[1]陀思妥耶夫斯基堅定地認為,他筆下的苦難是當時俄國人民的真實生活的寫照。
當然,陀氏的偉大并不僅限于對苦難的描寫,為那些無辜受難者伸張正義才是他的目的。陀氏一直苦苦思索解決這種困境的答案,但一直不可求。直到從西伯利亞流放歸來,陀氏完全皈依了宗教之后,才有了答案。答案即是受難,像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一樣受難,在受難中播撒愛的種子。小說《白癡》似乎把基督精神做了寫實,并發揚光大,小說中梅什金即是受難的基督的化身。
二、基督式的人性美的展現
在陀氏筆下,由托茨基礎、羅果仁、葉欽潘們組成的魑魅魍魎的世界象征著一個混亂荒唐的現實世界。而在這種混亂之時,就得有一個象征性的新人作為隱喻出現。但是陀氏明白,要“描繪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難的了。特別是現在,所有的作家,不僅是俄國的,甚至是全歐洲的作家,如果誰想描繪絕對的美,總是感到無能為力,因為這是一個無比困難的任務。”[2]陀氏曾明確表示過,梅什金公爵就是基督的形象,他到這個世界中來就是為了洗滌骯臟抑制邪惡。用愛和受難的犧牲讓人警醒,使人團結。梅什金帶到這個世界里來的正是這種受難的愛。他的信念是:“同情是全人類生存最主要的,也許是唯一的法則。”[3]
陀氏授予梅什金以基督的靈魂,讓梅什金帶著這嬰兒般圣潔的靈魂步入苦難的世界,用溫柔和愛彌滿人間,進而排除一切粗暴、分裂、殘酷等丑陋的社會現實。而這樣一種靈魂的洗滌是經過凈化而來的,凈化的過程就是宗教的深入骨髓帶來的靈魂的震顫。梅什金以一顆仁愛之心對待所有人,包括朋友、親人、甚至仇人,而這種人性的光輝又恰恰在耶穌基督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三、結論
《白癡》最后的結局是那么的悲涼凄慘,梅什金這么一個圣潔的如嬰兒般純凈的人兒成了真正的白癡。很多人把這最后的篇章理解成不折不扣的悲劇。在小說的結尾,依波利特注視著霍爾拜因的那幅畫,畫上是一具慘不忍睹的尸體被釘在十字架上,這讓人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耶穌。受難的耶穌也是以被釘在十字架上來代表其生命的終結。此時的耶穌雖然是死囚的身份,但是他卻用這種形式寬恕了蕓蕓眾生。被釘在十字架上并不代表失敗,恰恰相反這是一場偉大的勝利。梅什金作為基督的化身,必然要歷經苦難,而深受病痛的折磨就是他的十字架。在小說結尾,他寬恕了所有人,包括殘忍殺害納斯塔霞的病態的羅果仁,這是一顆多么感人至深的純凈的仁愛之心。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分析到此,我們便明白了陀氏之所以創造出這么一部怪誕陰郁的小說用意之所在。《白癡》中所頌揚的倫理觀是要以宗教為基礎的。所謂倫理,就是指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關系時要遵循的道理和準則。是指一系列指導行為的觀念,是從概念角度上對道德現象的哲學思考。而相比之下,道德雖然也是指社會行為的準則,但是它更具有主觀性,不同人的主觀性必然會導致自由意志的濫用,所以倫理觀必須是一種上帝的無條件的指令。因此,陀氏認為,宗教的介入才是最終的救贖。
參考文獻:
[1]馮春選編.岡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羅連科文學論文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2]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選[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192.
[3]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癡[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5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