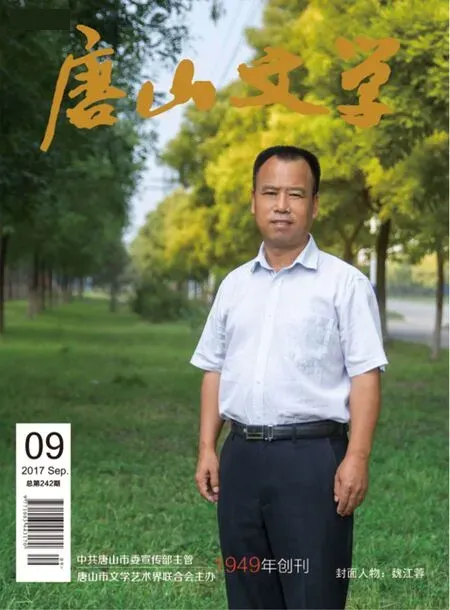聽媽媽講故事
張學強
聽媽媽講故事
張學強
又一個夏天來了。走在小城寬闊的馬路上,陽光肆意地灑下一地的金線,垂柳輕拂行人的臉龐,樓宇鱗次櫛比,汽車如潮水般奔向遠方。心思被一種東西牽著,穿過車流,飛向天邊,飛過原野,飛到幼年。
我生在玉田縣農村。那里沒有城市的繁華,但富饒美麗。燕山橫亙在遠方,沃野一望無際,藍泉河白亮亮的河水繞過村莊,水塘中長滿翠綠的蘆葦。夜晚時分,天空像藍絲絨的緞子,滿天的星斗像灑在絲絨上的金星。夏天到了,母親把飯桌搬到院子里。吃過晚飯,我們就坐在桌子旁看天,看紅云退去,看第一顆星從東南的天宇鉆出頭,看滿天星星眨動眼睛。天空遼遠,星斗慢慢地匯成銀河,北斗星的大勺子在夜空燦爛地閃現。
母親收拾完家務,坐在飯桌旁,縫補衣服或拿了針錐納鞋底。我問母親哪顆星是牛郎星,哪顆是織女星。母親隨意往天上一指。順了母親手指的方向,總能找到兩顆閃亮的星星。于是,我搖著母親的手臂,讓她講牛郎織女的故事。
“牛郎家里很窮,但心地善良,人又勤快。天上美麗的織女喜歡上了他,就下凡來到人間,和牛郎一起過活。他們一個耕田,一個織布,日子過得很幸福,還生下兩個可愛的小孩。但是王母娘娘……”母親語調輕柔、緩慢。我開始犯困,眼皮直打架。母親接著講:“牛郎披上牛皮,擔子里擔著一雙兒女飛到天上,王母娘娘看到牛郎上了天,非常生氣,拔下頭上的簪子就那么一劃——”常常母親沒有講完,我就睡著了。小時候,我覺得王母娘娘是天地間最可惡的人。我總是盼望七夕到來,因為七夕來了,喜鵲就給牛郎織女搭橋。母親曾說,七夕的午夜,兩顆星會慢慢地滑動,靠近。然而我從未堅持到那么晚。
小時候,我很想成為沉香那樣的小孩,因為我聽了母親講的“力劈華山”的故事,希望生出無窮的力量來保護母親。我特地讓父親給我做一只木斧子,常掄著它和小伙伴的刀劍對打。每到過節,我最希望能有雞吃,因為我想驗證雞的腦袋里有沒有法海。母親講過,當年法海被白娘子和小青追趕,走投無路,看到一只公雞,便鉆到雞的腦袋里,再也不敢出來。又一次,爸爸把雞的腦髓完整地撥出來,果真像一個小人兒,讓我更加堅信母親的故事。
長大一些了,母親會帶著我下地干活。大秋時候,母親要擗玉米,割豆子,種小麥,忙活好一陣子。閑的時候,母親會教我:這個是車轱轆菜,那個是苦麻子,那個是剌剌蔓……遇到野生的甜瓜或者狗奶兒,母親會摘來給我吃。我在田野里瘋跑,逮螞蚱,捉蛐蛐,玩得不亦樂乎。晚上,趁著月光,母親坐在院子里剝玉米,撕開玉米皮,手一扭,胖胖的白玉米就跑出來。我不懂母親的勞累,又纏著母親講故事。母親就給我們講“岳飛傳”、“楊家將”。我最愛聽“岳母刺字”,雖然還沒有國家的概念,但潛意識里對岳飛、岳母充滿敬佩,“精忠報國”深深地印在腦海,震撼著一個孩子的心。
村子西面有大片的葦塘,水越來越少,只在中間還有一片水洼,但蘆葦依舊茂盛。葦塘就像一個迷宮,藏著無窮的秘密,每次進入葦塘,心里總是緊張。有一次端午節前我和母親去采葦葉,走著走著,母親突然止住腳步。我躲在母親身后向前望去,一條足有兩米的花蛇正緩緩爬行,滿身的鱗甲泛著美麗的光澤。我嚇得心“砰砰”直跳。母親并不在意,只是示意我別動。一會兒,蛇爬進一個石頭堆里。晚上,母親給我講了幾個和葦塘、蛇有關的故事。如,有一家人打死了蛇,招來蛇的圍攻;看到蛇大量遷移,不久就發水了。故事大多模糊不清了,但有兩個故事,至今記憶猶新。
一個是秀才救龍王。有一個讀書人在快要枯竭的水洼里發現了一條銀色的小蛇,而天上有一只老鷹正要俯沖下來。讀書人趕走了老鷹,救下了小蛇,并把它養在家里。小蛇喜歡水,他就每天提了水澆在它身上。過了幾天,小蛇突然說話了,說他是龍王,因降錯了雨,被罰到世間,幸虧書生救了他,明天被罰期滿,要回到天上了,要書生在第二天下雨時,把它放回原地。第二天早晨陰雨連綿,讀書人把小蛇放回水洼。突然電閃雷鳴,小蛇變成一條白色巨龍騰空而起,剎那間消失在天空。第二天,人們發現水洼旁葦塘的蘆葦倒了一大片,大家都說是龍騰空時給壓倒的。后來,那個秀才受了龍王的保佑,順利地考上了進士,做了大官。
另一個是后湖的故事。玉田林南倉東北面的后湖,原來是一片沃野。遼國的蕭太后看上了那里,開始建城,并設立了行宮。蕭太后統治殘暴,冤死了太多無辜的百姓,觸怒了天神,一夜間,天翻地覆,城池陷入了地下,成為一片汪洋,后來長出了大片蘆葦。后湖里常有帶著紅冠子的蛇在水上飛,那是冤魂化成的;在陰雨天里,人們常聽到腳鐐的聲音從湖底傳上來。
這些故事雖然有些荒誕,但體現了人們對自然的敬畏,對知恩圖報的贊許,對殘暴統治的憤恨。母親一輩子不打蛇;遇到刺猬常常放生;堂屋窗子總留出空隙,讓燕子進出。想來,是這些故事影響了母親的一生。
母親的故事總也講不完。冬天,天寒地凍,屋里的水結了冰碴子。我們貓在被窩里,母親一邊做針線活兒,一邊給我們講故事。講姥爺闖關東,說東北的雪能沒過膝蓋,說二姥爺在東北被熊瞎子舔了;講抗戰的故事,說村里成立了大刀隊,日本兵躲在炮樓里不敢出來,后來有人告密,大刀隊遭鬼子伏擊,死了很多人;講修河的故事,說縣領導在村里蹲點,親自參加勞動,說她們也參加了勞動,送水送飯。母親還會講評戲里的故事,“花為媒”“劉巧兒”母親都會。母親有兩張沒出嫁時的照片,一張梳著粗大的辮子,一張正在演戲。一次,我問母親演過什么角色。母親低下頭,似乎有些害羞,只說是跟著村里人張羅。我非要母親唱一段,母親沒辦法,開始哼唱:“小酸棗,滴溜溜地圓,滴溜溜地掛滿懸崖邊……”,或者唱:“春季里風吹萬物生,花紅葉綠,草青青,桃花艷,梨花濃,杏花茂盛……”在故事和哼唱中,我幸福地睡著了。
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老家沒有了葦塘,村莊少了神秘,母親的那些故事似乎也不合時宜了。我曾經想給女兒講母親給我講的故事,但女兒不是說功課忙,就是纏著妻子給她講“小紅帽”,“白雪公主”。然而,我依然常常想起那些故事,那個時代。
其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每個人也都在傳承著、演繹著故事。新的時代有許多生動、美好的故事,值得我們記取,講述。我只是希望新的故事多一些地域的色彩、民族的特性。這樣,人這棵蘆葦就可以找到一方靜美的水塘,深深扎下根,在陽光下茁壯成長。
夏天又到了,周末回一次老家,搬出那方陳舊矮矮木桌,擺上小板凳,再聽媽媽講故事。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