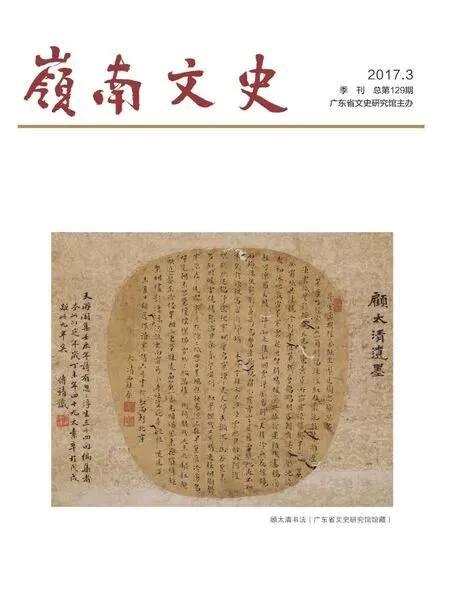增城蓮花書院小考
張百祥
增城蓮花書院小考
張百祥
一 南香山及蓮花書院名考
南香山位于增城市永寧街,海拔433.2米,自古名號為南樵山,與東樵羅浮山和南海西樵山合稱為粵中“三樵”。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廣東新語》記載:“廣州有三樵,曰東樵,曰南樵,曰西樵”。南樵山靠近珠江口,瀕臨南海。清乾隆年間增城知縣管一清遠眺南樵山,寫下《舟中望南樵山》一詩,其中有:“一曲娥眉橫海上,南樵風致勝東樵”的詩句。“一曲娥眉橫海上”的娥眉,是古代南香山的正式名字。古時除號為南樵山外,正名稱娥眉山,以其山勢遠眺形似一彎娥眉而得名(圖一)。據明嘉靖十七年(1538)修《增城縣志》記載:“南鄉嶺,一名峨眉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山麓,周回一百二十里”。南鄉嶺、峨眉山、南樵山即如今的南香山。
清雍正時,文淵閣大學士蔣廷錫重新編校《古今圖書集成》一書。其中《廣州府部匯考》記述廣州所轄各縣山川風貌。此時增城歸廣州管轄,該書在介紹增城山川時有娥眉山條目:“娥眉山,一名南鄉嶺,在縣南七十里,清《湖都通志》作南樵山,極高峻,周迴百里,上有丹室下有石庵。湛文簡建書院於此,曰蓮花書院,上有霍文敏墓。”可見蓮花書院位于峨眉山(南香山)之上。至于蓮花書院命名的由來,可以從湛若水的《娥眉蓮花洞開創書館記》中找到一些端倪:“自娥眉之西北登其巔,十余里,以至東南,則俯見豁然一洞,后如屏,左右如椅,中有一莖如梗,垂若芙蓉然。廣明叟曰:‘此非所謂蓮花乎?’”。這是文獻中關于蓮花書院最早的記錄。今日蓮花書院遺址正位于南香山的東南部,《館記》中所記述的“豁然一洞”應為今位于蓮花書院東南部的湛子洞,距離蓮花書院遺址不足50米。在湛若水的《再宿蓮洞有作中》有記:“吾愛峨眉山,峨眉淡不如;吾愛蓮花蕊俗以此洞似蓮花,故名之云。”進一步印證了蓮花洞名字源于現在湛子洞所在的地形,左、中、右之山峰高大,而中間像花蕊一樣橫出一梗,整個形狀就好似蓮花,故名蓮花洞。而蓮花洞作為其書院的門戶,是登上書院的必經之路,所以其上的書院為蓮花書院。
根據明嘉靖十七年《增城縣志》的記載:“南鄉嶺一名峨眉山……地產名茶丹荔品果,下有石庵一所,高僧居之,今廢。嘉靖間甘泉湛子登覽至此,邑士因立書院于其上,請名于湛子,遂改其嶺為蓮花洞額。蓮花書院以其地形似蓮花。云洞門大石高四五丈,大二丈余,碑立刻湛子洞三字大書于其上”。所以蓮花書院的命名源于蓮花洞(湛子洞),蓮花洞之命名源于其所在的地形似蓮花。

圖二 湛子洞
但根據《湛若水全集》中有關蓮花書院的文章除蓮花書院這一稱謂外,有的名字卻是蓮洞書院,如《游蓮洞書院》、《蓮洞書館贍田倉記》等。追根溯源,《峨眉蓮花洞開創書館記》、《蓮花洞書館上梁祭告文》等這些文章記述了蓮花書院開創修建的情況,也是書院修建的第一手史料。從這些文章的名稱中可以看出,蓮花書院的全名(原名)應該是蓮花洞書院,蓮花洞的來由源于上文所述,而蓮花書院或者蓮洞書院都是該書院的簡稱,這兩個稱謂在湛若水生前就已使用,而后來多版本《增城縣志》有些是使用“蓮花書院”(如明嘉靖版),有些使用“蓮洞書院”(如清康熙、嘉慶及民國版)。
二 蓮花書院所在位置考
根據清康熙年二十五年(1686)修《增城縣志》載:“南樵山縣治西南六十里,亦名南鄉,高千仞,周迴百里,層巒疊嶂,前瞰大江,上有丹室,下有石庵,項有蓮花書院,乃明尚書湛若水所建。”在乾隆十九年(1754)和民國8年(1919)《增城縣志》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所以,湛若水所建的蓮花書院應位于現在增城的南香山,結合縣志相關的記載說明當時的南香山山上有丹室,山下有石庵,而山腰上就有蓮花書院。因此,該書院應該位于南香山的山麓。
湛若水的《娥眉蓮花洞開創書館記》有載:“自娥眉之西北登其巔,十余里,以至東南,則俯見豁然一洞……泉水潺潺出乎兩崦之間,合而南,東出乎石淙,以流無窮。俯下諸山伏地,其前左則有羅浮蔽天、飛云映空、石樓拔地,如蜃氣者……其前右則有黃旗獵獵、銀瓶卓峙。其前磊磊則有三臺之石、有窮窿之崖。下之仰觀,如高碑千丈,斬削特立,大書所謂湛子洞者也。懸飛鳥之徑,度棲鶻之巖,如行空中、如升天上,路出三臺者也。天下之偉觀無以尚之矣!”根據這些記錄,蓮花書院位于南香山東南部的山麓,蓮花洞(湛子洞)的附近。“泉水潺潺出乎兩崦之間,合而南,東出乎石淙”,說明蓮花書院位于兩泉水(小溪)交匯處,面朝東南,溪水環抱之處,正好位于現今湛子洞往上約50米溪水交匯的山麓平臺上。
三 蓮花書院興廢考

圖三 蓮花書院遺址所在的地形圖(粗線范圍為蓮花書院遺址)
關于蓮花書院的興建,湛若水全集里多有記及。湛若水《蓮洞書館田倉記》有“甘泉子丙申南歸,既創蓮洞書館于峨眉山”句;《初卜筑蓮花洞祭告土地文》有“維嘉靖十五年(1536),歲次丙申,十一月癸丑朔,越二十二甲戌,南京吏部尚書湛”句;及《蓮花峒書館上梁祭告文》有“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閏十二月壬子朔,越初三日甲寅,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敢昭告于蓮花峒土地之神”句。根據這些記載,蓮花書院開始興建于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而根據湛若水年譜的記載,這時候正好是湛若水休假南歸之時。但蓮花書院位于南香山山麓,山路崎嶇,海拔較高,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短期內建好。根據湛氏《峨眉蓮花洞開創書館記》載“文侯與縣博湯君仁從予復往觀之,定厥宅……己亥正月二十五日”句,說明至嘉靖十八年(1539)時,蓮花書院建設已頗具規模。而湛若水于嘉靖十九年致仕,回家鄉講學。他輪流講學于包括蓮花書院在內的幾所書院,所以蓮花書院這時不僅建成,而且已正式開始授課講學。因此,蓮花書院應始建于嘉靖十五年,十八年前后正式完工,并于十九年(1540)開始授課講學,且致仕后的湛若水曾長期在此講學。
關于蓮花書院辦學的費用來源,在湛若水的《蓮洞書館贍田倉記》中有記載:“學者往居,不可以裹糧,則見增益北郭外阮、唐、廖、蔣四村之間,有荒埔無主者,可墾為贍田……卑隰而為湖者塞之,凡為田約十余傾,以其附郭,歲收租谷可千余石……故其費也博,而吾一二十年俸入之囊罄於此矣。”蓮花書院位于娥眉山山腹,山高路陡。學生背負糧食上山十分困難。湛若水經過調查,知道書院附近四村交界處有很多荒地,就想置下這些荒地開墾用作贍田。但由于很多荒地都無主,加上四村交鄰,當地鄉紳覺得難于處理。于是,若水便派兒子柬之與學子代表一齊向縣官申請,承諾以開墾田地中的一定比例納稅為條件,終于獲準把書院四周十多頃無主荒地納入蓮花書院范疇,供書院開墾以作“贍田”、“義田”之用。經過數年開墾耕耘,“館谷”收入越來越多,除用于資助貧困與品學兼優的學生外,還用于修建院舍,改善排水系統。除設置“贍田”、“館谷”,書院還設置了嚴格的審核制度:“凡生徒不審其兼習二業,為古之德行道藝之學者,而冒以來居斯屋、食斯谷者,有如此誓!其懶者,及不為舉子業而以虛名為浮夸,無實得者,不館不谷焉。”可見,贍田制度為蓮花書院的興盛和學子的生活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嚴格完善的審核制度也為學子們學有所成提供了鞭策。由此增城民間有“九個學子十個秀才”的傳說,說明蓮花書院大大促進了增城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
而蓮花書院的荒廢,史書上少有提及,但也能從縣志的記載中找到一些線索。根據清康熙版《增城縣志》記載:“南樵山……項有蓮花書院乃明尚書湛若水所建,今廢。”可見,蓮花書院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建成,至清康熙年間已經荒廢。而在此期間,書院遭受了兩次致命性的打擊,可能與它的荒廢有直接關系:一是明萬歷七年(1579),首輔張居正奏請朝廷“詔毀天下書院”、“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實行統一思想、言論、道德、倫理,蓮花書院可能毀于這一政策;二是明末清初時兵荒馬亂,生靈涂炭,書院可能毀于這場動亂。但前者根據《明紀》卷四○載:萬歷“七年春正月戊辰,詔毀天下書院。自應府以下,凡六十四處,盡改以為公廨。”可見朝廷的政策是毀書院,但其實書院的建筑還是能夠保留的,只是改用途而已,且萬歷十年(1582)張居正死后,各地書院又紛紛復辦,所以張居正改革這一措施并未使蓮花書院被毀。結合對蓮花書院遺址的勘探試掘,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明嘉靖-萬歷年間的瓦當和瓷片,遺址內蓮花書院的地層內沒發現任何的清代遺物,所以書院的倒塌時間應為明末,這符合縣志等文獻的記載,所以蓮花書院的被毀時間應該是明末清初。

圖四 蓮花書院遺址出土的明代青花瓷片及瓦當

圖五 蓮花書院遺址勘探航拍圖(東南-西北)
四 蓮花書院結構布局考
湛若水在《峨眉蓮花洞開創書館記》中有蓮花書院的記載:“文侯與縣博湯君仁從予復往觀之,定闕宅,卜其上為正堂三間,左右為偏堂各三間,左右為翼廊。”從考古勘探試掘的情況看,該遺址南北長約48米,寬約30米。現存蓮花書院遺址的原有地面已不復存在,但墻體的建筑基礎還保存較好。從墻基保存情況看,蓮花書院是坐西北朝東南的走向,呈中軸對稱的結構。建筑主體結構是四進三路,四進分別位于遺址的四個平臺上,由左、中、右三條通道連通。根據目前勘探的情況看,四個平臺上的建筑基礎保留較好,能看到每一進基本都分為中堂和左右廂房。中路是通過階梯連接每一進,且中路為建筑的中軸線,書院建筑基本以此為對稱軸,呈左右對稱分布。左路右路為建筑的東西翼廊,右路為西翼廊。根據勘探的情況,目前只保留了部分的石頭階梯,且階梯與西邊小溪緊緊相臨,但東翼廊可能由于現代修筑山路時被破壞,現已不存。
增城蓮花書院為明代大儒湛若水所創建。研究蓮花書院,可以了解明清時期增城的教育事業發展;對研究明代書院結構布局,在建筑學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單位: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