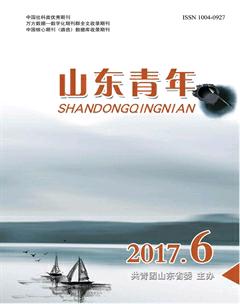展覽體制下書家的創(chuàng)作心境
朱志民?オ?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的成立,使得全國性書法展覽成為當代書法向社會集中展示的主要方式,由此開創(chuàng)了一條讓普通書法愛好者晉升為書法家的重要路徑。尤其是近三十幾年來,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以及各省、市書協(xié)均把獲獎、入選作為協(xié)會新增會員的入會條件認定標準,使展覽對于書法愛好者來說便有舉足輕重的價值取向。如何創(chuàng)作出奪人眼球的書法作品,怎樣才能獲獎成為書法翹楚,是每個想要被大眾認可的書法人所殫精思索的問題。
然而書法在古代是文雅又閑適的文人藝術(shù)形式,樸素的自然經(jīng)濟決定了古代文人追求寧靜的精神狀態(tài)。古人書法的創(chuàng)作之樂,大多時候是靜居一隅揮毫潑墨,體驗筆墨對眼與心的細膩撫摸,這種較為自由閑散的書寫活動,從而作為一種生存方式融入日常,成了感悟藝術(shù)之美的樂趣。現(xiàn)如今當作品進入公共審美空間之后,展覽賽事上入展獲獎引發(fā)的成就感和所獲得價值實現(xiàn)的自由感,為書家?guī)碛忠韵矘贰G罢呤菫榱藗€人審美生活需要,不受侵擾,無需外求,所以很容易就能叢中獲取樂趣。而后者則要將自己處在和他者競爭的關(guān)系當中,同是投展,誰入展誰就洋洋得意,如果拔取上籌獲獎了,無疑會有鶴立雞群之感。如此帶有名利目的的書法創(chuàng)作,卻往往只是短暫之樂,也并非日常所能得到,如若變成精神的苦役就很難有純粹的樂趣可言了。因此,當下的每一個書法家都面臨著展覽時代對心境自由的兩難選擇。
對于古代的文人書法家來說,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沒有展覽,其作品展示和傳播的空間相對有限和閉塞,要么是文人案牘間的把玩,或者是私人寓所間的“壁上觀”,即使是雅集上的交流,也只是一定的社會小群體,他們大多是故友舊人,有著共同的美學趣味,在情感交流上心有靈犀。因此,它與不同趣味間的主體沒有構(gòu)成競爭性的關(guān)系其展示行為也并非迎合外在的非審美目的,如獲獎、入展、市場等,不必過多考慮外在利益或意識對自我審美的壓迫。因此,書法創(chuàng)作便成為了個人雅玩的有效手段,它是文人豐富社會生活方式的延伸和補充,他們追求一種內(nèi)傾性的體驗之樂,破煩襟、解孤悶,心境自然也就從容而舒展。
當下的社會節(jié)奏高速多變,加之各種物質(zhì)利益的功利驅(qū)使,與人們休戚相關(guān)的一切都變得“物化”了,也使得書法家的精神狀態(tài)也隨著“物化”而不得不屈從于現(xiàn)實社會。一方面使書法家原本寧靜的心變得躁動起來,其書法創(chuàng)作也不再是最初的暢神達意。鋪天蓋地的展覽信息,豐厚的獎金和隨之而來的知名度,入展就意味著許多現(xiàn)實利益和權(quán)力的實現(xiàn),導致書家成天沉浸在投稿創(chuàng)作之中。有了名利的誘惑,必定會提升書家的投展積極性,投了作品才有機會入展獲獎,沒投就肯定沒有結(jié)果。勤奮練字原本是好事,可當書法變成書家追求既得利益和功名利祿的手段和方式之后,其書法藝術(shù)本有的功能與效用便失去意義。另一方面也使書法家的身份開始變得邊緣化,使書法家成為市場經(jīng)濟大潮中的趕場之人。現(xiàn)實中的書家并非全職,其往往背負工作、家庭壓力,在額外時間從事書法創(chuàng)作。在有限的時間里要多投乃至多入展覽,對于作品的質(zhì)量就很難保證,于是就不管好壞撒網(wǎng)式地投向各種各樣的展賽。
心靈對于世情的適應能力總是超乎想象,從純粹的私心之樂,到公共性的競爭體驗,二者的取舍本應該很容易就能判斷。然而為什么依然還有這么多書家趨之若鶩?當下的書家已經(jīng)揭下藝術(shù)自我消日的清高面紗,很快地適應了農(nóng)耕文明時代的展示方式到工業(yè)聞名的展示方式的轉(zhuǎn)變。隨著社會生產(chǎn)力的不斷提高,經(jīng)濟水平繁榮發(fā)展,文化事業(yè)也越來越被得以重視。展覽的規(guī)格近年來不斷提高,展廳的空間、視覺效果也隨之增強,于是乎征稿的尺寸也一再擴張到八尺。為了應付展事,尤其是權(quán)威性大展,許多書家不惜耗費巨大的精力琢磨展賽的要求和標準,創(chuàng)作出令人贊嘆的巨幅作品。甚至詳細到琢磨評委的喜好、展覽的趣味走向,心靈的自由早已被這外在的力量牽扯起來而難以舒展。為了投一幅作品,書家通常從形式布局的安排,到文稿內(nèi)容的選取,最后設計底稿,不厭勞煩地再三推敲,致使完成一幅作品所消耗的時間短則月余,長者數(shù)月,可謂慘淡經(jīng)營之極。基于競爭的殘酷性,眾多投稿者大多選擇篇幅長、字數(shù)多的內(nèi)容,都希望自己的辛苦之作在和他人同等技術(shù)水平的情況下,能夠獲取評委的同情心,體現(xiàn)出自己對于展賽的格外重視,以此爭取更大的入展可能性。
如此艱辛的創(chuàng)作過程,對于書法癡迷者來說或許已是一種生活常態(tài),也完全會有一種“痛并快樂著”的精神體驗。然而現(xiàn)實生活中,從作品寄出的那一刻開始,就伴隨著無盡的牽掛,初評能否順利通過?復評會不會被刷掉?有沒有機會獲獎?它到底能在此次展賽中走多遠?其實這一系列擔心從創(chuàng)作之初就已經(jīng)埋下了,因為從一開始,書家對展覽便抱有一種明確的外在目的,這種制約正是影響身心自由的重要原因。
正如前文所說,全國性書法展覽成為當代衡量書法水平的重要尺度,也是書法學習者由初學走向成名的唯一通道。因此,獲獎、入展,成為當代書法作者相應追求的鮮明目標,更是大家掛在嘴邊常談不衰的話題。由展覽會主導的展廳審美趣味或者評委會的審美口味,通過媒介等信息化渠道以及展覽公共性平臺,自上而下進行傳遞,從而形成了同質(zhì)化的展廳流行藝術(shù),因此展廳藝術(shù)總是制造著流行和時尚的藝術(shù)走向。國展上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的現(xiàn)象,是入會最殘酷的一種應試。每逢展覽,必是數(shù)千上萬人拼搏以求進入幾百人“入展者”之列。有人為之每日挑燈夜戰(zhàn),那些投展專業(yè)戶在投這屆展賽的時候,順便已經(jīng)也把下屆的作品都準備好了,不得不贊嘆其效率之高。有人為之四處拜師,不惜財力到處報名國展高研班,為的是和高研班導師攀上關(guān)系,混個臉熟,順便學習國展的游戲規(guī)則。有人因為國展終日憂悶,明明入展的作品就是不如自己的,為什么是他入展?明明這次寫的很滿意,為什么沒有入展?還有的人從未明確自己的學書路線,只知道盲從跟風。畢竟現(xiàn)行的展覽體制,只有評委手握每件作品的生殺大權(quán),所以就有很多人揣摩評委的審美傾向,臨摹抄襲往屆的獲獎、入展作品,甚至請搶手為自己代寫。諸如此類情況都是投展時的心境呈現(xiàn),一旦入展或獲獎了的書家,從此以后就有可能不在投稿,因為他們擔心下次如果投稿沒中或者獲不了獎會“丟面子”,讓人覺得水平下降,或者意味著這路書風已經(jīng)過時了。種種因素之下,多數(shù)人開始告別國展。
因此,處好私心之樂和展覽賽事之間的矛盾,需要的是理性和智慧。功利與淡泊,浮躁與寧靜,激情與閑情,成為當代書壇長期共存且難以統(tǒng)一的矛盾體。然而文變?nèi)竞跏狼椋覀兒茈y無視展覽對當下藝術(shù)的巨大作用,面對歷史和來者,捫心自問,我們是順應之,還是退守精神一隅,自娛自樂?這些對立矛盾因素均在不同層面影響著書家的書法創(chuàng)作和藝術(shù)道路。對于當代的書家來說,藝術(shù)生存的文化環(huán)境和展示環(huán)境已經(jīng)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藝術(shù)審美的方式和評價體系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對抗和逃避,顯然是一種消極的態(tài)度的。只要懂得在個體和展覽自由二者之間,找到適合自己生命狀態(tài)的契合點,掌握在藝術(shù)上退守與進取之間恰當?shù)摹岸取保谙硎芰怂叫闹畼返耐瑫r,卻不期然中收獲了在公共展示過程中的自我價值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顯然是一種相對完滿的狀態(tài),它需要心境抉擇的智慧,需要的是自我修為的提升、開悟以及面對環(huán)境超出常人的適應能力。中國書法的當下與未來也不能只是存在于全國性書法展覽的體制之下,更不應該成為書家追逐名利、評委從中獲利的工具,其藝術(shù)表達的終極目標和最高境界應該是回歸筆墨書寫的閑情逸致。
[參考文獻]
[1]《中國書法》雜志,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主辦。
[2]《書法》雜志,上海書畫出版社主辦。
[3]《書法報》湖北省文聯(lián)主辦。
[4]黃映愷,騎墻心境——展覽時代的書畫家心境抉擇,藝術(shù)生活,2013年5月
[5]彭貴軍,基于現(xiàn)行展覽體制下書法創(chuàng)作及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 美術(shù)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