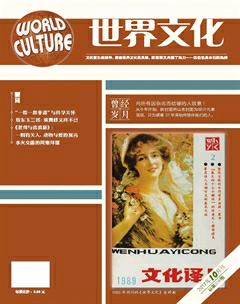女性寫作視域下的蕭紅與曼斯菲爾德
孫可佳
蕭紅(1911—1942)和曼斯菲爾德(1888—1923,英國女作家)的女性意識的形成,都與她們自身不幸的婚戀經歷有著很大關系,其中更因戰亂、漂泊、貧病、孤獨而加深了這不幸。
蕭紅的一生正值中國最多災多難的歲月,而她并不是個堅強而有勇氣的新女性。近代的新秩序至少在理論上倡導男女平等,青年一代以全部身心投入這所謂的現代化之中——然而,對于身心方面都欠缺準備的人,特別是女性,必將付出艱辛痛苦。蕭紅在保守的封建家庭中長大,自幼缺乏母愛,天性敏感、不更世事,成年后又置身于一個極不健全的環境中。我們從她的寫作和友人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她雖渴望自持自立,卻又需要依靠他人,特別是男人。她總令自己陷入極端困境中,然后選擇最困難的出路;她很少聽從那些關心她的女性朋友的勸告(如許廣平、池田幸子),而總依順于男人的需求和索取。
蕭紅初中畢業后被許婚汪氏,繼而出逃,與人同居后又遭遺棄,回到哈爾濱時潦倒困頓、懷有身孕,被蕭軍解救,與其結為伴侶。然而與蕭軍的遇合正是她不幸婚戀與女性意識萌生的開始。
蕭紅的敏感、柔弱、缺乏自信、猶豫不決,與蕭軍的健壯、粗暴、剛愎狂妄形成了鮮明對比。據蕭軍自述,他性格粗暴、酗酒、好打斗,蕭紅在與其同居的經歷中,不僅為其管理家事,還要忍受拳打腳踢甚至是感情不忠。蕭紅自己曾寫道:
我愛蕭軍,今天還愛,他是個優良的小說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患難中掙扎過來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卻太痛苦了!我不知你們男子為什么那樣大的脾氣,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為什么要對妻子不忠實!忍受屈辱,巳經太久了……
蕭紅開始不時流露出對自身女性角色的反思。她曾向聶紺弩這樣說:

你知道嗎?我是個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討厭呵,女性有著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還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災難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是這樣想的我呢,還是那樣想的是。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此時的蕭紅,正處在和蕭軍、端木蕻良的三角戀情中,她想要脫離困境,卻又流露出強烈的自憐情緒。她性情溫柔,“說話時聲音平和,很有韻味,很有感情,處處地方都表現出她是一個好主婦”,但是“她的溫柔和忍讓沒有換來體貼和恩愛,在強暴者面前只顯得無能和懦弱”。對此她自己在《呼蘭河傳》中有一段敘述,可看作對自身和中國女性的深刻洞察:
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溫順,似乎對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兇猛,似乎男性很不好……那么塑泥像的人為什么把他塑成那個樣子呢?那就是讓你一見生畏,不但磕頭,而且要心服……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來為什么要那么溫順,那就告訴人,溫順的就是老實的,老實就是好欺負的,告訴人快來欺負她們吧!
……怪不得那娘娘廟里的娘娘特別溫順,原來是常常挨打的緣故。可見溫順也不是怎么優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結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蕭紅女性主義觀點的形成,也與蕭軍的性別地位觀念(大男子主義)有關。與蕭軍在一起的這段時期,蕭紅在《生死場》等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反男性”的態度。她常常刻畫女性在男性中心社會中的可悲地位和悲劇命運,引起人的共鳴。譬如《生死場》中的王婆、金枝、月英,她們是在丈夫的權威下忍聲吞氣,忍受肉體的折磨;她們沒有獨立的人格,如同工具和奴隸,更無法獲得應有的理解與尊重。
蕭紅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之后,其悲劇命運并未扭轉,女性意識仍然強烈。從前是身體傷痛,此后是精神冷暴力。她曾跟聶紺弩抱怨端木是“膽小鬼,勢利鬼,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裝腔作勢的”。靳以也認為“端木是個自私、矯飾的懶蟲,他好像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梅志曾敘述蕭紅和端木在重慶北碚之時,兩人看起來如何冷淡,蕭紅的模樣如何頹唐。端木的冷漠是顯然的。1938年夏,日軍轉向武漢三鎮,7月間端木計劃由武漢入川,8月和梅林、羅烽坐小船去了重慶,卻未帶上蕭紅。蕭紅在漢口的最后一個月里寫下了短篇小說《汾河的圓月》:一個和小孤女相依為命的老瞎女人,兒子戰死了,媳婦也出走了,最終老瞎女人瘋了,汾河邊的月夜下,她依稀聽到愛國宣傳隊在演戲。其實這正是當時蕭紅沮喪心情的寫照。蕭紅在《呼蘭河傳》中對團圓媳婦、王大姑娘兩位年輕女性生命毀滅的敘寫,以及《小城三月》里翠姨向往愛情卻無法掙脫封建束縛的悲劇,說明她已認識到根深蒂固的封建積弊對女性的殘害。

到了香港,多年在饑餓邊緣掙扎、一再被打擊的蕭紅終于病入膏肓,戰亂之中又染肺病。此時的她仍然是被女性解救的——史沫特萊送她到香港瑪麗醫院,供她衣服和金錢。蕭紅去世后,駱賓基和端木蕻良又因蕭紅發生沖突:駱拿出一封蕭紅痛罵端木的信,并透露自己和蕭紅約定等她康復后共結秦晉之好。據孫陵回憶,駱賓基于蕭紅生前記下了有關她作品版權的遺囑:《商市街》給她弟弟,《生死場》給蕭軍,《呼蘭河傳》給駱自己,端木一無所得。盡管駱賓基事后否定孫陵的回憶,稱沖突與版權無關,但這些足以證實,蕭紅一生所遭不幸確是屢受男性的欺凌所致。正如她臨終前那句:“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為我是個女人。”endprint
蕭紅的痛苦與不幸大半是為遇人不淑及所處時代所牽連,而非其天性反叛使然。曼斯菲爾德同樣歷經了幾番戀愛的失敗和婚姻的痛苦,在戰亂與貧病中萌生和發展了女性意識——但她的每一次痛苦掙扎都是源于自由浪漫的天性和堅定的自主選擇。
曼斯菲爾德的家庭環境對其女性主義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啟蒙作用。曼斯菲爾德生在一個傳統的資產階級家庭,其父哈羅德是銀行家,母親安妮是家庭主婦。母親的全部時間都在“拯救他(曼的父親),照料他,使他安靜下來,聽他說自己的事”,“與其說是溫柔忍耐,不如說是無精打采,得過且過,她關心丈夫的需要,但對孩子疏遠冷淡”。為了生兒子,安妮連續生下4個女兒(一個夭折),身心俱疲,但卻并不愛自己的孩子——這正是一種試圖逃離女性傳統角色的表現。在曼斯菲爾德的許多作品中,我們都能找到母親安妮的影子。
1906年,曼斯菲爾德從倫敦皇家學院歸來時,放棄父姓,改用外祖母娘家的姓“曼斯菲爾德”,并開始使用筆名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她不想讓自己陷入傳統家庭里,于1908年7月獨自前往英國,開始了文學生涯,并走上反抗“維多利亞傳統家庭中女性所扮演的傳統的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的道路。
曼斯菲爾德的家庭經歷與蕭紅極為相似——同樣在傳統父權家庭長大,缺乏母愛,與祖輩親屬要好,接受教育后便擺脫了封建家庭。如許廣平所說,“她(蕭紅)喜歡像魚一樣自由自在的吧,一個尋求解放舊禮教的女孩子的腦海,開始向人生突擊,把舊有的束縛解脫了,一切顯現出一個人性的自由……可憐的是從此和家庭脫離了,效娜拉的出走!從父親的懷抱走向新的天地,不少奇形怪狀五花八門的形形色色的天地,使娜拉張皇失措,經濟一點也沒有。”蕭紅、曼斯菲爾德,都是各自時代環境中的“娜拉”。
曼斯菲爾德是個早熟且熱烈追求愛情的女子。她13歲時愛上了小提琴手加納特,18歲時第一次真正戀愛:在返回惠靈頓的途中與一位英國板球運動員相遇,“我想激怒他,在他心底喚起奇特的感情,他見過那么多世面,這真是一種征服”。戀情在她父母的監控下不了了之。回到惠靈頓后,曼斯菲爾德經歷過短暫的同性戀。在倫敦,20歲的曼斯菲爾德與大她11歲的聲樂教師波登一見鐘情,結識數周便舉行了婚禮。但結婚當晚她就不辭而別,去利物浦追隨小提琴手加納特,并以加納特妻子的身份成為合唱隊的一員,不久懷孕。此后,她客居比利時和德國,在巴伐利亞時不幸流產——這是她一生唯一的孩子,她的身心受到嚴重打擊。她在1909年5月的日記中寫道:
將來如有一天孩子問我:“媽媽,我是在哪兒生的?”我便回答:“在巴伐利亞,親愛的。”我想那時我會重新感到今天的寒冷,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寒冷,心里的,手上的,靈魂里的寒冷。
將近十年后,曼斯菲爾德將失去孩子的痛苦寫進《巴克媽媽的一生》中,“她感到難以獨自忍受失去孩子的痛苦,她渴望有一個孩子可以照料”。
掙脫了傳統家庭,歷經各種戀愛失敗的曼斯菲爾德此時已有了顯著的女性意識和大膽看法。她在1908年5月的日記中寫道:

我剛讀完伊麗莎白·羅賓斯的《來找我》……我確實已經意識到婦女在未來的世界上能發揮多大的能量,盡管這一意識還有些模糊。說實在的,到目前為止,她們還從未得到任何機會來發揮自己的能力。還說什么“開明的時代”,“解放了的國家”,純系一派胡言!我們被牢牢地套在自制的奴隸枷鎖中。是的,我現在認識到這些枷鎖是自制的,所以必須自己去把它銷毀。
總之,我所需要的是力量、錢財和自由。有一種令人感到乏味的理論認為,在世界萬物之中歷代婦女真正繼承下來的只有愛情。這種理論嚴重地妨礙了我們前進。我們必須逐走這個可怕的妖魔,然后,然后就會得到幸福和自由。
1912年,曼斯菲爾德結識了《韻律》雜志主編約翰·米德爾頓·默利,他們墜入愛河,后來一直同居。1918年,凱瑟琳的名義丈夫波登提出了離婚申請,默利才與凱瑟琳正式結婚。同默利在一起的日子給了她不少幸福。但后來隨著曼斯菲爾德的肺結核不斷惡化,他們輾轉于歐洲各國進行治療,曼斯菲爾德感到默利對自己疏于關心,時常覺得孤獨、恐懼,兩人之間的感情也不斷出現危機。
和默利在一起后,曼斯菲爾德筆下有了更多女性意識的直接表達,且充分體現了她的性格特點。1913年夏她在給默利的信中寫道:
我想我是個很不合格的家庭主婦。如果沒有適當的方法,理家就會占去許多時間……我討厭做這些事,討厭得很,討厭極了,而你呢?跟別的男人一樣,認為由女人伺候理所應當。我來當女仆的態度是不會太溫和的。沒有其他事可干的女人干家務沒有什么……而你卻說我是暴君,夜晚我累了,你還要感到奇怪。像我這樣的女人面對的難題是無論如何我也忘不了手頭的工作……然而,我愛你。我既感到驕傲同時又感到屈辱。你不理解我,然而卻愛我,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她和蕭紅一樣不喜歡做管家主婦,但她顯然沒有蕭紅那樣溫順。

1920年曼斯菲爾德評論D.H·勞倫斯《失去的女孩》時,表達了她的一些女性寫作觀點:
他說他的女主人公是非凡的,不同于一般。這是多么有意義的呀!但是看看她。譬如她年輕的時候——她高興地和醫生們一起做粗鄙的、喧鬧的游戲。他們可能是互相沖撞的野獸——僅此而已。再譬如男主人公把她推入廚房,與她發生關系,然后她又唱著歌繼續洗碗。這是恥辱。再譬如那個干活的婦女邀請那個意大利人到她的臥室去,一場腐化、骯臟的丑劇。全都是虛假的。一派胡言!
1913—1915年間,曼斯菲爾德來去奔波,同默利的關系從熱戀到疏遠,并與法國作家弗朗西斯·卡爾科互寫情書。1915年2月,她直赴卡爾科的部隊駐扎前線格雷城,月底才回到默利身邊。
曼斯菲爾德與默利的分合一直持續到她去世前。1920年12月至1921年5月是一個紛亂的時期,曼斯菲爾德再次病倒,同時由于默利與貝白絲科公主(牛津區伯爵的女兒,其丈夫是羅馬尼亞貴族)的友情關系,他們發生誤解。1922年6月,曼斯菲爾德同默利一起回到瑞士。由于二人對曼斯菲爾德病情治療的分歧,他們分居了:默利住在朗東,凱瑟琳則住在山另一側的謝爾。他們每天通電話,并且默利會在周末看望她。曼斯菲爾德向他保證“我非常地愛你”。這期間曼斯菲爾德反思過自己的“任性”:“我的唯一憂慮是約翰。他應該同我離婚,和一個真正快樂、年輕、健康的人結婚,生兒育女,而讓我做他們的教母。我根本做不了妻子。” 8月7日,她寫下給默利的遺書。在遺囑中她把所有手稿都留給了丈夫,并希望默利再婚,還將自己的小珍珠戒留給了繼任者。
蕭紅和曼斯菲爾德所處的時代,一個是新舊交替、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思潮東漸的中國近代,一個正值西方女權運動聲勢日益浩大之時。她們女性意識的覺醒與成熟,與二人相似的婚戀經歷密切相關,當然也脫離不開家庭環境的影響:生于傳統父權家庭,缺乏母愛,青少年時代沖破家庭羈絆,歷經婚戀的挫折與喪子之痛,得不到丈夫足夠的關懷,在貧病孤獨中英年早逝。她們在短暫的一生中逐漸形成了女性意識,并深刻地體現在各自的文學創作中。盡管她們都沒有像弗吉尼亞·伍爾芙那樣,形成系統的女權主義理論,甚至從未自稱過女權主義者,但是她們以作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關注并書寫人類諸多苦難中女性的悲劇命運,流露出深刻的女性主義思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