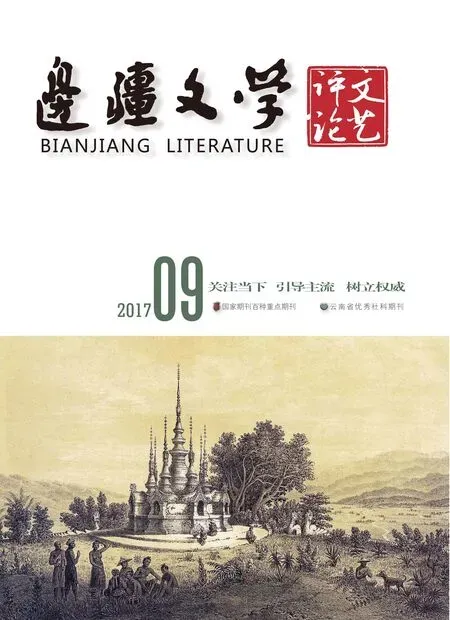文學應當引導人類仰望星空
張 偉
學人觀點
文學應當引導人類仰望星空
張 偉
·主持人語·
文學評論與創作一樣,都是用真心去體味真心,用善意去激揚善。本期推介的《用善良替靈魂贖罪》,就是通篇貫穿著正能量、傳遞著溫暖和愛、昭示著舍己為人的善良的人性道德情懷。論者高度贊譽作家陳倉在用一顆善良的心書寫著一部有溫度的作品,用文字表達著對人民命運的悲憫、對人民悲歡的關切。其在創作談中說到的:“善是一味藥,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別人。”這種思想很有價值。余德莊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在生活的深水靜流中會有更多令人驚艷的文學綻放!”也是很有意思的思想。(蔡毅)
一
從古到今,人類的生命都充滿了諸多痛苦:必須在大地上長年揮汗勞作,才能夠獲取衣食;人與人之間充滿欺詐、掠奪、殺戮和不平等;要受到無窮無盡的欲望的驅迫與煎熬,卻又不可能都獲得滿足;要受到生老病死的折磨,最終回歸塵土;作為一種有主體意識的動物,人類總有一種追問生命意義的沖動,但實際上并不存在確定的生命意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追問生命的意義也不過是自尋煩惱罷了。正因為人類有太多的痛苦,所以許多悲觀主義哲學家從根本上否定了人生的意義,認為人完全不值得活,生命是上帝贈給人類的最壞禮物。比如中國古代的莊子就是一位登峰造極的悲觀主義者,他曾講述過一個“髑髏見夢”的故事:“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丑,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之上,無臣之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至樂》)可見莊子對人生的否定是多么徹底!古今中外為人類的苦難處境發出過悲憫太息的哲人還不知有多少。
盡管個體的生命旅程短暫、痛苦且終有一死,但人類畢竟還是戰勝了一切苦難,繁衍下來了,并且創造出了燦爛的文明,這固然是因為人類有頑強的與生俱來的生存意志,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還有一個富有詩意的理想境界,讓人類的靈魂能夠棲息其間,蕩瑕滌垢,凈化自身,獲取勇氣和力量,從而戰勝苦難。這個詩意的境界很大程度上是文學建構的。文學是人類痛苦的心靈中綻開的花朵,現實世界有許多的假,文學世界卻有赤子之真;現實世界有許多的惡,文學世界卻有最高之善;現實世界有許多的丑,文學世界卻有無盡之美。能夠在平庸、齷齪、痛苦的現實世界之外建構一個美好的理想世界,就是文學最大的魅力之源。文學不同于宗教,世界各地的宗教雖然流派繁多,教義不同,但一些主要的宗教流派幾乎都異口同聲地告訴人類:一切皆苦,現世的生活沒有意義,只有刻苦修行,皈依宗教才能獲得最后的解脫,永恒的幸福。所以宗教盡力貶抑此岸世界的生活,而另外建構了美好的彼岸世界。宗教能讓人類感受到天國的光輝,當勞苦抑郁時,可以仰望著冥冥的蒼天進行祈禱。但宗教的彼岸世界是那么遙遠,它的各種戒律又是那么嚴酷。當肉體回歸塵土之后,靈魂究竟能否升入天國依然是一個謎,但這個渺茫的天國卻讓人類不得不忍受此岸世界痛苦的煎熬。所以除了少數意志堅定者以外,很少有人能夠真正如宗教家倡導的那樣,做一個苦行者。文學卻與此不同,雖然它也可以建構一個不同于現實世界的理想世界,但它卻又美化著我們此岸世界的生活,使平庸的生活富有了色彩、詩意、情愛和美。可以說,文學是人類精神的一方凈土,對現實的齷齪感到悲觀絕望的人們,可以在文學這一方凈土里尋找到靈魂的棲息地。
有了文學,今人可以與古人進行精神對話;有了文學,足不出戶的人們可以將思緒放飛到遠方;有了文學,異鄉漂泊的游子能夠感受到家園的溫馨;有了文學,住在茅草屋里的人們能夠把屋前的小菜園想象成百花盛開的花園;有了文學,被愛情遺忘的灰姑娘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美麗多情的白雪公主;有了文學,陷身于罪惡泥潭里的人們也能感受到神圣的召喚,從而幡然悔悟,棄惡向善。文學可以直接描寫并謳歌真善美,文學也可以通過描寫并否定假丑惡來間接地謳歌真善美。古往今來,誨淫誨盜的作品并不少,但那種沉湎于假丑惡之中而看不到理想光輝的作品是不配進入文學的神圣殿堂的。如果不是在始終不渝地鞭撻著假丑惡,謳歌著真善美,那么文學早已死亡了。為什么?就是因為作為一種從低等動物進化而來的高等動物,人類雖然不能徹底擺脫自身的動物性,并因此使得世間充滿了假丑惡,但人類畢竟是天地間唯一具有精神性的動物,高度的精神性注定了人類身永遠不會以不完美的現實為滿足,正如詩人屈原說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其內心必然要追尋真善美,則是毫無疑義的,古往今來的人類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作為一種有著與生俱來的局限性的動物,人類追求真善美的沖動是不可能取得完全成功的。非但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甚至可能招致慘重的失敗,這使得歷史充滿了悲劇意味。人類的心靈固然有可能因為悲劇而氣沮,但不同樣也可能因為悲劇而獲得凈化與升華嗎?神秘的真善美之山啊!哪怕你的腳下倒下了一千名追求者,第一千零一名追求者又來到了你的腳下。莫笑世人的執著,因為這正是人類的特征啊!除非把心靈從人類的體內取走,使其只剩下一個軀殼,否則人類怎么可能停止追求真善美的腳步呢?如果停止了對真善美的追求,那么人類還是人類嗎?文學是表現人類心靈的,又怎么可能不謳歌、不追尋真善美呢?正是因為文學能夠建構一個美好的世界,所以千百年來,文學一直在凈化著人類的心靈,建構著人類的精神家園,使人類雖然充滿了苦難,但依然能夠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
二
在中國的現當代文學里,依然有作家在執著地謳歌著真善美。比如沈從文,他以一顆悲憫之心,建構了一個由青山綠水,白塔渡船,古老風俗以及樸素淳厚的人間情愛組成的充滿自然美、風俗美、人情美的湘西世界,其中還有最美麗純真、執著專一的愛情方式。這個世界一出現,就獲得了悠久的藝術魅力。在那個血與火的時代里,它宛如一個世外桃源,是戰亂與饑荒中的人們心中的一方樂土。而在當今這樣一個技術時代里,人類遠離了自己的童年境界,在高速度、快節奏、世俗化、功利化的生活中精神無限焦慮,因而返樸歸真的浪漫心弦不斷在靈海深處奏響。湘西世界又獲得了新的美學意蘊,它宛如一汪甘冽的清泉,滋潤著現代人干涸的心田。又比如女作家冰心,她在一個人與人之間相互殘殺的時代里,依然用溫婉的筆,謳歌著人與人之間的仁愛。正如她在小說《超人》中說的:“天下的孩子都不是彼此疏遠的,而是彼此結合的。”這使她的作品成了一曲曲愛的頌歌。也許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敵意與殘殺使這種愛的頌歌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幼稚可笑。但不正因為如此,愛的頌歌才如此可貴嗎?又比如徐志摩,在“一個荒歉的年頭”里,不斷地謳歌愛與美的理想,信仰“人與人之間互助的動機一定會超過互殺的動機”(《新月》發刊詞)。為尋找愛與美的理想,他不怕“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沖入了茫茫的黑夜”,最后竟以身殉了。他的生命雖然如劃過長空的流星一般短暫,但他留下的謳歌愛與美的清麗詩篇不是讓許多心靈感受到了藝術的恒久魅力嗎?
但我們不得不悲哀地指出,由于時代的原因,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真善美。文人們起初則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烏托邦理想,將千百年來的無數哲人關于仁愛的訓誡拋到了九霄云外,賣力地鼓吹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殘殺。他們希望在人間建立天國,但根本不明白依靠血腥的相互殘殺,不可能殺出一個人間天國。即使天國降臨人間,也會被滔滔血河卷走。
其實人間就是人間,人間不可能建立天國,在人間進行天國實驗,收獲的只能是千百萬人的尸骨和血淚。后來中國大地上發生的無數夫妻相互告密,朋友相互出賣,子女批斗父母,學生毆辱老師的事件,以及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無知而又暴戾的青年發狂一般橫行神州大地,使得無數人成了人間天國的祭品的慘劇,不就證明了這一點嗎?那些擅長挑撥人與人之間相互殘害的政治人物當然要負更大的責任,但作家們真的清白無辜嗎?作家的責任應當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愛啊,為什么要謳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殘殺呢?為什么不干脆改行去充當劊子手呢?在同樣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殘害被發揮到了極至的時代,俄羅斯的索爾仁尼琴卻創作出了震撼人心的《古拉格群島》,對人迫害人的現象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為人類的相互迫害推波助瀾的中國作家們能不感到慚愧嗎?
等到烏托邦理想坍塌,消費主義的時代來臨后,作家們則又放肆地嘲弄一切的理想與崇高,以為人間的一切都是虛假的,只有現世的感官享樂才是真實的。以《廢都》而言,那就是一個肉欲至上精神頹敗的世界,那里并不缺乏文化人,但那些文化人只會為了權力、地位、金錢、女色而進行無休止的欺詐與爭奪。那里只有卑賤污穢,而沒有高貴純潔的心靈。其他大多數作家的作品也差不多,他們甘愿充當精神上的侏儒。與群星璀璨的古典文學相比,現代尤其是當代的大部分文學作品,卻只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平庸、卑賤、狡詐、虛偽、墮落、殘忍,卻難以看到詩意的理想的光輝。當代作家們似乎已經喪失了感悟和抒寫真善美的能力,而幾乎被污穢淹沒了。或許這不全是作家們的錯,是中國的現狀本來如此,我們所處的本來就是一片干枯的荒漠。但作家難道不能把心中的真善美理想化做甘泉,從筆底滔滔流出,澆灌腳下這片干涸的土地,讓它滋長出濃密似錦的花木嗎?替墮落中的人類守護住一片精神圣地,是作家們的神圣職責,否則為什么要當作家,不去做商人、政客呢?
中國現當代文學什么都不缺,不缺狂熱、血腥、淫穢、齷齪、卑鄙、無恥,獨獨缺乏一種執著地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品格,就像久旱的稻田缺乏霖雨一樣。為什么現代文學不能向我們提供一個具有美好圣潔心靈的人物形象呢?也許后代的人們會把現代文學當作研究我們時代社會風貌與精神狀態的資料,但作為文學作品,它們的生命將會是十分短暫的,也許不過是過眼云煙罷了。
三
我們當然知道,在人類的宗教精神早已失落,烏托邦的理想也已坍塌,物質主義席卷天下的現代社會里,人心充滿了卑瑣的欲望和污穢的東西。人類整天追逐的不過卑俗的感官欲望的滿足,已經沒有什么高尚的精神追求了。我們看到的是,人類的精神境界不但沒有隨著物質文明的進步而提升,反而日趨污下,人性的丑惡面是赤裸裸地、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既然現代社會里充斥的是由污穢的靈魂里流溢出來的污穢言行,那么要文學完全脫離現實就是不可能的。以愛情而論,它本是人類最美好的感情,無數的作家曾經向往它、追求它、贊美它、謳歌它。但在我們時代,愛情早已被性取代了。愛情本來也應當包含性的因素,這是我們承認的事實,但在當代社會里只剩下了性,愛早已不見了。當純真的愛早已在人間消失之后,當代作家怎么可能寫出愛情的美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中的污穢,不過是人心和社會的污穢的寫照罷了。文學除非想粉飾現實,否則就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我們反感作家們粉飾現實。有一段時間歌功頌德的作品連篇累牘,泛濫成災,將丑惡的人間地獄妝扮成了美麗的塵世天堂。時過境遷之后,此類作品終于引起了普遍的厭惡,被扔進歷史的廢紙簍里去了。但文學并沒有回歸真正的真善美,而是跳進了另一個污水潭里,樂此不疲地寫放縱、寫物欲、寫墮落,挑逗讀者的感官欲望,迎合讀者的粗鄙心理,滿紙齷齪。當然他們說文學是現實的反映,現實如此,文學也只能如此。但問題是,文學只需要實錄現實的丑惡就可以了嗎?
否!文學絕不能失去理想性,因為文學是人類的精神產品。如果僅僅是照抄現實,甚至以欣賞的態度來描寫生活中的假丑惡,文學就只能為人性的淪喪推波助瀾,而根本不可能凈化人的心靈世界。現實可以是齷齪的,但文學永遠應當是純潔的。文學應當是淤泥濁水中盛開的潔白的蓮花。《紅樓夢》不是也描繪了驚心動魄的丑惡嗎?但它卻建構了一個無比純潔的女兒國。如果文學僅僅是照搬現實,而沒有更高尚的東西在里頭,那么人類還要文學做什么呢?人類曾自詡為萬物之靈,但一旦喪失了精神的追求,那么跟低等動物還有什么區別呢?
在現代社會里,有太多的東西誘惑著人類,使人類降低自身的尊嚴,甘心做粗俗欲望的奴隸,人心充滿了冷漠、貪婪和丑惡。也正是因為如此,文學才更需要真善美。作家應該通過自己的作品讓冷漠、貪婪和一心追求粗俗物欲的人類知道,這個世界上除了雞蟲得失以外,還應當有真誠、善良、淳樸等美德,應當有純真的愛情,以及其他許多比物欲的滿足更值得追求的東西。當人類的心靈被卑瑣的欲望填塞了,變成了一個黑暗世界的時候,文學是可以照徹人心的一束普照光,如果文學都墮落了,那么人類的精神境界還有一絲一毫提升的希望嗎?人性可以墮落,而文學卻不能跟著時代一起沉淪,只要文學領域還保留著一份圣潔,那么人性就還有一絲提升的希望。如果文學也徹底沉淪了,那么人類精神將重新落入茫茫的黑暗之中,并永遠沉淪下去。“哀莫大于心死”,難道這將是人類最后的結局嗎?
這是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假丑惡曾經把自己妝扮成真善美,光天化日之下橫行,捉弄著愚昧的人類。而真正的真善美卻被不斷潑上了污水,以至于人類已經不相信世界上還有真善美的存在。所以現代人類如同生活在一個虛無的荒原上,像幽靈一樣漂浮著。作家也是人,有人的各種欲求,也有人的各種缺點,我們并不奢望作家們個個都是圣人。但畢竟創作是一項崇高的事業,我們真誠地希望作家們能夠秉持良知進行創作,讓作品中少一些偏激、暴戾、誨淫誨盜,讓筆下多一分溫暖、多一分情愛,多一些真善美。
即使是一個假丑惡充斥的鬼蜮世界,只要作家的心靈中有真善美,他也會在一個鬼蜮世界里開辟出一個至真至善至美的世界,我們也必定能從他的作品中讀出真善美。可怕的是作家完全被假丑惡同化了。
這是一個工具理性統治的時代,人類的性靈在工具理性的重壓下呻吟著;這又是物質主義的時代,人類沉湎于對物欲的追逐,似乎已經忘卻了神圣的事物,也忘卻了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而僅僅在物質世界里自娛自樂,所以需要一種力量把人類從平庸卑賤的狀態中拯救出來,使人類能夠仰望天空,仰望星辰。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描繪過宗教衰落后人類的精神狀況:“人的精神已顯示出它的極端貧乏,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獲得一口飲水那樣在急切盼望能對一般的神圣事物獲得一點點感受。從精神的如此易于滿足,我們就可以估量它的損失是如何大了。”在一個人類的心靈茫然無歸的痛苦時代,文學對真善美的謳歌,或許并不足以引導人類踏上通向真善美的征途,甚至只能給人類帶來無名的哀愁、詩意的傷感。對人類的心靈來說,無名的哀愁、詩意的傷感也許是一種重負,但對人類的長遠生存來說,它們也許并不完全是不祥之物,而是不可或缺的。當文學平面化了,再也沒有無名的哀愁、詩意的傷感,乃至對于神秘命運的敬畏,那么生命將變得多么蒼白!
在當代社會里,那些挑逗性的文字或許能引起轟動,真正的文學是寂寞的。真正為了堅守人類精神家園而寫作的人,就不要期待鮮花、掌聲和其他各種世俗的功利。作家應當像夜鶯在黑暗里歌唱一樣,執著地謳歌真善美,謳歌人類古老的美德和理想,哪怕沒有聽眾,也要為之嘔心瀝血,無怨無悔。只要有一個讀者在讀了你的作品以后,變得更純潔,更高尚,更仁愛,更景仰真善美,你就功德無量了。我們的社會充滿了貪婪與丑惡,人心需要凈化。文學至少可以用真善美的光輝,照燭幽暗的人心,凈化被貪欲污染的靈魂。文學應當引導人類超越塵世的得失,去仰望美麗的星空。

王光林 日常no.3 46x69cm 紙本水墨 2015年
(作者單位:昭通學院人文學院 )
責任編輯:楊 林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昭通鄉土小說創作研究》研究成果 類型:基礎性研究,項目編號:2016ZZX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