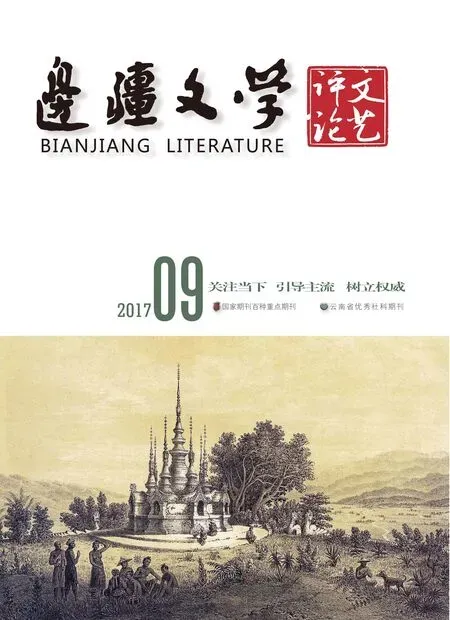淺析《薩拉辛》敘事中隱含的邏格斯權威
孫佳麗
淺析《薩拉辛》敘事中隱含的邏格斯權威
孫佳麗
“邏格斯”(Logos)來源于希臘文,它有兩層含義,既指詞語,更為常用的是表示本原性的或終極的真理,類似于我們所說的“道”。而“邏格斯中心主義”則是雅克·德里達為適應其解構主義思想而提出的一個概念,德里達認為,西方自柏拉圖以來的理性主義思想傳統是一種邏格斯中心主義傳統,即總是把真理的本原歸結于邏格斯,或是口說的話,或是理性的聲音,或是上帝的話。“在一個傳統哲學的二元對立中,唯見一種鮮明的等級關系,而絕無兩個對立項的和平共處。一個單項在價值、邏輯等等方面統治著另一個單項,高踞發號施令的地位。解構這個二元對立,便是在一特定時機將這一等級秩序顛倒過來。”因此,可以認為,邏各斯中心傳統總是試圖追求一個永恒的中心或一種絕對的權威,而這種中心或權威是通過一系列等級分明的二元對立表現出來的,在二元對立中,總會有一方處于中心地位,而另一方被棄之邊緣。總之,就現代的學術觀點,“邏格斯”代表的就是一種權威性的、上帝般的存在,而這種權威在《薩拉辛》中如何體現呢?在此,先簡單介紹一下文本《薩拉辛》,《薩拉辛》是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的作品,在《人間喜劇》中處于“風俗研究·巴黎生活場景”部分,它大體上講述了如下內容:在巴黎上流社會的舞會上,一個年輕人“我”為了討好一位少婦,就用一個故事來吸引她,從而達到滿足自己情欲的目的,而這個故事就是薩拉辛和贊比內拉的“愛情”故事:年輕雕塑家薩拉辛帶著對藝術的狂熱愛戀來到羅馬,并在這里愛上了歌唱家贊比內拉,通過種種努力,他和贊比內拉有了親近的機遇,然而在“愛情”就要達到頂峰時,他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原來贊比內拉是個被閹割的男人,在他惱羞成怒,打算殺了贊比內拉時,卻被贊比內拉的保護人——紅衣教主所殺。下面筆者將從非線性敘事時間結構、“潛變化”敘述者、身體倫理敘事三個角度來論述文本的敘述策略中內蘊的“邏格斯式”的話語權威。
一、非線性敘事時間
作為現世的存在,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超脫于時間,具有一定長度的文本也必須是有一定時間度量的讀物,而時間維度也是作為敘述彼此之間區分的依據。敘事學對敘述時間的硏究主要是指對敘事文本的時間的關注。敘事文本時間又可以劃分為:寫作時間、事件時間和敘述時間。事件時間是指事件真實發生的自然時間,敘述時間則是指文本中故事呈現的時間方式,事件時間與敘述時間的關系一直是理論家關注的重點。就《薩拉辛》來說,按照事件時間應該是先敘述薩拉辛的故事(過去時)——“我”與少婦的故事(現在時),然而實際上文本呈現的時間是現在時(“我”與少婦的故事)——過去時(追憶“薩拉辛”故事)——現在時(“我”的故事)。這兩種時間順序是有出入的,前者可以說是“線性的”敘事時間,中間不存在回溯的時間結點,而后一種敘述則是“非線性的”。這種時間呈現方式用專業術語來說就是“錯時”。關于“錯時”(anachronie)又譯“逆時序”、“時序倒錯”,又稱“時間畸變”。克里斯丁·麥茨說,由于敘事中包含有敘事和故事兩個時間序列,“這種雙重性不僅使一切時間畸變成為可能,挑出敘事中的這些畸變是不足為奇的,更為根本的是,它要求我們確認敘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種時間兌現成另一種時間。”托多羅夫認為:“敘述時間(話語時間)的順序永遠不可能與被敘述時間(事件時間)的順序完全平行;其中必然存在前與后的相互倒置。這種相互倒置的現象應該歸咎于兩種時間性質的不同:話語時間是線性的,而故事時間則是多維的。兩者之間既不可能平行,則必然導致錯時。”而這種“錯時”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故事的斷層。敘述者本身處于一層故事層,成為“故事外層”,而他所追憶的故事屬于故事中的故事,成為“故事內層”。由逆時序的時間敘事所形成的兩個故事層面相互之間也有些微妙的關系。下面結合文本《薩拉辛》來具體分析。
《薩拉辛》的非線性敘事時間表現為“故事套故事”的結構模式,“我”和少婦的故事是屬于外故事層面,而薩拉辛的故事則屬于內故事層面,從而把整個故事分裂成兩層敘事。這兩個故事內部的敘事時間都是嚴格按照傳統的線性敘事來完成的,將兩者并置,在結構上是平行相對、相互獨立的。一層是發生在18世紀,講述了薩拉辛小時候童年上學經歷,跟著老師布夏東學習繪畫與雕塑的過程,以及到意大利羅馬進一步深造,直到遇上女歌手贊比內拉,然后一步步墜入情網,最終認識到真相,故事終結于薩拉辛的死亡,關于薩拉辛這個人一生的故事就結束了。而另一層故事發生在19世紀,也可以簡單概括為這樣的一條敘述線:“我”在舞會與一個美麗的少婦相遇、交談,為了吸引她的注意從而滿足自己情欲的目的,就給她講了一個“薩拉辛”的故事,最終少婦拒絕了“我”。這兩個故事都遵循著“開端、中間、結局”的時間敘事模式。這是表面上的分離與獨立,實際上兩者之間關系并非如此“涇渭分明”,而是相互糾纏與粘連的,這種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表層結構來看,兩個故事的敘述是相互穿插的,這種穿插并不是毫無關系的套入。“我”給少婦講關于薩拉辛的故事,在此,這個故事已變得不純粹,它變成一種類似工具的存在,而少婦對此很感興趣,從這里可以證明內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推進外故事前進的手段,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外故事的“催生”使得內故事的價值得以實現,更有甚至,內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外故事的故事走向:少婦聽了薩拉辛的故事,對現實很失望,從而拒絕了“我”的請求。另外,“我”在進入內故事敘述層面中也是隨時被受述者不斷拉回現在時間,這里面包含的技巧將在下一部分分析。
實際上,兩者之間更為深層的關系反映在各自所包含的思想內蘊中。巴特對兩層故事關系的分析是這樣的,他認為導致薩拉辛愛情悲劇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對閹割的恐懼,在整個薩拉辛的故事中時時籠罩著閹割的氛圍,而且這種閹割具有傳染性,而少婦最終拒絕“我”也是因為受到閹割的傳染,而“閹割”象征著“去中心化”、“無根”等。從內故事表現的內涵來看,實際上表現的是對“閹割”的厭惡和痛恨:薩拉辛作為一個情欲旺盛而又癡情執著的男人,遇到一個心儀的女性本來可以促成一段佳話,誠然,因為贊比內拉的“閹割”成為悲劇的導火索,這點與巴特的論述是相符合的,但巴特止步的地方并不是文本最根本的要義所在。“閹割”實際上是掌權者實施權利的一種暴力手段,被閹割者是受害者,進而再變成間接施暴者,欺騙、玩弄、傷害無知者,在整個內故事層面,到處充盈著紅衣教主的壓迫勢力。在外故事層面,“我”給伯爵夫人講這個故事本來是為了取悅她進而滿足自己的欲望,然而伯爵夫人卻因為聽到這個故事對激情、愛欲產生了厭惡,直致“我”的企圖落空。伯爵夫人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薩拉辛的故事引起了她對“閹割”的恐懼和反感,更深層地說,引起了她對巴黎,甚至是整個現實社會中那種毫無底線的欲望化的反感和憎惡,正如她所說,“您的故事使我對生活、對種種激情感到厭惡,而且這種態度短時間內不會改變。除了沒有心肝的人,所有人類感情不都是以痛苦的失望而告終嗎?友情!世上有友情嗎?今后,如果在生活的狂風暴雨中我不能像巖石那樣巋然不動,我就進修道院。雖然基督徒的未來也是個幻象,可是這個幻象至少到死后才破滅。”這段文字既可以說是她的“聽后感”,更可以理解成她對現實的指控。
二、“潛變化”的敘述者
敘述者(narrator)是敘事文分析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敘事學,“敘述者”被定義為“陳述行為主體”(托多羅夫《文學作品分析》),文本中的聲音或講話者。“敘述者代表判斷事物的準則:他或者隱藏或者揭示人物的思想,從而使我們接受他的‘心理學’觀點;他選擇對人物話語的直述或轉述以及敘述時間的正常順序或有意顛倒。”)敘述者具有五種功能:敘述功能、管理功能、交際功能、見證功能和思想功能。“這個只能說明敘述者在多大程度上以該身份介入他講的故事,他和故事有什么關系。自然這是情感關系,但也是精神或智力關系。當敘述者指出他獲得信息的來源,他本人回憶的準確程度,或某個插曲在他心中喚起的情感時,該關系可表現為單純的見證,似可稱為證明或證實職能。但是敘述者對故事的直接或間接的介入也可采取對情節作權威性解釋的、更富說教性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職能可稱作敘述者的思想職能。”就像熱奈特自己所說,這幾種功能并不是相互獨立、單獨起作用,“我們知道巴爾扎克大大發展了這種解釋和辯解性話語的形式,它在巴爾扎克和其他許多作家的作品中傳遞出現實主義的動機。”而所謂的“潛變化”敘述者,這是筆者根據《薩拉辛》的敘述者特點所提出的一個概念,也可以稱為“局限視點轉換”,主要是指在故事敘述層面,敘述行為表面上是由同一敘述者發出,實質上已在潛層改變了敘述者的身份,從而達到通過話語控制敘事距離的效果。局限視點(limitedpointofview)這一視點包括兩種主要形式: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和采用第三人稱的敘述。華萊士·馬丁指出:“這種‘局限視點’常常既含有心理上的也含有視覺上的限制:敘述者表現的僅僅是這個人物所看到的,好像他是通過這個人物的眼睛看的,或者是作為‘不可見的目擊者’站在他身邊。”局限視點因而也成為“戲劇式呈現”或“客觀展示”的主要方法。而巴爾扎克正是通過這兩種局限視點的轉換技巧使其文本表現出一種既顯得“客觀”、“不干預”的敘事風格,卻又在思想上牢牢控制著受眾的道德倫理走向。
《薩拉辛》整篇故事的敘述行為是由“我”一個人承擔的,“我”講述舞會的繁華場景,講述“我”內心深處的感受,講述薩拉辛的故事,毫無疑問,“我”承擔了所有的敘述行為,但實際上在雙層故事敘述中,通過細致的分析,可以發現視點已經改變了,由“我”潛變成薩拉辛,最后又變成“我”,實現了敘述者的“潛變化”。首先,在外故事層面,文本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敘述”(first-personnarrative),文本在開篇提到“我”處在上流社會的舞會上,這時“我”眼中的景象是這樣的:“大廳里不時突然爆發出賭客們的大聲吼叫。錢幣的撞擊聲、舞樂聲和賓客的低語混成了一片。此外,彌漫在空氣里的各種各樣的香氣和普遍的狂熱情緒也刺激著人們興奮的想象力,使那些被上流社會所有這些迷人之處所陶醉的人完全神魂顛倒了。”這是一種直接感受,隱含了對現實的一種態度,敘述者對這種情況的評價是“活人的狂舞縱飲行樂圖”,這里敘述者和作者的態度都不明了。隨著情節的發展,“我”的思考行為被打斷,從而也融入現實的一派繁榮之中并且看到了老年的贊比內拉,“我”眼中看到的老年贊比內拉是“這張臉焦黑,瘦骨嶙峋,布滿縱橫交錯的皺紋,下頜和太陽穴全凹進去,眼珠消失在黃色的眼眶里。因為出奇的瘦,上下顎骨非常突出,雙頰成了兩個大陷窩。”這里都是以“我”的第一敘述視角來觀察周圍的行為和人物,從而使讀者獲得了一種以受限制的全知方式來接近文本。“我”給少婦將薩拉辛的故事,包含了對少婦美麗肉體的覬覦,這都是第一敘述給予的方便之處。正如福勒認為:“以第一人稱視點敘述故事有種種顯而易見的長處,例如它可以使作者十分自然地進入主人公的內心深處,并用意識流或其他方式將他最隱秘的思想公之于眾。”但同時他也提到“然而這種敘述方式也有其短處:如果說隨意深入小說主人公的內心的權利是破格特許,那么基于同樣的理由,小說中其他人物的思想感情就成了一個謎。”正是因為由“我”的第一人稱敘述視點會導致在進入薩拉辛的故事有心理上的阻礙,所有巴爾扎克很聰明地使用了“潛變”敘述者的技巧。整個內故事層的敘述是以第三人稱的局限視角來完成的,所以雖然在內故事敘述中,實際上“我”的敘述是被移置在主人公薩拉辛的身上,從而以薩拉辛的視點來展開敘述的,因此整個內故事雖然都是用第三人稱敘述,但這并不妨礙讀者近距離地來體會薩拉辛的心理變化歷程。
在內故事層面,實際上是薩拉辛在敘述,只有這樣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其內在的感情,從而達到一種震撼的效果。首先,“得到她的愛,否則就去死,這就是他給自己的命運做出的選擇。532”這是薩拉辛初見贊比內拉時所許下的諾言,正因為讀者也被這種限制型視角的牽引,所以總會陷入對美好愛情的幻想之中。然而最終的結局是薩拉辛發現贊比內拉是個“閹人”,這種結果對薩拉辛所起的效果是致命的,對讀者同樣起到震撼的效果,原因是我們和主人公一樣一直被蒙在鼓里。這種效果在作品中的受述者(少婦)身上得到驗證。在內故事中,薩拉辛瘋狂地愛著贊比內拉,千方百計地向其求愛,最終因為“閹割”而使一切打破,在這層關系中,受閹割的贊比內拉作為一個被追求者,是掌控著薩拉辛的喜怒哀樂與最終結局的。然而,贊比內拉也是受害者,他作為歌唱家,受制于當時羅馬教皇的規定,而成為一個“受閹割者”,最終淪為人們眼中的“怪物”,這說明了他的一生也是被控的,真正背后操縱的是紅衣主教,即他的保護人和包養者西科尼亞拉——傳統威權的代言人和執法者。因此可以說,內故事整體是處于一種黑暗權勢操縱下生命與金錢被吞噬的恐怖氛圍之中。由于“潛變化”敘事的轉移,這種恐懼直接外涉到外故事層面,在現實的巴黎,以最卑劣的方式換來的金錢得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德·朗蒂先生和他的夫人從不談他們的出身,他們過去的生活,以及在世界各地的社會關系,這種謹慎本來不會長久使巴黎人感到驚奇。因為巴黎也許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理解韋斯巴薌的那句至理名言。在這兒,金錢哪怕沾有泥污和血跡,也不會引起任何懷疑,而是能代表一切。一旦上層社會得知你的家產數目,它就把你歸入擁有同等家產的那類人之中,從此,誰也不會問你是否真有貴族頭銜,因為大家知道,這些頭銜是多么不值錢。”巴爾扎克就是以一種“局外人”的身份通過拉近薩拉辛與受眾的距離,進而使之產生同情,再文本結束處讓文思會聚在一起,以達到一種震撼人心與批判現實的寫作目的。
三、身體敘事
身體,是一個復雜的存在,從物理學上來講,身體即肉體,它是獨立的、個體的。同時,身體承載了諸多社會性的內涵,這時它可以說是非自由的、符號化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個體與社會的集合體。身體敘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性別敘事與權力敘事。首先,性別敘事在文本中主要體現在薩拉辛對贊比內拉性別的“誤讀”和“中間性”身體的存在。造成薩拉辛悲劇的直接原因是他對羅馬文化的無知,而這種無知是由他外來者的身份所決定的,所以當他見到贊比內拉時,他僅僅通過視覺印象來確定贊比內拉的性別,在他作為藝術家的眼睛里,“他看到一張表情豐富的嘴,一雙含情脈脈的眼睛,白得耀眼的皮膚。胳臂與上身連結得那么優美,頸子那么渾圓,雙眉、鼻子的線條那么和諧,還有那毫無瑕疵的橢圓形臉龐,輪廓明晰而純凈,濃密而翹曲的睫毛,寬寬的、令人銷魂的眼瞼,他欣賞著這一切,真是百看不厭。”這說明他認為的女人就是具有這種氣質的身體。繼而,“他向贊比內拉做了一個會心的表示,贊比內拉羞怯地垂下了她那令人銷魂的眼瞼,好象因為自己的心意被情人理解而感到幸福的樣子。”薩拉辛對此也解讀成女人的嬌羞。特別是當贊比內拉告訴他自己是個男人的時候,可由于他害怕蛇,從而再次使薩拉辛相信她是女人,“‘嘿!現在您還敢說您不是女人嗎?’藝術家微笑著問。他看到這個柔弱無力的女人有著賣弄風情、脆弱而且嬌滴滴的性格。她那突如其來的驚嚇,莫名其妙的任性舉動,內在的心煩意亂,難以理解的冒險行為以及細膩入微的感情變化,都是典型的女人的表現。”這些實際上都是對贊比內拉行為的“誤讀”,而造成這種“誤讀”的根源則來源于薩拉辛意識中對女人的定位:害羞、任性、膽小、柔弱。這種對女性的傳統定位是西方在一直以來評價女人的標準,但這種標準在《薩拉辛》中卻失去了其準確性,也從側面說明傳統權威文化的失效與無力。在文本《薩拉辛》中,有很多存在于“中間分界”的身體,比如,在文章開頭,“在我的右方是一幅沉寂陰森的死亡圖景,在我的左方是活人的狂舞縱飲行樂圖;一邊是冷冰冰的、陰沉沉、披著喪服的大自然,另一邊是尋歡作樂的人類。而我則置身于這兩幅畫的交界處,我本身也是一個既令人好笑又令人悲傷的精神大雜燴:左腳打著舞曲的節拍,右腳卻似乎已經跨進了棺材。原因是舞廳里常有一股穿堂風,能把你的半邊身子吹得徹骨冰涼,而另外半邊身子仍感受著大廳里騰騰的熱氣。”“我”在這里實際上是一個清醒的沉淪者,是一個中間者。贊比內拉受閹割的身體,導致其非男非女,成為一個中間者,巴特認為這是一種中間敘事,最終走向得是一種增補的平衡。實際上,無論是“我”還是贊比內拉的身體,都二元對立的結果。而二元對立中的兩項從來都不是平等的,“我”最終會有給少婦講故事這樣一種行為,其實是“我”的中間狀態被打破,從而跌入現實舞會紙醉金迷的結果,從這一效果可以看出“金錢”的權威與誘惑力緊緊控制著人的心智;贊比內拉受閹割的身體則是教會權威和財富欲望共同作用的結果,總之,中間狀態被打破與被塑造的背后都是有一個巨大的操縱力量。
存在于社會生活中的身體總是會和政治、文化等相聯結,正如尼采所說,“肉體乃是統治的產物。”贊比內拉“非男非女”的身體正是強權文化,抑或是強權政治施暴于肉體的結果。然而除了一種暴力的方式外,文化政治更多地是通過一種潛移默化的“冷暴力”方式來控制人的思想、限制人的行為。薩拉辛從一開始便受到這種“冷暴力”的鉗制。出身于一個傳統保守的小鎮,薩拉辛卻從小就表現出一種旺盛的激情,“他帶著一種不尋常的熱情,古怪的性格,他不好好學習希臘文的基礎知識,卻在那兒給可敬的神甫畫速寫,他還畫數學教師、省長、聽差的、閱卷的,他把所有的墻壁都涂滿了一幅幅難以辨認的草圖。在教堂望彌撒時,他不唱贊美詩,卻在長凳上畫畫刻刻,或者要是弄到一塊木頭的話,便在木頭上雕刻某個圣女的形象。不管是臨摹用來裝飾祭壇的畫幅上的人物,還是即席創作,他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留下粗野的圖畫,內容淫蕩,連最年輕的神甫也看不下去,而老年的神甫呢,據有些說話刻薄者稱,他們看了暗暗微笑。他被趕出學習,因為有一個星期天,他在懺悔室等待懺悔時,把一塊大劈柴雕成了耶穌像。這個雕像太褻瀆神圣了,不能不給作者招來懲罰。他不是還曾經膽敢在圣體柜上方了一個形象猥瑣的雕像嗎!”從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薩拉辛的“不安分”是其反抗傳統文化與宗教文化壓抑人性的一種反抗,最終成功了(被教會學校開除,才華得到認可)。然而這種成功只是短暫的,在布夏東那里其本性再次受到壓抑,“他盡量把薩拉辛那非同一般的狂熱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看到他陷入某種構思不能自拔時,就不讓他工作,叫他去消遣消遣;當他想要縱情放蕩時,則交給他一些工程浩大的任務。”而當薩拉辛獨自一個人來到羅馬時,雖然對這里文化顯得格格不入,但至少他可以自由地投身于藝術創作、釋放天性,而這種釋放在碰到贊比內拉時達到頂峰,“雕塑家先是感到全身一陣寒冷,繼而又感到身體的最深處,就是我們缺乏其它詞稱之為心的地方,有一妒火在噼啪燃燒!薩拉辛想沖上舞臺,搶走這個女人。他精神上感到一種壓抑,這一現象很難解釋,因為發生在人所觀察不到的區域,可是他的體力卻因精神上的壓抑而百倍增強,這力量快要以令人痛苦的沖擊力迸發出來了。”最終的結局是薩拉辛的反抗最終斷送了他的性命,他喊道“你們欺騙了我”是對心中藝術理想破滅的呼喊,更是對傳統文化虛偽、丑惡、殘暴一面的控訴,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中,他只能無力地嘲諷道:“你們做了件好事,稱得上是基督徒的善行。”
四、隱含的“邏格斯”權威
羅蘭·巴特對《薩拉辛》的解讀可謂獨樹一幟,他顛覆了文本的整體意義和中心意義,將小說分解成561個意義單元,由此證明小說表面看來連貫的意義系統實際只是一大堆能指碎片的集合。然后,巴特進一步指出,這些能指碎片并不直接與所指相關,而是受制于其在文本中辨認出來的五種不同的符碼代碼,這五種不同的符碼分別是闡釋性符碼、能指符碼、象征符碼、行動性符碼、文化性符碼,它們集合起來完成了一個開放的文本“構成”過程。這些都讓我們看到,文本是沒有整體意義和向心結構,甚至沒有穩定的意義,而是一種“無中心”的存在。實際上,從巴特對文化符碼的闡述就可以看出他規避了文化意義在文本中的效應。羅蘭·巴特說:“文化代碼是對一種科學或知識的指稱,當目光轉向它們的時候,我們只是指出這知識的類型,如物理的、生理的、醫學的、心理的、文學的、歷史的等等,而不更進一步去建構或重構它們表現的那一文化。”但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遜在《文本的意識形態》一文中尖銳地指出文本中文化內蘊的巨大影響力,“文化代碼有點像格言式的智慧或對普遍的行為、事件和生活的常識的倉房,當需要某個具體細節的時候,它就會被說出來。因此這種代碼也幾近意識形態的孳生地。所有現存的意識形態本應是那樣的,而總是趨向于看到某種舊意識形態斷片的倉房。當敘述的策略需要選擇另一條道路或需要為自身的發展辯護的時候,就可以向它去求助。”在文本中,每個人都受著其所處文化的牽制,在薩拉辛故事的,“邏格斯”的具象化身就是教會及傳統文化,而在巴黎則是金錢,這二者的權威使人們敬畏、尊崇。這是在這樣的文化控制下,薩拉辛那純真的愛情變成了一種被人取樂的噱頭,而最終扭曲的傳統現實則扼殺了這種純潔愛情的所有苗頭,在這里也隱含了薩拉辛對贊比內拉的愛,對雕塑的狂熱其本質是來源于對一種純粹美的追求,最終這種美被所謂的權威摧毀了,這也證明了,在強大的“邏格斯”權威面前,任何的反抗都是無力的。
在巴爾扎克時代,資產階級日益成長,貴族階層日趨沒落,財產和貴族封號一起成為涌向權利巔峰的兩個必要條件。人們毫不諱言對金錢的貪欲,人成為金錢的奴隸,整個時代的風氣就是追逐金錢和權勢。而一直把創作小說看作是書寫歷史的巴爾扎克立志如實書寫法國的這種充滿污穢的現實,為了規避檢查機制,同時也為了吸引讀者閱讀興趣贏得賴以生存的生活費,選擇了這樣一種“客觀化”的寫作策略,事實證明獲得了成功。他借薩拉辛的故事向我們展示了“邏格斯”權威的巨大殺傷力,特別是在開頭時眾人對丑陋的贊比內拉的追捧與結尾處對其錢財來源的解釋,讓人們對巴黎所謂的上流“貴族”們產生了厭惡,最后由受述者少婦來發出內心的吶喊,“巴黎真是個好客的地方;”她說,“它對一切都來者不拒。不光彩的家產也罷,沾滿鮮血的家產也罷,它一概歡迎。罪惡和污穢全能在這里得到庇護和同情,只有道德廉恥不受崇敬。是啊,純潔靈魂的樂土在天上!”550作者這種借人物之口成功把自己隱藏起來,而又以最殘酷地方式驚醒依然沉睡在迷夢中的人們,引起受眾心靈最深處的反思。
結 語
作為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有著一個文人的自覺性——拿起筆桿,反映現實。他的“非線性”敘事時間巧妙地講故事分層,既有對傳統敘事時間表達的繼承,又帶有現代性“錯時性”的先鋒性;而“潛變化”敘述者則進一步將分層的故事展現得既脈絡清晰,又增加一種神秘性,通過“局限視點”的相互轉換,在結尾處會聚,從而使整個文本達到高潮,借人物之口傳達寫作的動機,取得震撼人心的警示效果;而身體敘事也是巴爾扎克對身處在巴黎這個大染缸中人的身體該如何歸置的一種思考,并且表達了在這樣一種正常欲望被扭曲,天才式的欲望被懸置和扼殺的一種深深的焦慮與擔憂。總之,文本從三個角度闡明在“邏格斯”——金錢、權利的統治之下,巴黎乃至整個法國道德人性底線無限淪喪的現實的批判與反思,可以說,《薩拉辛》整個文本無不籠罩著一種強大“邏格斯”權威的壓抑與殘酷的高壓氛圍,但同時也展現了小人物的不同流合污與無力掙扎的動人魅力。
[1] W·C·布斯.小說修辭學[M].華明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2] 弗里德里希·尼采.權力意志[M].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3] 巴爾扎克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4] 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M].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5] 張隆溪.道與邏格斯[M].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6] 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7] M.H.艾布拉姆斯.歐美文學術語詞典[M].朱金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8] 王先霈,王又平.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 羅蘭·巴特.S/Z[M].屠友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 黃曉華.小說敘事的身體符號學構想[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
[11] 黃晉凱.巴爾扎克文學思想探析[J].外國文學評論,2000(3)
[12] 羅智文.巴爾扎克短篇小說敘事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5
(注:此篇論文為“2016年云南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項目”研究成果)
責任編輯:楊 林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學雨花校區文學與傳媒學院15級文藝學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