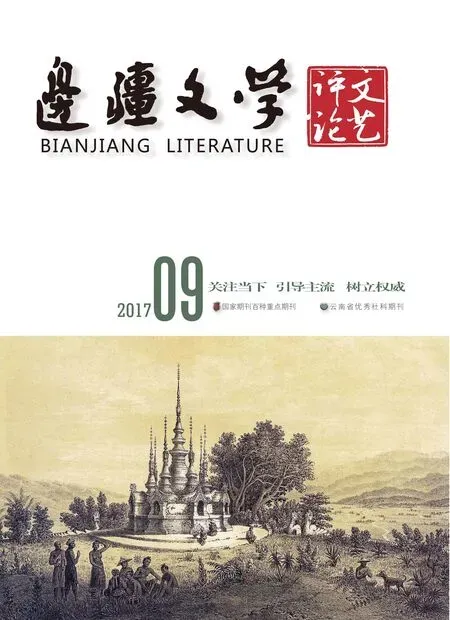風格故事:馬爾克斯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解讀
孫金燕
經典重讀
風格故事:馬爾克斯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解讀
孫金燕
·主持人語·
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固然是傳世名篇,但他的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也同樣是一部經典。青年學者孫金燕博士的論文,從四個層面完整地對這部小說進行解讀,立意不凡,論證有力,見解獨到。作者認為馬爾克斯的每一本小說“都在寫作‘自己的經歷’,不是為了‘擺脫自我’,而是‘實錄’他眼中風云變幻的哥倫比亞和南美大陸神話般的歷史,盡管這些向來被視為‘魔幻現實’。” 而《枯枝敗葉》作為他的開山之作,奠定了這種敘述基礎。
巴爾扎克的《薩拉辛》之所以如此著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羅蘭·巴特。巴特的《S/Z》對這篇小說的拆解式細讀,成為后結構主義解讀策略的先行者。然而真正把《薩拉辛》作為一個獨立文本來做一種敘事技巧的閱讀卻是寥寥無幾,大多數學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巴特思想的影響,將文本強制與巴特的論調粘合在一起,這對作為個體存在的《薩拉辛》是不公平的。本文試圖將文本看成一個獨立的個體,以敘事學理論作為依據,主要從非線性敘事時間、“潛變化”敘述者以及身體倫理敘事三個方面對該文本的敘事技巧進行解讀,并嘗試進一步論述隱含在文本敘事背后的“邏格斯”敘事權威,由此證明《薩拉辛》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所具有的傳統思想主題,而并非巴特所謂的該作品思想主題的“虛無性”、“無中心性”。文章有自己的獨特想法,值得推薦。(李 騫)
“眾所周知,初次進行創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作品的強烈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個替代者放進他的第一部小說中,這樣做與其說是由于現成題材的吸引力,不如說是為了擺脫自我后可以去輕裝從事更美好的事情。這是我接受的極少數的一般規則之一。”這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關于其第一部小說《瑪麗》的表述。然而這種“規則”對于某些作家并不適用,加西亞·馬爾克斯就是其中一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的真實生活。從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到最后一部《苦妓回憶錄》,他都在寫作“自己的經歷”,不是為了“擺脫自我”,而是“實錄”他眼中風云變幻的哥倫比亞和南美大陸神話般的歷史,盡管這些向來被視為“魔幻現實”。所以,想要了解馬爾克斯,從哪一部作品進入都不會失望。《枯枝敗葉》作為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說,則更可當作他此后所有小說的“雛形”來閱讀。
一、討論這部小說的原因:馬爾克斯難以釋懷的“傷害”與“同情”
從寫作意義上說,《枯枝敗葉》(1955)是馬爾克斯的第一部小說,盡管它的發表遲于《第三次辭世》(1947)。大學二年級,他隨母親回出生地阿拉卡塔卡(Aracataca)小鎮出售外祖父的房子,此次重返故地即使他萌生寫一部家族史小說《家》的意愿,但把握一個大家族的命運,在他當時還有些力所不逮。于是,他五易其稿,最終在整體上成為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部中篇小說《枯枝敗葉》:通過為一位自殺的大夫斂尸送葬的事件,以三個人物視角,描繪了一個叫馬孔多的小鎮上人們精神和物質雙重困境的生活。書名則來自“當年外婆曾以遺老遺少的姿態,用這個既顯輕蔑又富于同情的說法描述聯合果品公司造成的破壞:枯枝敗葉。”
關于這部小說,馬爾克斯有著難以直言的發表困惑,也有著深刻的“同情”。
《番石榴飄香》對這部作品如此評價:“《枯枝敗葉》是一本內容充實的書,它已經包含了馬孔多所有的荒涼以及對昔日的眷戀,完全有理由使它的作者名揚拉丁美洲。然而事與愿違。任何一位作家只要寫出一部優秀的作品便有權享受公眾的承認、聲譽或者說酬謝,卻在許多年之后才來到他面前。當時,他的第五部作品《百年孤獨》,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先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后來在整個拉丁美洲,最后在全世界,像熱香腸似的出售。”“熱香腸”的比喻,來自馬爾克斯對全世界評論界和讀者追捧《百年孤獨》的自嘲:“為什么我的一本我估計只有幾個朋友會看的書會像熱香腸一樣到處出售。”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馬爾克斯的自傳《活著為了講述》中,也常將《枯枝敗葉》與《百年孤獨》放置一起對比表述,重點不在它們的寫作精神與形式,而在出版與發行問題上,盡管評論者更在乎前者:“早期的《枯枝敗葉》無論從題材、主題,還是敘事風格上都可以看成是《百年孤獨》的雛形。”以此,足見這部不僅未帶來“公眾的承認、聲譽或者說酬謝”,甚至連面世都厄運連連的“優秀的作品”,與“熱香腸”《百年孤獨》一樣,于馬爾克斯這位后來的大師級寫手而言,都有一種關于接受的困惑。比如下面這段描述:
“四年后,哥倫比亞文化基礎圖書館館長愛德華多·卡瓦列羅·卡爾德隆將《枯枝敗葉》收入一套口袋叢書,在波哥大和其他城市的街頭銷售。稿費不多,但會按時支付。那是我拿到的第一筆稿費,對我而言意義非凡。這一版有幾處改動,我認為并非出自我之手;在之后的版本中,我也沒有刻意刪去。差不多是三年后,《百年孤獨》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發行,途徑哥倫比亞時,我在波哥大街頭書攤看見多本首版《枯枝敗葉》,每本一比索。我能拿多少,就買了多少;此后,這版又在拉丁美洲各大書店出現過,被當作古董書賣。兩年前,一家英國古董書店出售了一本有我親筆簽名的首版《百年孤獨》,售價三千美元。”
相比而言,對于“售價三千美元”的《百年孤獨》,馬爾克斯常常想淡化它的存在,比如在自傳《活著為了講述》中每每涉及到,也不過寥寥數語;倒是這部“每本一比索”的《枯枝敗葉》,幾乎貫穿他的整部自傳,經常性大篇幅地講述它的成書、出版、銷售歷史,即使是后來被普遍認可的《族長的秋天》《霍亂時期的愛情》《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等,都未能如此地被馬爾克斯“在講述中”重視。
多年后,馬爾克斯稱:“我非常珍惜隨著我的榮譽而來的各種榮耀;但是,我更珍惜從我童年起就經受的種種打擊、挫折乃至失敗。我至今當然仍然清楚地記得偉大的編輯家吉列爾莫·德托雷先生,是他毫不留情地退回了我的第一部小說。”這位讓馬爾克斯“清楚地記得”的吉列爾莫·德托雷何許人也?便是當年有意愿出版《枯枝敗葉》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的董事長,并在退稿信中措辭生硬:“此書毫無價值,但藝術上卻有可取之處。”當然,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即另一位大師級寫手博爾赫斯的胞妹諾拉的丈夫。
雖然聲稱“珍惜”《枯枝敗葉》挫敗的馬爾克斯,看上去非常大度;然而“至今當然仍然清楚地記得”,又顯露出某種難言的傷害。事實上,他的真實感受確實并非如此。他認為,退稿信判決書“回蕩著委婉的措詞、裝腔作勢和卡斯蒂利亞白人的自負”;當年洛薩達出版社沒有選中出版《枯枝敗葉》,“這是一個錯誤或者是一個惡意安排的事實,因為這不是一種文學競賽,而是洛薩達為借助哥倫比亞作家進入哥倫比亞市場而確定的項目。而我的小說不是在同另一部小說的競爭中被拒絕的,而是因為堂吉列爾莫·德托雷認為它不值得出版。”
而與難以釋懷于《枯枝敗葉》的發表挫敗相似,另一件讓其耿耿于懷的事實,便是《枯枝敗葉》的寫作狀態。他對當年創作這本書的小伙子“有點兒同情”,“因為他當時寫得非常倉促,以為此生再也沒有寫作的機會了,這是他唯一的創作機會,于是他就把當時學到手的東西一股腦兒地塞進這本書中,特別是他當時從英美小說家那兒學來的創作技巧和文學手法。”
事實上,無論是吉列爾莫·德托雷所承認的“藝術上的可取之處”,還是馬爾克斯“同情”的“學來的創作技巧和文學手法”,最終都成為了他在作品形式上的無可替代的風格標記。
二、一條濃縮的時間軸:兩點半、一個下午與25年
后來的馬爾克斯,無疑已被公認為是操縱時間的高手,《百年孤獨》中那句被人談論過無數次的開頭:“許多年之后,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將過去、現在和未來擠壓進一條濃縮的時間軸,為文學敘事提供了新的時間視點。以至于后來,連馬爾克斯本人都急迫地想要逃避自己的影響的焦慮,終于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以不顯山不露水的方式開始,寫過50來頁才慢悠悠地讓第一主角登場。而這種處理時間的方式,馬爾克斯坦誠最初是受到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影響:
“如果我在二十歲的時候沒有讀到《達洛維夫人》中的這段話,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樣子了:‘但是,毫無疑問,(車子)里面坐著的是一位大人物;大人物遮掩著經過邦德街,凡夫俗子們伸手可及;他們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離英國的君主、國家的不朽象征這么近。等到倫敦淪為一條雜草叢生的道路,這個星期三上午在人行道上匆匆走過的人們全都變成了白骨,幾枚婚戒散落其中,還有無數腐爛的牙齒里的黃金填塞物,好奇的文物學家翻檢時間的廢墟,才能弄清車里的人是誰。’”
馬爾克斯聲稱:《達洛維夫人》“完全改變了我的時間概念”,“為撰寫第一部長篇小說鋪好了道路”[14]。
伍爾夫因其對時間的非常規處理,常常被歸入意識流作家。她注重瞬間的心理真實,而非所謂的社會現實,在《現代小說》(1919)一文中,她明確表示:“讓我們按照那些微粒落下的順序,把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留下的印象記錄下來;讓我們把每種情景、每個事件在我們意識中留下的圖像,不管表面看來多么支離破碎、互補連貫,都描繪下來。我們不可以想當然,認為生命中通常所謂的大事中比重通常所謂的小事中能夠更完滿地存在。”可以說,得其精髓的馬爾克斯,在《枯枝敗葉》中充分演練了這種時間技巧。
其一,他以“一個下午”的時間,回溯馬孔多小鎮“25年”的歷史。
小說以第一句“這是我第一次瞧見死尸”的停尸待殮,到最后“棺材便晃晃悠悠地懸浮在燦爛的陽光里了,看上去好像一直沉船”,完成了三個人物外祖父上校、母親伊莎貝爾和孩子為上吊自殺的大夫守喪送葬的緩慢過程。這“一個下午”的時間,通過孩子的疑問“我不明白為什么沒有人來參加葬禮”,和母親與外祖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懸念中追憶了大夫與小鎮的糾葛:
25年前,他帶著大西洋沿岸總監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寫來的信來到小鎮找外祖父,從此寄居于外祖父家中行醫4年,“因為香蕉公司開辦了職工醫院,四年來找他瞧病的人都不來了。他眼瞅著‘枯枝敗葉’踩出了新路,但是沒有吭氣。他依然敞開臨街的大門,成天坐在皮椅上,眼瞅著人們熙來攘往,可就是沒有人登門求醫。于是,他上好門閂,買了張吊床,往房間里一躲,不再出來了”;又4年,他與外祖父的養女梅梅搬到街角小屋公開姘居;11年前,人們發現梅梅失蹤,在他家掘地三尺、追查未果;10年前,馬孔多小鎮陷入破產,“‘枯枝敗葉’帶來了一切,又帶走了一切”,他作為當時留在小鎮唯一的醫生,因不肯救治暴動中的傷員而與小鎮所有人斷絕交往;17年來一直被小鎮人怨恨、詛咒:“讓大夫在這棟房子里腐爛發臭吧!”3年前救治了病入膏肓的上校,有了與上校的關于送葬的約定,及最后上校逆小鎮所有人之意愿的踐約。
這“一個下午”,既呈現了大夫越來越孤寂的人生,也呈現了在20世紀初美國投資家引起的香蕉風暴后,馬孔多小鎮表面的繁榮與實質上的貧瘠,“整個小鎮顯出一副像破爛家具一樣的可憐相兒。似乎上帝已經宣判馬孔多是個廢物,把它撂倒了一個角落,那里堆放著所有不再能為造物服務的鎮子。”
其二,他在同一時間節點“兩點半”的火車汽笛聲中,讓三個人物的心理伸展向不同的時間方向。
(孩子)“汽笛又響了,聲音越來越遠。猛然間我想到:‘兩點半了’。我記得每天這個時候(就是火車站最后一個彎道鳴汽笛的時候),同學們正好在校園里列隊,準備上下午的第一節課。”
(母親)“我聽見火車在最后一個彎道上鳴汽笛的聲音。我想:‘兩點半了。’這會兒,整個馬孔多都注視著我們在干些什么。我總是排遣不掉這個念頭。”
(外祖父)“這時候,剛好火車拉響汽笛,隨即在鎮子的最后一個彎道那兒消失了。‘兩點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的兩點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們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時候,大概就是一九〇三年同一天的幾乎同一個時辰。當時阿黛萊達問他:‘什么草,大夫?’他帶著濃重的鼻音,用反芻動物特有的那種慢吞吞的聲音說道:‘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驢吃的青草。’”
這與《達洛維夫人》中“大本鐘鏗鏘有力的鐘聲,報告半點鐘”,在克拉麗莎、伊麗莎白、彼得·沃爾什三者之間引起的思維震動有點相似,卻在時間指向上走得更遠。當年,年輕的馬爾克斯拿著《枯枝敗葉》的初稿向年長的加泰羅尼亞學者堂拉蒙·賓耶斯請教,對方就如何處理時間大致說了幾句:“您應該意識到,事情已經發生,人物的出現只是為了回憶。因此,您要駕馭兩種時間。”
因此,在修改后的小說中,孩子、母親伊莎貝爾與外祖父上校分別站在三個深具個性觀察點上:總想離開現場的孩子向往的是與自己的小伙伴們玩耍,每次的表述都暗含著“如果此時不在這里,那么我將在做什么”,在時間上指向“將來”;母親伊莎貝爾擔心的是當下,即小鎮人對自己一家人冒天下之大不韙來為引起公憤的大夫送葬的憤怒,在時間上指向“現在”;外祖父上校想的更多的是大夫在馬孔多25年的孤獨生活,“枯枝敗葉”涌入后對大夫的影響,以及他對大夫充滿著理解和同情,在時間上指向“過去”。
也就是說,這種對時間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濃縮式處理方式,在其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中“兩點半”這個時間節點上已經嶄露無疑。于是,也就不必訝異于后來《百年孤獨》中首句的那次經典呈現了。
三、一個神奇的文學地理空間:“馬孔多”小鎮
小說《枯枝敗葉》在第一節之前,有一段以“我們”為敘述者所做的類似日記或筆記的文字,末尾標注為“一九〇九年于馬孔多”。
閱讀馬爾克斯者,對“馬孔多”肯定不會陌生,它反復出現在他的《伊莎貝爾在馬孔多觀雨時的獨白》《蒙鐵爾寡婦》《格蘭德大媽的葬禮》《惡時辰》等小說中。當然,最著名的還是《百年孤獨》:在這場述說中,“馬孔多”在布恩迪亞家族第一代帶領的遷居而來的人們的努力下,由原來的一片無人的沼澤地變成繁華市鎮,最后又在跨國資本的侵襲下遭到毀滅,颶風席卷了它,它在大地上消失。一場持續了4年11個月零2天的暴風雨將馬孔多重新化為了洪荒和虛無,這個小鎮象征整個拉丁美洲的的興衰史,也暗示人類在不斷的循環和輪回中永劫往返。
當年,關于《枯枝敗葉》的寫作,堂拉蒙·賓耶斯除了關于時間的提議,還曾指點馬爾克斯:“小說里的城市不能叫巴蘭基亞——初稿里是這樣寫的——否則,讀者受地名所限,缺乏想象空間。……要不,您就裝傻,等天上掉餡餅。反正,索福克勒斯生活過的雅典絕不是安提戈涅生活過的雅典。”馬爾克斯自然沒有“等天上掉餡餅”,但“餡餅”就一直在他童年在外祖父家生活的那段時光里,最終在隨母親重返故地“火車會在十一點經過馬孔多種植園”時找到:
“火車停靠在一個沒有鎮子的車站,沒過多久,又途經路線上唯一一片香蕉園,大門上寫著名字:馬孔多。外公最初幾次帶我出門旅行時,我就被這個名字吸引,長大后才發覺,我喜歡的是它詩一般悅耳的讀音。我沒聽說過甚至也沒琢磨過它的含義;等我偶然在一本百科全書上看到解釋(熱帶植物,類似于吉貝,不開花,不結果,木質輕盈、多孔,適合做獨木舟或廚房用具)時,我已經把它當作一個虛構的鎮名,在三本書里用過了;后來我又在《大英百科全書》上見過,說坦嘎尼喀有一個名叫馬孔多的種族,居無定所,四海為家。也許,這才是詞源。不過,我沒做過調查研究,也不知道馬孔多樹長什么樣,在香蕉種植園區問過幾次,誰也說不清楚。也許,這種樹根本就不存在。”
《枯枝敗葉》的結構方式,多少會使人聯想到他的“導師”福克納的小說《我彌留之際》,同樣是一個關于葬禮及其回憶的故事。在其自傳中,馬爾克斯曾記錄在陪母親重回阿拉卡塔卡小鎮時,他一路“重讀威廉·福克納的《八月之光》。當年,他是我最牢靠的精神導師”;為《民族報》撰稿期間,“我急切地想從逝去的時光中汲取某種好處,坐在打字機前,試圖盡可能快地寫出站得住腳的東西:《家》的片段,對《八月之光》所展現的可怕的福克納……的拙劣模仿。”所以,緣于這種密切的精神吸引,很難說馬爾克斯對“馬孔多”的反復塑造,除了應和堂拉蒙所說的“想象空間”問題,他就沒有向其“導師”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靠攏的野心。
終于,經過馬爾克斯的反復勾勒,“馬孔多”成了一個神奇的空間,一個獨特的文學地理形象,一個“以密碼形式容納一切的世界村”。而最初在《枯枝敗葉》中,馬爾克斯已搭建起“馬孔多”大致的歷史發展與演變:
戰爭期間,上校一家在馬孔多落腳,“那時候,這兒還是個正在形成的村落,只有幾戶逃難的人家。他們竭力保留傳統的生活方式,恪守宗教習俗,努力飼養牲口。對我父母而來說,馬孔多是應許之地,是和平之鄉,是金羊毛”;
隨著香蕉公司的到來,“鐵路通車了,馬孔多變成了一個繁華的集鎮”;
當香蕉公司“壓榨夠了,帶著當初帶來的垃圾中的垃圾離開了馬孔多。‘枯枝敗葉’——一九一五年繁榮的馬孔多留下的最后一點遺物——也隨之而去,留下的是一座衰落的村莊和四家蕭條破敗的商店。村里人無所事事,整日里怨天尤人”;
當人們希圖重建家園時,才發現“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類渣滓和物質垃圾組成的雜亂、喧囂的‘枯枝敗葉’”,已對當地人現實生活及精神的沖擊和影響,“‘枯枝敗葉’經過天然發酵,終于融入到大地中默默發育的種子里去了”,重建家園幾乎已成為無望的事件。
至此,我們也可看出,與最初的“應許之地,和平之鄉,金羊毛”相比,隨著小鎮人傳統的生活方式的被沖擊,心靈無所寄托,“馬孔多”小鎮已在香蕉風暴中“枯枝敗葉”化了,最終成為孤獨的權力(《格蘭德大媽的葬禮》)、以無名帖中傷他人(《惡時辰》)的實施地,并最終隨百年孤獨家族消散在颶風中(《百年孤獨》)。
可以說,也正是從這部小說開始,“馬孔多”這個神奇的小鎮,成為了馬爾克斯指稱拉丁美洲歷史與現實的一個投影與符號空間。
四、死亡與孤獨:縈繞馬爾克斯一生的小說主題
“這是我第一次瞧見死尸”,《枯枝敗葉》第一句即狂暴地指向死亡。正如拉爾斯·吉倫斯坦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中說的那樣:
“一種生命的悲劇意識體現了加西亞·馬爾克斯作品的特點——一種命運至高無上和歷史殘酷無情破壞的意識。但是這種死亡的意識和生命的悲劇意識被敘述的無限而機智巧妙的活力沖破了,這活力代表了現實與生命本身的既使人驚恐又給人啟迪的生氣勃勃的力量。”
在馬爾克斯的小說中,與其敘述的“活力”相伴的,總是“死亡”這個置身幕后的導演,這已成為其小說的一個恒久的主題。《禮拜二午睡時刻》述寫一位母親帶著女兒乘火車遠道而來,在全鎮人的暗暗目光中,有尊言地為被人打死的小偷兒子掃墓;《惡時辰》始于塞薩爾·蒙特羅輕信了自家門上的匿名帖,妒火中燒中沖去巴斯托爾家,將其槍殺在鴿房;《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中,納賽爾在鎮上大部分人知情而自己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被殺害;《霍亂時期的愛情》中杰勒米雅·德薩因特·阿莫烏爾選擇在60歲時自殺,為的是“我永遠也不會變老”;這種對死亡的感知或生命的悲劇意識,以及企圖超越終點的生命力量和激情,又使人想到《苦妓回憶錄》中報社老記者幽默又張揚的想法:“活到九十歲這年,我想找個年少的處女,送自己一個充滿瘋狂愛欲的夜晚。”
而死亡的荒誕的、不可思議的來臨,或對死亡的幽默恐懼,又總是與馬爾克斯另一個重要的小說主題“孤獨”如影隨形。“孤獨的幽靈始終追隨著他”,馬爾克斯曾表示“描寫孤獨的書”是他一生唯一的書。他曾提示:“請你注意,《枯枝敗葉》中的核心人物一輩子就是在極端孤獨中度過的,可謂是生于孤獨,死于孤獨。”
外祖父上校深刻地了解著大夫的孤獨:“我感受到他生活中那間黑黝黝的、令人窒息的小屋中的苦惱。環境把他擊敗了,使他變得郁郁寡歡,惶惶不可終日。……我終于看透了他那迷宮般的孤獨的秘密。”擊敗他的“環境”是什么呢?是香蕉公司帶來的“枯枝敗葉”,以及馬孔多小鎮自身的“枯枝敗葉”化。
大夫在馬孔多行醫四年之久,終被香蕉公司開辦的職工醫院排擠,到了1907年,馬孔多已經沒有一個病人記得他了。“他分明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敗仗”,然而卻“找不到一個知心朋友,可以談談自己的憧憬或幻滅”,于是,“每到夜深人靜,就能聽到他像瘋子一樣在屋子里翻來覆去地折騰,仿佛在跟他過去的幽靈打交道。過去的他和現在的他進行著一場無聲的戰斗,過去的他在奮力保衛自己的性格:孤僻、堅毅不屈、說一不二;而現在的他一心一意地要擺脫過去的他。”他的孤僻與堅毅不屈,使他拒絕向香蕉公司屈服,辦理一個“醫生證明”,也拒絕向那些曾經拋棄和遺忘他的小鎮之人再次伸出救助之手。只向曾幫助過他并從未遺棄他的上校,提出身后事的踐約要求:“我只希望在我咽氣的那天,您能往我身上蓋一層薄土,免得兀鷲把我給吃了。”
馬爾克斯曾指出:“孤獨的反義詞是團結。”而團結的反義詞卻是分裂、散亂,那是否意味著孤獨是一種分裂與散亂。如此,像安提戈涅一樣,一意孤行、逆全鎮人意愿而為、堅持要為大夫送葬的上校,才會感到:“我似乎從漂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氣中呼吸到一種苦澀的東西,那就是把馬孔多引向毀滅的聽天由命的氣氛。”可怕的“枯枝敗葉”,不僅是由外界而來的“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類渣滓和物質垃圾組成雜亂、喧囂的”物質,更在于小鎮的人們內心中的那種隨波逐流的狀態,那些與優良傳統相對立的觀念:喪失傳統道義,缺乏同情心,庸俗、勢利等等。可以說,是上校,也是大夫,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憑“至高無上的意志”在對抗人們內心的“枯枝敗葉”。
而這種“枯枝敗葉”的馬孔多小鎮或其他世界,充滿危機并具有自我毀滅的能力,唯有堪與“孤獨”對抗的“團結”,才能做到如其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所預言的:
“反轉這個趨勢,再烏托邦一次,還為時不晚。那將是一種全新的、顛覆性的生活方式:不會連如何死,都掌握在別人手里,愛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經受百年孤獨的家族,也終于永遠地享有了這大地上重生的機會。”
五、結語
馬爾克斯曾堅稱:“一般而言,一個作家只能寫出一本書,不管這本書卷帙多么浩瀚,名目多么繁多。巴爾扎克、康拉德、梅爾維爾、卡夫卡都這樣;自然,福克納也不例外”,他也確實以其寫作踐行著這種堅持。于是,對其第一部小說的解讀,便如此切實地感受到那些具有他的風格的故事。
【注釋】
[1]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瑪麗》(前言),王家湘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2]馬爾克斯在自傳《活著為了講述》中寫有:“二十七歲的我創作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參見加西亞·馬爾克斯:《活著為了講述》,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0頁。
[3]加西亞·馬爾克斯:《活著為了講述》,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39頁
[4]加西亞·馬爾克斯、P.A.門多薩:《番石榴飄香》,林一安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82頁。
[5]同上,第103頁。
[6]格非:《加西亞·馬爾克斯:回歸種子的道路》//邱華棟選編:《我與加西亞·馬爾克斯》,,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頁。
[7]加西亞·馬爾克斯:《活著為了講述》,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23頁。
[8]林一安:《有感于成名之前博爾赫斯的遭遇》,《中華讀書報》1999年9月2日。
[9]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的妹夫拒絕出版我的書》,朱景冬譯,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c 5MTkwNQ%3D%3D&idx=1&mid=201715403&scene=20 &sn=251467b882f0ef49a5ba6bdb87a3bdc9,2016年8月26日。
[10]加西亞·馬爾克斯、P.A.門多薩:《番石榴飄香》,林一安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69頁。
[11]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黃錦炎、沈國正、陳泉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12]加西亞·馬爾克斯、P.A.門多薩:《番石榴飄香》,林一安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59-60頁。
[13]同上,第60頁。
[14]同上,第55-56頁。
[15]弗吉尼亞·伍爾夫:《現代小說》//《伍爾夫讀書筆記》,黃梅、劉炳善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頁。
[16]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劉習良、筍季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頁。
[17]同上,第144頁。
[18]同上,第9頁。
[19]同上,第72頁。
[20]同上,第133頁。
[21]同上,第21頁。
[22]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劉習良、筍季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39頁。
[23]同上,第10頁。
[24]同上,第14頁。
[25]同上,第25頁。
[26]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衛夫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7頁。
[27]加西亞·馬爾克斯:《活著為了講述》,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4頁。
[28]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劉習良、筍季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頁。
[29]加西亞·馬爾克斯:《活著為了講述》,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4頁。
[30]加西亞·馬爾克斯:《活著為了講述》,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6頁。
[31]1982年,馬爾克斯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演說中稱福克納為“我的導師”(參見加西亞·馬爾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獨》//《我不是來演講的》,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26頁);甚至在與堂拉蒙會面時,他自稱:“當時,能找到的‘迷惘的一代’作家的所有西班牙文譯本我都讀過,尤其是福克納,我讀得很細,好比用剃須刀一點點刮,謹防出血,就怕日后再讀,發現他不過是一個敏銳的修辭學家。”(參見加西亞·馬爾克斯:《活著為了講述》,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2頁)。
[32]加西亞·馬爾克斯:《活著為了講述》,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頁。
[33]同上,第391-392頁。
[34]達索·薩爾迪瓦爾:《回歸本源——加西亞馬爾克斯傳》,卞雙城、胡真才譯,外國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頁。
[35]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劉習良、筍季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6頁。
[36]同上,第73頁。
[37]同上,第118頁。
[38]同上,第1頁。
[39]同上,第3頁。
[40]宋兆霖主編:《(1901-2013)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974頁。
[41]加西亞·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楊玲譯,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6頁。
[42]加西亞·馬爾克斯:《苦妓回憶錄》,軒樂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頁。
[43]加西亞·馬爾克斯、P.A.門多薩:《番石榴飄香》,林一安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27頁。
[44]同上,第68頁。
[45]同上,第68頁。
[46]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劉習良、筍季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97-98頁。
[47]同上,第72頁。
[48]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劉習良、筍季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84頁。
[49]同上,第84頁。
[50]同上,第137頁。
[51]同上,第98頁。
[52]《枯枝敗葉》正文前引用了古希臘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的一段臺詞,提示《枯枝敗葉》對此劇的呼應:安提戈涅反抗克瑞翁王的禁令、安葬她哥哥,既是一種對親情的尊重,也是對宗教信仰、對“神律”和道義的尊重。參見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劉習良、筍季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頁。
[53]加西亞·馬爾克斯:《枯枝敗葉》,劉習良、筍季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32頁。
[54]同上,第1頁。
[55]加西亞·馬爾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獨》//《我不是來演講的》,李靜譯,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26-27頁
[56]加西亞·馬爾克斯、P.A.門多薩:《番石榴飄香》,林一安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67頁。
責任編輯:楊 林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學副教授,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