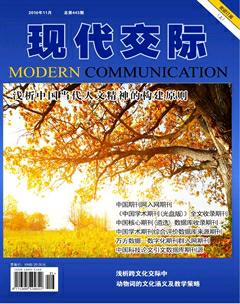西方文化傳統(tǒng)中的學(xué)科分類與人文教育
姚興富

摘要:在西方文化傳統(tǒng)中,伴隨著知識的分科化和科學(xué)的不斷發(fā)展。人文科學(xué)概念的內(nèi)涵和外延逐漸明晰。人文科學(xué)研究有其自身的特點(diǎn):運(yùn)用規(guī)范性的方法、不回避價(jià)值判斷、企望崇高理想。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培養(yǎng)具有批評意識、自治能力而又全面發(fā)展的人。面對現(xiàn)代性的挑戰(zhàn),人文科學(xué)在當(dāng)代高等教育和學(xué)術(shù)研究中的領(lǐng)地被收窄、作用被弱化。恢復(fù)人本主義的精神、重建人文教育的體系是學(xué)者和教育工作者們義不容辭的責(zé)任。
關(guān)鍵詞:西方文化傳統(tǒng)學(xué)科分類人文教育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1-0018-02
在人類文化的早期。并無明顯的學(xué)科分類,所謂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和人文知識都是雜糅在一起的。隨著知識的增長和科學(xué)的進(jìn)步。不同領(lǐng)域知識的區(qū)分逐漸明顯。學(xué)科分類也日益多元細(xì)密。其中人文知識是探究人的本質(zhì)和價(jià)值等問題,應(yīng)該說尤為根本和重要。本文梳理西方文化傳統(tǒng)中學(xué)科分類的大致過程。旨在喚醒人們充分認(rèn)識人文教育在促進(jìn)人的完善和社會進(jìn)步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學(xué)科分類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認(rèn)為各種工藝都是低賤的、機(jī)械性的學(xué)習(xí),這些并不是可以達(dá)到所尋求的那種善的學(xué)習(xí)。亞里士多德把科學(xué)(science)劃分為三類:一是實(shí)踐的(practical)科學(xué),相關(guān)的學(xué)科有政治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倫理學(xué)等。二是生產(chǎn)的(productive)科學(xué),此類學(xué)科有各種技藝和修辭學(xué)等。三是理論的(theoreti-cal)科學(xué),都是關(guān)涉存在之所以為存在的,包括物理學(xué)、數(shù)學(xué)和神學(xué)。亞里士多德的學(xué)科分類較之于柏拉圖更明晰和更系統(tǒng)一些,但他們有一共同特點(diǎn),就是學(xué)科分類的標(biāo)準(zhǔn)都是以某類學(xué)科與存在本身的親疏遠(yuǎn)近關(guān)系為依歸的。
到了歐洲中世紀(jì),學(xué)科分類更加細(xì)密規(guī)范。中世紀(jì)的大學(xué)以神學(xué)、法學(xué)、醫(yī)學(xué)為主導(dǎo)學(xué)科,在進(jìn)入專門學(xué)習(xí)這三科之前,要接受從古希臘沿襲下來的“七藝”(文法、修辭學(xué)、邏輯學(xué)、算術(shù)、幾何學(xué)、天文學(xué)、音樂)等核心課程的教育。“學(xué)生修完語法、修辭學(xué)及邏輯學(xué)‘三藝后,方可被授予學(xué)士學(xué)位。碩士和博士則是修完算術(shù)、幾何、天文及音樂‘四藝后,以及修完其他三科,才可獲得執(zhí)教的資格。”
19世紀(jì)德國哲學(xué)家威廉·狄爾泰認(rèn)真審視了自然科學(xué)(the natural sciences)與人文科學(xué)(the human sciences)的知識論前提。他認(rèn)為這兩種科學(xué)都是從人的日常生活和經(jīng)驗(yàn)出發(fā)的。自然科學(xué)通過外部的觀察和測量去建構(gòu)一個(gè)客觀的世界。而人文科學(xué)利用內(nèi)在和外在的生活體驗(yàn)去定義一個(gè)歷史的世界。19世紀(jì)中后期,“科學(xué)”一詞的內(nèi)涵變得越來越狹窄,僅指物理或?qū)嶒?yàn)科學(xué)。
1959年,英國科學(xué)工作者兼小說家斯諾(1905-1980)發(fā)表演講并提出有關(guān)學(xué)科分類的“兩種文化”(two cul-tures)的說法:一組是由文學(xué)知識分子組成,另一組是由物理科學(xué)家組成。四年后,斯諾發(fā)表了關(guān)于“兩種文化”的第二次演講,他承認(rèn)忽略了“第三種文化”的出現(xiàn)。即社會科學(xué)(the social sciences)。20世紀(jì)50年代以后,在歐美的各大學(xué)中從事社會研究、應(yīng)用研究、專業(yè)研究和職業(yè)研究的學(xué)者日益增多。而他們的研究對象既不屬于“人文”領(lǐng)域也不屬于“科學(xué)”領(lǐng)域。
針對斯諾學(xué)科分類觀點(diǎn)的缺陷和偏頗,美國心理學(xué)家、哈佛大學(xué)教授卡根指出。大多數(shù)知識活動包括三個(gè)方面的因素:一,要有一套不容置疑的前提或假設(shè),它使得某類特殊問題及其解答具有優(yōu)先權(quán)。二,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針對所得證據(jù)的分析工具。三,要有一套精心選擇的作為解釋的核心概念。他認(rèn)為,社會科學(xué)家和人文主義者比自然科學(xué)家擁有更多的前提假設(shè)、分析工具和概念術(shù)語。自然科學(xué)家強(qiáng)調(diào)物質(zhì)進(jìn)程,將歷史文化背景及相關(guān)倫理價(jià)值的影響最小化。并且主要關(guān)注概念和一系列觀察之間的關(guān)系。社會科學(xué)家和人文主義者抵制過多的生物學(xué)方面的影響。更倚重于語義學(xué)的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通常要追尋一個(gè)在倫理學(xué)上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卡根還列表系統(tǒng)地比較了三種文化各方面的異同:
卡根教授的劃分嚴(yán)謹(jǐn)細(xì)密。相當(dāng)準(zhǔn)確地概括了三大學(xué)科的本質(zhì)特征,標(biāo)志著知識發(fā)展和學(xué)科分類已進(jìn)入成熟時(shí)代,人文科學(xué)的內(nèi)涵和外延已經(jīng)變得更加清晰。
人文科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社會科學(xué)區(qū)分明顯,但也有交叉滲透、界限模糊的地方。比如,歷史、人類學(xué)、心理學(xué)既可歸屬于人文科學(xué)也可歸屬于社會科學(xué)。而且當(dāng)今有關(guān)性別、團(tuán)體、族群等熱點(diǎn)問題研究就屬于跨學(xué)科的領(lǐng)域。不過社會科學(xué)與人文科學(xué)的研究方法各有側(cè)重。前者會更多地借用自然科學(xué)的物理語言或數(shù)字統(tǒng)計(jì)的方法去描述社會事實(shí)。而后者不回避使用隱喻性或象征性的語言去表達(dá)人的存在狀態(tài)并作出道德的或?qū)徝赖膬r(jià)值判斷。
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和人文知識都是人類創(chuàng)造或發(fā)現(xiàn)的,其目的是服務(wù)于人類自身的各種美好需要,如果說自然科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主要是解決人類物質(zhì)和制度方面的外在需求。那么人文科學(xué)大致是要滿足人類內(nèi)在的心靈需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當(dāng)代以色列教育家阿拉尼指出,人文教育有三大基本目標(biāo):一是讓學(xué)生理解文化中的高質(zhì)量因素。文化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是描述性的或說中性的,指各種不同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表達(dá)方式的堆積和累加;另一方面文化是規(guī)范性和理想性的,與野蠻、無知和魯莽相反,它指向一種進(jìn)步的、高尚的和精致的生活方式。人文教育就是讓學(xué)生能夠?qū)Ω呒壩幕屯昝兰內(nèi)芯薮蟮臒崆楹涂释@種教育采取的不是非黑即白式的二元對立的方法。而是堅(jiān)持避免絕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多元對話的態(tài)度立場。二是培養(yǎng)學(xué)生自覺的和批評性的思維方式。人文教育不是灌輸、教化或洗腦,而是讓學(xué)生養(yǎng)成理性的、批評性的和獨(dú)立的質(zhì)量風(fēng)格,讓學(xué)生成為自己思想和行為的主人,而不是受外在權(quán)威、社會習(xí)俗和迷信偏見所左右的奴仆。批評性的自覺自治是第一的或最重要的知識質(zhì)量和美德,如果人們不去獨(dú)立地思考和判斷他們的父母、老師和雇主的想法,那么科技的發(fā)展、倫理和人權(quán)的進(jìn)步是不可能的。三是教育學(xué)生實(shí)現(xiàn)并完成真正的自我。這一點(diǎn)與前面的批評性的自治不同。它并不局限于自覺的和反思性的知識活動,而是全方位的自我個(gè)性的充分展開和實(shí)現(xiàn)。自我的真實(shí)性不僅意味著“想自己所想的”(thinking for themselves),而且包括“做自己要做的”(being what they are),即對自己忠誠。這種人關(guān)注、尊重并忠實(shí)于自我的存在狀態(tài)與獨(dú)特本質(zhì),執(zhí)著于內(nèi)在世界與外在行為的統(tǒng)一和協(xié)調(diào),而不是墨守成規(guī)、自我異化和裝腔作勢。
面對現(xiàn)代性的不斷挑戰(zhàn),人文科學(xué)在當(dāng)代高等教育的領(lǐng)地逐漸被收窄,其作用也不斷被弱化。某些研究態(tài)度和方法的弊病在逐漸突顯:首先是人類知識的碎片化。知識的分科化有利于專業(yè)性的深入探究,但卻造成了故步自封、畫地為牢甚至壁壘森嚴(yán)的學(xué)術(shù)格局。專家學(xué)者們往往以自己的專長而壟斷吹噓、自以為是,常常以非自己的領(lǐng)域而規(guī)避責(zé)任。人文科學(xué)重視個(gè)體性和差異性,但其研究的視角必須是綜合性的。它不能不考慮或參照自然科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的研究結(jié)果,這是其自身的超越性和理想性所要求的。其次是研究內(nèi)容的數(shù)據(jù)化。這是受到了自然科學(xué)或數(shù)理統(tǒng)計(jì)方法的過度影響,有時(shí),冰冷而枯燥的數(shù)據(jù)并不能真實(shí)地反映人性深層的存在狀態(tài)。正如《文化中國》編輯子夜所言:“包括量化比較手段和數(shù)據(jù)至上觀念。都是西方現(xiàn)代性的理性主義和工具主義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的體現(xiàn)。尤其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市場因素介入到人文學(xué)術(shù)研究。將會導(dǎo)致學(xué)術(shù)的變形和泡沫現(xiàn)象。”最后是學(xué)術(shù)成果的功利化。今天的人文學(xué)術(shù)研究已經(jīng)很少是內(nèi)在的“為己之學(xué)”,更多的是為外物左右的功利之學(xué)。這也是受無序的商業(yè)市場和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所驅(qū)動的結(jié)果。在價(jià)值迷失的時(shí)代,恢復(fù)人本主義的精神、重建人文教育的體系是學(xué)者和教育工作者們義不容辭的責(zé)任。
責(zé)任編輯:楊國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