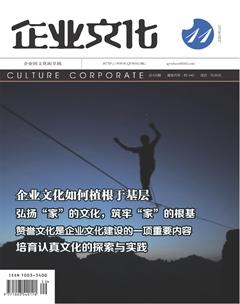論偵查監督的完善
鄭博
作為刑事訴訟活動的基礎性階段,偵查階段尤其體現國家權力與被指控方權利的對抗性,如何平衡這種對抗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國家的法治發展水平。從權力特點看,偵查權的行政權力屬性有必要受到監督與制約,鑒于我國尚未建立法院對偵查活動的司法審查機制,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仍然由檢察機關承擔。在權力行使方面,偵查權的行使通常具有高效性、封閉性等特征,且這種“封閉”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為偵查階段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尚未定論,保持偵查活動一定的封閉性有助于降低其名譽風險,因此更有必要對偵查行為予以監督。
一、偵查監督存在的問題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今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強調,加強對認罪認罰案件偵查和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防止冤假錯案發生。偵查監督是我國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法定職權,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偵查監督權的有效行使對于從源頭上預防冤假錯案具有重要意義。當前,完善偵查監督應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以司法責任制為核心的司法體制改革以及以完善檢察監督體系為目標的檢察改革的背景下進行。然而,無論從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還是一些地區的實踐探索來看,偵查監督職能均有待進一步發揮。
雖然我國檢察機關介入偵查活動的時間節點較早,但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往往較為滯后,其監督方式多表現為一種程序性職權,懲戒力稍顯不足,以致于實踐中的監督效果較為有限:其一表現為偵查監督方式的訴訟性不足,而更多的體現為一種被動式監督。其二表現為相關法律依據的授權性不足,立法對偵查權的規定多以限權性規定的形式出現,從而導致對偵查活動的監督欠缺一定的針對性,使偵查權的行使中可能存在較大的運作空間。其三表現為監督方式較為被動,往往通過審查案卷材料及證據行使監督職能。
從監督范圍來看,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檢察機關執法工作基本規范(2013年)》,偵查監督工作涵蓋九項業務范圍,總體上可歸為審查逮捕、立案監督、偵查活動監督等三方面內容。從監督重點來看,200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在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工作中加強證據審查的若干意見》,要求高度重視證據審查工作,全面客觀審查證據,以及嚴格依法排除非法證據。201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十三五”時期檢察工作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建立書面審查與調查復核相結合的親歷性辦案模式,推行以客觀性證據為主導的證據審查模式。可見,完善偵查監督重點在于強化對證據的審查力度和效果。另外,從偵查監督的有效性仍待進一步發揮的實踐現狀來看,也應強化證據審查對偵查監督的推進作用。
二、偵查監督完善建議
證據的收集與運用在實體意義上是定罪量刑的基礎,在程序意義上是取證行為規范性的體現,偵查活動實質上也是一種證據收集活動,對偵查活動的監督本質上則表現為對偵查機關取證行為合法性的監督,檢察機關行使偵查監督職能主要是通過審查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相關證據來實現。從偵查監督的范圍來看,無論是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過程中,還是在對具體偵查活動的監督過程中,強化證據審查,完善偵查監督,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避免審查過程的主觀傾向,即單純從有罪推定思維出發進行證據審查,這種主觀思維主導下的證據審查多是不全面的,全面性不僅是證據收集活動的要求,也應適用于證據審查活動,否則難以發揮監督偵查取證的作用。同時,為保障證據審查的全面性,首先應對客觀性證據進行審查,相較于偵查機關收集的犯罪嫌疑人口供、證人證言等主觀性證據,物證、書證等客觀性證據更能較為真實、穩定的顯示出偵查活動對查明案件的進展情況,或者說在案證據體系的牢固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客觀性證據所占比重,通過優先審查偵查活動中收集的客觀性證據,才能更準確的把握辦案方向,以客觀性證據檢驗主觀性證據的真實性,從而提高公訴質量。
其次,審查證據的形式合法性與實質合法性并重。對證據合法性的審查既包括取證主體的合法性,也包括取證行為的合法性,二者缺少其一則應否定該證據的證據力。然而,檢察機關在偵查監督過程中對證據的實質合法性審查與審判機關審查證據從而定罪量刑的職能之間并不存在沖突,相反正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要求,實踐中對取證主體合法與否相對容易把握,而問題多出于對取證行為合法性的監督方面,因為多數非法證據來源于違法的取證行為,對該證據應嚴格予以排除。兼顧審查證據的形式合法性與實質合法性,尤其應重視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證據的審查,并重點審查是否存在非法取證的疑點,以使過濾后的證據之間能夠相互印證。
再次,引導偵查取證。除承擔法律監督職能外,檢察機關還承擔著支持公訴的職能,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引導則主要集中于對偵查機關取證活動的引導,而非對偵查機關其他專門性調查工作的引導。基于行使公訴職能的考慮,以及偵查機關在偵查技術、偵查設備、取證技巧等方面的優勢,為更好的實現捕訴銜接,檢察機關應將引導取證作為切入點,從而一定程度上降低證據審查的時間、人力、物力等成本,以發揮輔助證據審查的作用。一方面應加強檢警協作,如建立檢察引導偵查的溝通與反饋機制,避免案件介入機制的虛置性。另一方面應強化監督,避免出現以引導取代監督的傾向。
最后,通過拓展監督渠道強化證據審查力度和效果。相較于對偵查活動的人大監督、輿論監督等監督形式,作為刑事司法體系內的監督形式,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具有較突出的司法屬性,正是基于此,應借助這一優勢強化捕訴銜接,如建立案件督辦機制及時糾正違法偵查取證行為;介入案發現場固定、保全相關證據,增強證據審查的親歷性,必要時通過對案件進行跟蹤調查、走訪,變被動監督為主動監督;充分利用互聯網平臺,實現與偵查機關之間的信息共享,增強監督的時效性,從而一定程度上弱化偵查活動的封閉性。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