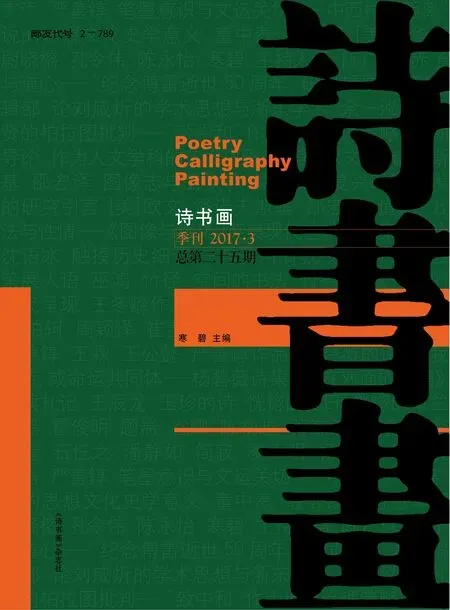道路、方法與性情
——《圖像與意義:英美現(xiàn)代藝術(shù)史論集》導(dǎo)論
沈語冰
道路、方法與性情
——《圖像與意義:英美現(xiàn)代藝術(shù)史論集》導(dǎo)論
沈語冰
一九一七年,當(dāng)杜尚(Marcel Duchamp)將一個現(xiàn)成品送到紐約獨(dú)立藝術(shù)家大展上展出之時,他發(fā)動了對古典美學(xué)的最后顛覆。①參見蒂埃爾·德·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沈語冰、張曉劍、陶錚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4年。版本下同。康德(Immanuel Kant)建立在與日常對象相區(qū)別的審美對象獨(dú)特性之上的整個傳統(tǒng)美學(xué)思想的大廈坍塌了。②Immanual Kant, Kritik der Utreilskraft, Ausgabe der ko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02.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erner Pluhar,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對康德美學(xué),特別是其第三《批判》的讀解,參見Henry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Taste: A Reading of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Judg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aul Guyer, Kant and The Claims of Taste, 2nd.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隨著概念藝術(shù)、大地藝術(shù)、行為藝術(shù)和裝置藝術(shù)的出現(xiàn),藝術(shù)的邊界得到了擴(kuò)展,藝術(shù)理論也作出了巨大變革,以回應(yīng)藝術(shù)實踐所提出的問題。③參見H. H. 阿納森《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繪畫、雕塑、建筑》,鄒德儂、巴竹師、劉珽譯,沈玉麟校對,天津:天津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佐亞·科庫爾《1985年以來的當(dāng)代藝術(shù)理論》,梁碩恩編,王春辰、何積惠、李亮之等譯,王春辰審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上世紀(jì)七十年代以來,在哲學(xué)、文學(xué)理論等人文學(xué)科的影響下,藝術(shù)理論獲得了迅猛發(fā)展,大有凌駕于實踐之上的趨勢,以至于從上個世紀(jì)下半葉以來,二十世紀(jì)開始有了“理論的世紀(jì)”之稱。④參見沈語冰《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3年,第1-11頁。版本下同。
早在十九世紀(jì)初,出于對現(xiàn)代性社會的分化規(guī)律的尊重,不以藝術(shù)創(chuàng)作為鴣的,而以歷史探索為旨?xì)w的獨(dú)立的藝術(shù)史學(xué)科,率先在德語區(qū)創(chuàng)建。⑤施洛塞爾等《維也納美術(shù)史學(xué)派》,陳平編選,張平等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二十世紀(jì)初,這個學(xué)科空前繁榮,并在西方英語國家及世界其他各國建立起來。⑥參見陳平《西方美術(shù)史學(xué)史》,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8年;張堅《視覺形式的生命》,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4年。從一開始,藝術(shù)史學(xué)科就設(shè)在綜合性大學(xué),而不是藝術(shù)學(xué)院;隸屬于人文學(xué)科,而不依附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因此,藝術(shù)史是一種智性的和獨(dú)立的科學(xué),不受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制約,就成為這個學(xué)科的基本規(guī)定性。⑦潘諾夫斯基《作為人文學(xué)科的藝術(shù)史》,載《藝術(shù)史的視野——圖像研究的理論、方法與意義》,曹意強(qiáng)等主編,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7年,第3-17頁。
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史學(xué)科發(fā)生了重大改變。因科技發(fā)展而來的視覺文化的飛速發(fā)展,電影、電視、廣告等新興視覺媒體的滲透,迫使藝術(shù)史重新思考傳統(tǒng)杰作之外的大量視覺現(xiàn)象,文化研究、電影研究、視覺文化研究等學(xué)科相繼建立,“新藝術(shù)史”(New Art History)也應(yīng)運(yùn)而生。⑧參見喬納森·哈里斯《新藝術(shù)史——批評導(dǎo)論》,徐建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2010年。在這個背景下,對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的評論和學(xué)術(shù)研究,也開始納入藝術(shù)史、“新藝術(shù)史”或視覺文化研究的范圍。以美國為例,七十年代,羅莎琳·克勞斯(Rosalind Krauss)以二十世紀(jì)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大衛(wèi)·史密斯(David Smith)為題,獲得哈佛大學(xué)藝術(shù)史博士學(xué)位,開創(chuàng)了以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學(xué)術(shù)研究獲博士學(xué)位的先例。⑨帕梅拉·李《當(dāng)代,那時與現(xiàn)今:個人以及一代人的觀點》,載《立場·模式·語境——當(dāng)代藝術(shù)史的書寫》,高名潞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其后她在紐約大學(xué)、哥倫比亞大學(xué)開設(shè)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史課程,特別是提出并實施以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史論為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計劃,培養(yǎng)了一大批現(xiàn)今活躍在各國的藝術(shù)史家、藝術(shù)批評家和策展人。⑩迄今為止,活躍在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史研究、策展和評論的一線的北美學(xué)者,如哈爾·福斯特(Hal Foster)、大衛(wèi)·喬塞利(David Joselit)、帕梅拉·李(Pamela Lee)等等,都師從羅莎琳·克勞斯。與此同時,受到美國當(dāng)代藝術(shù)實踐、批評和理論研究的活力的感召,許多才華橫溢的歐洲學(xué)者紛紛前往美國主要大學(xué)擔(dān)任教職,包括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學(xué)生、法國人伊夫-阿蘭·博瓦(Yve-Alain Bois),德國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傳人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以及比利時學(xué)者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關(guān)于美國藝術(shù)實踐與批評對歐洲藝術(shù)史學(xué)者的吸引力,參見本雅明·布赫洛《新前衛(wèi)與文化工業(yè)》,何衛(wèi)華等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4年,第1-2頁;以及伊夫-阿蘭·博瓦《圓桌會議: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困境》一文中的評論,載Foster, Hal, Rosalind Krauss, Yve-Alain Bois & Benjamin Buchloh.Art Since 1900: Modernism, Antimoder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 2005, p.671.
遺憾的是,受到前蘇聯(lián)學(xué)科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我國從一開始就將藝術(shù)史學(xué)科設(shè)在藝術(shù)院校。在強(qiáng)調(diào)“學(xué)以致用”、“實踐高于理論”,特別是在“理論要為實踐服務(wù)”等實用主義和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下,我國的藝術(shù)史學(xué)科一直處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附庸地位。在我國,廣義上的“藝術(shù)理論”(與“藝術(shù)實踐”相對稱)包括藝術(shù)史、藝術(shù)理論(狹義)和藝術(shù)批評。從一開始就處于邊緣和附庸地位的它,發(fā)展非常不理想,其直接后果便是使藝術(shù)創(chuàng)作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智識支持和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由急功近利和短視所帶來的“使用說明書”式的藝術(shù)理論——理論研究要為實踐提供說明——從根本上缺乏獨(dú)立和智慧,也因此失去了自主學(xué)術(shù)的引領(lǐng)作用和超越作用。以學(xué)術(shù)自身的價值言之,這種實用主義的小聰明卻以智識的大智慧為代價。以學(xué)術(shù)的大功用言之,藝術(shù)理論在我國遠(yuǎn)未形成一種獨(dú)立自主的力量,因而也未能與政治和資本形成博弈之勢。其結(jié)果,正如我在其他場合曾多次指出的那樣,二十世紀(jì)的中國藝術(shù),不是被政治綁架而走,便是為資本裹挾而去。
理論實用主義的一個間接后果則是,在一般品味和大眾審美方面,我國的情形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世界的潮流和趨勢。不消說,我國公眾的一般趣味還停留在古典藝術(shù)上。在藝術(shù)院校或綜合性高校里,通史課或通識課也還以古典藝術(shù)為主;間或提到一點現(xiàn)代藝術(shù),通常也到印象派為止。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學(xué)院里,除了個別涉及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專業(yè),總的情形仍然是對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充滿了無知、偏見和漠視。有關(guān)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研究,基礎(chǔ)十分薄弱。簡單地說,與西方研究機(jī)構(gòu)已經(jīng)將重心轉(zhuǎn)向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不同,在我國,對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研究,基本上還處于散兵游勇狀態(tài)。
作為一個學(xué)科,藝術(shù)史論在我國的發(fā)展尤其不利的原因,可由一個顯而易見的史實加以說明:滕固作為我國近代接受過歐洲藝術(shù)史學(xué)科正規(guī)訓(xùn)練的極少數(shù)藝術(shù)史論專家之一,英年早逝,只留下了令人欷歔的著述和數(shù)十年寂寞的身后名。①滕固《美術(shù)史論著三種》,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與西方哲學(xué)和外國文學(xué)相比——盡管二十世紀(jì)后半葉的社會環(huán)境,對這些學(xué)科的發(fā)展總的來說是極為不利的,但薪火相傳,到上世紀(jì)晚期改革開放之時,這些學(xué)科的巨擘碩儒尚存——美術(shù)史論的研究是何等寂寥!
我長期執(zhí)教于綜合性大學(xué),對學(xué)科之間發(fā)展的不平衡有切膚之痛。與外國文學(xué)和西方哲學(xué)這樣的大學(xué)科相比,西方美術(shù)史的文獻(xiàn)少得可憐。人們可以看到世界文學(xué)名著基本上都已經(jīng)譯成中文了,大多還不止一個版本;西方哲學(xué)大家的選集甚或全集,也都有了中譯本。而西方美術(shù)史,之前除了范景中先生主持的貢布里希(E. H. Gombrich)著作的翻譯②E. H. 貢布里希《藝術(shù)的故事》,范景中譯,楊成凱校,桂林: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08年;《象征的圖像——貢布里希圖像學(xué)文集》,楊思梁、范景中譯,2015年;《秩序感——裝飾藝術(shù)的心理學(xué)研究》,楊思梁、徐一維、范景中譯,2015年;《理想與偶像——價值在歷史和藝術(shù)中的地位》,范景中、楊思梁譯,2013年;《藝術(shù)與錯覺——圖像再現(xiàn)的心理學(xué)研究》,楊成凱、李本正、范景中譯,2015年;《圖像與眼睛——圖畫再現(xiàn)心理學(xué)的再研究》,范景中、楊思梁、徐一維、勞誠烈譯,2013年;《木馬沉思錄——藝術(shù)理論文集》,曾四凱、徐一維等譯,2015年;《偏愛原始性——西方藝術(shù)和文學(xué)中的趣味史》,楊小京譯,2016年;《敬獻(xiàn)集——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解釋者》,楊思梁、徐一維譯,2016年。,陳平先生主持的維也納學(xué)派文獻(xiàn)的翻譯③李格爾《羅馬晚期的工藝美術(shù)》,陳平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維克霍夫《羅馬藝術(shù)》,陳平譯,2010年;德沃夏克《作為精神史的美術(shù)史》,陳平譯,2010年;施洛塞爾等《維也納美術(shù)史學(xué)派》,陳平編選,張平譯,2013年;德沃夏克《哥特式雕塑與繪畫中的理想主義與自然主義》,陳平譯,2015年;沃爾夫林《美術(shù)史的基本概念》,陳平譯,2015年。,是較為系統(tǒng)的以外,其他藝術(shù)史大師的作品,甚至其代表作,都還沒有介紹到中國來。
與之相應(yīng)的是,我國的外國藝術(shù)史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幾位學(xué)者的系統(tǒng)翻譯外,注重學(xué)術(shù)淵流、重視史學(xué)史、具有目錄學(xué)意識的也不多。以二○一三年Thames& Hudson公司出版的Books That Shaped Art History(中譯本《塑造美術(shù)史的十六書》)為例。此書介紹了西方藝術(shù)史上十六位大家的十六部代表作,作為初涉藝術(shù)史學(xué)科的入門津梁。④理查德·肖恩、約翰-保羅·斯托納德《塑造美術(shù)史的十六書》,萬爽等譯,桂林: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6年。但到目前為止,大約只有八部有中譯本。范景中先生等翻譯了其中的四種(包括沃爾夫林、潘諾夫斯基和貢布里希的書),我翻譯或組織翻譯了另外四種(分別是羅杰·弗萊的《塞尚及其畫風(fēng)的發(fā)展》,格林伯格的《藝術(shù)與文化》,羅莎琳·克勞斯的《前衛(wèi)的原創(chuàng)性及其他現(xiàn)代主義神話》,漢斯·貝爾廷的《圖像與崇拜》)。《十六書》所提供的書目當(dāng)然不是唯一的選擇,而且偏重于英美藝術(shù)史著作的缺點也非常明顯,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歐美學(xué)者對藝術(shù)史這一學(xué)科形狀的基本看法。從這份書目中,我們不難看出我國西方藝術(shù)史視野的局限性。
一、起源即道路
在這種情況下,翻譯、梳理和研究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史論,就顯得尤為重要。藝術(shù)史論的翻譯涉及目錄學(xué)、翻譯學(xué)、藝術(shù)史等眾多學(xué)科。而藝術(shù)史又涉及文史哲和社會科學(xué)的大量學(xué)科。因此,翻譯工作最能考驗譯家的目錄學(xué)修養(yǎng)、外文和母語水平、藝術(shù)史學(xué)科的訓(xùn)練以及綜合素質(zhì)。
書目的選擇可以見出翻譯家的眼光。從浩如煙海的文獻(xiàn)中遴選出值得翻譯的經(jīng)典著作,不僅需要譯家熟諳文獻(xiàn)目錄,而且需要長時間的深入研究為前提。關(guān)于目錄之學(xué),清代學(xué)者王鳴盛說過一段經(jīng)常被引用的文字:“目錄之學(xué),學(xué)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xué)精究,質(zhì)之良師,未易明也。”又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xué)。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①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可見,苦學(xué)精究與質(zhì)之良師,乃趨近目錄學(xué)之法門。無論是在策劃和推動“鳳凰文庫·藝術(shù)理論研究系列”時,還是在我本人的外國美術(shù)史學(xué)習(xí)中,我大概都稱得上是這一至理名言的踐行者。

羅杰·弗萊(自畫像)
早在二○○一年初,我還在英國做訪問之時,就致信范景中先生,就翻譯出版一套藝術(shù)批評譯叢之事,專門列出一個書目,征求他的意見。這個書目后來成為“鳳凰文庫·藝術(shù)理論研究系列”的基礎(chǔ)。正式執(zhí)編鳳凰文庫時,我又專門去南山路拜訪范先生,并就書目一節(jié)請求教益。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再請美國芝加哥藝術(shù)學(xué)院的詹姆斯·艾爾金斯(James Elkins)教授專門為中文讀者撰寫了一個西方當(dāng)代藝術(shù)史方法論的書目。
艾爾金斯教授在其《1970年以來的西方藝術(shù)理論概覽》(“A Brief Look at Western Art Theory, 1970 to the Present”)中羅列了17種趨勢或取向:現(xiàn)代主義(Modernism)、盛期現(xiàn)代主義(High Modernism)、女性主義(Feminism)、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批評(Marxism or Marxist Criticism)、藝術(shù)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Art)、后結(jié)構(gòu)主義(Post-Structuralism)、符號學(xué)藝術(shù)史(Semiotic History of Art)、反現(xiàn)代主義(Anti-Modernism)、體制批評(Institutional Critique)、社會學(xué)藝術(shù)史(Sociological History of Art)、經(jīng)濟(jì)學(xué)藝術(shù)史(Economic History of Art)、科學(xué)的藝術(shù)史(Scientific History of Art,指用自然科學(xué)的方法來理解藝術(shù)史的趨向)、述行批評(Performative Criticism)、關(guān)系美學(xué)(Relational Aesthetics)、藝術(shù)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 of Art),以及精神分析批評(Psychoanalytic Criticism)。②詹姆斯·艾爾金斯《1970年代以來的西方藝術(shù)理論概覽》,陶錚譯,沈語冰校,《美術(shù)研究》,2010年第3期。艾爾金斯教授一再強(qiáng)調(diào),這只是他的個人所見,是不完全的,而且一定帶有個人偏好。我也絲毫不想讓讀者誤以為,我相信這就是西方藝術(shù)史、藝術(shù)理論與批評的全部。但是,僅僅作為一個出發(fā)點,它為我提供了方便。
艾爾金斯教授的單子中所列的各種潮流,并非沒有交集或可歸入大類的共同點。事實上,它們可以清楚地歸入幾個大類。例如,現(xiàn)代主義、盛期現(xiàn)代主義可以明確地歸入一類。女性主義、批判理論、馬克思主義批評、藝術(shù)社會史、體制批評,也不妨歸入一個大類。如果說前者致力于從現(xiàn)代藝術(shù)史的內(nèi)在邏輯(羅杰·弗萊的形式主義理論、格林伯格的現(xiàn)代主義繪畫理論、邁克爾·弗雷德綜合后期維特根斯坦的慣例理論)來解釋現(xiàn)代藝術(shù)史,那么,后一個大類則傾向于從藝術(shù)的外部因素來解釋藝術(shù)史。此外,后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學(xué)藝術(shù)史、反現(xiàn)代主義、述行批評、關(guān)系美學(xué)等等,接近于,或者干脆構(gòu)成了,通常被稱為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種種。而社會學(xué)藝術(shù)史、經(jīng)濟(jì)學(xué)藝術(shù)史、科學(xué)的藝術(shù)史、藝術(shù)接受理論,以及精神分析批評,則又屬于另一大類。總之,它們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個板塊:即形式主義-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社會史、后現(xiàn)代主義及其他(包括精神分析)。
這個框架結(jié)構(gòu),與我在《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中架構(gòu)上個世紀(jì)西方藝術(shù)史論(特別是批評史)方法論的框架,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在交代《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一書的結(jié)構(gòu)時曾經(jīng)這樣說:
他們是本書圍繞著現(xiàn)代主義、歷史前衛(wèi)藝術(shù)、后現(xiàn)代主義這三個關(guān)鍵術(shù)語組織起來的敘述線索上的關(guān)鍵人物。現(xiàn)代主義以波德萊爾作為引子(導(dǎo)論),接著過渡到羅杰·弗萊的形式主義批評(第一章),再到阿波利奈爾的立體主義批評(第二章),可以讀作現(xiàn)代主義基本主題的呈示部;接著,在展開部中,本雅明(第三章)與赫伯特·里德(第四章)、格林伯格(第五章)與羅森伯格(第六章),則代表了歷史前衛(wèi)藝術(shù)與現(xiàn)代主義的交替展開;而詹克斯(第七章)與克萊默(第八章),不妨稱之為后現(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的曲折展開,最后,在再現(xiàn)部中,鄧托的后現(xiàn)代主義(第九章)與阿多諾的現(xiàn)代主義(第十章)則代表了當(dāng)代藝術(shù)理論與批評中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xué)總結(jié)。①沈語冰《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第12頁。
換句話說,二○○三年,我就以現(xiàn)代主義(Modernism)、(歷史)前衛(wèi)藝術(shù)(Historical Avant-garde)與后現(xiàn)代主義(Post-Modernism)這樣三個術(shù)語來組織二十世紀(jì)西方藝術(shù)批評的主要線索。稍后,我將現(xiàn)代主義、前衛(wèi)藝術(shù)與后現(xiàn)代主義視為現(xiàn)代藝術(shù)研究與批評的三大范疇。②詳見沈語冰《現(xiàn)代藝術(shù)研究的范疇性區(qū)分:現(xiàn)代主義、前衛(wèi)藝術(shù)與后現(xiàn)代主義》,載《藝術(shù)百家》,2006年第4期。
無獨(dú)有偶,在美國學(xué)者哈爾·福斯特、羅莎琳·克勞斯、伊夫-阿蘭·博瓦及本雅明·布赫洛所撰寫的《1900年以來的藝術(shù):現(xiàn)代主義、反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Hal Foster, Rosalind Krauss, Yve-Alain Bois & Benjamin Buchloh,Art Since 1900: Modernism, Antimodernism,Postmodernism)一書里,四位作者以現(xiàn)代主義、反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這樣三個術(shù)語來架構(gòu)其二十世紀(jì)的藝術(shù)史敘事。盡管他們的反現(xiàn)代主義概念與我所說的(歷史)前衛(wèi)藝術(shù)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它們在指稱達(dá)達(dá)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特別是“無形式藝術(shù)”(“formless art”)時,又有驚人的一致性。③參見Hal Foster, Rosalind Krauss, Yve-Alain Bois & Benjamin Buchloh. Art Since 1900: Modernism, Antimoder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 2005。他們在該書導(dǎo)論中列出二十世紀(jì)西方藝術(shù)史書寫的主要方法時,又提出了形式主義-結(jié)構(gòu)主義(Formalism-Structuralism)、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藝術(shù)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Art)和后結(jié)構(gòu)主義(Post-Structuralism),作為主要的方法論。④筆者在《藝術(shù)史經(jīng)典文獻(xiàn)導(dǎo)讀書系·美術(shù)學(xué)卷》里收入了這四篇導(dǎo)論的中譯文,(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
細(xì)心的讀者應(yīng)該可以發(fā)現(xiàn),這與眼前這本書的主要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非常接近:從羅杰·弗萊的形式主義理論,經(jīng)格林伯格的現(xiàn)代主義學(xué)說,到列奧·施坦伯格的現(xiàn)代圖像學(xué)研究,再到邁耶·夏皮羅的精神分析和T.J. 克拉克的藝術(shù)社會史,最后是喬納森·克拉里的視覺考古學(xué)。
如果說“質(zhì)之良師”是我的治學(xué)道路的第一步,那么走出這一步前提則是“苦學(xué)精究”。到目前為止,我的治學(xué)過程大約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主要的著述是一本概論性的書《透支的想象:現(xiàn)代性哲學(xué)引論》。這本書與其說是寫給讀者看的,還不如說是寫給自己看的。因為我想弄清楚現(xiàn)代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究竟如何看待傳統(tǒng)、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關(guān)系。通過這本書,我大體上為后來的治學(xué)道路準(zhǔn)備了一種較為宏闊的框架,使我得以在現(xiàn)代性這一大視野里來觀照現(xiàn)代藝術(shù)問題。⑤參見沈語冰《透支的想象:現(xiàn)代性哲學(xué)引論》,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2003年。版本下同。此書實撰寫于2000年之前,但出版滯后。第二個階段是二○○○年前后,我想在現(xiàn)代性這一宏觀視野下來研究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問題,特別是現(xiàn)代藝術(shù)批評問題。我有一個直覺,即如果從現(xiàn)代藝術(shù)史本身入手,那么,眾多藝術(shù)流派、藝術(shù)家、藝術(shù)作品、藝術(shù)思潮和理論,會使你如墜五里霧中,失去方向。而假如我們循著藝術(shù)批評的理論與思潮,那就相當(dāng)于抓住了主要問題,抓住了綱要,可以將現(xiàn)代藝術(shù)這張大網(wǎng)拉起來。這就是《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這本書的由來。⑥參見沈語冰《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第三個階段,就是從《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出版以來直到現(xiàn)在,進(jìn)一步完善、細(xì)化和深化前一個階段的工作。《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寫了十大批評家,每一個批評家都只得到了粗線條的勾勒。例如,我在那本書的第一章就寫了羅杰·弗萊,但只有兩萬字。后來,我翻譯了弗萊的兩部著作,寫出了關(guān)于弗萊的將近二十萬研究性文字。這自然不是當(dāng)年那兩萬字可以比擬的了。⑦參見羅杰·弗萊《塞尚及其畫風(fēng)的發(fā)展》,沈語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此書除正文6萬字外,包含了譯者導(dǎo)論、注釋、附論約14萬字;由南寧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6年修訂再版。羅杰·弗萊《弗萊藝術(shù)批評文選》,沈語冰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2013年。除譯文外,筆者為此書撰寫了約4萬字的譯者導(dǎo)論。
不妨這么說,伴隨著我學(xué)術(shù)起步的是羅杰·弗萊(Roger Fry)。在我看來,他是西方美術(shù)史上非常罕見的那種能夠?qū)⑴u家的敏銳與史學(xué)家的博學(xué)結(jié)合起來的偉人。作為意大利古典藝術(shù)的鑒定大師,他在非常年輕時就被任命為美國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的歐洲繪畫部主任,并與意大利繪畫鑒定大師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美國古典藝術(shù)鑒定家和意大利文藝復(fù)興藝術(shù)史專家伯納德·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一道,構(gòu)成歐洲古典繪畫鑒藏圈的金字塔塔尖。①參見Bernard Berenson & Kenneth Clark, My Dear BB: The Letters of Bernard Berenson and Kenneth Clark, 1925–1959,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弗萊還是“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這一藝術(shù)運(yùn)動的命名者,以及塞尚等后印象派畫家的主要評論家和藝術(shù)史家。②參見筆者為《塞尚及其畫風(fēng)的發(fā)展》所寫的譯者導(dǎo)論,以及 “Roger Fry: Found Vision and Made Design”, in Richard Shiff, Cézanne and the End of Impression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143-152。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與弗吉妮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一道,弗萊等人形成了布魯姆斯伯里團(tuán)體(Bloomsbury Group)的核心,對二十世紀(jì)的整個美學(xué)現(xiàn)代主義運(yùn)動,乃至對歐洲的全部智識生活,都產(chǎn)生了難于估量的影響。③這方面,也許沒有比弗萊的后繼者、英國著名藝術(shù)史家肯尼思·克拉克“一言而為天下法”的總結(jié)更精彩的了:“如果說趣味可以因一人而改變,那么這個人便是羅杰·弗萊。” Kenneth Clark, introduction to Fry’s Last Lectur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9, p.ix
而將羅杰·弗萊的形式主義方法向前推進(jìn),從而形成對現(xiàn)代主義最清晰陳述的,便是美國大批評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④參見格林伯格《藝術(shù)與文化》,沈語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2015年。格林伯格的學(xué)術(shù)思想及其批評理論,已經(jīng)遭到了后來者的批評,但是,幾乎沒有人會否認(rèn)他在美國紐約畫派的思想自覺的過程中,以及在這一畫派被世界所接受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關(guān)鍵角色。⑤參見邁克爾·萊杰《重構(gòu)抽象抽象表現(xiàn)主義》,毛秋月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5年;奈菲、懷特·懷特-史密斯《波洛克傳》,沈語冰等譯,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啟真館),2017年即將出版。更重要的是,格林伯格對現(xiàn)代主義理論高度濃縮概括和至為明晰的辯護(hù),既成為后現(xiàn)代主義者最主要的攻擊目標(biāo),⑥參見阿瑟·丹托《藝術(shù)的終結(jié)之后》,王春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也成為今天討論整個二十世紀(jì)西方藝術(shù),乃至整個藝術(shù)現(xiàn)代主義(格林伯格認(rèn)為始于馬奈[Manet])的起點。想象一下弗雷德在對馬奈的卓越研究中,對格林伯格的重要參照,以及在弗雷德與極簡主義(Minimalism)藝術(shù)家和批評家的論戰(zhàn)中,對格林伯格的反復(fù)指涉吧。⑦參見 Michael Fried, Manet’s Modern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邁克爾·弗雷德《藝術(shù)與物性》,張曉劍、沈語冰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3年。版本下同。
正是在梳理格林伯格的學(xué)術(shù)理路和批評方法時,我遭遇了美國另一個杰出的藝術(shù)史家和藝術(shù)批評家列奧·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某種意義上與羅杰·弗萊類似而比格林伯格更了不起的,乃是這樣一個事實:施坦伯格同時是意大利文藝復(fù)興藝術(shù)和戰(zhàn)后美國當(dāng)代藝術(shù)的權(quán)威。⑧參見Leo Steinberg, Michelangelo’s Last Pain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Leo Steinberg, The Sexuality of Christ in Renaissance Art and in Modern Obliv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Leo Steinberg, Encounters with Rauschenber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Leo Steinberg, Leonardo's Incessant Last Supper, Cambridge,Mass.: Zone Books, 2001;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Confrontations with Twentieth-Century Ar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對于這樣一位曾獲得過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xué)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有人文社科“諾貝爾獎”之稱)的藝術(shù)史家和藝術(shù)批評家,在我的翻譯和介紹之前,國內(nèi)美術(shù)史界幾乎聞所未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驚訝,也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可原諒的缺憾。⑨2011年5月,筆者應(yīng)邀參加了由美國亞洲文化協(xié)會主辦的“西方藝術(shù)和藝術(shù)史高級工作坊”,結(jié)識了美國著名文藝復(fù)興藝術(shù)史專家、國際公認(rèn)的米開朗琪羅研究權(quán)威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教授。兩人就施奧·施坦伯格對意大利文藝復(fù)興藝術(shù)史研究的貢獻(xiàn),進(jìn)行了坦誠而高效的交流。華萊士對施坦伯格的研究方法所做的即興演講,筆者作為“修訂版后記”的一部分,予以實錄,請參閱列奧·施坦伯格《另類準(zhǔn)則:直面20世紀(jì)藝術(shù)》,沈語冰、劉凡、谷光曙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3年,第503-506頁。如今,隨著施坦伯格的批評杰作《另類準(zhǔn)則:直面20世紀(jì)藝術(shù)》(Leo Steinberg,Other Criteria: Confrontations with Twentieth-Century Ar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中譯本的出版,人們對他的重要性終于有所認(rèn)識了。
一旦發(fā)現(xiàn)了格林伯格歷史和思想的雙重意義,我們也就不難發(fā)現(xiàn)同一時期美國另一位了不起的藝術(shù)史家和藝術(shù)批評家邁耶·夏皮羅(Meyer Schapiro)。夏皮羅通常被認(rèn)為是美國本土成長的最偉大的藝術(shù)史家。同時也是將藝術(shù)史家的淵雅博洽與批評家的敏銳睿智融會貫通的大師。在藝術(shù)史界,夏皮羅一直享有傳奇之名。如今的哥倫比亞大學(xué)還設(shè)有兩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席:哥倫比亞大學(xué)藝術(shù)史夏皮羅講席教授,以及現(xiàn)代藝術(shù)與理論夏皮羅講席教授。他一生獲獎無數(shù),包括美國國家書評獎和米切爾藝術(shù)史獎,均頒給他的名著《現(xiàn)代藝術(shù):19與20世紀(jì)》(Meyer Schapiro,Modern Art: 19th& 20th Centurie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8)。⑩邁耶·夏皮羅《現(xiàn)代藝術(shù):19與20世紀(jì)》,沈語冰、何海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5年。
在我國,夏皮羅的名字因為他一篇批評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文章而知名。但是,在中文語境里,他的名字和形象似乎也因為這篇文章而被固定。他對德國哲學(xué)家海德格爾的這一批評,后來又遭到法國哲學(xué)家德里達(dá)(Jacques Derrida)的批評。也因此,夏皮羅似乎成了夾在兩座哲學(xué)高峰之間的“落后”和“保守”史學(xué)家的典型。夏皮羅批評海德格爾的文章,收入《藝術(shù)的理論與哲學(xué)》(Meyer Schapiro,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1994)。后者是代表夏皮羅一生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的四卷本自選集的最后一卷。這部書還收入了藝術(shù)史上至為重要的論文《風(fēng)格》(“Style”,中譯本第一次全文譯出)。國內(nèi)讀者通常只知道夏皮羅批評海德格爾的那篇論文《作為個人物品的靜物畫:關(guān)于海德格爾與凡·高的札記》(“The Still Life as a Personal Object: A Note on Heidegger and van Gogh”),卻不知道夏皮羅在九十歲高齡時撰寫的《再論海德格爾與凡·高》(“Further Notes on Heidegger and van Gogh”)。①邁耶·夏皮羅《藝術(shù)的理論與哲學(xué)》,沈語冰、王玉冬譯,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6年。在我看來,這是將這一事件定于一尊的力作。

邁耶·夏皮羅

克萊門特·格林伯格

列奧·施坦伯格
在《現(xiàn)代生活的畫像:馬奈及其追隨者藝術(shù)中的巴黎》(T. J. Clark,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的譯后記中,我曾指出,T.J. 克拉克原本不在我的翻譯和研究范圍內(nèi),但他卻陰差陽錯地長久佇留在我的視野里。克拉克的名頭很響,在國內(nèi)也多有人提到他,但是,無論是對其代表作,還是對其藝術(shù)社會史方法,人們似乎都缺乏足夠的關(guān)注。盡管我承認(rèn)閱讀和翻譯他的著作都是痛苦的經(jīng)歷(克拉克語言晦澀,又好微言大義),但是他的重要性無可置疑。②T.J. 克拉克《現(xiàn)代生活的畫像:馬奈及其追隨者藝術(shù)中的巴黎》,沈語冰、諸葛沂譯,徐建校,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4年。關(guān)于克拉克的文風(fēng),請參閱筆者為該書所寫的譯后記。其學(xué)說和方法,當(dāng)然還有他的研究主題——現(xiàn)代主義,特別是法國現(xiàn)代繪畫——都是我心儀已久的對象。他和他的著作還因為接地氣的原因而備顯尊榮:作為一個自稱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以及公認(rèn)的“新藝術(shù)史”的代表人物,他的學(xué)術(shù)路徑和著述經(jīng)歷,足以架構(gòu)起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我國藝術(shù)類教科書之間的橋梁。③克拉克作為“新藝術(shù)史”的代表人物,參見喬納森·哈里斯《新藝術(shù)史——批評導(dǎo)論》,徐建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Jonathan Harris,Writing Back to Modern Art: After Greenberg, Fried and Clark,Routeledge, 2005.如果我們想要擺脫庸俗唯物論和機(jī)械反映論的羈伴,同時又認(rèn)可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的解釋力,那么T.J. 克拉克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
以上各種,或因作者地位顯赫而醒目,或以內(nèi)容重要而突出。但就我個人偏好而言(在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的基礎(chǔ)上,作/譯者當(dāng)然會有一點個人偏好),最令我傾倒的還是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及其代表作《知覺的懸置:注意力、景觀與現(xiàn)代文化》(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MIT Press, 2001)。克拉里現(xiàn)在是哥倫比亞大學(xué)現(xiàn)代藝術(shù)與理論夏皮羅講席教授。他只寫過兩三本書,卻已被譯成十多種語言。臺灣已有他《觀察者的技術(shù)》(Jonathan Crary,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T Press, 1990)中譯本。④強(qiáng)納森·柯拉瑞《觀察者的技術(shù):論十九世紀(jì)的視覺與現(xiàn)代性》,蔡佩君譯,臺北:臺北行人出版社,2007年。我很榮幸與友人合作,將他的《知覺的懸置》奉獻(xiàn)給國內(nèi)讀者。個人認(rèn)為,此書是學(xué)界運(yùn)用法國理論,對十九世紀(jì)末的巴黎現(xiàn)代性和視覺機(jī)制所做的最為出色的研究。⑤參見喬納森·克拉里《知覺的懸置:注意力、景觀與現(xiàn)代文化》,沈語冰、賀玉高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7年即將出版。
順著這幾個人物推下探,就能發(fā)現(xiàn)幾個鮮明的學(xué)術(shù)淵流和脈絡(luò)。格林伯格有兩個最重要的學(xué)生:羅莎琳·克勞斯與邁克爾·弗雷德。在羅莎琳·克勞斯、邁克爾·弗雷德、T.J. 克拉克等主要人物之外,我還發(fā)現(xiàn)了其他歐洲學(xué)者。例如比利時學(xué)者德·迪弗,法國學(xué)者伊夫-阿蘭·博瓦,德國學(xué)者本雅明·布赫洛。再接著往下探,我就摸到了中生代學(xué)者,他們基本上是羅莎琳·克勞斯、T.J. 克拉克和邁克爾·弗雷德的學(xué)生輩,比如羅莎琳·克勞斯的學(xué)生哈爾·福斯特,T.J. 克拉克的學(xué)生托馬斯·克洛(Thomas Crow)、邁克爾·萊杰等等。①參見羅莎琳·克勞斯《前衛(wèi)的原創(chuàng)性及其他現(xiàn)代主義神話》,周文姬、路玨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5年;邁克爾·弗雷德《藝術(shù)與物性》;伊夫-阿蘭·博瓦《作為模式的繪畫》,諸葛沂譯,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7年即將出版;本雅明·布赫洛《新前衛(wèi)與文化工業(yè)》,何衛(wèi)華等譯,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5年;哈爾·福斯特《實在的回歸:世紀(jì)末的前衛(wèi)藝術(shù)》,楊娟娟譯,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5年;托馬斯·克洛《大人文化中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吳毅強(qiáng)、陶錚譯,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6年;邁克爾·萊杰《重構(gòu)抽象抽象表現(xiàn)主義》,毛秋月譯,江蘇鳳凰美術(shù)出版社,2015年。
本人的翻譯和研究工作,始于羅杰·弗萊,主要集中在格林伯格-施坦伯格-夏皮羅那一代,稍晚一代的代表人物即T.J. 克拉克,以及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喬納森·克拉里。從時間上看,這份名單大致已經(jīng)勾勒出二十世紀(jì)英美現(xiàn)代藝術(shù)史論的基本輪廓,從方法論上看,它們也已經(jīng)涵蓋了從形式和風(fēng)格分析,到圖像學(xué),再到藝術(shù)社會史和精神分析,直至視覺文化研究的前沿——視覺考古學(xué)。
如果說我近十年學(xué)術(shù)研究有什么目標(biāo)的話,那就是在西方二十世紀(jì)以來浩瀚的藝術(shù)史論文獻(xiàn)中,選取最有代表性的、具有方法論示范價值的核心文獻(xiàn),在前期研究的基礎(chǔ)上,輔以外籍專家和良師益友的幫助,將這些基本文獻(xiàn)翻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逐步厘清這些代表性作家的思想背景、方法論特點、主要觀點和結(jié)論、重大理據(jù)和理念創(chuàng)新,然后將西方當(dāng)代藝術(shù)理論的基本面貌逐漸深化和清晰化。在此基礎(chǔ)上,我還在就其他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理論名著的版權(quán)事宜,與外方出版社或作者本人聯(lián)系,希冀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內(nèi),通過進(jìn)一步翻譯和深入研究,把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史論的大致脈絡(luò)呈現(xiàn)出來。
二、翻譯與研究
翻譯遠(yuǎn)不止是單純的語言轉(zhuǎn)換,而是兩種不同語言背后的思想文化的整體板塊的對接。沒有比翻譯更好的理解兩種語言的同一性和差異,同時使一種外來文化融入本土血脈的方法了。翻譯是真正洞悉語言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差異的最佳途徑。翻譯還是最好的細(xì)讀。人們經(jīng)常遇到這樣的情形:每當(dāng)有人自認(rèn)為已經(jīng)很好地理解了原文的時候,你叫他翻譯出來,他就會頗感躊躇,頓時發(fā)現(xiàn)原來還沒有吃透原文的意思!因此,通過翻譯,人們能夠培養(yǎng)起對外文和母語的高度敏感性。
翻譯其實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闡釋。從“翻譯即背叛”、“翻譯即闡釋”等諺語中,人們不難理會翻譯涉及一個復(fù)雜的過程。翻譯不是兩種語言之間的機(jī)械的和物理的轉(zhuǎn)換,而是母語與外語之間發(fā)生的復(fù)雜的化學(xué)反應(yīng)。沒有一個文本會產(chǎn)生兩個完全相同的譯本,就是這種化學(xué)反應(yīng)的復(fù)雜性的最好證明。每本書都有自己的命運(yùn)。被翻譯的書就更是如此。一本書遇到一位好譯者,那是它的幸運(yùn);遇到一個壞譯者,則是它的不幸。我常常想,如果貢布里希遇到的不是范景中先生和他的團(tuán)隊,那他在中文世界里的命運(yùn)一定大為不同。我還認(rèn)為,壞的譯者常常毀掉原作,與其不負(fù)責(zé)任地胡譯亂譯,還不如不譯。所以翻譯者責(zé)任重大。
對藝術(shù)理論著作的翻譯來說,藝術(shù)史論方面的訓(xùn)練尤為重要。簡而言之,翻譯需要大大超出外語水平之外的能力。僅僅精通外語,不足以高質(zhì)量地翻譯藝術(shù)理論文獻(xiàn)。這方面的專業(yè)知識,同樣需要一個長時間的學(xué)習(xí)過程。將Iconography譯為“圖像學(xué)”(應(yīng)為“圖像志”),而將Iconology譯為“圣像學(xué)”(應(yīng)為“圖像學(xué)”)都是不了解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基本思想和圖像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所致。當(dāng)然,由于翻譯涉及對一個學(xué)科深入了解的過程,涉及對不斷深化的背景知識的消化和吸收,在翻譯中出現(xiàn)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我也呼吁人們理解翻譯工作的特點,形成一個寬容但不縱容的學(xué)術(shù)氛圍。避免偏執(zhí)一點,不及其馀的棒殺,或者熱嘲冷諷,以顯示自己比他人高明;提倡經(jīng)過合理的批評,逐步提高翻譯的水平。
自從有了建造通天塔的想法,上帝就以變亂語言來阻止人類的這一野心,因此,翻譯注定是一樁西西弗斯式的事業(yè)。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翻譯工作十分重要。中國從漢末開始翻譯佛經(jīng),經(jīng)過魏晉南北朝,直到唐代,某種意義上才真正吃透了佛教的精華,創(chuàng)為禪宗。近代以來,國人開始大量翻譯西方文藝和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其數(shù)量規(guī)模或許已經(jīng)超過了譯經(jīng),但其深度和高度似乎還難以與長達(dá)千年的譯經(jīng)事業(yè)相比擬。
然而,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說,近代的西學(xué)(翻譯和研究)意義非同小可。其一,它深刻地影響了漢語,從而影響了國人的思想。正如對佛經(jīng)的翻譯豐富了古代漢語一樣,近代的漢譯西學(xué)名著也極大地豐富了現(xiàn)代漢語的表達(dá)方式,甚至影響到我們的思維方式。其二,任何翻譯都是詮釋,佳譯通常是對原作的最好詮釋。就像一位偉大的鋼琴家能夠激活一份樂譜,以自己的詮釋來表現(xiàn)音樂家的樂思一樣,了不起的翻譯家同樣能夠激活原作,使它在異域中生根發(fā)芽,煥發(fā)出燦爛的生命之花。
更為重要的是,翻譯還是“原初詮釋”。公開出版的譯著,往往擔(dān)當(dāng)了最初解釋原典的責(zé)任。不管是對是錯,是佳譯抑或拙譯,它都提供了一個可供進(jìn)一步討論、批判的藍(lán)圖。深入的學(xué)術(shù)細(xì)究功夫,便是建立在這張藍(lán)圖之上的。不然的話,如果不能給出完整的譯本,那么,即便是最優(yōu)秀的翻譯之才,往往也不能探究原典的全貌和精髓,為母語文化奉獻(xiàn)試錯和校勘的文本。錢鍾書先生那些片光吉羽的翻譯片斷,盡管以其博雅機(jī)智令讀書者津津樂道,卻仍然因其浮光掠影而未能在學(xué)界形成有效的琢磨和切磋機(jī)制,讓人徒喚奈何。
我倡導(dǎo)“研究性翻譯”。這是基于我前面講過的對翻譯工作的性質(zhì)和特點的認(rèn)知。翻譯需要建立在長期深入的研究之上,倒過來,研究也需要建立在系統(tǒng)而深入的原典的閱讀之上。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翻譯的質(zhì)量和研究的水平,從而使翻譯和研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并使核心文獻(xiàn)的翻譯、作家介紹與述評、理論的厘清與闡釋、史學(xué)建構(gòu)與美學(xué)提升,聯(lián)袂出現(xiàn),綜合一體。
翻譯必須建立在長期研究的基礎(chǔ)之上,這本來是任何翻譯的題中之義,根本不需要強(qiáng)調(diào)。但是,由于我國美術(shù)史翻譯(其他翻譯亦然)災(zāi)難性地出現(xiàn)不經(jīng)過長期研究就擅自翻譯的情況,才迫不得已提出“研究性翻譯”這樣一個本屬多馀的概念。就我個人而言,與友人合作翻譯一本書平均需要半年左右的時間,但是為了研究這位作者的思想,我就不得不閱讀該作者的其他著作,查閱同時代學(xué)者對他的評論,后世學(xué)者對他的研究等等大量資料。這導(dǎo)致我寫作相應(yīng)的研究性論文或譯后記,通常需要花費(fèi)數(shù)倍于翻譯的時間。因此,這些研究絕不是翻譯的附添,而是翻譯的要件。經(jīng)過這些研究后,再倒過去校對原譯,常常出現(xiàn)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大概就是“解釋學(xué)的循環(huán)”(Hermeneutical Circle)吧。
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就是過去的十多年里,我在翻譯的同時從事研究,在研究的同時進(jìn)行翻譯的部分成果。如果說翻譯是“原初詮釋”,那么,眼前的這些研究性文字,則是“詮釋的詮釋”。它們大體上圍繞著所譯對象(作者、文本、接受史)展開。作為一個譯者,同時也作為一名研究者,我覺得有責(zé)任為這些文本提供一個更為寬廣的上下文,以便國內(nèi)讀者更好地理解它們。在翻譯中,我常常感到臨深履薄、戰(zhàn)戰(zhàn)兢兢,盡量貼著原文行進(jìn),不敢稍加穿鑿。我希望讀者在閱讀類似的段落時,能夠設(shè)身處地、移情想象地領(lǐng)會列奧·施坦伯格遠(yuǎn)超古典作家“藝格賦詞”(Ekphrasis)的圖像讀解水平,同時,也能稍稍體會譯文在化解外語之玄奧,融貫體氣之微芒,圓通語感之超妙時所際遇的體悟之功和興會之情:
畢加索一幅藍(lán)色時期的水彩畫,畫下了二十三歲的藝術(shù)家本人。他沒有畫藝術(shù)家們在通常的自畫像中所畫的東西。他沒有探索自己的鏡像,也沒有帶著鄙夷的神情望著觀眾,更沒有眼睜睜地盯著模特兒。他似乎既不在工作,也不在休息,而是深深地介入了一種無為之中:看一個熟睡的姑娘。
姑娘躺在彌漫的光里,一條抬起的手臂枕著她的腦袋。她近在咫尺,卻幾乎要悄悄溜走,她背后那糊了墻紙的角落也融化在午睡的暖流里。正是畫家的形象傳達(dá)了對這一情景令人憂郁的關(guān)注。微暗的藍(lán)色墨水弄平了他的杯子與頭發(fā)。他那冰冷的陰影與她的明亮適成對比;他坐著的樣子則與她平趟著的姿勢形成呼應(yīng);他那硬朗的身軀又與她敏感的肌膚構(gòu)成強(qiáng)烈的對照。他們之間的對比是全方位的。正如她的光輝暗示了身體的極大歡悅,他不知所措的意識則成了一種被放逐的狀態(tài)。①列奧·施坦伯格《畢加索的窺寐者》,載《另類準(zhǔn)則:直面20世紀(jì)藝術(shù)》,第115頁。
然而,我并不想暗示,在眼下的這些研究性文字里,我就變得膽大妄為,“強(qiáng)制解釋”或“過度解釋”了。毋須強(qiáng)調(diào)的是,這些解釋仍然是緊緊圍繞著文本展開的,盡管在文本之外,我也廣泛搜求,剔抉爬梳,力圖將作者所隸屬的學(xué)術(shù)淵流,路徑傳承,方法新變,及其內(nèi)在理路,后世影響等等,盡量簡潔明快地發(fā)明出來,以呈于讀者目前。在這一點上,我對羅杰·弗萊《塞尚及其畫風(fēng)的發(fā)展》所作的注釋和研究堪為代表:
還有一點需要向讀者交代的是,弗萊的原著寫得極其濃縮,如果不稍作稀釋,則恐怕“濃得化不開”,因為它將有關(guān)塞尚生平、時代背景、趣味時尚、美學(xué)思想種種,基本芟荑凈盡,只剩下高密度的形式分析。因此,我相當(dāng)冒昧地為弗萊的著作做了一些注釋。但這一工作幾乎脫離了我的控制,盡管,最后為了壓縮篇幅,我已經(jīng)全部刪除了一般工具書能查到的人名和術(shù)語的解釋,但其規(guī)模仍然達(dá)到了原作的雙倍之巨。注釋大致分為兩類。一類關(guān)于弗萊的美學(xué)思想與批評理論,這是他在分析和評論塞尚作品時動用的“支援意識”,完全保留在文本的背景里,現(xiàn)在我的意圖是盡可能將它們發(fā)于讀者眼前。為此目的,我還特地撰寫了《羅杰·弗萊的批評理論》一文,作為對本書作者的一種述評,以便為讀者提供一個弗萊美學(xué)和批評觀的概覽。第二類(所占的比例約為全部注釋的四分之三)是關(guān)于塞尚繪畫的,重點是補(bǔ)充弗萊之后塞尚研究的最新進(jìn)展,尤其是在涉及塞尚重大觀念及其主要代表作的分析方面,我廣泛參照了歐美塞尚研究的文獻(xiàn),以資比較參證,與正文形成相互發(fā)明之勢。本書另一個附錄《弗萊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窺》,其宗旨亦基本如此。①《塞尚及其畫風(fēng)的發(fā)展》,第19頁。

《塞尚及其畫風(fēng)的發(fā)展》

《藝術(shù)與文化》

《另類準(zhǔn)則:直面20世紀(jì)藝術(shù)》
當(dāng)然,我也從不忌諱承認(rèn),在對作者思想傳承、方法厘定的過程中,偶有一得之見,也會徑直寫入。我以為,在深描弗萊對塞尚工作方式的闡釋中,我是充分發(fā)揮了“移情想象”的力量的:
說到弗萊的文本,我就感到必須向讀者表示歉意。盡管想要翻譯這部杰作的念頭已在心中盤桓將近十個年頭,從去年夏天試筆到現(xiàn)在也快一年,主觀意愿上我確實想盡我所能,較完美地譯出弗萊的這一不朽篇章。但我終于意識到,用中文迻譯弗萊的書,與塞尚以繪畫語言譯解自然,弗萊以言語語言譯解塞尚的繪畫,性質(zhì)上或恐接近(雖然其意義不可同日而語)。然則我如何可能去追配弗萊,一如弗萊之追配塞尚?我深感學(xué)養(yǎng)所限,而力有不逮,當(dāng)此講究效率,不容磨劍的時代,似亦無可奈何之事。惟態(tài)度尚算認(rèn)真,一校再校,盡量想使它少些遺憾,差可告慰師友。②同上,第18頁。
我還認(rèn)為,對英美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史學(xué)的宏觀視野和統(tǒng)盤考量,賦予我一種有利視點,能夠?qū)⒛切┰谝话懔阈欠g和研究工作中不可能發(fā)現(xiàn)的關(guān)聯(lián)和全局呈現(xiàn)出來。舉例來說,假如沒有研究過格林伯格,那么,對施坦伯格在紐約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MoMA)所做的三次針對格林伯格的批評性演講的認(rèn)識,就會大打折扣。不僅施坦伯格的主旨會淪為無的放矢,而且格林伯格為其經(jīng)典論文《現(xiàn)代主義繪畫》(“Modernist Painting”)所做的長長的附注及其自我辯護(hù)的功效,也將付諸東流。同樣地,假如不懂邁克爾·弗雷德與格林伯格的師承關(guān)系及其叛逆行動,讀者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他與格林伯格的分歧,以及各自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差異(格林伯格的實證主義VS弗雷德的現(xiàn)象學(xué))。再比如,假設(shè)對弗雷德與克拉克之爭,夏皮羅與海德格爾之爭缺乏藝術(shù)史和思想史的觀照,那么,讀者也就無法深刻理解,他們之間的論戰(zhàn)遠(yuǎn)不止是方法論上的差異所致,而是世界觀意義上的分殊促成。
如果說細(xì)讀和深描更多地體現(xiàn)在對原作的反復(fù)閱讀,揣摩和迻譯之中,那么對這些文本背后的作者所處的歷史背景,思想脈絡(luò),以及概念、術(shù)語和范疇轉(zhuǎn)移的考證,需要的則是學(xué)養(yǎng)和識見。對于這些文本,畢竟我仍有一得之見。在刻畫羅杰·弗萊的文字繹解之于塞尚的繪畫,猶如塞尚的視覺繹解之于自然的時候,在對格林伯格的雙重遺產(chǎn)——不獨(dú)擁有理論寫作的學(xué)術(shù)向度,更有藝術(shù)批評的實踐向度——的總結(jié)方面,在深度描繪施坦伯格圖像學(xué)的新變的時候,在揭橥夏皮羅對藝術(shù)史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捍衛(wèi),與海德格爾論戰(zhàn)的本質(zhì),作為批評家的藝術(shù)史家,以及他對現(xiàn)代藝術(shù)價值的贊美及其以今觀古的視野——從現(xiàn)代和當(dāng)代藝術(shù)中發(fā)現(xiàn)古代藝術(shù)未見之風(fēng)格特征——等等之時,在洞察T.J. 克拉克的問題意識——他既想要避免前輩藝術(shù)社會史學(xué)者粗陋的“階級決定論”,又想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決心——的時候,最后,在將喬納森·克拉里的方法概括并命名為“視覺考古學(xué)”等等方面,我相信,我的一得之見都是清晰無誤的。至于這些愚見能否稱得上“原創(chuàng)性”,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現(xiàn)在人們在苛求“原創(chuàng)性”。在一個思想貧乏的年代,對原創(chuàng)性的要求反而會更加迫切。而這正是思想貧乏年代的一個錯不了的癥候。處于文化繁盛時期的人們是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的,他們自然而然就做出了高度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xiàn)。可惜的是,吾生也晚,沒有趕上那樣的好年代。我認(rèn)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老老實實地做點翻譯和文獻(xiàn)積累工作,為后人真正富有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做些鋪墊,乃是我這一代學(xué)者的基本使命。當(dāng)然,我希望我的工作能超越單純翻譯和文獻(xiàn)積累的基礎(chǔ)層次,達(dá)到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史學(xué)史的建構(gòu)乃至傳統(tǒng)美學(xué)(古典與現(xiàn)代美學(xué))的重審的境界。《繪畫與意義:英美現(xiàn)代藝術(shù)史論集》就是這樣一種思想指導(dǎo)下的產(chǎn)物;是耶非耶,則留待讀者評議。
三、學(xué)術(shù)乃性情
我所希望的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史學(xué)史的建構(gòu),以及傳統(tǒng)美學(xué)(古典與現(xiàn)代美學(xué))的重審,是建立在對現(xiàn)代性問題的長期癡迷和關(guān)切之上的。現(xiàn)代性可以意味著康德意義上的學(xué)科劃分,每一個學(xué)科(科學(xué)、道德和藝術(shù))都奠定在各自的合法性之上;①參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2002年;哈貝馬斯《現(xiàn)代性的哲學(xué)話語》,曹衛(wèi)東譯,南京:譯林出版,2005年。現(xiàn)代性可以理解為韋伯(Max Weber)意義上的社會分工或社會領(lǐng)域的分化,理解為這一分工或分化過程中的科層制和理性化;②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xué)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2013年。現(xiàn)代性可以理解為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所說的對當(dāng)下的領(lǐng)悟,一種將合法性透支性地奠定在未來之中的世界觀。③參見沈語冰《透支的想象:現(xiàn)代性哲學(xué)引論》,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2003年,以及沈語冰《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導(dǎo)論”,第3-51頁。當(dāng)然,現(xiàn)代性還可以理解為笛卡爾(Rene Descartes)意義上的“我思”,理解為個體主體性的確立。④笛卡爾《第一哲學(xué)沉思錄》,龐景仁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談?wù)劮椒ā罚跆珣c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0年。多爾邁《主體性的黃昏》,萬俊人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或者,直接理解為宗教改革和近代自主個體的誕生。⑤雅克·勒戈夫《中世紀(jì)的知識分子》,張弘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2年;托馬斯·馬丁·林賽《宗教改革史》,孔祥民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6年。
無論人們?nèi)绾卫斫猬F(xiàn)代性,它的基本輪廓都是可以確定的:這既可以見諸十七世紀(jì)有關(guān)古代與現(xiàn)代孰優(yōu)孰劣的論戰(zhàn)中,⑥汪堂家、孫向晨、丁耘《十七世紀(jì)形而上學(xu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也可以從十八世紀(jì)以來的大量哲學(xué)話語中見出。⑦卡西爾《啟蒙哲學(xué)》,顧偉銘等譯,濟(jì)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賽亞·伯林《啟蒙的時代》,孫尚揚(yáng)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根據(jù)康德-韋伯-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哲學(xué)和社會學(xué)論述,我曾將對現(xiàn)代性的理解概括為:現(xiàn)代性不僅僅是一個首先發(fā)生于西歐,隨后擴(kuò)展到世界各地的現(xiàn)代化過程的實然問題,它更是有關(guān)“一個健全的現(xiàn)代社會應(yīng)當(dāng)怎樣”的應(yīng)然問題,因此它題中就包含著一定的規(guī)范內(nèi)容。⑧參見沈語冰《透支的想象:現(xiàn)代性哲學(xué)引論》。我還曾將現(xiàn)代性的規(guī)范內(nèi)容概括為“五自”原則:即哲學(xué)層面上的自我;科學(xué)層面上的自然(一種現(xiàn)代的科學(xué)自然觀);政治層面上的自由;道德層面上的自律,以及藝術(shù)層面上的自主。⑨沈語冰《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導(dǎo)論”,第3-51頁。
從這樣的現(xiàn)代性觀念出發(fā),我們就能夠發(fā)現(xiàn),當(dāng)代中國其實是一個高度混雜的社會。它在某些方面是前現(xiàn)代的、某些方面是現(xiàn)代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則是后現(xiàn)代的。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它同時混雜著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拿藝術(shù)領(lǐng)域來說,你毋需仔細(xì)研究就可以觀察到,我國的美術(shù)學(xué)院仍然在教授前現(xiàn)代的東西(你可以發(fā)現(xiàn)人們以畫得像宋畫而自豪,而書法也以寫得像王羲之為最高標(biāo)準(zhǔn));你也可能看到,現(xiàn)代藝術(shù)的基本原則,集中表現(xiàn)在某些類型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特別是包豪斯式的設(shè)計中;當(dāng)然,你還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后現(xiàn)代的或反現(xiàn)代的“當(dāng)代藝術(shù)”早已堂而皇之地涌現(xiàn)在雙年展或別的展場里。
我的翻譯和研究工作都是圍繞著現(xiàn)代性這一核心問題來進(jìn)行的。為了做到書目選擇的經(jīng)典性,我摒棄了經(jīng)濟(jì)效益更佳的一般通史,而專注于精深獨(dú)到、更具學(xué)術(shù)價值的專題研究。為了從藝術(shù)現(xiàn)代性這一角度反觀整個現(xiàn)代性問題,我特別注重那些直接參與在歐美現(xiàn)代主義進(jìn)程中的批評文獻(xiàn),從羅杰·弗萊(他是“后印象派”一詞的締造者),到格林伯格(他極大地推動了美國抽象表現(xiàn)主義),再到邁克爾·弗雷德(他是晚期現(xiàn)代主義的見證者和極簡主義的最尖銳批評者)。因此,不深入到現(xiàn)代主義運(yùn)動內(nèi)部,人們就無法真正有深度地看到藝術(shù)現(xiàn)代主義的整個發(fā)生和發(fā)展過程。
另外,這也與我的一個野心有關(guān)。我認(rèn)為,真正的現(xiàn)代藝術(shù)體系在我國尚未建立起來。“現(xiàn)代藝術(shù)體系”的概念來自保羅·克里斯特勒(Paul Kristeller)的名篇《藝術(shù)的近代體系》(“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①克里斯特勒《藝術(shù)的近代體系》,載《美術(shù)史與觀念史》,范景中、曹意強(qiáng)主編,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437-522頁。在這篇論文里,克里斯特勒詳盡地論證了一個有關(guān)“藝術(shù)”的現(xiàn)代體系是如何形成的。在他看來,那些占統(tǒng)治地位的現(xiàn)代美學(xué)概念,例如趣味與感傷、天才、原創(chuàng)性、創(chuàng)造性想象等,在十八世紀(jì)以前,并不擁有確定的現(xiàn)代意義;只有到了十八世紀(jì),才誕生了一種文獻(xiàn),可以把各種不同的藝術(shù)進(jìn)行比較,并在共同的原則下加以討論。盡管術(shù)語“藝術(shù)”或“美術(shù)”經(jīng)常被等同于視覺藝術(shù),但它也常常在一種更寬泛的意義上得到理解。它們首先是指以下五種藝術(shù):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詩歌。這五種藝術(shù)構(gòu)成了現(xiàn)代藝術(shù)體系不可還原的核心。這樣,我們不妨將“現(xiàn)代藝術(shù)體系”理解為:1.藝術(shù)從宗教與政治權(quán)威中獨(dú)立出來,成為自主的領(lǐng)域;2.藝術(shù)獲得了現(xiàn)代的意義,即其審美意義,而不再是宗教教義、政治信條或道德寓意;3.“藝術(shù)”成為有著固定內(nèi)涵的能指詞,它指的就是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與詩歌。②沈語冰《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第5-6頁。
自從梁啟超通過日語將西語Beaux Arts或fine arts翻譯成“美術(shù)”以來,以及蔡元培提倡“以美術(shù)代宗教”以來,我國至少在術(shù)語上已經(jīng)引入了來自西洋的現(xiàn)代藝術(shù)概念。③梁啟超《梁啟超美學(xué)文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年;蔡元培《蔡元培美學(xué)文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年。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并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確立現(xiàn)代藝術(shù)體系。通觀二十世紀(jì)中國近代美術(shù),除了在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短暫間隙外,藝術(shù)不是被政治所利用,就是為市場所主宰,很少成為真正自主的領(lǐng)域。④沈語冰《藝術(shù)是謊言,但它述說真理》(2006年在浙江人文大講堂的講演),未刊稿。而這造成了國人對近代美術(shù)的混亂見解。例如倡導(dǎo)“美術(shù)革命”或“革命美術(shù)”的寫實派被理解為具有現(xiàn)代意義,而提倡“畫不為人,畫乃為己”的黃賓虹則成了傳統(tǒng)派。我認(rèn)為,就藝術(shù)自主的原則著眼,從傳統(tǒng)里打出來,從而走向與歐洲現(xiàn)代主義不約而同的會通之路的黃賓虹才是真正的現(xiàn)代派。⑤參見沈語冰 “The Convergence of the Modernist Pain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ézanne and Huang Binhung”(在第34屆世界藝術(shù)史大會上的發(fā)言稿),部分以《中西現(xiàn)代主義繪畫的會通之路:塞尚與黃賓虹》為題,發(fā)表于《藝術(shù)界》,2016年十月號。
在理論上建立“中國的現(xiàn)代藝術(shù)體系”是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的前提。很難想象一個對現(xiàn)代藝術(shù)發(fā)生和發(fā)展的脈絡(luò)和規(guī)律一無所知,對中國社會的混雜性缺乏了解的人,能做出有意義的當(dāng)代藝術(shù)。最主要的是,現(xiàn)代與當(dāng)代的關(guān)系,遠(yuǎn)不是一刀兩斷,涇渭分明的。這里我想舉美國當(dāng)代最了不起的藝術(shù)批評家和藝術(shù)史家邁克爾·弗雷德為例,來闡述現(xiàn)代與當(dāng)代的復(fù)雜糾纏。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中后期,他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一群被稱為極簡主義的藝術(shù)家,其作品從根本上已經(jīng)背叛了現(xiàn)代主義的遺產(chǎn)。他們以跨媒介性來反對現(xiàn)代主義的純粹性,以物性(objecthood)來代替現(xiàn)代主義的媒介性,以劇場性來替換現(xiàn)代主義的在場性。作為一個現(xiàn)代性價值的捍衛(wèi)者,弗雷德強(qiáng)烈認(rèn)同晚期現(xiàn)代主義美學(xué),旗幟鮮明地批判極簡主義。⑥參見邁克爾·弗雷德《藝術(shù)與物性》。當(dāng)然,從回顧的角度看,他似乎站錯了隊,因為從他的《藝術(shù)與物性》(“Art and Objecthood”)一文發(fā)表以來,當(dāng)代藝術(shù)多多少少是以他所批判的“劇場性”為主導(dǎo)的。如今,“劇場性”(Theatricality)、“跨媒介性”(Inter-medium)“、場域特定性”(Site-Specificity,或譯“在地性”)已然成為以裝置藝術(shù)為代表的當(dāng)代藝術(shù)的三個美學(xué)特征。①Juliane Rebentisch, Aesthetics of Installation Art, Sternberg Press, 2012。盡管現(xiàn)在還遠(yuǎn)不是說劇場性已經(jīng)戰(zhàn)勝一切的時候,盡管在歷史的短時段內(nèi),弗雷德的觀點確乎是錯誤的,但是,人們同樣不得不驚嘆,他恰好卷進(jìn)了現(xiàn)代藝術(shù)與當(dāng)代藝術(shù)復(fù)雜糾纏的漩渦之中。對當(dāng)代藝術(shù)最顯著特征的概括,卻是這位現(xiàn)代藝術(shù)價值的捍衛(wèi)者做出的,這就是歷史的復(fù)雜和吊詭之處。

沈語冰部分譯著
當(dāng)然,我并不否認(rèn)經(jīng)典的現(xiàn)代主義技術(shù)-美學(xué),也許可以說已經(jīng)終結(jié)了(它終結(jié)于極簡主義和概念主義的出現(xiàn)),但是,要在現(xiàn)代藝術(shù)與當(dāng)代藝術(shù)之間劃清界線,強(qiáng)分軒輊,仍然是不可能的事。試問杜尚屬于現(xiàn)代,還是當(dāng)代?就他從事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主要時期,以及隸屬于達(dá)達(dá)運(yùn)動這一點而言,他是標(biāo)準(zhǔn)的現(xiàn)代;可是,就他采用現(xiàn)成品和“觀念藝術(shù)”的手法而言,他又是典型的當(dāng)代。我主持翻譯德·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De Duve,Kant After Duchamp, M.A.: MIT Press, 1999)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也是為了平衡在國內(nèi)藝術(shù)界流行甚久的阿瑟·丹托的理論。②德·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阿瑟·丹托似乎成了國內(nèi)唯一流行的當(dāng)代藝術(shù)理論,這種狹隘性很可怕。阿瑟·丹托走的是黑格爾路線,認(rèn)為藝術(shù)的終極理據(jù)是理念,而美只不過是披在理念身上的一件漂亮外衣,因而藝術(shù)終究將成為純粹理念,從而被哲學(xué)所取代。因此,丹托會撰文指出沃霍爾(Andy Warhol)是哲學(xué)家,而不是藝術(shù)家。③對阿瑟·丹托的批評,參見《阿瑟·鄧托:哲學(xué)對藝術(shù)的剝奪》,載拙作《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第283-309頁;以及《藝術(shù)沒有終結(jié):對阿瑟·丹托藝術(shù)終結(jié)論的反駁》,載《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7期。與丹托構(gòu)成對立的是,德·迪弗走的是康德路線,認(rèn)為藝術(shù)的終極理據(jù)仍然是情感,因此促使人們在想象的博物館中放進(jìn)杜尚小便器的也還是情感,當(dāng)然是一種排斥感、異己感、厭惡感。但不管怎么說,導(dǎo)致人們接受杜尚小便器的并不是單純的理念。④參見德·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第五章,以及筆者為中譯本所寫的譯后記。對德·迪弗藝術(shù)哲學(xué)的一個較為詳盡的討論,參見沈語冰《藝術(shù)邊界及其突破:來自藝術(shù)史的個案》,載《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2016年第6期。全世界都意識到當(dāng)代藝術(shù)面臨著失去觀眾的困境。設(shè)想一下,如果藝術(shù)真的只是理念,那么,世界還需要藝術(shù)家嗎?有哲學(xué)家不就足夠了嗎?所以,德·迪弗的方案,對解決當(dāng)代藝術(shù)這一根本問題而言,是阿瑟·丹托一個極佳的替代。
盡管如此,在本書里,我并沒有置入對德·迪弗的研究。其原因有二:一則,德·迪弗是比利時人,與本書劃定的“英美”范圍不合;二則,關(guān)于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理論與批評,以及一般意義上對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哲學(xué)論述,我希望將來有機(jī)會單獨(dú)成書。
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初,我介入國內(nèi)的藝術(shù)批評,最初是書法批評,后來擴(kuò)展到整個藝術(shù)批評領(lǐng)域,稍后還卷進(jìn)了一場關(guān)于當(dāng)代藝術(shù)意義問題的論戰(zhàn)。①參見沈語冰《從語言的意義到話語的有效性:批評話語的一次轉(zhuǎn)換》,《江蘇畫刊》,1995年第7期;《語言唯我論與陌生化的歧途》,《江蘇畫刊》,1996年第4期;《通向意義之途:主題與問題》,《江蘇畫刊》,1997年第8期。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這場論戰(zhàn)所采用的術(shù)語、范疇和方法,幾乎全部來自哲學(xué)和文學(xué)批評,唯獨(dú)沒有藝術(shù)批評理論和方法。從那時起,我就意識到,藝術(shù)批評在我國幾乎還處于原始狀態(tài),要么還在繼續(xù)使用老掉牙的前蘇聯(lián)教科書的文藝反映論和庸俗社會學(xué),要么直接從西方哲學(xué)和文學(xué)批評中搬用方法論。這促使我花了數(shù)年時間寫出了《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
在我看來,國內(nèi)藝術(shù)批評最大的問題,除去將批評視作政治正確的站隊或江湖利益的瓜分外——這屬于體制問題,不屬于批評本身的問題——就是缺乏學(xué)科意識和方法論意識。在歐美,藝術(shù)批評雖然很難說構(gòu)成一個學(xué)科,但它確實處于作為學(xué)科的藝術(shù)史和美學(xué)之間,至少構(gòu)成藝術(shù)史學(xué)科和美學(xué)學(xué)科的一部分。可是,在我國,這種學(xué)科意識完全闕如。批評家往往既沒有受過良好的藝術(shù)史訓(xùn)練,也缺乏審美判斷力。
眼下,不僅作為一個學(xué)科或?qū)W科一部分的藝術(shù)批評不受待見,而且整個外國美術(shù)史的教學(xué)和研究狀況也不盡如人意。你稍微留意一下美術(shù)史的教師隊伍和學(xué)生構(gòu)成,當(dāng)不難發(fā)現(xiàn),大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從業(yè)人員是學(xué)習(xí)和研究外國美術(shù)史的,而在這四分之一的成員中,大多還是從事西方古代和中世紀(jì)藝術(shù),特別是文藝復(fù)興藝術(shù)研究的,真正做歐美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研究和學(xué)習(xí)的,則又不足四分之一。高蹈者或許會說,似這種道術(shù)為天下裂的言論是多么不合時宜。然而,道術(shù)未裂的理想也許值得珍視,但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那種以學(xué)貫中西自命的做法,本質(zhì)上是對現(xiàn)代性分化規(guī)律的漠視,好比以十項全能去對抗各個單項的競賽,往往只是掩蓋田忌賽馬式的偷換游戲規(guī)則的謀略罷了。
話雖如此,“道術(shù)未裂”的理想?yún)s很能吸引一部分青年人,在其思古的鄉(xiāng)愁情結(jié)外散發(fā)出一層返本復(fù)元的光暈。最近我遇到的一件事就很能說明問題。某君聰明穎悟,年紀(jì)輕輕卻早已從美國某名校藝術(shù)史系畢業(yè)。他跟我說雖然他最喜歡的是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攝影和電影,但他卻想從事古代西域地區(qū)文物和考古研究。我問其所以。他回答說:“古物研究很吃香,更何況政府正實施‘一帶一路’政策,西域古物研究大有可為,將來找工作也容易。”我感嘆說,現(xiàn)在連博士生找工作都不易,你的想法當(dāng)然可以理解。但學(xué)問乃性命攸關(guān)之事,清代章實齋云,“言學(xué)術(shù)功夫,必兼性情”,又云,“令學(xué)者自認(rèn)資之所近與力之所能勉者而施其力”②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校注》,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似你這樣不顧性情,唯以時尚為襲,稻粱為謀,終非上策。
此事使我疑惑,莘莘學(xué)子對“古代西域之學(xué)”之類的學(xué)問趨之若鶩,無乃緣于此乎?所以,道術(shù)未裂或返本復(fù)元之理想,固未易易之,但其“語用效果”卻讓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學(xué)者迷失本性,墮入反時髦的時髦之中。更有一種敗壞的風(fēng)氣,凡言史者,必欲滅論而后快。如果說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的美學(xué)熱,某種意義上確實是一種以美學(xué)代美術(shù)史的空疏之風(fēng),那么,晚近談美色變,必欲劃清界線,復(fù)在美學(xué)(或任何理論)之上再踏上一腳方解心頭之恨者,難道不是一種校枉過正的姿態(tài),徒存詐嚇之技的面目?
我主張,問學(xué)者當(dāng)以尊重現(xiàn)代性學(xué)科劃分規(guī)律為本,以道術(shù)未裂、中西會通為用,而不能倒過來,徒以通人面目嚇唬年輕人,于各門各科卻既無實學(xué),也無專攻。另外,學(xué)問必兼性情。我的學(xué)問做得怎樣,是深刻還是膚淺,是高明還是浮薄,文集在此,當(dāng)有時論,也立為后證。但無論人們?nèi)绾卧u價我,有一點似可肯定,那就是它們都是見性情的文字。而循著自己的興趣做學(xué)問,是我向來的原則。故杜子美詩“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可為我作寫照。我雖無桑麻田,也不住南山邊,然“自斷此生休問天”則是一定的了:終生學(xué)習(xí),亦復(fù)終生流浪和漫游。
終生學(xué)習(xí)的益處是,它本身就是快樂的。更何況理論學(xué)習(xí)同時還是一種靜觀功夫。從柏拉圖的時代起,關(guān)于實踐生活與理論生活孰優(yōu)孰劣的爭論就沒有中斷過。我絕不會無知到否定實踐的重要性,但是我也確實不想浪費(fèi)時間去跟那些認(rèn)為實踐高于理論的人辯論。就理論是解釋世界的系統(tǒng)假設(shè)而言,理論是真正求真的智性活動,也是一項高貴的事業(yè)。我很慶幸自己選擇了這一事業(yè)。如果這種選擇并非出于利害關(guān)系或權(quán)宜之計,而是出于一己性情的“為己之學(xué)”,那它本身就應(yīng)該更有價值。我認(rèn)為我已經(jīng)找到了令我無限喜愛的工作,對此,我無怨無悔。
論壇

約稿 寒碧 責(zé)編 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