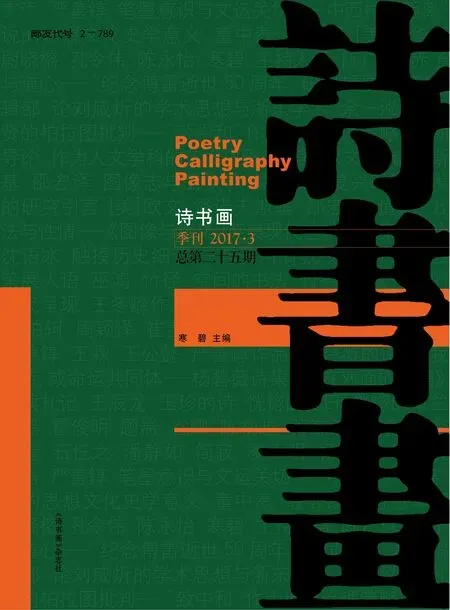觸摸歷史細節
——與黃河清教授商榷
王瑞蕓
觸摸歷史細節
——與黃河清教授商榷
王瑞蕓
一直以來,黃河清先生在藝術界宣稱一個觀點:“當代藝術”是陰謀是騙術。他在所著《“當代藝術”:世紀騙術》一書的序言中這樣概括說:“奇奇怪怪的‘當代藝術’不是藝術……當代藝術是騙術,是巫術,是傳銷(洗腦)”,“其最大的騙局或騙術,就是把杜尚的小便池奉為‘藝術品’。……為了讓這場人類文化史上空前的騙局得以持續,除了洗腦蠱惑之外,美國人一手拿著大棒,一手拿著胡蘿卜。所謂大棒,就是美國人動用政治和體制的力量,在全世界強力推行這種美國式騙術的同時,全力在輿論上打壓、抑制那些質疑‘當代藝術’的聲音。”①河清《“當代藝術”:世紀騙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序言1-4頁。版本下同。今年四月,河清先生在西安當代藝術研討會上,再次亮出這一觀點,遭到眾多在場學者的反感,但“引來會場上九○后學生的共鳴”。②黃河清“中國當代藝術的末日正在來臨——西安2017當代藝術研討會小記”,大河美術網站,2017年4月18日。這讓河清先生感到自己真理在握。
河清先生的觀點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因這些年也在研究美國藝術,也知道美國在世界上相當霸道,倘若河清先生的論點屬實,我是要為他叫好的。于是,就把他披露的那段“美國陰謀”仔細檢視了一遍,卻非常失望地發現,他的觀點史料不足,不能成立,因此也在報紙上發表了質疑河清先生立場的文字③王瑞蕓“‘當代藝術’可以被否定掉嗎?”,《中國美術報》,2017年5月29日。。事后就有很多人對我說,你又何必在意呢,圈里誰都知道的,他這些年來一直就是像這個樣子說話的。
自己也納悶,為什么要在意。學者之間,觀點不同,太正常了,自己又不是新手,沒見過這世面;更不是一個強人,只覺得自己才對,別人都不對。細想了想,我所在意的已經超出了觀點對錯的范疇,能理出頭緒的部分是:我們吃飽穿暖,好端端的為什么要去做學問?對全中國人民來說,不知道美國的藝術發生了什么,對于我們整個生活進程,對于國民經濟的GDP,決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那么我們究竟是為什么做呢?其根本原因,我想,應該是期待這類活動能夠對于我們的人心起到某種塑造作用吧。凡明晰公正的學術,會引導人細細地看,靜靜地想,會有興趣去了解他國他人他事——無論對象是美國,還是南太平洋小島上的原始住民,進而對世界每一處地方每一種人群每一件新鮮事物多一份理解和尊重。這也就是為什么,所有國家和民族都設有藝術、音樂、詩歌、學問等等的“上層建筑”,每個民族和國家都肯在“上層建筑”上花錢,顯然是期待自己國民能得到優質的精神熏陶,變成一個心靈寬廣而又細膩,誠懇而又優雅的人吧。
這話如果能被同意,有人大概就會說,河清先生也是為此來攻擊看著臟、亂、差的“當代藝術”的,而且他正是為提倡中正清明的中國民族藝術出手攻擊的,他所做的應該正符合著這個大方向。看著是的。但這個事情的蒙蔽性也在這里:一個美好的大方向并不意味著就給人發放了可以粗暴行事的通行證。對學者尤其是這樣。在一個民族中,如果連一個學者都不能做到尊重事實,公正客觀,而捏造歷史……那就太過分了。從常識就能知道,一個民族要想在世界上受人尊重,不在于是否拿出一種新的美術樣式,別人更加留心和在意的,是看這個民族如何思考,如何待人,如何處事,不是嗎?
因此我們要特別小心,小心表象和實質錯位——而表象和實質常常錯位。
就比如說杜尚拿出小便池時,乍一看,豈止粗野,根本就是下流——整個西方都被激怒。可是他們經過半個世紀,終于懂得透過表象看實質:這個人居然是借用一個最下等的東西,表達了一個最高貴的思想:我們要在藝術上,乃至方方面面都學會建立起一種“平常心”。西方人一旦明白這個立場的珍貴,對小便池的看法就有了180度的轉彎……雖然我忍不住奇怪:河清先生這么多年來始終只盯在那只小便池的表象上,對西方認識由表象到實質的轉變過程拒絕弄懂,堅持把小便池作為火力最集中的那個靶子,我還是得尊重他的立場——他完全可以一輩子都不必喜歡那只小便池的。只是,由此而來的一個現象讓我們不得不對于優雅和粗暴的內涵要重新揣摩。
拿出“粗暴作品”的杜尚,他身邊的每一個人都由衷地喜歡他,死后更加贏得了世界聲譽(這種事美國應該無法“強行”),他確立的藝術價值觀至今沒有過時。美國著名女畫家奧克弗回憶起這個“粗暴作品”的創作者時,這樣說道:“他是我平生見過的最優雅的男人。”可究竟是為了什么,一直以來在拼命抵制“粗暴作品”的河清先生,卻會在西安會議上遭到在場眾多中國學者的反感(除了九○后們——他們因為年輕,尚未對“粗暴作品”后面的內涵下足夠的功夫吧)……于是,我們便躲不過這樣一個問題了:“粗暴作品”的作者憑什么如此受人待見,反“粗暴作品”之人,為何如此不受人待見?是什么東西讓表象和實質的反差如此之大?
這就必須來考察一下河清先生的表象和實質了。
河清先生否定西方當代藝術的邏輯鏈是這樣建立的:當代藝術是個騙局,這個騙局主要是由美國操縱的(因為在歷史上他們曾經陰謀操縱過抽象表現主義的宣傳和推廣),他們這么做為了擴張自己,推行自己的文化,達到稱霸世界的目的。這就是說,河清先生是借助一種政治立場來建立他的“藝術敘事”,乃至“仇恨敘事”——借人們政治傾向之力,先去仇視一個國家,然后因那個國家去仇視一種文化。他等于是把國家之間的政治立場替換成學術立場。一旦把學術立場和政治立場綁在一起,整個事情就可以變成:誰在學術上反對這一點,誰就是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支持美國——這還了得!這種思路的政治色彩和暴力傾向,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太熟悉了:只需把當代藝術戴上美國這個“家庭出身”的帽子, “當代藝術”必定就是個“狗崽子”。
一個學者到了二十一世紀,還能把學術拉回到曾經大面積摧殘過中國人身心的成分論上去,這是要叫人觸目驚心的。具備這種品質的“學問”,恐怕是不能幫助一個國家和民族在建立上層建筑時所期待的:培養公民寬容、平和、公正、文雅的內心風景……它所能提供的,只會叫人增加更多的戾氣和敵意,這才是整個事情的可怕之處。做不做“當代藝術”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一個民族斷不能接受一個做學問的人行使精神暴力。尋常之人信口開河,簡單粗暴就罷了,一個學者習染如此,則意味著降級的精神品質甚至侵蝕到學術界了。學術研究,本屬于一個民族精神層面中純凈的部分,是受到理性和良知照耀的區域,如果連這個區域都被蠻橫,粗暴,不講理給污染了……我們這個民族還能靠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去建構人心的細膩、優美、高貴?這個民族的希望何在?
……
希望上面把自己在意的部分說清楚了,現在,讓我們回到學術,與河清先生一起商榷,看看他做“學術”中漏掉了什么和篡改了什么。如果我的研究和史料有錯,恭請河清先生批評指教,也恭請同行們斧正。
一、美國為什么要把一件“陽謀”做成“陰謀”
河清先生把整個西方當代藝術定義為“騙局”,主要依據來自英國學者桑德斯的《文化冷戰》一書,內容陳述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美國中央情報局從四十年代末接插手了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現代藝術)在世界范圍內的推行,促成了美國藝術取代歐洲藝術的領導地位,最終讓美國在藝術界做大。河清先生于是將此當成一記重拳:美國國家在陰謀操控藝術!盡管西方學者桑德斯呈現的歷史發生在美國“現代藝術”時期,“當代藝術”不包括在其中,因河清先生極度不喜歡“當代藝術”,可巧美國又是“當代藝術”重鎮,他就順手把“當代藝術”也一起裝進了桑德斯的“陰謀”敘事之中,于是結論說:“當代藝術”也正是美國陰謀操控的結果。
這樣的做法在學術上通不過。
在一個歷史時期中發生的事件,不能隨便就拿來涵蓋其他時期。如果要涵蓋,請出示證據。假如說,西方人根據中國六十年代文革時期的現象和統計數據,說中國的年輕人(紅衛兵)很善于打砸搶,然后就把這個說法一直擴大到我們的八○、九○年代,甚至把當今時期全都涵蓋進去,我們能接受嗎?當西方學者桑德斯說美國政府插手美國現代藝術傳播時,她采用的是科學性研究態度。她那本厚達500頁的《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by Frances Stonor Saunders,The New York Press,New York,1999)英文原版從428頁開始直至500頁,全部為引文注釋,讓我們看到,她參考了很多的書,挖掘了許多檔案信件,并且采訪了相關的人,才能向讀者確認:從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這二十來年中,美國中情局在推動抽象表現主義的傳播時在背后做了支持。然而桑德斯的揭露到此為止,她沒有寫美國政府在之后繼續“陰謀”支持當代藝術這回事,因為沒有證據。這就是西方的治學:一切從事實出發。而在中國學者河清先生那里,學問不是像桑德斯那樣去做的,他所做的,是對桑德斯證據詳實的事實動了兩個手腳:一是縮小,一是放大。

桑德斯《文化冷戰》
“縮小”是指,河清先生不僅沒有把桑德斯原著的完整內容呈現出來——美國為什么要把一件“陽謀”做成“陰謀”(桑德斯書中對這一點有清楚的敘述),而且他干脆讓那段美國歷史在讀者面前缺席:在那個時期,美國究竟發生了什么,民心和民意如何,藝術家們在想什么,又如何做……他只突出他唯一喜歡的那一部分:美國政府耍了陰謀。只強調這一點,等于是把層次繁多、經緯復雜的鮮活歷史壓縮進一個貼著“陰謀”標簽的真空袋子里,讀者于此嘗不到歷史的原汁原味,更無法從那種“學術”中看到事情的真相。然后,河清先生就進入了他的下一個步驟:“擴大”。在完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他僅憑“估計”、“很有可能”、“我認為”……就直接把“陰謀”擴大到“當代藝術”部分了。換句話說,原先在西方人桑德斯的“陰謀”袋子里,只裝著抽象表現主義(現代藝術),中國人黃河清順手把“當代藝術”也一起裝進去了。這種做法,學術上更加通不過,這相當于“捏造”。這不是學者該干的事。社會養活著學者,是需要他們把所有不清不楚的事物、所有被歪曲或者捏造的歷史盡量還原,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古代的史官們即使冒著被殺頭的危險,也要直筆記錄事實,否則就是缺乏職業道德。
下面,請讀者耐心跟我們一起來還原歷史原貌。
有一個問題是不能不先問的:美國為什么要把一件“陽謀”做成“陰謀”?誰都知道,在這個太陽底下,任何一個國家政府出面出錢支持本國藝術,推廣自己的文化影響力,天經地義,完全犯不著偷偷摸摸,避人耳目。比如現在中國政府肯拿出大把的錢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就是在推廣中國文化和中國影響力的一個“文化策略”。如果我們不用“文化戰爭”這個大詞的話,那么,憑什么我們中國政府出錢推行自己文化時,就落落大方,不藏著掖著,美國政府卻偏要把一個全球通行的“陽謀”,做成一個遭人恥笑的“陰謀”,他們政府全體成員難道全都笨成了脫褲子放屁的蠢貨?這不讓我們好奇嗎?
歷史實情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二戰結束后,美國面臨兩個當務之急:一是與蘇聯冷戰開始,需要自己的文化形象;一是要對歐洲在文化上稱大(美國長期在歐洲面前伏低做小,現在有了重新洗牌的機會),也需要自己的文化形象。于是,政府有意支持藝術,并選用前衛派作品代表美國新形象送出國門做巡回展。但那種抽象的“前衛派”一經選出,立刻碰到兩個阻力:1.政治家和民眾因不懂抽象,討厭這些“混涂亂抹”的畫來代表美國;更困難的是,政府一些高層官員還把看不懂的抽象藝術視為來自共產主義勢力的陰謀(當時正遇上美國反蘇反共情緒高漲的歷史時期)。2.畫下那批抽象表現主義繪畫的人過去基本親共,拿親共分子的作品去和共產主義的蘇聯對抗,這成什么話!?結果,在二戰后美國越來越嚴厲的反共氣氛中,美國國務院剛開始撥款送這些畫出國門展覽,給美國文化造勢,但后院馬上起火,在國內引起普遍的抵制——國會不同意,美國人民也不同意。美國國務院變得兩邊為難:一方面外交官在叫喚,我們的文化戰爭要輸給蘇聯了,他們每年花重金在海外宣傳自己,我們卻做得微乎其微;一方面國會堅決不批準國家撥款送現代派作品出國展覽,于是,政府高層只能把這個任務交給中央情報局①美國中央情報局是美國政府在1947年成立的情報機構,其中技術人員多具有較高學歷、或是某些領域的專家。該機構的組織、人員、經費和活動嚴格保密,它無需公開其預算,雇員人數或工作情況,即使國會也不能過問。去悄悄操作——把政府的錢轉到私人基金會的賬面上,包裝成私人基金會出資的展覽。這就是美國政府把一件“陽謀”做成“陰謀”的故事梗概。
詳細了解一下這個“陰謀故事”可以讓我們中國人接觸到不太熟悉的一種三權分治的政治體制,一個國家中民心民意對于一個政府可能的影響力。只要把美國的現實特點看清楚,我們對當年美國中情局行使推動藝術的“陰謀”,就無論如何也不會如河清先生那樣吃驚得“目瞪口呆”了。①河清先生在他的《“當代藝術”:世紀騙術》中說:“桑德斯的這本厚達570頁(英文原版是500頁。引者注)的書,收錄了大量第一手檔案資料和當事人采訪記錄,通篇都是超乎人們想象的真情實例。一件件見不得人的幕后策劃,一筆筆讓文化人斯文掃地的金錢交易,讓人目瞪口呆。”第35頁。
“故事”要從上世紀美國的三十年代開始講起。
二、美國二戰時期的政治選擇
在三十年代,美國發生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蕭條。全國至少有1500萬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窮得幾乎吃不上飯。《商業周刊》做過調查,有不少人不再喜歡美國了,有的已經離開美國,有的正設法離開。三十年代初期,遷居國外的人數年年超過遷入的人數。這情況讓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嚴重懷疑,都愿意相信共產主義會是社會改造的正面力量。在二戰前,美國知識分子們普遍左傾,美國共產黨員從一九二九年的一萬兩千,到了一九三九年發展到十萬人。知識界思想界的親共的傾向在美國不僅合理合法,而且還有相當勢力。這個寬容局面的存在還因為,美國除了面臨經濟蕭條之外,法西斯德國已經漸漸成長為全世界的威脅,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黨派有了共同的敵人,因此國家、黨派之間的對抗也被減弱。就連共產黨一直強調的階級對立,也被調整得溫和了。美國和歐洲的共產黨都愿意接納知識分子……整個局面就像一位美國作家兼學者Daniel Aaron說的:“現在你可以介入任何社會改革力量,可以是蘇聯的,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文學的——任何東西現在都與激進的,反抗的,摧毀的,革命的,反不切實際的立場有關——你做了,就是跟那些政治天使們站在一邊了;你可以是站在羅斯福政權一邊,站在勞動者一邊,站在黑人一邊,站在中產階級一邊,站在希特勒勝利的一邊,站在這個世界上所有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一邊。總之,在世界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一個熱切的革命者也罷,一個堅定的保守主義者也罷,美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都是支持的。”②Daniel Aaron,Writers on the Left-Episodes in American Literary Communis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1961,p.278.
在美國歷史上也是第一次,作家、演藝者、畫家不被社會邊緣化,不再被視為社會中的黑馬,而是和社會的命運聯結在一起,為共同的事業抗爭。美國共產黨尤其愿意插手文化藝術,讓它們為政治派上用場。一九三五年,美國共產黨和美國知識界著名的左傾雜志Partisan Review建立了“美國作家協會”,受邀名單上的作家幾乎都是共產黨員。同年六月,他們派人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保衛文化國際作家大會。這個大會是由蘇聯派的代表團和法國共產黨主辦的。美國作家第一次和其他國家的作家達成共識,組成了“保衛文化國際作家聯盟”。而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美國藝術家同樣在美國共產黨支持下建立“美國藝術家協會”,協會成員有360人,第一次大會同時用了兩個會場開了三天。在第二年的會議上,協會甚至得到了畢加索的聲援。畢加索不僅是現代藝術中的領軍人物,也是法國共產黨員,他對這個美國共產黨主持下的美國藝術家協會表示了熱情的支持。他送去的發言稿大意是:藝術家要關心社會,用藝術推動社會。

1930年大蕭條期紐約的失業大軍
但是這個局面好景不長。分裂的力量不是來自右翼,而是左翼自身內部。首先是一九三六年震驚世界的“莫斯科審判”③莫斯科審判是30年代蘇聯大清洗時期由斯大林主導的三次舉世矚目的對外公開大審判,分別為1936,37,38年,被審判者的罪名是陰謀顛覆,他們全是蘇聯政府中的老布爾什維克。三次審判,西方記者、外交使團或獨立知識分子都可以出席旁聽。結果在全世界人面前呈現出這樣一個場面:在法庭上,所有被告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辯護,個個都把自己描述成惡魔,并贊頌領袖斯大林。所有經審判的人全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全部被槍決。直至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揭示莫斯科公審根本就是“作秀公審”,審判對象是通過各種手段被威逼摧殘之后,尤其是利用審判對象的親人為威脅手段,導致他們強行服從認罪。以及蘇聯大肅反運動,蘇聯大批大批的官員和知識分子遭到屠殺和迫害。然后是一九三九年蘇聯和德國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①《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納粹德國在莫斯科簽訂的一份秘密協議。是斯大林為了保護蘇聯的安全及利益,決定放棄與英、法共同對抗納粹德國,反而去向德國示好,可以保護自己在東歐的利益,同時爭取時間及空間備戰。而希特勒為了執行1939年4月3日制定的閃擊波蘭的“白色方案”,避免過早地與蘇聯發生沖突,陷入兩線作戰的困難境地,所以也愿意與蘇聯簽訂非戰條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對波蘭實施閃電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隨后蘇聯紅軍也入侵波蘭第二共和國,同年9月17日,蘇聯紅軍和納粹德國國防軍在布列斯特會師,9月25日,蘇德兩軍舉行聯合閱兵式,標志著兩國對波蘭的瓜分占領。——蘇聯可恥地用犧牲波蘭來保全自己。這些鐵一樣的事實對西方知識階層親共傾向構成了沉重打擊。對西方的左翼而言,一直以來,不是共產黨,主要是蘇聯,代表著摧毀腐朽資本主義的力量(蘇聯也是這么樹立自己形象的)。可是這個被視為共產主義樣板的國家,暴露出這么露骨的利己主義和如此駭人的殘暴專政,導致西方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大夢初醒,開始在組織上或者在立場上站到了蘇共的反面。他們中間即使有些人繼續保持左翼立場,但都采取了鮮明的反斯大林態度。美國代表共產黨立場的Partisan Review雜志一時停辦,等一九三七年重新再辦,雜志的立場就轉變為反斯大林了。
伴隨著對蘇聯的失望,美國人對自己的國家重拾信心。就連美國共產黨當時的理念也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其領袖Earl Browder認定,“我們是真正的美國人”。②Serge Guilbaut,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 1983, p.18.版本下同。這種民心扭轉的關鍵還在于,羅斯福政府推行的復興美國經濟的“新政”在一九三六年已經開始全面見效。在羅斯福一九三三年三月就職總統之前,美國經濟GDP已經由危機爆發時(1929)的1044億美元降至742億美元,失業人數由150萬升到1700萬以上,美國整體經濟水平倒退至一九一三年,而且信用危機已經讓美國銀行系統瀕臨崩潰。一九三三年初,全美國銀行庫存黃金不到60億元,卻要應付410億元的存款,每家銀行門前人山人海,擠兌風潮遍及全國。就在羅斯福宣布就職的那一天,美國金融的心臟停止跳動,證券交易所正式關閉……羅斯福完全是臨危受命。他上臺后第一件事就是挽救金融界。他別出心裁地在CBS廣播公司開設“爐邊談話”節目,用輕松親民的方式,向全美國人民解釋政府的新政,恢復人們的信心。幾天后,美國人不光不再去銀行擠兌,還把取出的錢再放了回去,金融界開始正常運轉。照這樣,羅斯福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新政……從一九三五年開始,美國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穩步回升,國民生產總值從一九三三年的742億美元,到了一九三九年已經增至2049億美元,失業人數從1700萬下降至800萬。羅斯福新政取得了顯著成效,恢復了美國國民對國家制度的信心。美國知識分子心中不再計較支持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種問題了,而開始流行的是“民主,自由”的信念。共產主義的思想基礎顯然開始“流失”。
那么藝術在這個局面里該采取什么立場呢?對藝術家來說,究竟什么算是美國的藝術,在那個時期是不清楚的。當時的美國藝術很駁雜,有寫實有抽象,而且基本是從歐洲人那里學來的。我們如果翻閱一下美國三十年代的文化雜志Partisan Review或Marxist Quarterly,從上面的文章中明顯可以讀出那個時期美國文化人和藝術家的迷茫。Partisan Review雜志一九三六年四月發起一個討論,題為“什么是美國主義?”,論題的焦點成為:藝術家在這樣一個文化迷茫期該起什么樣的作用,抽象藝術到底是該對社會改造承擔起責任,還是該離開社會紛爭,走藝術的純潔之路。不同的批評家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漸漸清晰,就是要把藝術從黨派的控制中獨立出來,尤其是從共產黨的控制中獨立出來。一九三八年托洛斯基和法國超現實主義領袖普呂東的文章,一九三九年理論家格林伯格的文章,一九四四年抽象畫家馬瑟韋爾的文章,都在理論上試圖說明法西斯和共產黨都是藝術要躲開的東西,否則,它們會被作為工具,而藝術應該是獨立的。
這種思路在現實中變成這樣的事件:由共產黨掌控的“美國藝術家協會”解體。那是在一九三九年芬蘭淪陷之后,美國藝術家協會的共產黨成員領導們對此保持沉默,引起了很多會員的不滿。不滿分子在藝術史教授夏皮羅身邊形成了另一個團體,開始指責這個協會根本是在追隨斯大林路線并以此來控制大部分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們,包括后來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羅斯科、戈特利普等人寫了倡議書,要求協會公開討論,這個協會究竟是共產黨的文化工具,還是獨立藝術家的組織,最后不歡而散。夏皮羅那一群人就結伙退出,另外成立了一個組織“現代畫家雕塑家聯邦”,打出藝術非政治性,提倡自由性的旗號。他們開始反對任何政治化的藝術,比如一九四○年在舊金山金門公園的宣傳招貼畫展覽那樣的藝術。
然而,在戰爭臨近的非常時期,藝術提倡自由獨立,肯定也不被看好,就像一九四○年紐約的一份新雜志《紐約藝術家》(是一份由共產黨控制的雜志),在第三期的一篇文章中指責:“在戰火越燒越高之時……在紐約時報藝術版上寫文章的美學教授讓藝術家避開戰爭回到象牙之塔中去,根本就是個臆想……眼下的局面鐵定會讓這種希望和臆想落空,象牙之塔是過時之物,它不該再出現了。”①New York Artist 1,nos.3-4,May-June, 1940.

40年代初的報紙宣傳:“美國不靠左翼或者右翼,靠自身的能量和光”
托洛斯基對藝術的論述稍能解決這個問題。一九三八年Partisan Review雜志刊登了他的系列文章。他在痛斥斯大林的專制,以及這種專制下的藝術奴性之后,推崇藝術的個性化和獨立性,但是他提倡的藝術獨立,是獨立于黨派控制之外,而不獨立于社會之外。他認定,任何藝術中出現新傾向都是因反抗意識導致的,這反抗,不是只針對藝術的,主要是針對社會的:“藝術,是文化中最復雜的部分,最敏感卻同時又最少受保護的部分,它會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腐朽衰落而受難。解決這個問題通過藝術本身是不可能的。這涉及的是整個文化的危機,根子在經濟基礎,顯露在上層建筑。藝術既躲不過去,也不能分離出去。藝術自己救不了自己……因此我們這個時代藝術的作用,根本就是被它和革命的關系決定了的。”②Leon Trotsky, “Art and Politics”,Partisan Review,1938/9, p.9.
藝術當然脫離不開社會。只看當時美國藝術的兩種立場:鄉土主義(寫實),強調本土性,國家主義;前衛藝術(抽象),希望超越狹隘的國家主義,進入國際藝術舞臺。這和當時的美國政治面臨的選擇一模一樣:美國是選擇國家主義還是選擇國際主義?在戰爭形勢中,這個問題被簡化成:美國是參戰,還是不參戰。不參戰一方代表國家主義,也被稱為孤立主義,他們認為保存了自己,才有可能去拯救墮落的西方文明。參戰一方希望美國成為支持國際正義的力量,保衛世界和平。其實更主要的是,參戰派看到,戰爭是災難,但同時也是機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就已經失去了一次登臺的機會,現在是歷史給予美國的第二次機會,美國該借此機會登上國際舞臺。
為了推廣宣傳“美國機會”這個立場,一批支持者甚至自發結為團體。其中有一位歷史學家James T. Shotwell咨詢了美國的五十位國際事務的專家,得出結論說,參戰對美國正是一個機會。這個團體還出資讓美國CBS廣播公司開辦一個廣播節目,從一九四○年一月開始,以“什么方式來延續和平”為題,對全美國民眾宣傳這一立場(當時民眾大部分不愿意美國參戰),并出版書籍文章,造成了可觀影響。比如,專欄作家Henry Luce一九四一年二月在《生活》雜志上發表一篇名為“美國世紀”的文章,明白無誤地定義,如果說十九世紀是英國和法國的世紀,而這個世紀將是美國世紀。美國的角色將是世界的領導者。他指出,當今機會已經推到美國的面前,現在還留戀于國家主義這種狹隘思想就太幼稚了。眼下美國根本已經置身于戰爭了,從任何方面說,都應該對這個世界性危機負起責任來,才可以盡快贏得這場戰爭。而“最重要的一點是,最大的一個機會放在眼前了,抓住它就是完成了讓美國做領袖的機會。”①Henry R.Luce,“the American Century”,Life,1941/2/17,p. 61-65.這篇文章在全美國反響很大,很多知識分子紛紛呼應。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政府開始給國際主義開放綠燈。副總統Henry Wallace做了講話,呼吁建立一個國際保衛和平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在藝術界,理論家Harold Rosenberg寫文章反對孤立主義,巴黎所以成為巴黎,就因為她是藝術國家主義的對立面,有明智頭腦的知識分子都在反對藝術上的所謂國家主義。

1934年美國的反戰宣傳畫
然而,最終導致美國參戰的動力還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珍珠港事件——日軍突襲軍港,美軍艦毀人亡,震驚全國。這個恥辱立刻將一個本來意見不齊的國家團結動員起來,美國總統羅斯福第二天就在國會發表講話,國會批準對日宣戰。美國經過新政建立起來的雄厚工業實力完全投入二戰,整個國家機器進入了戰時的軌道。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美、蘇、英、中四國在華盛頓率先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次日,再由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荷蘭等二十六個國家共同簽署。各簽字國承諾,保證運用全部經濟、軍事手段對抗法西斯集團國。而且任何一國都不能與敵國單獨講和,直到徹底打敗法西斯國家。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在此聯盟期,實力雄厚的美國向西歐和蘇聯分別提供了大量援助,為的是他們能分別在西歐和東歐兩處戰線拖垮法西斯德國。(于是一度,美國和蘇聯又走近了。)
無論是社會走向,還是思想走向,當然也包括藝術走向,都讓美國人看清楚了,狹隘的國家主義沒有前途。到了一九四三年,美國的民意測驗反映出,孤立主義已經沒有什么市場了。羅斯福總統的特使Wendell L.Willkie一九四二年受命周游列國,其中包括蘇聯和中國,歸后寫了《一個世界》(One World),出版即刻暢銷。除了鼓吹國際主義立場,其中另有一個樂觀看法:技術的進步將會把世界變為一個地球村,被戰爭摧殘的世界將重新建立起和諧。這是一本在當時非常提升美國士氣的書,現在看也是一本非常有前瞻性的書,“技術的進步將把世界變為一個地球村”之說,正是現在的“全球化”。就連“美國世紀”一說,也被證實。即使在當時,歐洲的衰落美國的崛起已經是有目共睹。
三、美國二戰時期的藝術選擇
德國在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占領了巴黎,法國人完全沒有抵抗,就向德國投降,這讓美國人非常瞧不起。當然,對法國人而言,這可以算是策略,他們用這個方式保存了自己珍愛的巴黎。但是巴黎已徒具空殼,變成了一座死城,其中的活躍分子和藝術家們都離開了。在德國侵略者的嚴密控制下,所有那些讓巴黎發光的東西全消失了,她的文明,她的自由,她的從容,她的創造力……都沒有了。全世界都知道,巴黎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她的文化氛圍。巴黎是這樣一個地方,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隨便什么人都可以去那里,那個城市里的任何男女都可以充分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才華——無論他們有什么樣的才華,在巴黎都能找到適合他們做的事。在那里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家會告訴他們該說什么,該做什么。巴黎的自由,不是文化人知識分子們才擁有的自由,在街上負責點煤氣燈的男人,在廚房里做事的女人都平等地擁有這種自由。住在巴黎就意味著呼吸真正的自由空氣和完全的個性化,這就是巴黎。巴黎在戰爭中盡管沒有遭到摧毀,藝術品都被藏好而保留了下來,可是,那個氣氛失去了,巴黎的榮光就失去了。巴黎就“死”了。
西方一直是把巴黎看成是自由和創造性的一面旗幟,現在這面旗幟倒下了,美國人多少躍躍欲試地想,他們如果在政治經濟上強大了,是否在文化上也該強大一把,有義務把這面旗幟舉起來。可是巴黎人對此全不領情,就文化藝術方面說,巴黎完全瞧不上美國,無論巴黎遇到了什么,巴黎就是巴黎,美國要來替代,休想!
法國人的嘴,真是夠損的。法國人的驕傲,真是打不倒的。即使山河即將破碎,國家風雨飄搖,可是他們不變地認定自己還有文化可資驕傲。在一九三九年紐約主辦的世界博覽會上,處在戰爭危機中的法國政府文化官員Olivier照樣嘴硬說:“美國邀請了各國來參加這個博覽會,它的主題是‘明天世界將如何?’法國在過去光榮的時代中體驗過疾風驟雨,體驗過壓力,然后總能再度抬起頭來給出簡單而尊榮的新答案。那么現在我們也能夠笑對被美國人提出來的問題,平靜地給出答案:明天的世界將如同過去的和現在的世界一樣,具有大量的法國靈感。”②Serge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p.51.
法國人驕傲的理由也在于,四十年代初的美國藝術的確還拿不上臺面。平行著看,美國藝術就是要比歐洲矮下去一頭:二十世紀初,當歐洲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風起云涌之時,美國本土出現的“前衛藝術”不過就是沖破學院規則,直接表現城市平民生活的“垃圾箱畫派”而已(因畫不修邊幅的市民而得此名)。一九一三年紐約舉辦第一次“國際現代藝術展”(軍械庫展覽),歐洲的現代藝術無異于在美國投了一顆炸彈,讓美國社會“炸了鍋”,民眾認定那批所謂現代藝術家根本是一群瘋子!紐約有一位開畫廊介紹歐洲現代藝術的人叫斯蒂格拉茲,那時向大都會美術館誠懇建議,應該乘機把畢加索的作品買下來,大都會負責人正色道:如果把這種東西當成藝術,除非自己腦筋出了問題。三十年代,美國占據主流的鄉土主義藝術,是用寫實手法畫本土題材,突出美國風土人情,然而從藝術手法看,它們風格落后,題材狹隘,拿這個去替代巴黎,根本就是笑話。當然,美國也陸陸續續出現了一些畫抽象藝術的人,但人數稀少,而且都在努力模仿歐洲,不具備美國特色,更無法形成氣候。因此,到四十年代初期,美國政治經濟是強大了,但在藝術上只能嘴上硬。

1913年紐約“軍械庫展覽”現場
《紐約時報》的藝術評論家Edward Alden Jewell提出,美國藝術家不妨繞過被法國人嘲笑的美國想要的國際性,直接用藝術表現宇宙普遍性——那可比國際性范圍更大,境界更高。“當國家在戰爭,在準備戰爭,政治傾向在往國家主義傾斜,藝術世界(我希望)是朝著更普遍性的范圍去的,最后達到的是人類共同經驗的表達。而在美國,又是這樣一個不同族裔的匯合而成的國度,給了藝術家特別的機會來實現探索普遍性的表達。”①Edward Alden Jewell,Have We an American Art? p.128-129.
美國文人兼詩人John Peale Bishop則援引歷史的相似性來證實美國的好:“未來的藝術在美國……都不必等到戰爭發生或者預言,就在現時,西方文化的中心已經不在歐洲,是在美國。現在我們是對未來的發言人,是負主要責任的人。藝術的將來會在美國……現在我們這里的確來了不少歐洲的作家、學者、藝術家、音樂家,這對我們的意義則如同歷史上發生過的那樣,拜占庭的輝煌過去及文明被土耳其蠻子掠奪時,他們的學者去了意大利。這個比較值得做,就我所知,拜占庭的流亡者們去了意大利后,拜占庭所造空空,而這些學者的到來,他們帶來的知識,卻讓意大利成果累累。”②John Peale Bishop,”The Arts”, Kenyon Review 3, Spring 1941, p.179.

垃圾箱畫派 John Sloan, Hirdresser’s Window
總算有人肯面對現實。有個叫Samuel Kootz的有學問的商人,一九四一年往《紐約時報》寄去一封“讀者來信”,指出,即使在戰爭時期,紐約已經代替巴黎做成了藝術家文人們的自由之地,可是紐約的藝術界是否真有能力拿出一種新的、原創的藝術,與已經死氣沉沉的巴黎對抗,還是令人十分懷疑的:“在紛紛認為代表將來的繪畫會在美國出現的輿論下,情形卻令人遺憾,我們現在能對世界藝術中心這個頭銜所作的貢獻還微乎其微。我們當然是可以期待在沒有外來的幫助下,今天的藝術家走新的路,有新想法。我們該把他們武裝起來去反擊巴黎這個施主——我們跟隨這個領導的時間也太長了——我們要找到自我……我本人處在這種焦慮的盼望中,因此在過去的十年中不斷地走訪畫廊,關注批評。可是我得到的結果是無法滿意的,我沒發現過一道希望的亮光,我沒見到過一個脫穎而出的畫家,沒有過一個要去進行實驗的意圖,要去找到一種新的繪畫方法。畫廊里現在展示的作品只是畫的題材不同(不是方法上的)。可憐的塞尚打了一場沒有打贏的仗,不是嗎?孕育出的不過就是這些愉悅的,無害的,沒有精神的勞什子。沒錯,若干年前,我們有過一股繪畫上的階級斗爭,但那些小伙子們沒有把他們的想法直抒出來,他們把那種想法扼殺在過去的畫框之內了——他們沒有去努力創造出一種新技術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在過去十年中那些首選的藝術家們,他們做了什么呢?他們還在那里,繼續戴著桂冠,呆在舊的堂廡里而不自覺。但也并沒有新的天才出現來挑戰他們呢。這些老家伙們肯定已經不是我們的希望所在,精神之光不在那里照耀了。那些曾經使老家伙們出色的實踐——現在已經成為陳腐的風格,波浪不興的念頭,缺乏想象的溫和據禮……總之,現在應該是動手創新的時候了。你們抱怨法國人偷走了美國的藝術市場這么些年了,可是,事情依然照這樣走著。畫廊需要新的天才,新的主義。在我們的大地上,到處能聽見錢響。所以,你們得動手干起來,男女青年們, 去走一條新的路吧,去做改變吧!”①Samuel Kootz’s letter, New York Times, 1941/8/10, section 9, p.7.

30年代美國鄉土主義作品:Grant Wood, Fall Plowing
Samuel Kootz的“信”引出很大反響,他倒是個有資格做這樣發言的人。這個人從年輕時就喜歡繪畫,一直關注藝術,一九三○他還寫了本《美國現代繪畫》,描述了當時的美國繪畫——大蕭條期間出現的鄉土主義藝術。他的聲音在一片一廂情愿的叫囂聲中,被《紐約時報》稱為“炸彈”——打破了人們的幻覺,其效果是讓人們開始真的去注意紐約畫界發生了什么,不再只玩觀念上的自欺了。呼應這篇文字,有一群人自命“炸彈群體”,一九四二年在紐約組織了一個展覽,試著展示一下他們認為有創意的美國作品,但展覽根本不成功。Samuel Kootz還被紐約的梅西大百貨公司請去,在他們的櫥窗里展示美國的現代藝術。被《紐約時報》評論說,展覽上看不到有才華的作品……無論這些事情能有多少效果,但是能看出人們愿意對美國本身的現代藝術來做點什么了。顯然Samuel Kootz的言論并不是要去打擊美國藝術家,而是給出忠告,告訴他們解決問題的途徑:必須走現代的,新的路。同時也告訴人們,美國這片土地上是有能量的,但是這些能量沒有轉化成藝術的形式。
美國人還意識到,美國藝術沒有地位,也因為它沒有市場。無論是在戰前,在戰時,哪怕歐洲藝術家已經落難到美國,美國已經做成了他們的恩主了,可藝術市場還是只認歐洲。“美國藝術家都看得到,在紐約賣畫是被巴黎的畫商經紀人統治的,他們會抓住任何一個機會讓他們的美國客戶別買美國藝術家的作品。從世紀初到現在為止,美國已經被狡猾的巴黎畫商不停洗腦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之久,結果是那些毫無才華的作品,只要被巴黎藝術交易所提過,在美國才賣得好。那些畫得又差又虛偽的東西,都比有才華的美國藝術家又誠實又好的作品容易賣得多。”①Forbes Watson, American Painting Today, Washington, D.C.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Arts,1939,p.15.
[4]China has engaged in by far the world’s largest campaign to steal trade secrets.It has also pressured foreign companies for years to‘cooperate’with Chinese firms in developing and applying technology.(2018.3.23)
美國人挺想改變這個局面。
美國政府在巴黎淪陷以后,曾出面組織了一個“購買美國藝術周”的項目,即定期在美國不同城市開辦藝術集市,吸引民眾接觸藝術,更要吸引普通大眾能學著購買藝術作品,習慣把它們納入家庭的開支。當然,政府這么做有其實際考慮:美國三十年代羅斯福“新政”中的一個重要設置“工程興辦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簡稱WPA),通過“以工代賑”的方法,雇傭有勞力的失業者為政府興建公共設施,其中也包括雇傭藝術家。WPA機構中為救濟藝術家而設的“公共設施藝術項目”,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藝術“雇主”,有將近5300個藝術家受雇,他們承擔了全美國各地公共設施的裝潢和美化,比如飛機場、火車站、郵電局、市政府、法院、學校這類場所。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三年,這些人創作了近2500幅壁畫、18000個雕塑,還有其他畫作不計其數。積攢下的許多畫作對政府而言幾乎都是廢物,不妨拿出來賣,如能就此培養起一個民間的藝術市場,藝術家或許就可以靠那個市場來養活自己,政府便能卸掉扛在肩上的這個包袱了。因此,這個計劃等于是給取消WPA項目做鋪墊。然而,到一九四二年美國參戰之后,政府舉辦的這個“藝術周”也就結束。這個事情做得虎頭蛇尾,遭人嘲笑。因當時有人統計,一個藝術家大概需要2000美元生活一年,開發這樣的所謂市場,根本無法滿足這個需要。換句話說,美國藝術家還是無法靠市場來養活自己。有畫家這樣描述道:“到現在為止,對美國普通人來說,讓他們由興趣去買一幅畫超過他們對買車的興趣,顯然是不可能的——就像對一個海地農民一樣不可能。我們要的價格完全不貴,哪怕是放到海地也不算貴。在全國各地的單個展覽或者WPA組織的展覽中,你可以發現成堆的油畫和水彩畫,售價在25-50美元之間。可是,誰要呢?其中還有些很多人看不懂、只畫家自己才懂的抽象畫。有些干脆只能算是豬下水;還有的是斧頭鐮刀那種枯燥的東西,三流的里維拉。”①Byron Browne, New York Times, 1940/8/11, sec.7, p.6.即便如此,這個事情的作用卻也不可以完全抹殺,統計數據表明,這個項目在全國范圍內共有32000個藝術家參與了1600個展覽。這多少會刺激民眾對藝術的注意吧。根據俄勒岡州的美術館統計,那時,他們的參觀人數從每天的75人,增加到了400人。

George Biddle 30年代參與WPA藝術家援助計劃在畫壁畫

WPA藝術資助項目中藝術家創作的木版浮雕(William Zorach, Natural Resources and Man Power)


“我們的畫廊”以及它的主人E女士
這樣的努力在不同層面上進行著。政府開發普羅大眾的市場,畫廊則開發中產階級的市場。開在紐約曼哈頓西13街的一家叫做“我們的畫廊”(Our Gallery),殫思竭慮吸引美國人來買美國畫家的畫,這家私人畫廊主竟想出把所辦展覽起名為“為了一千三百萬人的藝術”,背后的意思是,通過調研發現,美國社會中有一千三百萬人能夠買車,買毛皮大衣,買電視……那么,這些人就有購買藝術品的能力。于是畫廊估計著客戶的消費能力,把展覽品的價位定在600美金,而且可以每月50美金分期付款,一年付清。另一個展覽起名為“為67%人口的藝術”,意思是,美國67%的成人是結了婚的,而夫妻雙方選擇畫作時,各自的口味不同,無法統一,因此這個展覽中的任何作品,允許買家先把畫拿回家掛一陣子,等夫妻兩人都覺得合適了再買下。這種推銷藝術的方式,真是聞所未聞。這也是被逼出來的,因為讓美國人關注并購買藝術,真的比歐洲難很多。比如一對底特律做地毯生意的年輕夫婦,發了財,到紐約去逛,被“我們的畫廊”說服,一下子買下了四幅畫。可是一出店門,夫妻兩個立刻慌了,太太事后回憶說:“我倆出來了,回到街上,互相看著對方,簡直不明白自己剛才做的事。”②Lindsay Pollock, The Girl with the Gallery,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2006 ,p.326.版本下同。
在高端層次上的努力是辦美術館。要提升美國人藝術品位,建立自己高水平的美術館非常重要。紐約現代藝術館由此而建,而且走精英路線,把目標鎖定在推介梳理歐洲現代藝術的脈絡,理由是,只有通過全面理解歐洲現代藝術,才能提升美國人的品位。但也因為此,現代藝術館一直被人批評眼里只有歐洲,沒有美國。現代藝術館也做出姿態彌補。但在四十年代初,他們也無法看好美國人自己畫的東西,只是在戰爭期間,配合政府用展覽館做了宣傳活動。比如一九四二年六月,現代藝術館做的“通向勝利之路”展,展覽了美國著名攝影家Edward J. Steichen的攝影照片,并配著詩和文字。選用的照片是美國軍隊的雄壯軍威,幸福的美國農民,滿面笑容的美國工人。這個展覽一掃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畫面——愁眉苦臉的窮人、失業者,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幸福自信的美國圖像。這樣的展覽很受民眾歡迎,有98000位參觀者留言說,身為美國人是一種驕傲。這個展覽獲得了左翼右翼的一致叫好。不過,這種展覽只是配合政治的宣傳,紐約現代藝術館真正關注美國自己的藝術,還要再晚一點,直到四十年代的后期,他們才開始力挺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正是中情局與他們聯手做“陰謀”之時。)
所有這些因素,無論大小,直接間接,肯定會幫助美國藝術積蓄自己的力量。有一個更加顯著的推動因素是:大量歐洲藝術家在二戰期間流亡美國。就地域上說,紐約不取代巴黎也得取代歐洲了,因為歐洲藝術家全挪到了美國的地面上辦雜志、辦展覽、辦教育、辦活動、辦派對……這些活動跟歐洲本土已經沒有干系了,歐洲一些國家的邊界甚至因戰時而封鎖。美國藝術一向存著心要從歐洲的牽連中獨立出來,這次至少在地域上并通過戰爭之手實現了。
戰爭還直接提升了抽象畫在美國的地位。法西斯勢力橫掃歐洲之際,整個西方文化都受到了踐踏。美國報紙上用“蠻族”一詞指稱法西斯德國,媒體上充斥的漫畫,是一只代表納粹德國的大靴子或者一只張牙舞爪的大猩猩去踩踏象征文明文化的火炬的畫面。尤其法西斯德國特別反對抽象藝術這種東西,這等于給了現代藝術一個在美國入場的機會。一方面,它可以拿來表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另一方面,如美國抽象畫家Ad Reinhardt在《新聞周刊》上的一張漫畫所表示的:抽象藝術能把美國藝術從各種爭執和糾結中拯救出來。
二戰后的幾年,是抽象藝術在美國迅速發展的年頭。美國畫家Milton Brown一九四六年四月發在《藝術雜志》上的文章,生動地說明了這個情況:三年前他離開紐約去當兵打仗時,社會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藝術覆蓋了紐約的畫廊美術館,占據著市場。現在,那兩種藝術幾乎銷聲匿跡了。“我一回來吃驚地發現,當時僅僅像臨時過客的那匹抽象主義黑馬,現在踢開一切沖到前臺來了。在每一條街上都證據確鑿地顯示今天的時尚是抽象。在三年前,這個趨勢只是隱約被感到,現在則是淹沒了整個舞臺。畫廊展出的很多抽象畫家,我連聽都沒有聽說過。”①Milton Brown, “After Three Years”, Magazine of Art, 1946/4, p.138.


紐約現代藝術館配合政府做的“通向勝利之路”宣傳展現場
美國藝術在三十年代曖昧不明搖擺不定的局面,在四十年代多少變得明朗了:美國藝術選擇抽象,可以擺平很多方面的關系。當然首先,是擺脫國家主義的狹隘;然后是擺脫國際上的法西斯(后來是擺脫共產主義);同時它甚至能擺脫由中產階級代表的資本主義的庸俗文化——格林伯格一九三九年發表的文章“前衛和庸俗”所以有名,就是把抽象藝術對于資本主義社會能產生的革命性說明白了:前衛藝術真正的重要功能是,將革命和資產階級一起否定,尋找到一條提升精神之路。尤其重要的是,格林伯格逐漸建立起的現代藝術理論替美國抽象繪畫掙到一份重要地位,即:被命名為“抽象表現主義”的美國抽象畫正好完成了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發展過程中的最后一步,讓繪畫徹底達到了自己的純粹性。格林伯格也因此成為現代藝術的旗手理論家,乃至成為藝術界一個權威的聲音。在政治民主的理念上,抽象藝術又被視為是可以自己被解放而且去解放別人的最佳方式,與戰后美國政治的主流理念一致。一九四八年的美國大選,提倡的口號是“新自由主義”,自由似乎成為最重要的價值。
至此,我們跟隨美國社會政治的進程,對抽象藝術在美國的發展和生長環境,作了基本描述。似乎從各個方面看,美國抽象藝術本身的性質和它可以擔負的使命,變得越來越清晰了。可是現實永遠比我們以為的要復雜,抽象藝術在美國漸漸清晰起來的使命,正好與美國社會在一段特殊時期中刺激出的對現代派的普遍恨意,沖撞了。

Ad Reinhardt漫畫
四、美國現代藝術遭遇的尷尬局面
讓我們再次回到現實,進入美國冷戰時期的歷史。
戰爭結束,人們滿心以為和平降臨,幸福開始,而現實并非如此。首先,第三世界國家內繼續內戰不已(比如中國),其次,國際政治布局從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大陣營對立,馬上轉變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了。這對立始于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會議,英美蘇三國領導在二戰結束前夕會面討論戰后問題。到這時候羅斯福才發現,一九四三年,他們三國領導在德黑蘭會議中決定美、英聯軍在法國開辟第二戰場,然后美國將軍火及各種戰爭物資源源不斷地援助給斯大林,讓蘇聯紅軍單獨在東線發起進攻,結果到了一九四五年美國已經養壯了一只老虎。彼時蘇軍力量已經發展到能和美國平起平坐,有足夠的實力獨霸、主宰、支配東歐各國的領土與命運了。即使這樣,在雅爾塔會議上,美英出于私利,又一次讓斯大林賺了大便宜。這次會議的全稱為《蘇美英三國關于日本的協定》,英國為維護自己已經日薄西山的殖民帝國利益,美國則是為提早結束對日戰爭,在沒有其他聯盟國出席的情況下,不按照當時被占領國家的期望——要求戰后被蘇聯“解放”的國家交由聯合國代管,而是把他們留給了蘇聯。同時還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出賣中國的領土主權換取蘇聯對日宣戰。原來,蘇聯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從建國那天起是受到西方國家敵視、孤立的,但借著反法西斯戰爭之機,蘇聯已經把勢力迅速擴張到近東、中東、遠東、非洲、南美……不光支配著東歐與東亞的所有戰略利益,而且和昔日宿敵平起平坐。
這讓美國不快而且緊張。一九四六年二月,接替了羅斯福的總統杜魯門派了一名出身歷史學者的官員George F. Kennan去蘇聯考察。他考察后從莫斯科發回美國國務院的電報,成為美國歷史上一份著名的文件——“長電文”(Long Telegram),內容是蘇聯政治的實況:1.蘇聯認定他們將對資本主義永不停息地作戰。2.蘇聯將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馬克思分子們作為同盟者。3.蘇聯把其他國家的非共產黨的左翼視為比資本主義更大的敵對勢力。4.蘇聯國策的制定不來自民眾意愿和經濟現況,而是來自俄國根深蒂固的國家主義和領導的神經質。5.蘇聯的政體遮蔽了內部和外部清晰準確的局面。這份“長電文”幾乎讓美國人第一次看到蘇聯內部的情形,而且開始知道,蘇聯一直都視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敵人,眼睛從不看客觀全局,只盯著資本主義爛瘡部分,他們是無法和資本主義國家結成任何聯盟的。這份“長電文”很快成為美國政府制定冷戰政策的主要依據。杜魯門讓自己的高級助理根據這電文做出一份詳細的“美國對蘇關系報告”。George F.Kennan也參與助戰了這份報告,并且把自己寫的部分獨立成篇,起名為“蘇聯行事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于一九四七年一月送交美國國防部長,作為一份內部文件傳閱,同時被《外交事務》雜志的編輯拿去發表出來,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影響很大。于是,二戰結束不久,新的敵意出現,對象就是蘇聯。
冷戰格局的最終形成還因為,美國打算推出一項幫助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劃”。戰后的歐洲滿目瘡夷,許多著名的城市很慘,比如華沙和柏林,幾乎成廢墟,沒成為廢墟的城市也斷壁殘垣,不忍卒睹。歐洲別說著手重建這些城市,就連維持人們生活都有極大問題。交通運輸已被戰爭嚴重破壞,物資無法流動運輸,到處缺吃少穿。此外還要加上東西歐之間開始形成鐵幕,導致西歐無法從東歐獲得糧食進口,這個情況在德國尤為嚴重。當時負責經濟事務的美國國務卿助理William L. Clayton在寫給華盛頓的報告中說,德國人每天攝入的卡路里,完全不足以維持正常的健康狀態,“數百萬人正在慢慢餓死”。雪上加霜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冬天,歐洲又經歷了罕見的酷寒,煤炭驚人短缺,德國有數百人直接被凍死。英國為了滿足民用煤炭需求,甚至不得不停止全國的工業生產。即使沒有政治的考慮,僅從人道主義出發,美國也應該對歐洲伸以援手。這就有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的目的是幫助歐洲,但對美國也會產生利益。經濟上,由于戰后美國經濟增長,經濟長期的發展,需要依賴貿易、一切短缺的歐洲正是美國的市場。政治上,美國需要建立資本主義同盟。可是在戰后,歐洲共產黨勢力明顯增長,因他們在反戰期間起的作用很大,所以在戰后的選舉中取得了普遍性成功。在法國,共產黨甚至一度成為議會的第一大黨,這讓美國感到緊張。就是為遏制共產黨勢力的擴張,落實“馬歇爾計劃”也顯得非常重要。美國總統杜魯門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國會兩院發表講話,“游說”兩黨議員投票通過“馬歇爾計劃”,卻一時未果。其中一個原因是,美蘇在戰時建立的聯盟關系還未結束,“馬歇爾計劃”的第一個版本中甚至把蘇聯及其在東歐的衛星國也都放在援助的范圍內,當然是有條件的:蘇聯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并允許西方勢力進入蘇聯的勢力范圍,這等于意味著要讓蘇聯“變色”。斯大林在開始還對該計劃表示了“謹慎的興趣”,一聽這個條件之后,馬上閃了。跟著,蘇聯的那些“衛星國”也一起“閃”了——他們不得不閃。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希望加入“馬歇爾計劃”,派人參與開會,蘇聯知道之后,把捷克外長叫到莫斯科,被斯大林一頓痛罵。后來“馬歇爾計劃”把援助對象修改為西歐諸國,國會通過的可能性也提高了。而蘇聯也因此有所對應,也做了一個援助計劃,籠絡周邊的衛星國,保護自己的勢力范圍。
即便如此,“馬歇爾計劃”還是很難獲美國國會批準——誰肯拿出大把的錢去幫別人呢。就在美國政治家們和民眾還在搖擺時,還是現實進場幫忙了。當時共產主義勢力開始有力地滲透到了希臘和土耳其,甚至愛爾蘭。蘇聯對歐洲的干預越來越明顯。二月二十五日,捷克總統在共產黨的壓勢下,把社會民主黨派的部長解職,替換成共產黨的部長,讓共產黨的勢力進入了內閣。幾個星期后,芬蘭加入了俄國陣營。三月,捷克著名的社會民主黨代表人物Jan Masaryk被暗殺。國際形勢驟然緊張。杜魯門和馬歇爾不停地提醒美國人,蘇聯的舉動已經開始威脅世界和平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杜魯門發表對全國的廣播講話,譴責蘇聯的外交政策,敦促國會盡快通過馬歇爾援歐計劃,可以遏制蘇聯的擴張。對于國內,杜魯門表示要支持大規模的軍事集訓,要讓每個美國人學會如何在戰爭中生存。這些事情改變了國會和民眾對歐洲救援計劃的冷漠之心,他們現在得重新換一個立場來考慮這件事了。馬歇爾在加州做的演講中,把蘇聯的外交政策等同于納粹在一九三九年的擴張政策。美國的軍事委員會提出了好幾項國防部的計劃,增加兵源和物資儲備。《紐約時報》披露:俄國潛艇正開往美國西海岸水域。《華盛頓郵報》稱,華府現在不再是戰后的氣氛了,而可以直率地說是進入了一種戰前的氣氛。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的民意測驗中有73%的人認為在最近的二十來年中會有發生戰爭的可能。而一九四六年的測驗只到41%。到這種時候,任何事情與共產黨有關聯,都被視為是危險的。
在緊張的戰爭氣氛壓力下,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國國會終于通過了“馬歇爾計劃”,這個計劃設施了四年時間,對歐洲的援助金額達130億美元,相當于現在的1300億美元。
這段歷史對于我們所論述內容的相關處是,“馬歇爾計劃”對美國政治標志兩件大事:一,兩大敵對陣營形成。二,援助導致了歐洲更加依賴美國,確定了美國在西方國家中的領導者的地位。到了這里,就可以進入我們“故事”的核心部分了:這兩件大事刺激著美國要在方方面面做得像一個領頭人,展示美國實力,穩住世界局勢。在這其中,美國的經濟,美國先進的工業化,都已經處于前沿,不成問題,問題是要充實藝術這個弱項。正如美國當時的國務卿助理William Benton所說,我們需要“對那些把美國只想成是一個物質化國家的外國人表明,這個國家不光有出色的科學家,工程師,同時也有具備創造力的藝術家”。①Gary O. Larson,The Reluctant Patron-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rts,1943-196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1983,p.24.版本下同。
這是一件冠冕堂皇的政治任務,也涉及全美國人民穩定、安全、強大的共同利益。然而吊詭的是,具有美國特色的一批新抽象藝術(抽象表現主義)卻在政治上和反蘇反共的主流撞了車。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是美國政治形勢轉變的關鍵時期,政府宣傳的蘇聯威脅,在社會上轉化成對國內共產黨和親近共分子的恐懼。一九四六年七月,《生活》雜志上發表Arthur Schlesinger, Jr.的文章,直接攻擊美國的共產黨根本就是蘇聯的走狗。在戰時,美國共產黨在議會中尚有一席之地,現在國會則要把他們清除出去。杜魯門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向國會發表一個提案:禁止一切顛覆勢力對政府的滲透。美國勞工部“出于國家安全考慮”,把美國的共產黨分子從政府的工作崗位上剔除。美國司法部列出一份顛覆分子名單,公布于眾,所有那些有反對美國政府傾向的俱樂部、組織、學會等都在名單上。愛國主義在民眾中成為一種公眾道德,愛國的具體表現就是抵制敵對政治勢力,支持民主,任何親近敵對勢力有害民主的人,就是不愛國。美國教育部把國家安全作為對青少年的主要教育內容:“在所有的需要中,通過教育強化國家安全,是唯一最重要的教育前沿陣地。”②Serge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p.147.一九四七年美國的教師協會(AFT)年會的題目就是“為國家和世界的安全強化教育”。他們選擇教科書的內容,也必須是符合“民主成長”的內容。
這就是美國政府著手開始資助前衛抽象藝術時的政治背景。
起先沒人知道這個“背景”的力量有多厲害。美國政府只管一件接一件做該做的事。好,現在冷戰開始,要把文化作為“炮彈”往外“發射”了,因為蘇聯已經做到前面去了。早在三十年代蘇聯與歐洲結盟之際,他們就已經通過在歐洲設立豪華的辦事處,主持開世界文化大會,送展覽出國,竭力用文化替自己做宣傳了。那么,趕緊拿出自己的文化形象來為美國造勢成為當務之急,藝術在其中尤其重要。可是選什么樣的藝術來代表美國呢?因為美國在藝術上不及蘇聯的藝術具備風格和觀念的統一。但這可并沒有把政府難住——交給懂行的人去辦唄。于是,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四六年指派了一位過去擔任過明尼阿波勒斯藝術中心副主任的官員戴維德森(J. LeRoy Davidson)負責此事,組織一個“前進中的美國藝術”展。此前,戴維德森已經辦了兩個展覽,一個叫“美國工業界贊助的藝術”,一舉兩得地展示美國的兩面,工業和藝術。展品都借自美國工業界的巨頭們(他們的私人收藏相當可觀)。另一個展覽是應埃及之邀,送美國繪畫去參加開羅的國際藝術大展。展覽也做得順利,戴維德森繼續從那批工業巨頭的收藏中選出一個“1800年以來六十位美國人”展。接下來要辦的“前進中的美國藝術”展,國務院打算做成巡回展,送到歐洲和南美洲兩地,用五年時間來好好地宣傳一下美國的藝術。為此,國務院還特別撥款叫戴維德森直接買下一批畫來做巡回展,理由很實際:長期向收藏者借用作品,租金很高,買下作品,一勞永逸,而且也能成為政府收藏。
戴維德森是個懂藝術的人,知道美國學院派或者鄉土寫實派的作品太過保守,不合適拿出來作為美國的新形象,他打算“通過用美國現代藝術的樣本,來反擊蘇聯的攻擊:把美國說成只是個物質主義的國家,有的不過是遍地的洗衣機和閃亮的比克轎車”。③Lindsay Pollock, The Girl with the Gallery, p.319.因此他用國務院專款4.9萬美元買下的79件作品,基本是前衛派的抽象或者半抽象的畫作,選的藝術家有John Marin,Max Weber, Stuart Davis, Ben Shahn, Byron Browne,Phillip Evergood, Philip Guston, Georgia O’Keeffe, Jack Levine, Charles Sheeler等人。在一九四六年秋天,這個展覽先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對美國公眾展出,反映還不錯,有一些贊揚聲,認為美國政府總算肯對藝術投以關注(與歐洲國家比,美國政府對藝術的不關注不過問是很出名的),并肯出手支持現代藝術了。還有人因此開心道:“世風終于轉了:如今世界各地都急著想看看美國的藝術,她已經不再被看成是一個被巴黎過繼的窮孩子了。”④同上,p.319。
不料,反對聲音的聲音開始出現,而且聲浪漸高。Gary O. Larson在他的《勉強的贊助人——美國政府和藝術,1943-1965》一書中這樣告訴我們:“還真不知道是誰先開始對‘前進中的美國藝術’展發難的,但這竟釀成了這一年藝術界最厲害的一個爭議。就像國務院設了WPA項目后備受攻擊一樣,現在國務院又成了個受到各方面攻擊的受氣包——有來自共和黨議員們的攻擊(他們多熱衷于去挑民主黨在執政上的毛病。譯者注);有來自保守媒體的,他們成天盯著政府可能的靡費;有來自反對現代藝術的學院派畫家的;還有干脆是來自那些政府沒有買他們作品的心懷不滿的畫家們。”①Gary O. Larson, The Reluctant Patron-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rts,1943-1965, p.26.
代表學院派保守勢力的“美國職業藝術家團”開始鬧得最歡,他們當然不喜歡看到現代派得勢啦。他們不停地給國務院寫信抗議,并在雜志上公開發表出來。他們指責國務院辦了個一邊倒的展覽,那些所謂現代派,不過就是美國藝術中一個小小的流派而已,怎么竟能拿出去代表美國的藝術形象呢?這根本就是拿一小撮人的作品制造藝術中的壟斷。他們自己寫信不算,還串聯其他保守藝術團體一起發難,比如國家設計學院、美術聯盟、插圖畫家協會、自治藝術會社……他們全討厭現代藝術,當然一呼百應,連篇累牘地給國務院和國會寫信,吵得國會上下全都知道了。媒體上用“納稅人的錢買來的藝術”做題目,對面積越來越大的“眾怒”火上澆油。
在這樣洶涌的國內輿論前,批評的聲音終于從最高層傳了出來,總統杜魯門表態否認了“前進中的美國藝術”,否認那些抽象畫可以被算作美國“所謂的現代藝術”,它們僅僅只是“一群腦殘的懶漢們吹的牛皮”,“如果這能叫藝術,我就該算是個蠻子了”。②Lindsay Pollock, The Girl with the Gallery,p.321-322.總統杜魯門這么說話,實是暗示自己是個懂藝術的人。因為他在任職白宮期間,習慣早起,在華盛頓整個城市醒來之前,這位勤勉的總統已經散步到距離白宮不太遠的華盛頓國家美術館門口,有指定好的門衛會一早等在那里替總統開門,讓他面對歷史名作進行早餐前的漫步。他常常會在日記里記下他觀畫的體會,比如在一九四八年的某一天,他在看了德國十六世紀的荷爾拜因、荷蘭十七世紀倫勃朗作品之后,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在看了這些完美的作品再去想想那些糟糕懶惰的現代派們,倒是不失愉悅的一件事。這等于是把耶穌和列寧在作比較。”③Harry S.Truman, 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Truman,edited by Robert H. Ferrell,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p.129.
事情鬧到這個程度,美國國務院只能舉手投降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國務卿馬歇爾在對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作報告時承認說:“對于這件事已經收到了各方面的提醒。到現在為止我至少已經收到了50到100封談這個事情的信,我已經跟總統在不同場合口頭討論過這件事。”馬歇爾對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示意,眼下這個展覽正在海地和葡萄牙兩地舉行,一俟結束,就會考慮取消撤回。可是撥款委員會的人依然不依不饒,擔任委員會主席的Karl Stefan甚至帶了一張抽象畫去咨詢現場,一直問到國務卿助理的鼻子底下:這幅畫畫了什么?助理答,我可說不出來。又問:我拿遠一點,你能看出是什么嗎?助理答:主席先生,我甚至都不敢冒險去猜。再問:你為它付了多少錢?你付了700美金,卻不知道它畫了什么,對吧?!④Gary O. Larson, The Reluctant Patron-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rts,1943-1965,p.27.到了這個份上,國務卿也好,他的助理也好,恐怕也只有鼻尖冒汗的份了。

美國媒體反對“前進中的美國藝術”展,標題為“納稅人的錢來買的藝術”
五月份,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在正式否決國務院撥款支持藝術的文件中這樣寫道:“這個項目已經收到了成千上百封抗議信……如果我們送展覽出國是為了影響人們,我們要影響的是應該是普通大眾,而不是藝術領地里的一小撮人。”就此,國務院出國辦展的申請款項被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取消。⑤同上,p.28。
于是,“前進中的美國藝術”被撤回,組織者戴維德森被解職。國務卿馬歇爾下令,為展覽買下的所有畫作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拍賣,希望至少能把花出去的錢再收回來,結束這件叫國務院丟臉的事情。但拍賣的結果并不如愿。一方面輿論已經搞臭了這批現代藝術,另一方面美國法律規定,凡政府機構和退伍軍人機構來買政府所拍的東西,會有百分之五的折扣,結果,阿拉巴馬州的Auburn大學在享受折扣之后花了21453美元買下了36幅畫。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買下了另外36件作品,價格便宜得驚人。不少作品價格落到了100美元,50美元,甚至30美元。這次拍賣讓這兩所南部不起眼的大學一下子獲得了如今相當有價值的美國現代藝術藏品,他們成了這個丑聞中的獲益者。

John Marin, Buoy

Stuart Davis, Mural (Radio City Men's Lounge Mural: Men without Women)
然而,展覽撤回之后事情并沒有結束。因為有政治家把抽象繪畫及創作者和敵對勢力聯系起來了。這一來事情的嚴重性就遠遠超出先前抱怨的“風格上的一邊倒”、“藝術上的壟斷”或者“腦殘的懶漢們”那種問題了。首先是共和黨議員Fred Busbey向國會發了一篇關于藝術的咨文(其后陸續有續篇跟進,把這個話題一直延續到50年代)。他除了指責國務院組織的展覽是“美國的恥辱”,是被“共產分子影響”了,是“花了納稅人的錢,卻在國外做有損美國的事”之外,最厲害的一棒是:“有記錄顯示,45位參展藝術家中有20位受過共產主義影響,其中有些和革命組織有直接的聯系。”①Gary O. Larson, The Reluctant Patron-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rts,1943-1965,p.29。這等于把美國現代藝術穿上了佩有“共產黨”紅字的背心。
國會中另一位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議員George Dondero對抽象藝術的攻擊甚至顯得有相當的想象力:“所有的現代藝術都是共產主義氣味的……立體派的目的是通過設計的扭曲走形來作破壞;未來派是用機器的神話來作破壞……達達通過散布荒謬來作破壞。表現主義是通過原始和不正常來作破壞;抽象派是通過在頭腦里引起風暴似的混亂來作破壞……超現實主義是通過否定正常理性來作破壞。”②George Dondero, quoted in William Hauptman, ”the Suppression of Art in the McCarthy Decade”, Art Forum, 1973/9.
來自媒體的更具“創意”的說法是:“那些頭號現代派的藝術家們無意中已經成為克里姆林宮使用的工具”,或者,“抽象畫實際是秘密的地圖,直指美國的防御部署”,“現代藝術根本就是間諜用的一種手段,如果你知道怎么讀懂它們,那些抽象畫就會揭示出美國防御中的某些薄弱之點和胡佛大壩那種重要的國家設施”。③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New Press, New York,1999, p.253.版本下同。
這種思路和言論不可笑,是動真格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與聯邦法院聯手起訴逮捕美國共產黨12位領袖。司法部在一九四八年受理了一起美國攝影協會的案件,這個協會成員中的103人被指控為思想危險分子,他們要請律師設法辯護才可以過關。一九四七年好萊塢有300多名電影界人士受到親共罪名的牽連,十數名導演和劇作家直接被國會傳證,到聽證會上去洗涮自己的“共產分子”之嫌。Jane De Hart Mathews在他的“美國冷戰時期的藝術和政治”一文中告訴我們,那時美國政治對藝術上確定的三個“反對”是:1.反對左翼的有涉社會評價的那些寫實藝術。2.反對那些有政治嫌疑的藝術家。3.反對有共產黨陰謀的所謂“現代藝術”。④Jane De Hart Mathews, “Art and Politics in Cold War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1/4, 1976/10, 762-77.國務院對全國下達了一個命令:“以后任何參加或追隨共產黨的藝術家不得參加任何政府資助的藝術巡展。凡有反美國性質的前衛藝術,從現在起將不能進入任何政府的行為。”⑤同上。
此后,任何展覽,特別是其中包括現代藝術的展覽,都會招致人們——政治家或普通民眾——嚴厲的挑剔和把關。我們不妨看看下面的例子。
一九四九年,紐約現代藝術館在紐約州的一家海軍醫院做了個“犒軍”的藝術展覽,題為“輪子上的畫廊”(Gallery–on-Wheels),國會議員 George Dondero 看了之后,馬上對國會發出警告:各位睜大眼睛,一九四七年容忍激進藝術的事件尚未停止!參加這展覽的17人中,有15個屬于激進分子,這15人中,又有9人正是“前進中的美國藝術展”參加者。這說明“炮制這種藝術的人一刻也沒有放棄過把手伸進國家的款項中,同時也伸進私人慈善家那里(指紐約現代藝術館。譯者注),然后讓自己繼續生長”。這個事想想都叫人不安,“這些激進分子在兩周之久的時間里,在這個重要的海軍醫院中,對躲都躲不開這些東西的觀眾們直接傳播他們的理論,這對他們無疑是碰上了一個大好機會,不光是可以做宣傳,甚至可以做間諜——如果他們想這么做的話”。有議員對他的聳人聽聞多少有點異議,問,是否其中只是一兩件作品不合適而已?George Dondero警惕性更高地回答:“我們一向無視這樣的事實,共產主義是一條劇毒的蛇,它能傷到各個領域內真正的民主、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化。”他還援引美國共產黨主席 William Z. Foster發表在《新大眾》(New Masses)文章中的話“要用藝術‘作為階級斗爭的武器’”作為自己言論的依據。⑥此段中的引文均來自GaryO. Larson, The Reluctant Patron-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rts,1943-1965, p.27-28。
真正說來,美國很多前衛藝術家的左翼立場發生在三十年代,如前面介紹,美國很多文化人和藝術家到四十年代已經放棄這個立場了。他們更愿意獨立于任何政治派別,尤其要脫離任何政治的羈絆。可是在那樣的政治氣候中,國會的政治家們根本不會有時間去分辨對錯,同時抽象畫的難懂也遭人討厭。George Dondero這種言論封住了國會中很多人的口。他卻因為對現代藝術的“上綱上線”之功,在一九五七年還獲得了“美國職業藝術家團”(AAPL)頒發的金質獎,表彰他“不懈地揭露在藝術中的共產主義傾向”。
到了五十年代,這樣的形勢沒有改變。一九五六年由美國新聞署出面與一家《體育插圖》雜志(Sports Illustrated)聯手做一個“藝術中的體育”展,分別在波士頓美術館和華盛頓的一家畫廊(Corcoran Gallery)展覽,然后將作為美國藝術展送一九五六年澳洲舉辦的奧運會。偏有一位喜歡藝術的德克薩斯州房地產商人好事,自己掏腰包安排這個展覽到達拉斯美術館去展覽一段時間,立刻節外生枝。展覽一開幕馬上受到一個民間組織“達拉斯愛國協會”者的抵制。這些愛國的市民們指控說,這個展覽中有四個畫家涉嫌為共產分子。達拉斯美術館的理事會立刻慌了,忙聯系畫展的組織者出面正式澄清。《體育插圖》雜志只能去請了律師出具正式的法律文件,證明那幾個受指控的畫家既不在政府“顛覆活動控制委員會”的赤色分子名單上(凡上了名單的人都需要經過15個月的傳證來洗刷自己),也不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共產分子名單上。但這樣一鬧之后,美國新聞署已經不敢把這個展覽作為奧運會期間的美國藝術展送出去了。①Lindsay Pollock, The Girl with the Gallery, p.342-343.
一九五九年,美國政府又一次要送藝術出國門,那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一個官方文化交換活動,誰也不能來隨便阻止。蘇聯送到紐約市議會中心的展覽,幾乎是打造出了一個微縮的莫斯科。美國人研究后決定,把展覽主題放在呈現美國普通人生活上,他們把展覽做成一條仿制的街道,場地就在離克里姆林宮不遠的一個公園里。政府委托加州一位很著名的家具設計師收集整理了一套幻燈片,每12分鐘放映2200張,用密集的形象向蘇聯人展示美國人民的幸福生活。當然,展覽中除了有現代化的住宅、摩登家具和閃亮的轎車之外,一定不能缺了精神產品——藝術。“經歷所有這些自1940年代起政府支持的藝術展而弄到惹火燒身之后,叫人大跌眼鏡的是,政府居然又一次要染指送藝術出國門的事情了。”②同上,p.343-344。(恐怕連讀者都要替美國政府捏一把汗吧。)當然,美國政府又不是呆子,這次可做得非常非常小心了,一下子起用四個策展人,而且名單都拿去讓總統艾森豪威爾批準后才執行。其中兩位代表保守派,兩位代表前衛派,公平無欺。Franklin C. Watkins是學院派大本營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院長,Henry R.Hope是印第安納大學美術學院院長,這是保守派;另外Theodore Roszak是抽象雕塑家,Lyoyd Goodrich是溫特尼美術館的主任,是前衛派。四位策展人挑選了五十幅畫,三十件雕塑。參展作品從一九二○年代的寫實作品到“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波洛克、德庫寧、羅斯科、馬瑟韋爾的畫。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日星期六,報紙上公布了入選作品的兩天后,周一,這些作品迅速裝箱海運蘇聯,時間短得讓反對派來不及下手做任何事。

全力攻擊現代藝術的國會議員George Dondero
可是該來的還是來了,報紙上公布展品的第四天(作品上路后的兩天),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發難了,指稱這個展覽是反美的。這個委員會的主席Francis E. Walter宣布說,在入選的67名藝術家中,有34人有涉及共產黨組織的記錄,其中22人是鐵桿的共產分子,他能拿出最少465份文件來證明這一點。他還說,民眾已經紛紛給他寫信了,對這個展覽的選擇大為憤怒,他要求把這些人從展覽中剔除。
保守的藝術家當然也積極參與攻擊,學院派的寫實雕塑家Wheeler Williams也是“美國職業藝術家團”的主席,指責其中那些親共分子說:“這些人想要的就是摧毀我們文化的各個方面;如果他們想摧毀我們對上帝的信念,摧毀對美,對文化的傳承,包括藝術文學音樂等方面的信念,他們不必用上氫彈就可以做到了。”他也呼吁提議撤回展覽。①Lindsay Pollock, The Girl with the Gallery, p.347-348。
艾森豪威爾總統只能站出來為此事表態了。他承認自己并不很喜歡所選的作品,也責怪了四人組的評委們對普通美國人的趣味缺乏理解。“也許應該有一兩個像我們這樣的人在那里把關,我們雖然不很知道藝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們知道自己喜歡什么,美國喜歡什么——無論美國喜歡的是什么,就應該被展示出來。”他還挑出Jack Levine參展的一幅畫《歡迎回家》,指說入選的這種作品根本就像是張漫畫,而不是藝術。不過總統表示,這次他不打算干涉太多,“我可不想對那些已經運出去的藝術做個檢察官”。于是決定,那些運走的作品就不再追回了,但總統要求另選些作品添進去。在展覽開幕的前三天,26件臨時添加的作品用飛機運去了莫斯科。選的都是美國十八、十九世紀的畫作,包括十八世紀美國畫家斯圖亞特(Gilbert Stuart)那張著名的華盛頓像。艾森豪威爾甚至把自己收藏的一幅十九世紀美國寫實畫家畫的死鴨子,也出借給了這個展覽。②同上,p.348-349。
派去布展的E女士,是一位在紐約經營現代藝術畫廊若干年的內行,又是俄國移民的后代,連她也受到了牽連。她在美國的畫廊接到不止一個威脅電話,她緊張得從蘇聯直接打電話給紐約警察局,要求他們保護她在美國的家。而她到達了莫斯科之后,遭到的不是蘇聯人的盤查,而是派去那里的美國官員的盤查。她感覺那些人對她的態度簡直拿她當蘇聯雇的間諜了,他們顯然很不喜歡她這種人——經營現代藝術畫廊,支持現代藝術,當然,她還是俄國移民。

艾森豪威爾總統批評的Jack Levine 《歡迎回家》
順便知道一下那個展覽現場的情況,倒也不失趣味。在美國似乎每個人都在關心甚至插手過問的藝術展覽,其實被送到蘇聯后,沒人在意它們,那些裝箱的作品一直擱在普希金美術館,只在開展前一天才掛出去。E女士大汗淋漓地跑到舉辦美國展覽的公園里,問了好幾個在路邊賣糖果的小攤和賣冰激凌的小販之后,才好不容易在公園深處找到了圓頂的展館。展覽的內容很多,涉及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還包括空間探索、核能運用、計算機開發……藝術展被安排在一個4千英尺長的玻璃頂房子里。E女士看了不快,一看就知道這樣安排的人根本是外行,陽光直射的場所不易于展覽畫作。但是也顧不得許多了,她匆忙指揮著工人們把作品在空間里掛起來。最后,E女士一圈看下來,心里覺得還行,展覽雖是個雜拌兒,各種時期、各種不相干的作品擱在一起,倒也能體現美國文化的多樣性。頭一天預展,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松陪著蘇聯總理赫魯曉夫參觀。E女士站在人群里看他們喝著美國的可樂,研究一棟民居的復制品,再細看美國的洗衣機。尼克松朝赫魯曉夫說道,這種一萬四千美元房子,是美國一個普通公民完全可以支付的。赫魯曉夫馬上不客氣地回他,你們美國人覺得蘇聯人會對這些東西就很吃驚嗎……事實是,我們不缺新房子,而在我們的新房子里,所有的這些設備都有。(他的話立刻被在場的美國三個電視臺播放給全美國。)尼克松見話不投機,就很機智地轉移話題說:“你不覺得我們來談談洗衣服的機器,不比談論戰爭的機器,比如火箭什么的更好嗎?這才是你們想要做的競爭吧,對不對?”E女士等在人堆里,特別期待著要看那兩位重要人物進入藝術展區后會有什么反應。結果,她吃驚地看到,在記者簇擁下,尼克松帶著赫魯曉夫目不斜視,直穿過藝術展區,那塊區域對于他們只是一條通道而已。
不過蘇聯民眾對于藝術的態度沒有讓E女士失望。第二天展覽對公眾開放時,藝術展區內擠得水泄不通。參觀的人數每天達到兩萬。E女士看到,蘇聯觀眾的反應和美國人差不多,他們喜歡寫實畫家懷斯(Andrew Wyeth)的《兒童醫生》那樣的作品,對于波洛克的抽象“滴畫”感到摸不著頭腦。蘇聯的批評家對于抽象藝術,與美國政治家的立場完全一樣,他們都不喜歡現代藝術。
……
總之,美國政府出面支持藝術,弄成了這副局面,糾結可笑得叫美國人自己都不懂:“它們原本是打算拿來做成反共產主義武器的,卻先在自己國內被攻擊為共產主義的武器。”①Gary O. Larson, The Reluctant Patron-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rts,1943-1965,p.59.就連他們的對頭蘇聯,對此也一樣不懂,E女士在莫斯科看到蘇聯人在報紙上這樣發問:“他們是在害怕,給我們送來了這些抽象畫,這些現代藝術,意味著他們就會歸順我們的共產主義了嗎?”②Lindsay Pollock, The Girl with the Gallery, p.349.

1959年在莫斯科的美國國家展覽中的藝術廳,墻上是波洛克的名為“教堂”的抽象畫
這種現實導致的結果是,由于輿論的壓力,由于美國三權分治政治體系的操作方式,國會對政府機構所花的錢仔細把關檢查,讓美國政府能做的對外文化交流變得及其有限,范圍小到只能派一些少數專家學者出去,做一些小圈子里的交流活動了。國務卿助理Edward W. Barrett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次會議上說,美國在“文化戰爭”中已經輸給了蘇聯。蘇聯僅在一九五○年一年中,送出國的運動員、科學家、作家、藝術家、音樂家、舞蹈者共計有39000人。僅對法國一處,蘇聯在一年中花去的文化外交費用就高達1.5億美元①Edward W. Barrett1951年11月14日在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主辦的會議上的發言,發言稿發表在New York Times,1951/11/15,p.12。。一九五五年,政府專管文化外交的部門American National Theatre and Academy給政府報告中披露的數字是:在兩年時間中,蘇聯用于文化外交的錢超過20億美元,大大超過了美國。而美國政府在一年中的花費只到250萬美元。②Gary O. Larson, The Reluctant Patron-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rts,1943-1965,p.111.

馬瑟韋爾 Elegy to the Spanish Republic
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對國會抵制現代藝術非常憤怒,一方面,政府部門中不斷有人向國會提案,要求改變政策,增加開支,“我們在這個區域內的費用斷不可少過蘇聯,否則我們會把自己的內衣都輸掉的”。③同上,p.112.另一方面的反對力量來自民間,一批支持現代藝術的畫廊主、策展人、評論家,以及他們所支持的藝術家……有上百人之數,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在紐約的首都酒店(Hotel Capital)開了抗議會,反對來自社會上這種反現代藝術的勢力。他們指責說,這些人這樣遏制現代藝術,才真的是共產勢力的典型做法。有三家支持現代藝術的美術館:紐約現代藝術館、溫特尼美術館、波士頓當代藝術學院聯名發表抗議:
我們抗議這種用政治的和道德的手段來壓制現代藝術的做法。這叫人會想到納粹德國壓制現代藝術用的“墮落”“布爾什維克”“反國家”“反德國”等詞;會想到蘇聯壓制現代藝術所用的“形式主義”“資產階級”“主觀性”“無政府”和“反俄國”等詞……我們相信,現在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對于我們時代的藝術客觀、開放的態度,需要的是對于創造力和藝術家真實感受的認可。④Lindsay Pollock, The Girl with the Gallery, p.324.
著名的左翼雜志Partisan Review編輯Dwight Macdonald在文章中批評道:這些玩政治的人“一方面標榜美國的民主,另一方面,他們對藝術的攻擊實際采取的是專制主義做法。當蘇聯以及歐洲大部分國家都在說美國是文化沙漠時,而美國國會的做法卻正好等于去證實這一點”。①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p.257.

波洛克 white light

德庫寧 Painting

羅斯科 No.37/No.19 (Slate Blue and Brown on Plum)
就連桑德斯也在《文化冷戰》一書中嘆道:美國的情況就是這樣尷尬和矛盾,政治家和民眾他們基本沒有時間去跟隨藝術發展的進程,去弄懂藝術進化的內部邏輯。多數人只依照自己的習慣,非常不喜歡現代派而反對它。懂的人卻看出,抽象表現主義體現的是自由的觀念和自由的創作方式,它們代表的自由狀態正可以和蘇聯的現實主義叫板,而且這些正是蘇聯抵制和憎恨的東西啊。

Tom Braden, CIA“陰謀”支持抽象藝術的主要官員
結論
至此,我們已經把美國在那個時期發生的事件基本考察了一遍,終于到達了桑德斯所揭露“陰謀”前:那些“急于要用藝術去向世界展現體現美國偉大和自由的那些高層的決策者,發現他們竟因為國內的反對聲浪而無法公開落實他們的計劃。那么他們該怎么做?他們轉向了CIA。這就有了支持贊賞抽象表現主義和反對抹殺抽象表現主義的一場較量”。②同上。
Tom Braden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操作那件“藝術陰謀”的核心人物。他把事情說得更加明白清楚:“這位國會議員Dondero給我們添了多少麻煩,他不喜歡現代藝術,覺得那是一種贗品,他覺得那是罪過,那是丑惡。他可惡地發起了一場對繪畫的攻擊,他讓整個國會跟著他對我們想做的事——把藝術、樂團、雜志送出國門——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這就是為什么這個事必須悄悄地做;如果這個事不悄悄地做,那么這事在民主投票中肯定會被否決。為了能做成這事,我們只能去秘密進行了。”③同上。
下面節選幾個段落,來自桑德斯一九九五年的一篇文章“現代藝術曾是中情局的‘武器’”④Modern art was CIA ”weapon”-Revealed: how the spy agency used unwitting artists such as Pollock and de Kooning in a Cultural Cold War.By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Saturday 21 October, 1995 BST.,以飺讀者:
現在來看當時的做法,就完全沒什么好奇怪的。中情局這個新機構的成員主要是來自耶魯和哈佛的畢業生,他們不少人平日里就好收藏個藝術或者業馀寫寫小說什么的。由這么一幫人構成的中情局跟受麥卡錫腦控的政治圈子或者胡佛治下的聯邦調查局比,可算是自由的國度了。當時如果有任何一個政府機構能與列寧分子們,托洛斯基分子們,還加上一幫子醉鬼們——那是紐約派的基本構成——一塊兒尋歡作樂,那必定只能是中央情報局。
至今還沒有第一手的證據表明這個聯系(中情局和抽象表現主義)是如何做成的。但是一個當時的官員,Donald Jameson,第一次打破沉默。他說:“沒錯,中情局看出抽象表現主義是一個可以拿來用的機會,是啊,就沖著去了嘛。……我們當時真正做到的是注意到了區別。那區別是,抽象表現主義是那樣一種藝術,它可以把蘇聯的現實主義對比得更做作,更僵硬,更顯出一種固化。而這種對比關系用展覽呈現就一目了然了。”
“我們這樣的理解挺管用的,因為那時莫斯科為了他們的固化的模式,正激烈地排斥任何非寫實的藝術。這一來事情就非常清楚了,他們竭力批判和強烈排斥的事物,就非常值得去支持了,事情就是這樣。”
去靠近他們暗中有了興趣的美國的左翼前衛派,中情局得十分小心,這位贊助者不能叫人給發現。“這方面的動作只能做到兩三成”,Donald Jameson解釋說:“得這么做才成,比如別讓波洛克感到與政府有染,或者是別讓其他的家伙們與中情局有染。總之這事沒法做得公開,因為那些藝術家們對政府絕少尊敬,對中情局一樣也絕少尊敬。如果你不得不利用的人恰好親近的是莫斯科,而不是華盛頓,得,事情只能這么去辦了。”
這就是“長線”(long leash)計劃。中情局落實此計劃的核心機構是“文化自由協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一個由有識之士,作家,歷史學家,詩人,藝術家的大雜拌團隊,一九五○年由中情局創立并領導。這是個先頭部隊,是用文化抵制來自莫斯科和它的西方“跟屁蟲”們的攻擊。這個組織在全盛期,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出版了20多種雜志,包括《邂逅》。
這個機構讓中情局可以來落實他們對抽象表現主義秘不示人的興趣了。那就是巡回展實際是由官方支持著的;對這類美國新繪畫提供正面評論的雜志實際也是官方支持的;沒人,包括藝術家們,能夠聰明到看得出來。
“文化自由協會”在一九五○年代組織了幾次抽象表現主義的巡回展。最重要的一個是“美國新繪畫展”在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之間把歐洲和美國大城市都走到了。另一個有影響的展覽是一九五五年的“現代藝術在美國”,還有一九五二年的“二十世紀的杰作”展。
因為抽象表現主義在運輸和展覽上都很費錢(作品尺度巨大。譯者注),闊佬和美術館都得作為資源動用起來。其中顯著的人是那個納爾遜·洛克菲勒,他母親是紐約現代藝術館的創立者之一。他是這個被他稱為“媽咪的美術館”的負責人,正是抽象表現主義最大的后臺。他的美術館和“文化自由協會”有合約,負責組織策劃這個流派最重要的展覽。
現代藝術館還和中情局通過其他的橋梁有聯系。William Paley,美國CBS廣播公司的總裁,也是中情局的建立者,是現代藝術館的國際展覽部的董事。曾在中情局的前身“決策辦”(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任職的John Hay Whitney擔任國際展覽部的主任。中情局第一任國際事務科(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Division)主任Tom Braden,在一九四九年擔任了現代藝術館的執行秘書長。
現在,Tom Braden八十來歲了,住在弗吉尼亞州,他的住宅里堆滿了抽象表現主義的作品,養著一群體型巨大的哈士奇守衛著。他解釋國際事務科的作用說:“我們要的就是把那些作家、音樂家、藝術家聯合在一起,去展示美國和西方為之努力的自由表達和理性成果,而從不會對人強硬控制說,你必須寫什么,你必須說什么,你必須做什么,你必須畫什么。然而這種強硬的控制卻正是蘇聯的現況。我認為這是中情局中最重要的一個機構,在冷戰期間,它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他確認說,他的機構行動秘密,因為公眾對于前衛派抱有敵意。“那時讓國會同意我們做想要的事——送藝術出國展覽,送交響樂出國演奏,在國外辦雜志——非常困難。這是我們需保密的原因之一。那就得是個秘密。為了鼓勵這種開放,我們不得不保密。”
一九五八年“新美國繪畫”的巡回展,其中包括了波洛克、德庫寧、馬瑟韋爾和其他那些人的作品在巴黎展出。泰特美術館渴想拿到下一個展覽機會,但資金短缺。一天的傍晚時分,一位美國闊佬兼藝術愛好者Julius Fleischmann帶著現金走進泰特美術館,于是展覽下一站就巡回到倫敦舉辦了。Julius Fleischmann帶去的錢,可不是他自己的,是CIA的。錢的名目來自一個叫遠野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的機構,Fleischmann是基金會的主席。這位闊佬的慈悲范圍可大不過CIA去,這基金會其實是CIA經費出入的一個秘密導管。
泰特美術館也好,公眾或者藝術家們也好,對此都不知就里,只見到展覽如期在倫敦展出了,實際花的是美國納稅人的錢,用于冷戰時期的宣傳。前CIA官員Tom Braden這樣描述遠野基金會這種管道設立的方式:“我們在紐約直接去找那種人人知道的闊佬,朝他說:‘咱們來建一個基金會吧。’跟著告訴他底細,并叫他發誓保密,他總是會說:‘行,我干。’然后去印出有他名字和基金會稱號的信箋,這種基金會就建成了。這個事做起來容易得很。”
如果沒有這個資助者存在,抽象表現主義會成為戰后美國本土的藝術運動嗎?也許會的。換句話說,當你在看抽象表現主義繪畫時,你被告知你其實是被CIA愚弄了,這話亦是不對的。
以上的史料研究作為我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美國為何要把一件“陽謀”做成“陰謀”。
希望這些史料能夠補充了河清先生“藝術陰謀”論中缺失的歷史實相。有了這個補充,會比較容易看出,由美國政府交給中情局去操作的這個“陰謀”,只出現在從國會到平民不接受抽象畫,并憎惡那些持左翼立場的抽象畫家,還要加上冷戰……那樣一段歷史時期。當歷史發展到美國的男女老少,從政治家到販夫走卒,都完全接受了抽象畫,并享受起它所點綴的現代環境,以及它給美國帶來的文化地位時;當柏林墻倒塌,冷戰陣營消失時;當早年忍饑挨餓的藝術家們一個個陸續轉變成腦滿腸肥的資產者時,需要中情局繼續“陰謀”操作的歷史條件就徹底消失了。事實上到了七十年代,中情局的“陰謀”就停止了。有了認識上的這樣一步,我們會比較容易來解決河清先生指說的“陰謀論”擴大部分——美國陰謀操縱了當代藝術。和上述部分一樣,河清先生似乎犯了一次同樣錯誤:缺失歷史。這將是隨后章節所要研究的內容了。
現場


“王冬齡:竹徑”展覽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