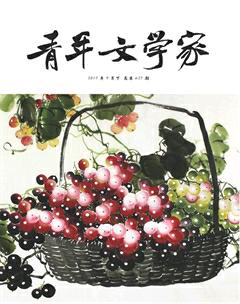論薩娜《多布庫爾河》敘事特色
摘 要:薩娜是達斡爾族代表性作家之一,在文學創作上成績突出,最近出版長篇小說《多布庫爾河》是其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展現了鄂倫春民族的生活畫卷以及在艱苦的生存條件下頑強生活、生生不息的精神世界。本文從獨特的敘述視角和重復的敘述結構上分析這部作品的敘述特色。
關鍵詞:薩娜;《多布庫爾河》;敘事特色
作者簡介:潘多,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2015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少數民族文學綜合。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7-0-02
薩娜是達斡爾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在眾多國內文學期刊上發表過作品,中短篇小說成績突出。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說《有關薩滿的傳說與紀實》《阿西卡》《一個感情理想主義者的死亡》等,短篇小說《結局》《幻想的河流》等。中短篇小說集《你的臉上又把刀》曾獲第八屆全國少數民族創作駿馬獎,有著不俗是創作實力。
《多布庫爾河》是薩娜最新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一個關于生死、關于信仰、關于選擇的故事。講述了多布庫爾河流域的鄂倫春人在惡劣環境下的游牧生活,展現了鄂倫春這個古老民族的日常生活及精神信仰,以及他們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由傳統走向現代舉步維艱的心路歷程。
一、獨特敘述視角展現鄂倫春風俗畫卷
《多布庫爾河》主要采用內聚焦型視角,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進行敘述。“我”(主人公古迪婭)是故事的同敘述者,既講述故事,同時也是參與故事的人物。文本中的主要故事的發生與展開都是由“我”來敘述。
“我”還沒有出生就可以感知世界,“我”的靈魂可以看見家人所發生的一切,失去父親后,母親艱難的帶著“我”的哥哥和姐姐一起生活,在寒冬里的大興安嶺深處,懷著身孕也不得不出門打獵囤積食物,“我”就降生在白雪皚皚的大地上。故事伴隨著“我”的成長展開,而后在“我”身邊發生的事情,家人的不斷意外去世的悲痛心理和在現代文明沖擊下的鄂倫春人的心路歷程都由“我”來觀察和展現。
通常情況下,“我”應該屬于第一人稱限制敘事方式,“我”作為故事的敘述者,只能講述“我”在場時的所見、所聞、所感。敘述內容僅局限在“我”的視野范圍之內,而未知故事要通過第三者提供后,“我”才能進行轉述,此外,敘事者“我”也不能進入其他人物的內心世界。而《多布庫爾河》中,文本雖以“我”的口吻展開敘述,貌似是第一人稱有限敘事視角,實則卻出現了全知全能視角下的敘述內容,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出現了越界的情形。例如文本中“我”叔叔愛慕母親的感情描寫和周圍人的心理描寫,都不是一個年幼的“我”所能觀察的事情。還有對于打獵場景的詳細描述,也并不是“我”親身經歷的場景,而這些都從一個非聚焦型視角進行了描寫,在這里敘述者的視角大于第一人稱的視角。人物突破單一的聚焦方式進入更廣闊的視野,向讀者提供超過敘述者或人物在某一位置上所了解的信息。
對于“視角越界”的界定,熱奈特在《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中指出:由于聚焦的每一類型都一一對應著敘述者所能感知到的信息數量,敘事聚焦類型的選擇,也就意味著敘事角度和信息數量的選擇,當敘述的內容超出了敘事者所感知的信息數量時,便出現了“視角越界”的現象。
“視角越界”的現象在薩娜的小說中經常出現,尤其是在民族題材的展現上。就《多布庫爾河》而言,這樣的敘述方式可以提升小說的表達空間,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呈現。
第一人稱內聚焦型視角是從人物的角度展現其所見所聞,在創作上可以揚長避短,多敘述人物所熟悉的環境,對不熟悉的東西保持沉默。在閱讀中縮短了人物與讀者的距離,使讀者獲得一種親切感,還能充分敞開人物的內心世界,不僅有利于展示小說中視角人物的心理與情緒內容,而且也能真切地反映出敘述者的心靈、情緒體驗。作者采用第一人稱內聚焦型視角,首先是民族身份認同的需要,在少數民族語境下,“我”是一個鄂倫春女孩,從“我”的視角看到的民族生活,是從民族內部的眼光來觀察生活,能更好地從心理上把握民族情感,更具有民族認同感。非聚焦型的視角則有可能會從民族外部,他者的眼光來描述民族生活,很難從細微處把握好民族特征。其次是創作內容的需要,鄂倫春族信仰薩滿,認為萬物有靈,在他們的森林世界,動物、植物都是有靈魂的。“我”是一個具有靈性的人,可以看到一些幻象,這些在他人的眼里可能是瘋魔,但對于鄂倫春人來說這些都是真實的存在。由“我”來作為敘述者,能更好地表現“我”所看到的靈性的世界。在文本中,薩滿烏恰奶奶具有能夠看透生死、預知未來、治愈疾的神性靈力,小說借助于“我”的第一人稱敘述視角,以一個同樣具有靈性的鄂倫春族少女的眼睛來直觀感受烏恰薩滿舍生取義、救死扶傷的傳奇故事。這樣的敘述視角帶給讀者親身經歷的真實感,拉近了讀者與神秘的薩滿儀式之間的距離。
但是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是限制性的視角,敘述者的所指不能超出作為敘述者的人物所感知的范圍,這樣就限制了作者的敘述空間。在文本中,在“我”還是女童的時候,并不參與打獵活動,鄂倫春族的狩獵文化就不能直觀的呈現。所以為了提升小說的表達空間,作者將非聚焦型視角交叉、滲透入第一人稱內聚焦型視角,在一些民族傳統文化上采用非聚焦型視角敘述。例如小說文本中三叔獵到一只熊后,“三叔垂下槍,肅穆地站在熊的尸體前,像對待去世的長輩那樣悲傷地說:我不是故意殺了你,而是誤殺呀……三叔獵到了熊,所以抬著獵物的人才佯裝哭泣,以示敬畏。快走到烏力愣的營地時,他們又學著烏鴉發出嘎嘎的叫聲,讓熊的靈魂知道,不是人傷害了它,而是烏鴉打它的主意……族人們在內心深處認為,熊是自己的祖先,是雅亞祖父。人是由熊變來的。”[1]作者通過非聚焦型視角為我們展現了鄂倫春族狩獵習俗。
《多布庫爾河》獨特的敘述視角在于第一人稱內聚焦型視角與非聚焦型視角相互結合、相互補充,達到人物內心世界表達與民族文化呈現完美融合,為我們展現了豐富立體的鄂倫春生活。endprint
二、重復敘事結構下鄂倫春人生死觀念
“重復敘事”,是指敘事者對發生過一次的事件進行多次講述。“重復”不是單純的情節敘述,也并非對情節進行補充和說明。重復的目的,是為了取得特殊的敘述效果,使敘述變得無限可能。具體而言,重復敘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宏觀的重復,如主題、結構的重復,另一類是微觀、細節的重復,如具體情節、場景的重復。“重復”由于具有獨特的藝術效果,也在《多布庫爾河》中得到運用,在這部小說中主要是主題重復,即同性質事件在文本中反復出現。具體的來講是死亡主題的重復,由“我”周圍人不斷死亡、新生伴隨的一系列事情構建鄂倫春族的生死觀念。
鄂倫春族生活在環境惡劣的大興安嶺林區,過去由于生存環境的險惡,人口死亡率非常高。在各種危險的直逼下,死亡是鄂倫春人不得不面對的主題,在一次次生死的沖擊下,鄂倫春人對生死觀念形成了獨特的認識。生與死是循環的,在一個生命獲得新生時,也會有另一個生命的結束。作者在這樣的生死觀念下采用重復敘事結構,不僅展現了這種萬物有靈的循環觀念,并且展現了鄂倫春族在死亡的威脅下,仍然樂觀向上、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我”還沒有出生時,父親在一次狩獵當中跌下山崖不幸去世,母親帶著年幼的哥哥各羅布姐姐蘇妮婭艱難生活。“我”出生后,我們一家四口生活漸漸好轉,隨著年紀的增長,哥哥各羅布慢慢可以承擔其父親的責任,外出打獵解決一家人的生計問題。然后好景不長,也是在一次打獵的時候,各羅布被好朋友庫列失手打死,庫列為了賠罪,代替各羅布承擔兒子的責任,進入到“我”的家庭。此時的蘇妮婭到了嫁娶的年紀,母親將蘇妮婭嫁給庫列,“我”家還是四口人。婚后蘇妮婭和庫列生了一雙兒女,也是在一次狩獵過后,庫列感染惡疾,不治而亡,蘇妮婭經受不住打擊也一同死去。留下一雙兒女由母親撫養,“我”家仍舊是四口人。不斷重復的死亡,將“我”家所面臨的生活一步步推向困境,但只要有生的希望,就不會向死亡妥協。
新生與死亡是平衡關系,預示著自然界生死循環的能量守則。鄂倫春人在險惡的環境下生活,依然生生不息、頑強生存,這是對生命的尊重。死亡是無可抗拒的,母親面對著死亡之神,并沒有畏懼,而是向它發起挑戰,要讓死去的人重新活過來。在兒子各羅布的身上,看到丈夫的影子;在各羅布和蘇妮婭這一雙兒女死去后,母親把蘇妮婭與庫列所生的兒子和女兒,分別命名“各羅布”和“蘇妮婭”。讓死去的人重新獲得新生,這既是鄂倫春人信仰中的生死觀念,也是一個普通生命個體所做出的、也是惟一能夠做出的反抗死亡的方式。
除此之外,還有薩滿烏恰奶奶為了救治得了破傷風的查魯,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在最后一次法事中,烏恰奶奶油盡燈枯,死亡邊緣的查魯重獲新生。“他從那里回來,她就回到那里”,這也是生與死循環的結構。面對生命的各種挑戰,鄂倫春人以積極的心態頑強生存,在死亡中尋找生命的曙光,在生與死不斷地重復下,尋求生命的意義。
“重復”是敘事作品中一種常見的頻率形式,重復的妙用,猶如音樂中的重奏手法,周而復始,構成藝術作品的循環效果,扣人心弦。《多布庫爾河》通過對敘事頻率進行藝術處理,使文本的敘述出現了重復的特點,小說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對生死主題進行強化和凸顯,啟迪了讀者對文本和文本意義展開思考,拓展了小說的藝術空間。
《多布庫爾河》是薩娜代表性的民族題材作品,小說世界里展現了鄂倫春這個人口較少民族的生產活動、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倫理觀念、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等。傳統文化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日漸消失,應該引起人們的反思,在我們去其糟粕時,是否也將精華一并拋棄,鄂倫春人萬物有靈、生死循環的觀念,讓我們看到了對生命應有的尊重和敬畏,是否對現代社會也具有借鑒意義。《多布庫爾河》敘事方式別具一格,獨具少數民族文化特色,有較強藝術魅力,還有待于更深的挖掘。
注釋:
[1]薩娜.多布庫爾河[M].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7.
參考文獻:
[1]薩娜.多布庫爾河[M].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7月.
[2]胡亞敏.敘事學[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
[3]曾斌.“我”:作為集體的對象化敘述——以少數民族小說第一人稱敘述者研究[J].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