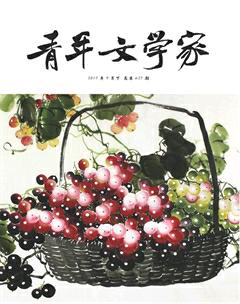接受美學下的《洛麗塔》翻譯研究
基金項目:2017年度湖南科技學院科學研究項目:譯介操縱與作品形象變遷——《洛麗塔》在中國的譯介研究(項目編號:17XKY023)。
摘 要:小說《洛麗塔》自從出世以來,其特殊的風格與矛盾的主題深深地吸引了人們。而在我國,小說《洛麗塔》則有多個譯本,不同的譯本自身,構建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同的文本。而這些文本,在接受美學的視域下,又展開著不同的期待視域與文本的召喚結構。本文試圖在對接受美學的簡要說明的基礎上,對小說《洛麗塔》開篇的名句,進行一個接受美學視域下的翻譯研究,以說明接受美學對于翻譯的巨大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接受美學;洛麗塔;文本的召喚結構
作者簡介:李靚(1982.7-),女,漢族,湖南永州市人,湖南科技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商務英語教學、英美文學。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7--02
一、接受美學的內涵
俄裔美國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小說《洛麗塔》(Lolita)以英文書寫,并于1955年出版于巴黎。該書享有世界級的聲譽,因為其獨特且創新的視角和極具矛盾性的話題——一名中年的男性,亨伯特(Humbert)與一位西班牙發音為Lolita的十二歲未成年少女的禁忌的,亂倫性質的,帶有情色意味的愛情故事。在幾十年之后,《洛麗塔》一書已經成為了影響世界的書籍。時代周刊將其列入從1923年到2005年中,以英文書寫的一百本偉大小說之中。
而關于該書的中譯本,首先第一個中譯本于1964年誕生于臺灣,隨著該書的逐漸升溫,越來越多的中譯本開始出現,至今為止已經有了二十多個中譯本。在國內,目前的中譯本有十余種,其中上海譯文出版社所出的王萬的全譯本,江蘇文藝出版社所出的于曉丹的譯本較為人熟知。不同的翻譯之中,滲透著譯者個人對于《洛麗塔》的理解,同時也顯現出完全不同的風格。而這與自1960年代所興起的接受美學下的美學理論,翻譯理念又有著深刻的聯系。
接受美學(Reception-Aesthetic)是一種文學批評理論,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理論,接受美學融入了后現代的思潮,其對于文學的批判不同于之前的文學理論。
在這之前,文學批評的視域往往限定于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關系,例如當人們試圖探究《洛麗塔》一書時,人們更為注重的是,作為作者的納博科夫的生平經歷以及人生思想,并試圖研究他對于自己的人生以及世界的思考、感受是如何融入在作品之中的。例如說,納博科夫有著不幸而憂傷的童年回憶,其對于家族的不幸的創傷就借由主人公亨伯特美好初戀的死亡表現了出來。相反的是,接受美學更試圖探究的是文本與讀者的關系,接受美學認為:文本的意義并不是在作者對于文本的完成中被完成的,相反,文本是在被眾多的讀者所閱讀的過程中,讀者自身參與進了文本的理解,從而構建起了讀者和作品之間的橋梁。這就要求作者在書寫的過程中,考慮到讀者的“期待視域”,作品中應當含有許多未定的向度與留白的空間。同樣的,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自身的翻譯作品也并非是在翻譯中被完成的,而是在眾多的讀者的共同地參與下,被不斷的循環地構建所完成的。所以,對于本文來說,在接受美學的視域下,重新地對特定的中譯本的翻譯作相關的探討,是富有意義的。
二、“期待視域”與“文本的召喚結構”
事實上,接受美學的興起,與后現代思潮的興起有著離不開的關系。其中,后現代思潮中最為重要的大師——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其的譜系學和知識考古學,將歷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極具創造力的發展出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論。該方法論所強調的是,去中心化,去結構化,話語體系的構建等要素。而從這一視角來看接受美學的話,那么毫無疑問的是,接受美學也接受了相當的后現代的思潮的影響并在美學的領域,發展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創新。而在這之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姚斯(Hans Robert J Auss)所提出的期待視域理論與伊瑟爾的文本召喚理論了。下文將簡要介紹這兩個理論。
正如上文所說,接受美學反對作者-文本的中心視角,強調讀者-文本的視角,試圖使得作者、文本、讀者能夠在時間的循環往復之中,不斷的解讀出新的文本的意義。對此,姚斯提出了著名的期待視域理論,他說道:“……他喚醒以往閱讀的記憶,讀者被帶入了一種特定的感情態度之中……于是這種期待便在閱讀過程中根據這類文本的流派和風格的特殊規矩則被完整地保持下去。[1]”于是,讀者,而非作者成為了文本的審判者。閱讀的過程變成了讀者的期待視域不斷地展開的過程,在同一類的文本過程之中,讀者不斷地展開的期待,期待的視域被不斷地放大,而只有當文本的脈絡與讀者的期待視域相一致的時候,文本才會獲得讀者的優秀評價。反之,文本的意義便無法被彰顯出來了。此時,讀者需要對其自身的期待視域與閱讀經驗進行再調整,方能夠使得作品自身被顯現出來。那么,文本的價值就以這種讀者的期待視域作為評價的標準了。姚斯認為,第一讀者是如何評價作品的,恰恰成為了作品是如何的,作品具備什么意義的基準。這一理論使得閱讀過程不再是單純的閱讀,而是一種立體式的,螺旋式的互動。
“文本的召喚結構”則與姚斯的期待視域有些許的不同。姚斯的期待視域更為強調的是,讀者的期待與文本自身視域的展開的一致性。但是,伊瑟爾則在這一基礎上,提出了更進一步的理論。首先,他認為,文學文本是一種讀者與作品之間的動態的交流形式,“文學作品是一種交流形式[2]”,在文學作品中,作品存在著許多空白點與不確定的區域,正是通過這些區域與空白點,讀者與作品建立起了橋梁,也正是通過這兩點,讀者與文學作品得以進行交流。在這一過程中,隨著讀者的期待視域的不斷的展開,作品的空白點與不確定區域也被不斷的進行著填充。換言之說,在文學作品中,存在著一種召喚結構,這種召喚結構令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去試圖填充,嘗試繼續閱讀,嘗試與作品交流。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隨著文本的召喚結構的不斷地填充與重新地被填充,讀者的期待視域也在不斷的被打破與不斷地重建之中。于是,讀者的期待視域與文本的召喚結構就形成了填充——打破——填充這一循環往復的構建過程。而這一過程,即是“文本的召喚結構”。這一理論的要處在于,將文本從作者的生平與思想中解脫了出來,將文本納入到讀者的視域之下,將文本的審視權交由給了讀者。在這一過程中,作品自身的價值,僅僅與作品自身有關,而與作品之外的無關。endprint
而在對接受美學的兩大理論作了簡要介紹之后,下文將以不同中譯本中的相關例子來說明接受美學對于《洛麗塔》的翻譯的指導意義。
三、《洛麗塔》中的具體例子
譯者的視野,往往決定了翻譯的整體基調與風格。在閱讀翻譯作品的過程中,我們不僅僅是在閱讀原文本,更是在閱讀譯者的文學作品。換句話說,我們通過譯者的濾鏡來看文本。所以,這一濾鏡自身的視域,這一濾鏡自身對于文本的詮釋,也影響到了讀者對于文本的詮釋。
由于小說《洛麗塔》自身的文學價值,加之庫布里克為之拍攝的,令人叫絕的電影。《洛麗塔》的開篇,已經成為了這部小說的象征。但,正是在開篇的這一段名言的翻譯上,中譯本中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趣味。納博科夫在開篇中寫道:“Lolita, light of my life, fire of my loins. My sin, my soul. Lo-lee-ta: the tip of the tongue taking a trip of three steps down the palate to tap, at three, on the teeth. Lo. Lee . Ta[3].”這一段文學以其邪惡而又不失文學性的深遠意蘊,挑逗性而又富有某種愛情的韻律為眾人所熟知。
而對此,于曉丹的翻譯為:“洛麗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惡,我的靈魂,洛—麗—塔,舌尖向上,分三步,從上顎往下輕輕落到牙齒上,到第三次再輕輕貼到牙齒上,洛.麗.塔”王萬的翻譯則為,“洛麗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時也是我的罪惡,我的靈魂。洛—麗—塔;舌尖得由上顎向下移動三次,到第三次再輕輕貼在牙齒上,洛—麗—塔。”
眾所皆知,在弗洛伊德的學說中,嬰兒的口腔期往往與性聯系在一起。在原文中,對于口腔的觸碰,毫無疑問地暗示了羅伯特對于洛麗塔的性的方面的欲望。并且,作者還采取排比式的短語的形式,更顯得富有挑逗性了。同時,“Loins”一詞的原意指向的是腰間的浴火,但是在這兩者的翻譯之中,一者翻譯為欲念之火,一者翻譯為欲望之火,可以看到,盡管其中依舊具備性方面的暗示,但是相對于原文而言,這一翻譯本身極度的減輕了性方面的提示。本文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的讀者并不如巴黎的讀者那么的開放,中西方文化在此有一個視域上的區分,東方的保守型的意識形態,使得譯者在翻譯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減少了這種開放的性暗示。同時,富有經驗的讀者一讀便知,原文是以某種迷醉的,輕佻的,輕柔的語調進行閱讀的。而從這兩個譯本上看,于曉丹的譯本在視域上與原文進行了融合,回應了翻譯過程中,原文所特意留出的期待視域與召喚結構,以同樣的短文的形式,盡可能的還原了隱藏于語詞背后的這一視域。而王萬的譯本,則稍弱一些,“同時”一詞透出了譯者更著意強調于“罪惡”之上,并落腳到了“靈魂”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譯本往往帶有不同的風格。譯者自身的期待視域與其自身如何回應文本造就了翻譯上的些微的差別。而這些些微的差別,在讀者的閱讀的過程中,又造就了新的期待視域與召喚結構。例如說,讀者假若讀的是于曉丹的譯本,那么讀者就會更加注意到這背后所隱藏的情色意蘊,并隨著這一向度而展開期待,并借由這一向度而進行文本的填充。但讀者倘若閱讀的是王萬的譯本,那么讀者更會注意到羅伯特內心的那份不舍的糾葛與罪惡,并借此展開一個新的期待視域。所以,盡管是相同的文字,但是不同的譯者,由于有著不同的視野,隨之而有著不同的期待視域,而不同的期待視域,則召喚著不同的文本結構。而這一意向,借由著譯者自身的意向,借由著譯者自身的期待領域,借由著譯者自身對于文本的填充與再填充的循環往復傳遞給了讀者群。不知不覺中,讀者自身又再一次的編制出了個人自身的獨特的期待視域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文本的召喚結構”的填充與回應。所以,可以看到的是,譯本的翻譯,在接受美學的視域下,不僅僅只是翻譯,更是一次再創作。而讀者的閱讀,則是在這一基礎上的與文本所進行的溝通與創造。
注釋:
[1]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p289.
[2]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p294.
[3]Nabokov,V.Lolit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2000,P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