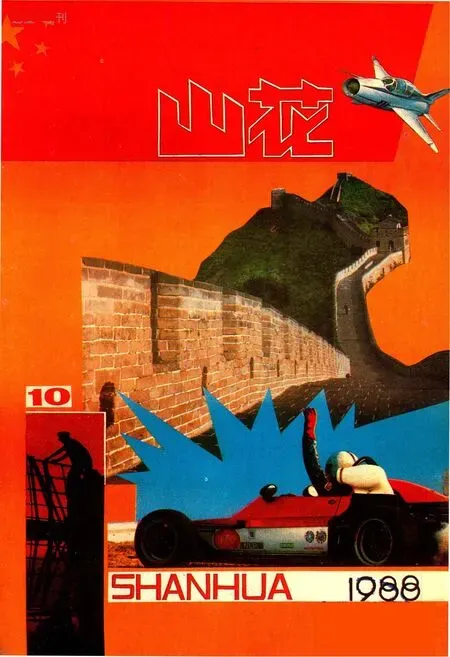東西方神話的歷史文化揭秘
李劼
小序
若要檢索世界各地人類文化的諸多緣起,從各個族群的神話入手也許是一條比較簡易的途徑。當法國人施特勞斯從南美部落里探究所謂的原始思維或者說野性思維的時候,不知他有沒有回首過當年高盧人在與羅馬人打仗的年代里遵循的是什么樣的思維方式。當另一個法國人福柯以危言聳聽的方式從性交與瘋顛中尋找歷史蹤跡的時候,不知他是否意識到那其實是一種置身于瘋狂的吸毒狀態和群交派對的自我夸張。然而,人類太初的種種神話,看上去似乎荒誕不經,實際上卻并非夸張,而是人類初民之于生命與宇宙的朦朧意識。那樣的意識之朦朧,猶如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定律,在難以定位的觀察對象面前,一頭霧水。盡管神話的不確定性通常是因為口耳相傳的緣故,但即便是經由文字而得以明確的神話故事,也依然處在眾說紛紜的模糊形態里。所幸的是,美國學者雷蒙德·范·奧弗編輯了一部《太陽之歌——世界各地創世神話》,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照譜系——雖然僅止于此書是遠遠不夠的,世人還需要閱讀大量的神話文本,才能一覽東西方神話諸山諸景。
一、華夏神話的人文品質與歷史奧秘
華夏民族的神話記載,主要是見諸《山海經》。《山海經》最早有圖,稱作《山海經圖》。據說至魏晉,圖失經存。有關《山海經》的成書,眾說不一。有說是大禹和伯益所作,有說是楚人所作,司馬遷說:“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有清代學者畢沅經過考證認定,《山海經》“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漢,明于晉”。亦即,該典成書有個歷史過程,從大禹時代一直到魏晉。作于禹益,應該是指此書作于大禹和伯益時代,并非指由他們君臣二人所作。從《山海經》記載的大禹治水故事看來,此說靠譜。君臣協力治水,在當時也算是有口皆碑。只是司馬遷在他們身上撒了個謊,《史記·夏本紀》有說:“帝禹東迅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因為按照《竹書紀年》記載,禹死后由禹之子啟繼位,而益因此與啟發生爭執,帝啟六年,被啟所殺。《晉書》引用《竹書紀年》有道是:“益干啟位,啟殺之。”《史通》也曾引《竹書紀年》說過:“益為后啟所誅”。可見,司馬遷太過醉心于他所編造的禪讓故事了。要不是有《竹書紀年》作參照,禪讓便成了鐵板釘釘的歷史定論。而事實上,炎黃之戰之后的黃帝時代,亦即所謂的堯舜禹湯時代,每一次的帝位更迭都不是和平禪讓的,而是血腥爭奪的結果。本筆在后文將繼續指證,司馬遷所杜撰的禪讓故事是如何的虛假。
《山海經》記載的神話當中,對后世影響比較重大的有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刑天舞戚,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等,精彩紛呈。然而,卻獨獨遺漏了華夏先民最為重要的創世神話,盤古開天辟地。盤古神話最早是由南方少數民族口耳相傳的。盤,有蛋殼的涵義;古,通固。早先的傳說里有盤瓠說,也有葫蘆說。盤古神話最早見諸漢語文字,據說是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魏晉時代的《魏大饗記碑》:“起尚盤古,羅天□焉。”八個字里還殘缺了一個。宋朝的《太平御覽》引述《風俗通義》如次:“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故天去地九萬里。”
將混沌的天地比作雞蛋的想象,與印度神話十分相似。據《吠陀經》記載,印度的創世神話,也是如此。一個金蛋漂在宇宙之水里,一千年之后,生出宇宙之主,當然不叫盤古,而是叫做:原人。盤古隨著天地而生長,原人的靈魂與宇宙精神同在。這兩個神話雖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其意蘊卻極其相近:宇宙是混沌的,最初的人類是從混沌中誕生的。更為重要的是,兩者都將宇宙比作蛋狀的,不管是雞蛋還是金蛋。在東西方諸多創世神話里,持宇宙蛋狀說的,大概也就數華夏民族和印度民族了。
但并非華夏民族中的所有族裔,全都持這樣的宇宙觀。按照張遠山《伏羲之道》的考證,華夏民族當中,惟最古老的先祖,伏羲族,是以渾天說解釋天地宇宙的。后來在炎黃之戰中打敗了伏羲族的黃帝族,其宇宙觀并非是雞蛋狀的渾天說,而是天圓地方的蓋天說。從盤古神話所持的雞蛋狀的渾天說來看,該神話是伏羲族被黃帝族打敗并遷徒到南方后,得以在南方少數民族當中流傳之說,是完全成立的。換句話說,盤古神話雖然來自南方少數民族的口耳相傳,但最初的發軔,卻源自伏羲農耕民族。必須留意的是,應該就是因為沒有被黃帝族改造過的緣故,盤古神話得以保留了蛋狀創世的渾天說。
女媧補天的神話,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淮南子·覽冥訓》曰:“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此處的斷鰲足以立四極,便是天圓地方的蓋天說,用鰲足作四柱以撐天地。漢朝以后,唐人的《三皇本紀》,宋人的《路史》皆承此說。但詭異的是,在《山海經》里的女媧神話,卻并不見補天事跡。《山海經·卷之十六》有言:“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也。人面蛇身,一日之中七十變。” 《山海經·大荒西經》又說:“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能夠從中讀出的歷史信息只是,古神女而帝者也。亦即,有神力的女媧,曾是一位政治領袖。至于蛇身之類,屈原《天問》有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東漢王逸注道:“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所謂傳言,顯然來自《山海經》。按張遠山《伏羲之道》所言,《山海經》將女媧描繪成人首蛇身,可能跟伏羲族畫在山西陶寺肥遺盤上的肥遺紋有關。所謂“伏羲鱗身,女媧蛇軀”是也。亦即《帝王世紀》中所說的,“庖犧氏人首蛇身,尾交首上”。然而,竊以為,《山海經》所說的女媧人頭蛇身,未必含有肥遺紋的天文歷法涵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從肥遺紋到女媧的蛇身造型,乃是黃帝族之于伏羲文化的誤讀,以為伏羲族所尊崇的女媧,不過蛇神而已。這樣的誤讀,多少帶有黃帝族之于伏羲族的偏見。
然而,有趣的是,那樣的偏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漸漸沖淡了。及至漢朝,有了《淮南子》里的補天事跡,又有了《風俗通義》里的摶土造人。順便說一句,不管摶土造人的傳說真假如何,倒是與《圣經·舊約》創世故事里的上帝造亞當之說不謀而合,仿佛人類真的是從泥土中生出來的。漢朝似乎是個為女媧形象全面正名全面重塑的年代,不僅有了補天、造人事跡,而且還在許慎的《說文解字》里獲得了高度評價:“媧,古之神圣女,化萬物者也。”并且又在《淮南子·說林訓》里與黃帝扯到一起:“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雙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淮南子》這么扯的時候絕對想不到,后世的唐人會揭開女媧的身世之謎:女媧并非黃帝時人,而是伏羲族人。司馬貞《史記·補天皇本紀》說:“女媧氏風姓,有神圣之德。”盧仝的《與馬異結交》詩云:“女媧本是伏羲婦。”五代的馬縞在《中華古今注》則認定:“女媧,伏羲妹。”清人《漢書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譜》指出:“華胥生男為伏羲,女子為女媧。”西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很正式地將女媧歸入伏羲族,與黃帝毫無干系。
可見,歷史上的女媧可能是伏羲族的一位女首領。倘若按《帝王世紀》的羅列,女媧乃是繼伏羲之后的部落領袖。倘若按照張遠山《伏羲之道》考證,伏羲只是一個族名并非人名,那么女媧就應該是伏羲族最早的領袖人物,因此會被《山海經》稱之為“古神女而帝者”。而之所以會生發出女媧補天、造人之類的創世神話,就因為女媧是華夏民族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族群領袖。倘若說,盤古神話很難找到對應的歷史痕跡的話,那么女媧神話卻有著鑿鑿可據的歷史線索。女媧的地位,大致相當于希伯來人《創世紀》里的耶和華,一如盤古形象有如印度神話里的梵天。
似乎是為了強調女媧的這種先祖意味,唐人李冗在《獨異志》卷下里描繪說:“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昆侖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昆侖山,兄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于是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為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不知李冗怎么會編出這樣的故事,因為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本古代的雙尊創世神話,伊奘諾尊和伊奘冉尊兄妹。唐朝時,多與日本人交流,且不說李冗的故事是否受人影響,即便是獨創,也有驚人相似之處。當然,相比之下,日本的雙尊神話更加完整豐滿;兄妹之間的性愛也更加直接,沒有唐人筆下的羞羞答答,而是愛得歡快不已,并且最后還生出八子,成為日本八洲。盡管唐朝在男女性事上是個非常開放的朝代,但比起日本神話的坦蕩如砥,還是有所遮掩。更為重要的是,女性在神話里的地位全然是被動的。須知,在日本雙尊神話里,做妹妹的可是一點不掩飾做愛瞬間所感受到的愛的歡快。不僅如此,女性在日本歷史上的地位,可能只有伏羲族的女媧時代可相媲美。不僅天皇家族的直系祖先天照大神是女性,而且此后歷代天皇,都是女性。直至公元八世紀,天皇才改由男性出任。公元十世紀左右,乃是日本文化最為輝煌的平安時代。其時,日本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經典《源氏物語》出自女性手筆;另一部經典《竹取物語》的主角,又是女性。日本女性的地位,直到十六世紀的戰國幕府時代才下滑至男性附屬。而那樣的男尊女卑,在華夏歷史上,早在商周之交之后就已經開始了。至于究竟是男尊女卑,還是黃帝族之于伏羲文化的誤讀,導致了女媧形象在《山海經》里被蛇身化,如今很難確然。能夠確定的只是,女媧是伏羲初民的首領,《山海經》為黃帝族后人所寫。男尊女卑,始于黃帝族位于西岐的姬氏家族。
作為女性在伏羲時代并非卑微的另一個佐證,便是精衛神話。《山海經·北山經》云:“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此中那句“溺而不返,故為精衛”的注解,可參見東晉葛洪《抱樸子·內篇》卷二:“精衛填海,交讓遞生。”及至南朝的《述異記》是這么說的:“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要而言之,女娃死后,復生為鳥,名精衛。
這是一個非常清麗的神話故事。女娃死后化作精衛鳥的凄美,不下于日本平安時代《竹取物語》里的輝耀姬。同樣是少女形象,女娃是死不瞑目,因而化作飛鳥銜木填海;輝耀姬是生不堪重負,屢屢為濁世濁男濁人濁物所擾所困,終歸天庭。由此可見,不僅華夏神話與日本神話頗有相通之處,華夏民族的伏羲時代與日本歷史上的平安時代,也有相似的審美品味。少女的清純,有如晨曦,照亮濁世,同時輝耀在整個族群的集體無意識深處。難怪后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都會情不自禁地寫下如此動容的詩句:“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詩中的刑天,是《山海經》的另一則伏羲族神話的主角。《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倘若說,《山海經》的女媧蛇身造型尚有出處可言,那么對刑天的鄙薄可謂一目了然。刑天被描繪成了一介莽夫,并且不自量力地與黃帝爭神,從而被帝斷首,死了還不買賬,操干戚以舞。然而,事實上,刑天并非如此草莽,而是炎帝文臣,擅長音樂,作有詩曲。炎帝戰敗之后始終相隨左右。后因蚩尤起兵復仇,被黃帝斬首身首異處,刑天才氣憤難平地找黃帝單挑,死在黃帝劍下。刑天其實是書生型的壯士,硬生生地被黃帝族所寫的《山海經》歪曲為莽夫。但即便如此,陶淵明照樣為之唱贊不已,可見彼此間的惺惺相惜。
從伏羲族的神話人物可知,該族不僅是華夏民族創世意義上的先祖,而且還是華夏民族精神上的元氣所在,或者說民族靈魂的本真之源。盤古、伏羲、女媧,從根本上架構了華夏民族,顯示了其恢宏和蒼茫;精衛、刑天從精氣上充實了華夏民族,使之具有人性的尊嚴和屬人的高貴。一個民族可以沒有皇帝,沒有軍隊,但不能沒有精衛沒有刑天。事實上,精衛始終不歿,其化身綿綿不斷,唐宋年間有才情并茂的魚玄機,遭受朱熹迫害而堅貞不屈的嚴蕊;明末清初見柳如是,清末民初現秋瑾,此后更有林昭,張志新。刑天在漢末被叫做陳蕃或李膺,在抗戰時期是英勇的國軍尤其是數百一飛沖天、去而不返的空軍英靈,全都是二十來歲年齡,清一色的書生。這個民族因為刑天不死、精衛常在,所以才能佇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始終不枯不朽。
《山海經》里另外兩則著名的神話,是夸父追日與后羿射日。《山海經·海外北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山海經·大荒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士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
后羿射日神話,在今本《山海經》里已失傳,唐人成玄英《莊子·秋水》疏引《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沃焦。”宋人《錦繡萬花谷》卷一引《山海經》云:“堯時十日并出,堯使羿射十日,落沃焦。”有關后異射日更為詳細的記載,見諸《淮南子·本經訓》:“逮至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兇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
僅從神話的故事敘述而言,很容易讀解為先民抗旱事跡的折射。再加上夸父與后羿又是同時代人,他們所處之地又是黃河流域,其時,黃帝族打敗伏羲族之后,已從原來的游牧民族南遷而居,成了農耕民族。對于農耕民族來說,旱澇無疑大事,因此有了抗旱的射日,有了后來的大禹治水。兩者皆以神話形式載入《山海經》。相比伏羲族的精衛、刑天神話充沛的民族精神元氣,黃帝族的這幾個神話似乎是折射了華夏先民戰天斗地的抗旱排澇事跡。然而,這只不過是對夸父與后羿神話的一種解讀。
今人劉宗迪《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提供了另一種解讀。劉宗迪從天文歷法的角度,重新解讀了夸父追日和后羿射日。劉著認為,夸父所追之日,并非是日輪本身,而只是太陽的影子而已。所謂的“欲追日景”,乃是《列子·湯問》里所說的“欲追日影”。所謂的“禺谷”,乃是立表測影的天文觀測。所謂的“逮之于禺谷”,并非是夸父跟著太陽跑到西方的禺谷,而是意指夸父觀測太陽的投影,從早晨一直觀測到黃昏。夸父棄杖化為鄧林,杖者,測影之表也。鄧林并非一片樹木,而是比肩而立的兩株樹木,加上毗鄰的“尋木”構成觀測日影定方位的三表之數。
劉宗迪對后羿射日的解讀,更為精彩。所謂十日,并非是指有十個太陽,而是一日之中的十個時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十日、十時的涵義在于,依據太陽一天之內在天空的十個不同方位(十日),將一晝夜劃分為十個時段(十時)。由此,劉宗迪進一步考證出了,所謂的后羿射日,并非是射落九個太陽,而是春分節慶活動中的射藝比賽,鄉射。射場上樹立的表木,既為日晷,又是射臬。劉著解釋說,后羿射日,其實是后世述者誤讀了《山海經》古圖,將古圖中十日圖像和射者圖像融為一體以示表木兼具日晷和射臬,說成了射者在射天上的十個太陽。本筆再作一個最后的補充,那樣的誤讀,又因為古圖的失落,變得更加容易令人信以為真。
倘若劉宗迪的詮釋是成立的話,那么夸父追日與后羿射日神話在文字表述上的象征意味,便讓位給了古圖原有的天文歷法涵義。不過,本筆在此更想論說的,乃是夸父與后羿兩者的歷史背景,因為這關系到司馬遷在《史記》杜撰的禪讓神話,如何掩蓋了歷史的真相。
《山海經》其實可分為兩部,一部是《山海經圖》,一部是文字表述的《山海經》。《山海經圖》已經失傳,而如今可以看到的文字《山海經》又是今本《山海經》而并非古本《山海經》,因此,對《山海經》的解讀必須非常小心。比如說,為什么今本《山海經》里不見了后羿射日,而只留下后羿射殺鑿齒的故事,以及后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的故事?今本《山海經》還刪去了有關后羿的什么故事?至于夸父,《山海經》里讀到的形象也是像刑天一樣被扭曲的,怪里怪氣的,耳朵上掛著蛇,手里握著蛇,并且還“不量力”去追日。為什么?
在司馬遷的《史記》里,世人找不到夸父和后羿在歷史上的真實形象。所幸,《竹書紀年》里保留了這二位的本來面貌。夸父是丹朱的大將,按《路史》中的描述,善奔跑,“以駛臣丹朱”,亦即是丹朱的信使。《竹書紀年》還記載了,后羿幫助虞舜,打敗了丹朱。可見,歷史上的夸父和后羿,屬于兩個交戰的陣營;一個站在失敗的丹朱這邊,一個站在勝利的虞舜那邊。于是,歷史由勝利者書寫的潛規則,悄然浮現。因此有了怪里怪氣的夸父形象,有了不量力的鄙薄之辭。而《山海經》文字之于后羿與唐堯之間的君臣關系,被一再強調,一再突出,似乎后羿射日、殺人、斷蛇、擒豨之類的事跡全都是在唐堯的指使下做的。后羿相助奪得帝位的虞舜不見了。虞舜與后羿之間的關系被全然隱去之后,虞舜與丹朱之間的那場戰爭就順理成章地可以完全不提了。
按照《竹書紀年》記載,堯舜之間,曾發生過很大的變故:“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丹朱是堯帝最鐘愛的長子,本姓祁,因為封地為丹故稱丹朱。《竹書紀年》說,丹朱得知父親被囚,并且被迫禪讓帝位于舜,率三苗之兵伐舜。雙方在丹浦大戰,丹朱大將夸父因逐日而誤入大澤至死,虞舜得善射箭的堯之射師后羿之助,打敗丹朱。
這段歷史,在《山海經》文字里,了無痕跡。在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變成了:“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權授舜。”所謂禪讓,就是這么打造出來的。當然,這也并非司馬遷一人之功,尚有各種所謂的歷史文獻,同心協力。諸如《尚書·逸篇》:“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曰丹朱。”郭濮的注《山海經·大荒南經》:“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舜伐三苗”。不奉儒學崇尚道家的《路史》倒是透露了一點微妙的信息:“帝堯崩,有虞氏帝舜封丹朱于房,為房侯”。“以奉其祀,服其服用,禮樂加之,謂之虞賓,天子弗臣。”當然了,直截了當道出真相,還得數《竹書紀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者,后羿也。稱丹朱為帝朱,似可解釋為何《路史》會說“天子弗臣”,因為丹朱本來就是天子。《尚書》所說的“舜使居丹淵為諸侯”,其實是后羿押著丹朱,將戰敗的帝朱流放到丹水。后羿幫著虞舜打敗堯帝之子帝朱,這無論之于后羿自身形象還是之于虞舜形象,都不太光彩。因此,《山海經》的文字作者會大書特書后羿與帝堯的君臣關系,一字不提后羿與虞舜之間的相助關系,更不提將帝朱流放到丹水之事。可見,神話故事里面隱藏著的歷史,是多么的微妙,多么的詭異。
在《山海經圖》與文字《山海經》之間,應該是圖像早于文字,先有圖像,后有文字。文字是對圖像的闡說。從劉宗迪發現的圖像與文字之間的錯位,可以想見《山海經》所涉及到伏羲族人物的圖像,應該早于后來的文字創作,或者說,早于禹益時代。即便是黃帝族人物的諸多圖像,諸如夸父、后羿,也應該早于后來的禹益時代。圖像與文字之間的這種錯位,從另一方面說,其實也是各言其事。比如夸父追日,圖像也許確如劉宗迪所言,乃天文觀察;但文字卻并非指涉天文歷法,而可能就是當時抗旱情景的折射。由此可見,抗旱與測影兩種解說,都是可以成立的。區分在于,抗旱是文字里的涵義,測影是圖像中的寓意。
當然,圖像與文字分說的情形,并不適用于解讀所有的《山海經圖》與《山海經》文字。由于圖像的失落,致使《山海經》的文字解讀相當困難。但又因為圖像與文字間的錯位,致使文字作者既可能誤讀圖像涵義,又時常會基于作者的主觀立場隨意發揮。正如司馬遷在《史記》里醉心于禪讓的杜撰,《山海經》的文字作者也會選擇為黃帝族站臺,當他們面對伏羲族神話時;也會按照勝利者的意志取舍史料,褒貶講說對象,當他們面對追隨丹朱的夸父和幫助虞舜取勝獲得帝位的后羿時。
《山海經》文字并非從天而降,而是有著極其鮮明的歷史背景。那樣的歷史背景,要而言之,便是炎黃之戰,黃帝族后來的朝代更迭,帝位易人。在黃帝族和伏羲族之間,《山海經》文字作者無疑取黃帝族立場;朝代更迭,帝位易人,他們一律為勝利者站臺。《山海經》的文字作者們雖然還沒有像后來的司馬遷那樣杜撰禪讓故事,但為尊者諱、為尊者隱,卻全都心照不宣。《山海經》文字作者的如此取舍,無意間證實了箕子對周武王姬發所說的《洪范九疇》,并非是黃帝族的政治原則,而應該屬于伏羲族的政治遺產。因為《洪范九疇》里的政治形象相當單純,沒有堯舜之間或者禹益之間那么的復雜那么的算計。再者,《洪范九疇》里的道德評判是指向王者的,而《山海經》作者卻在字里行間將褒貶投向了刑天或者夸父那樣的戰敗者。《山海經》文字的行文風格,與《洪范九疇》大相徑庭。
在筆者看來,華夏民族的歷史是由三場戰爭框定的,炎黃之戰,商周之交,秦統天下。這三場戰爭,雖然歷史情境有異,但本質相同,皆為野蠻戰勝文明。須知,后來的中國歷史,基本上以野蠻戰勝文明為主流的走向。這三場戰爭不僅構成了《史記》的取舍背景,同時也是《山海經》文字寫作的歷史語境。當然,更是當年孔丘作《春秋》的話語淵源,并且又給《尚書》中的諸多篇什造成根本性的影響。在文字和實物之間,在神話與史實之間,不知有多少錯位或誤讀,需要重新厘清。本筆在此的努力,不過拋磚而已。
二、東西方神話的兩個重大比較
筆者曾經有說,神話通常是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一如夢境緣自個人的無意識。那樣的無意識是隱形存在著的,即便訴諸文字,也相當朦朧。但無論怎樣的朦朧,神話都多少顯示出了一個民族的心理原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心理原型是很不相同的,一如人人皆有自己的指紋;同樣,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心理原型也是各各有異,無法用任何理念概念觀念作出整齊劃一的解釋,或者說隱伏在神話里的各個民族的心理原型,是沒有公分母可言的。以下的兩個比較,只是兩個不同的文化發生學意義上的詮釋角度罷了。
1、擔當型與享樂型以及善惡型
在筆者看來,華夏民族的心理原型無疑是隱伏在伏羲族神話里的,諸如盤古神話、女媧神話、刑天神話、精衛神話。黃帝族的夸父神話和后羿神話,更不用說大禹治水神話,全都因為歷史因素太重,從而大大地消減了其中的心理原型含量。從伏羲神話里可以看出,諸神的角色不一,但他們都具有同樣的擔當,或者說都是擔當者而不是享樂者。盤古開天辟地隨著天地而成長,是一種很有責任感的擔當。女媧補天也罷、造人也罷都是毋庸置疑的自我承擔,并且承擔得有如一位慈祥的母親。倘若說華夏民族有一個民族之母,那么就是女媧了。伏羲族神話里的擔當是如此的自覺如此的義不容辭,以致一個少女,都會在死而復生之后,變成以填海為己任的精衛鳥。更不用說像刑天那樣的書生,以寫作詩曲的手,撿起利斧,赴湯蹈火。在伏羲族這種擔當者的凜然正氣面前,孔武有力的黃帝族雖勝猶慚。遺憾的是,伏羲族留下了大量的圖紋,卻不曾留下文字,以致話語權不知不覺地落入發明文字的黃帝族之手,從而只能聽憑黃帝族的著述者們隨意發揮。但即便如此,伏羲神話人物依然不失擔當的大氣,以及因為擔當而自然而然產生的自尊和崇高。那樣的擔當,越是樸素,越有尊嚴,越具有崇高的美感。就此而言,伏羲族神話是相當嚴肅的。
相比之下,日本的雙尊神話比較輕松。在日本神話中的歷史,不是始于補天造天般的凝重,而是緣自男女做愛的歡快。那樣的歡快,在印度乃至西藏的佛教傳說中,是由歡喜佛表達的。當然,印度神話里的梵天,有如華夏神話里的盤古,并非是個喜樂形象,而是與盤古一樣,完成了創世義務之后,消逝于江河山川。梵天的神明地位,遠遠比不上守護神毗濕奴和毀滅神濕婆。印度的眾多神廟神像,大都屬于毗濕奴或者濕婆,據說只有一處是供奉梵天的。不知這是否讓古印度人覺得太過不公了,所以印度神話里又有一種傳說,仿佛是特意讓梵天有所補償。那個傳說如斯:宇宙之主躺在海面上孵化宇宙之蛋,一千年之后,生出了坐在蓮花里的梵天;而梵天又自生一女,然后與該女做了夫妻。
那樣的傳說是很難用生物學的單細胞繁殖理論加以解說的,因為那顯然不是生物學或者遺傳學現象,而是隱喻性的神話故事。而且,也不是只有印度神話如此不以倫常為意,在古希臘神話里,神明也照樣自產自愛自成婚姻。比如,大地女神蓋婭從指端里生出了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然后結為夫妻,生出了一大群泰坦。這比日本雙尊神話氣魄大多了。日本兄妹雙尊神話就像波姬小絲出演的《青青珊瑚島》那樣的青春片,蓋婭和烏拉諾斯神話才是成人的性愛成人的故事。而且,太過成熟。
希臘的創世神話不僅性的比重很強,而且還相當血腥。因為烏拉諾斯沒有善待他和蓋婭所生的孩子,蓋婭就教唆他們最小的兒子克羅諾斯,在他們夫妻同床的時候伏擊其父。結果,克羅諾斯用鐮刀割下了父親的生殖器,扔進大海。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逃回天空不再下來,就此將天空與大地永遠分開。那個被扔入海水里的生殖器也沒閑著,從浪花中,生出了希臘神話中最美麗的女神阿芙蘿黛蒂;其精血又生出了復仇女神,巨靈族等等。回到天空中的烏拉諾斯,沒有了生殖器也照樣活力充沛得不行,時常有精子落到大地上,滋生植物。可見,希臘神話中的生命意味,全部聚焦在強有力的性功能上。
生與死,往往是并存的。一方面是性能力帶來的生生不息,一方面則是因為父子間的仇恨導致相當血腥的冤冤相報。克羅諾斯閹割了父親,后來又被他自己的兒子宙斯所打敗。那場長達十年之久的父子戰爭,差點把宇宙給毀滅,可惜沒有被詳細記述下來,否則可能會讓荷馬史詩失色的。后來總算有了結果,宙斯成了宇宙之主。
與華夏神話有《山海經圖》一樣,希臘神話也有一部叫做《書庫》的繪畫手稿,雖然殘缺,卻被保存下來了。希臘創世神話故事記錄在赫西俄德的《神譜》里。盡管希臘歷史學者希羅多德曾聲稱,荷馬和赫西俄德一起決定了希臘諸神的形象,但荷馬史詩注重的是人世間的英雄塑造,《神譜》才是希臘諸神的本原故事。
與伏羲族創世神話的平和慈祥相反,希臘的創世神話可謂洶涌澎湃。然而,血腥過后,希臘神話顯示出來的卻并非是擔當式的崇高,而是太平盛世般的盡情享樂。希臘神話似乎沒有擔當的意識,即便是戰爭,也是冤冤相報式的復仇。或許是諸神之戰的這種了無擔當可言,凡世間的戰爭也同樣不是承擔什么責任,或者什么命運,而是起自于彼此爭奪一位美女。順便說一句,宙斯與希拉之間的夫妻之戰,也都是起因于宙斯愛上一個又一個的風流娘們。由此可見,享受性愛,既是希臘神話的人文基調,也是諸神乃至凡間諸多戰爭的起因。
希臘神話中的享樂主義經典,男版自然是那個風流得不像神明而像公子哥兒的宙斯神主,女版當推那位美麗的愛神美神阿芙蘿黛蒂,在羅馬神話里的對應者叫做維納斯。兩個版本,一樣風流。在后來的西方繪畫里,世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恐怕是宙斯化作天鵝追求羞答答的麗人莉達的畫面。當然,更為動人魂魄的無疑是波提切利的那幅《維納斯的誕生》。其實,準確的命名應該是阿芙蘿黛蒂的誕生。
希臘神話之于性愛的坦蕩,之于享受的無忌,可以說是希臘文化的精髓所在。古希臘諸多哲學流派中,就有享樂主義一脈,以伊壁鳩魯為集大成者。與古希臘陶器上的戰爭場面或者諸神形象對稱的是他們的諸多裸體雕塑藝術。斷臂維納斯展示的是女性的靚麗,擲鐵餅者高揚著的是男性的健美。據說,在當年雅典城里風行的時尚是,哲學大師通常攜帶著美少年出入。正如在古印度,擔任祭師的婆羅門乃是最為高貴的種姓;在古希臘的雅典城里,哲學家通常是最為令人矚目的牛人。有沒有思想,與男子是否練出健美的肌肉,具有同樣的審美效果。倘若說男子的裸體雕塑是單純的崇高,那么雅典城里的哲學家們則好比靜穆的偉大。而希臘文化這種優雅品性的源頭,則緣自希臘神話毫無禁忌的享受性愛享受生命。不管希臘神話以及荷馬史詩含有多少血腥的戰伐,但其基調卻是直言不諱地追求世俗的快樂,或者說是快樂至上的,即便悲劇,也快樂。順便說一句,希臘悲劇里的崇高有著天然的單純,了無愁云慘霧般的悲悲切切凄凄慘慘。
希臘神話以及整個希臘文化這種明亮的基調,是相當獨特的,就像伏羲神話的擔當一樣,都是絕無僅有的。記載于《金字塔書》的埃及神話,與希臘神話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也是自產自愛的創世方式。洪荒中產生最早的神明,阿塔姆,與太陽神拉合而為一,稱作阿塔姆——拉。阿塔姆以手淫的方式懷了二個神祇,舒,特弗內特;兩者創造了男性的塞勃,女性的努特,并且把男性的塞勃定為地,把女性的努特定為天。埃及神話至這一步,便與希臘神話迥然有異了。因為希臘神話里以男性為天空之神,以女性為大地之神。
這里有必要指出,按照張遠山《伏羲之道》里的考證,當初的伏羲八卦圖像,是坤卦在上,乾卦在下;后來至黃帝族,才變成乾上坤下。《伏羲之道》是從天文歷法的角度詮釋八卦圖像的,筆者關注的卻是,當年姬昌演易時,將八卦變成乾上坤下,是自有一番心思在其中。因為地處西岐的姬氏家族懷有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觀念,從而不是按照天文歷法的原則,而是按照姬氏的尊卑觀念,重新排列了八卦的順序。
很難說埃及神話的女天男地與伏羲八卦的坤上乾下之間是否有著相通的緣由,但倘若僅就尊卑觀念而言,男性并非天生為尊,女性并非生來為卑。也即是說,姬昌當年的尊卑排序并非天意,而是人為的杜撰。這與后來的司馬遷杜撰禪讓,如出一轍。
埃及神話雖然沒有希臘神話那么明麗,但依然有著本真的樸素。相比之下,記載于《巴比倫創世史詩》的巴比倫神話就沒那么單純了。巴比倫創世神話有善惡之分,一者是太陽神亦即巴比倫的大神馬杜克,一者是雌性的混沌之龍蒂阿馬特。善惡搏斗的結果,當然是代表善的馬杜克制服了代表惡的龍蒂阿馬特。巴比倫神話就是如此的善惡分明。但這種善惡型的神話卻影響不小,古希臘的阿卡得神話里就曾復制過馬杜克殺死龍蒂阿馬特的故事;這在迦南(腓尼基)神話里是殺死七頭龍洛坦,在日耳曼民族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里是齊格菲爾德殺死巨龍法夫納,甚至后來的基督教故事里都有圣喬治殺死惡龍之事。
相比這種善惡分明的神話故事,《波斯古經》里的創世說,則以光明和黑暗作劃分。光明之神阿胡拉·馬茲達,黑暗之神安格拉·邁紐。這影響到后來的祅教成了二神教,正直的神叫做馬茲達,邪惡的神叫做邁紐。這與希伯來一神教在《舊約》里的上帝耶和華與魔鬼撒旦,頗為相似。
享樂型的希臘神話雖然不乏戰事,但并不嚴格劃分善惡或者是非。無論是《伊里亞特》里的希臘聯軍與特洛伊之間的戰爭,不論是非,只作敘述;即便是后來亞歷山大的征戰,也不以是非為意,只是爭個輸贏而已。但善惡型的神話卻是非分明,一點都不含糊。基督教當年十字軍東征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是是非非,至今未果。
回首伏羲神話,與希臘神話一樣,沒有明確的是非意識是非觀念。可見,伏羲族是個很不好戰的氏族,可能也因為不好戰,所以被北方游牧民族黃帝族打敗了。及至黃帝族的后裔撰寫《山海經》,雖然皮里陽秋,不乏褒貶,卻并沒有明確的是非劃分。華夏歷史上的開始形成是非觀念,可能始于《尚書》所輯錄的諸如《甘誓》《湯誓》《泰誓》《牧誓》之類的討伐宣言。這種鏗鏘有力的是非性指責,并不見諸《山海經》神話。由此可見,伏羲時代之于后世的影響,是多么強勁深遠。比起巴比倫神話里的善惡之神,比起《舊約》里嚴厲的耶和華形象,華夏民族的創世諸神盤古、伏羲、女媧,實在是太平和、太可愛了。
2、多神造世與絕對意志
倘若將世界各地各族的神話像一張地圖似的,攤開在同一個平面上,那么就會發現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幾乎所有的創世造人神話,都是多神多樣的,惟有《舊約》里的創世紀是上帝耶和華打造一切,由此體現出一種空前絕后的絕對意志。倘若可以將多神造世標記為暖色,那么《舊約》的創世故事無疑是冷色的。
從華夏民族的伏羲神話說起。創世者盤古,非但沒有成為統治世界的絕對上帝,而且自己的身軀全都化作了萬物,從而達成了毫無保留的奉獻。補天造人的女媧,也并非一個統治者,而是慈母般的呵護者。伏羲族的這兩個創世造人神話傳說,成為華夏民族本性平和、不喜侵略的文化傳統。這雖然是伏羲族被黃帝族打敗的原因,但也是華夏民族骨子里與窮兵黜武天然格格不入的承傳所在。順便說一句,尚武在黃帝族是游牧造成的天性,及至戰國時期的秦國才成為爭奪天下的自覺,由商鞅的軍國主義開啟邪惡之門。秦滅六國的歷史,后來的經典演化,便是金滅北宋,元滅南宋,清兵入關。這一系列前赴后繼的野蠻,皆有悖于盤古神話女媧神話的人文精神。就文化承傳而言,華夏民族的歷史是一步步退化的,或者說一步步淪喪的。
相比于華夏神話的這種平和,日本雙尊神話展示的是與生俱來的歡快。性愛,成為日本神話的至關重要的精神主題。可能正是這樣的承傳,致使《源氏物語》的基調旨在帥哥王子的愛情傳奇。比起《紅樓夢》里賈寶玉由石而玉的艱辛歷程,光源氏可是風光亮麗地愛足一生,愛滿天下。相反,《竹取物語》的凄惻在于,世間無愛可覓的絕望。那樣的絕望,在后來的日本文學里,由芥川龍之介表達得最為淋漓盡致。
印度創世神話的主神梵天,幾乎是與伏羲神話的盤古一樣命運,創世完成即逝,將主神的地位讓給了守護神毗濕奴和毀滅神濕婆。毗濕奴在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化身為羅摩,在《摩訶婆羅多》里化身為黑天。可見,印度神話里的創世者并非至高無上,而主要的神明也并非是人世間的統治者。
這種創世神明的地位變化,在希臘神話中是通過父子間的兒子戰勝父親體現的;在美索不達米亞神話里,則是經由一代代神明的貢獻大小形成的。
希臘神話雖然不乏諸神之戰的暴力和血腥,但從烏拉諾斯到克羅諾斯、再到宙斯這祖孫三代的神主更迭,與其說是悲劇的,不如說是喜劇的。尤其是號稱宇宙之王的宙斯,成為神主之后,完全變成了一個喜劇人物。那樣的喜劇色彩可以說是神主不夠嚴肅,也可以說是神明熱愛凡世間的日常人生。因此,最后是愛情,而不是沒完沒了的戰爭,成為奧林匹斯山的底色。
希臘神話的另一個人文精神意味上的特征在于,豐富多彩的文化創造。諸神之中,宙斯除了忙于尋找風流,幾乎就是無為而治。赫拉克勒斯承擔了除惡揚善的諸多重任,普羅米修士擔當了為人類盜取火種的使命;阿芙蘿黛蒂是愛和美的化身,阿波羅同時象征著音樂、詩歌和射藝,如此等等。希臘神話里的每一個神明都沒閑著,都在為各自的事業忙忙碌碌。
希臘神話之于生命和生活的如此熱愛,不僅影響了古希臘時代的文化和文明創造,而且還經由后來的文藝復興演化成歐美現代文明的金碧輝煌。可以說,歐美現代文明的諸多人文精神,都可以溯源到希臘神話。與華夏民族的伏羲神話人文傳統被一斷再斷的情形截然相反,希臘神話的人文承傳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發揚光大。倘若說,亞歷山大的征戰只是帶給歐亞大陸一個希臘化時代,那么后來的文藝復興所創造的現代文明,則完全徹底地改觀了整個世界。
相比之下,被稱作人類文明搖籃之地的美索不達米亞,其神話卻是從另一種路徑衍化的。從歷史文化的淵源上說,美索不達米亞神話確實是至關重要的源頭;不僅影響過古希臘神話,而且更加深刻地影響了后來希伯來神話的創作,同時還可以從波斯神話里發現蘇美爾神話的影子。這里指的是,波斯神話里的黑暗之神安格拉·邁紐,音近蘇美爾神話中的恩利爾。當然,這里并不排除這兩個神名的音近,只是偶然的巧合。比如華夏民族的夸父追日神話就并非獨一無二,在古代西藏和緬甸北部之間有一個原始蒙古人種,加羅人,其中欽族的一個分支陶楊人也有個相近的傳說,說他們瘋狂地追捕太陽而導致了本族的毀滅。陶揚人追捕太陽的傳說,與華夏民族的夸父追日,應該沒有什么關聯。由此可見,偶然的巧合,也是有的。
但希伯來神話與美索不達米亞神話之間的諸多相似,卻絕對不是巧合。希伯來創世神話是七天,巴比倫創世神話持續六天。希伯來神話里提及洪水和諾亞方舟,蘇美爾史詩《吉爾伽美什》里就有洪水和方舟的故事內容。總之,《舊約》創世紀里有太多的細節,都可以在美索不達米亞神話里找到原形或者說出處。希伯來神話與美索不達米亞神話的區別在于,美索不達米亞神話里的神明,沒有一個是終極意義上的主宰者;而《舊約》里的耶和華卻是絕對意志的化身,說一不二的主宰者。
從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神話到巴比倫神話,再到希伯來神話,不僅有跡可尋,而且脈絡清晰。從十九世紀以來陸陸續續地發掘出來的泥板文書里,由楔形文字記述的諸如蘇美爾史詩《吉爾伽美什》、巴比倫史詩《埃努瑪·埃立什》,相當翔實地提供了美索不達米亞神話的原本風貌與歷史演化。在蘇美爾創世神話中,神主先是天神安,然后是天神之子風神兼空氣之神恩利爾。恩利爾因為吹開了天地,所以被尊為眾神之主。及至巴比倫神話,恩利爾的眾神之首地位又被他的侄子馬杜克所取代,因為馬杜克制服了怪物,結束了混亂的局面。這種神主地位的演變,與希臘神話祖孫三代的相繼,極其相似。或者說,希臘神話的祖孫三代神主更迭,最初的淵源很可能就緣自美索不達米亞神話。
饒有意味的是,這種神主更迭的演變模式,到了希伯來神話里,突然變成了一主至上的上帝說。如此的突變,有二個細節值得探究。為什么美索不達米亞神話里的神主輪流更替,到了希伯來神話變成了耶和華主宰一切?幾乎世界各地所有的創世神話,都是朦朧的,含糊的,多神崇拜的,諸多版本的,為什么惟有希伯來創世神話卻是極其清晰的、不容置疑的、一神至上的,獨一無二的?
美索不達米亞神話的神主輪流更替,非常明顯地基于一個重要因素,即神明具有屬人的品性。比如恩利亞,不僅有父親,而且還有妻子。更不用說后來的希臘神話,幾乎是一個神祇家族的演化史。在印度神話里,宇宙之主原人也具有人的屬性。盡管原人是宇宙之主,與宇宙同在,但原人的創造生命卻是自身分為兩半,一半男性一半女性,然后結合為夫妻,創造人類。更為有意思的是,原人并非宇宙主宰,只是給凡世帶來生命的起源。印度神話的另一種說法則是,具有原人意味的梵天,完成了創造使命之后,便將神主位置讓給了守護神毗濕奴與毀滅神濕婆。那是因為古印度人的宇宙起源說認為,宇宙是永無休止的創造與毀滅的不斷循環。
但這在希伯來神話,耶和華是毫無凡人意味的神主。所謂上帝的涵義,可能就在于這樣的超凡絕俗,沒有絲毫屬人的性質。倘若以本筆在前面章節中所論說的生命與宇宙的對稱性來觀察,那么就可以發現,在諸多神明多少具有屬人性質的神話里,生命與宇宙是合二而一的,或者說宇宙并非全然獨立于生命而存在。相反,在希伯來的耶和華神話里,上帝是完全凌駕于生命之上的存在物;或者說,生命與宇宙之間是沒有對稱性可言的。上帝既是宇宙的化身,又是所有生命的主宰。這與古印度人的宇宙觀截然不同,宇宙不是在創造和毀滅之間不斷循環的,而是聽命于上帝的意志存在的。上帝說要創造就有了創造,上帝說要毀滅就會毀滅。這可能就是那句“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原始涵義所在。
說希伯來神話大致承襲美索不達米亞神話,既可以說是成立的,也可以說是不成立的。說成立,是因為希伯來神話里確實有大量的細節,可以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神話;說不成立,則是因為古代希伯來人的創世神話,大幅度地、可以說從根本上,修改了美索不達米亞神話。
參照挖掘出土的由楔形文字書寫的泥板文書記載,世人發現,希伯來人的圣經《塔納赫》(亦即基督教的《舊約》)中不僅有許多故事與蘇美爾神話相近,而且諸如《詩篇》《雅歌》《耶利米哀歌》的諸多段落,都來自蘇美爾史詩《吉爾伽美什》。其中最突出的是洪水和諾亞方舟的故事,幾乎就是《吉爾伽美什》里的洪水故事的翻版。英國的BBC廣播電視公司為此專門制作過一個紀錄片《諾亞方舟》,揭示了希伯來神話里的方舟故事,其實是《吉爾伽美什》史詩里記載的洪水故事的改頭換面;或者說,它將蘇美爾史詩里記載的發生在兩河流域的洪水史跡,夸張成了整個地球上整個人類的洪水巨災。
希伯來神話的伊甸園故事,也可以從蘇美爾神話中找到最早的元素。從夏娃形象上,依稀可見蘇美爾神話里的愛情女神伊南娜。伊南娜也有一棵果樹,樹下也有一條蛇。那蛇讓伊南娜感覺不適。后來伊南娜請神明將那條蛇趕走了。這個故事演化到希伯來神話里,變成了蛇引誘夏娃偷吃樹上的智慧之果。至于伊南娜下陰間,爾后死而復生的故事,是否啟迪了《新約》里的基督復活,有待于專家的考證;但伊南娜形象與夏娃之間,很難說一點關聯都沒有。
希伯來神話中的肋骨細節,也可以在蘇美爾神話里追溯出原形。生命女神寧提,就是在肋骨部位醫治水神恩基的,以致有學者認為,這很可能就是亞當肋骨的由來。說到亞當,有必要提及蘇美爾神話里的另外一位女神莉莉斯。據說,莉莉斯的名字源自蘇美爾語“夜晚”,同時也是后來古希伯來語的“夜”。按理說,莉莉斯應該是一位夜神,但猶太教十世紀成書的《便西拉的字母》透露說她是亞當的第一位妻子。莉莉斯不喜歡亞當,離開伊甸園去了紅海。亞當向上帝訴苦,致使上帝放棄了莉莉斯,從亞當的肋骨里造出了夏娃與亞當為妻。傳說中的莉莉斯,顯然是非常有個性的女子,獨立特行,無所畏懼,很奇怪二十世紀以降的女權主義者為什么沒有引為先驅。這情形與圣經相仿,《舊約》僅一處提及莉莉斯,并且還含含糊糊地以夜鷹的命名加以搪塞。
不管怎么說,希伯來神話與美索不達米亞神話之間,實在是千絲萬縷;要不是彼此間形而上的精神氣質迥異其趣,庶幾可說一脈相承。它們最為根本的區別在于,蘇美爾創世神話是大自然的神力,亦即風神空氣神,分開了天地;而希伯來神話的創世卻是耶和華按部就班的很有計劃的工作成就。于是,一種可稱作絕對意志的東西,在這樣的創世過程中悄然形成了。天地間的劃分,既不是盤古那樣的天然混成,又不是梵天那樣的孵蛋卵生,也不是恩利爾風吹的神力所致,更不是日本雙尊那樣的做愛結果,而是耶和華至高無上的、不無威嚴的神創。倘若說,在其它各種創世神話里都有一種生命的隱喻在其中,那么耶和華的創世顯現的惟有絕對意志。生命是柔軟的,絕對意志是剛硬的;生命是溫情的,絕對意志是冰冷的。在有生命意味的創世神話里,生命與宇宙是合而為一的;在耶和華的創世過程中,生命與宇宙是截然有別的。先有光,后有天地,再有生命,然后再有人類,并且是男人在先,女人在后;女人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而已。在此,用科學的說法叫做從無機到有機,用哲學的說法叫做從物質到精神。這里的一切都是有安排的,這里的一切都是有秩序的,這里的一切都是由上帝的意志所左右的。可以說是太完美了,也可以說是太不可思議了。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后來西方的科學觀和哲學觀,大致上就發軔于如此這般的耶和華創世之宇宙觀。更不用說,后來的一神教,基本上就是源自耶和華的創世神話。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希伯來創世神話的如此嚴厲?若說是自然生存環境的惡劣,須知,希伯來人賴以生存的兩河流域,乃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發軔地,先后有蘇美爾人、亞述人、巴比倫人相繼生存過,何以在美索不達米亞神話里沒有那樣的剛硬?偏偏到了希伯來人才變得怒氣沖沖?本筆的看法是,耶和華創世神話,可能緣自古希伯來民族于顛沛流離生涯產生的某種自卑感。《摩西五書》中的《出埃及記》,就曾明確描述過希伯來民族在埃及所遭受的屈辱。那樣的屈辱,需要有一個強大的神明為之雪洗。其情形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日耳曼民族因為戰敗而產生的民族屈辱感,極其相似。倘若說希特勒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經由感覺屈辱的德國人呼喚出來的;那么同樣可以發現,要說有光就有光的耶和華也不是實際存在的神明,而是備感屈辱的古希伯來民族醫治心理創傷的心理需求。盡管《塔納赫》里的篇章順序是先有《創世紀》再是《出埃及紀》,但從這部圣經的成因追溯,卻是先有《出埃及紀》里所記載的遭受屈辱,然后才產生了威嚴強大、至高無上的耶和華。而希伯來人那個上帝選民的自我命名,并不僅僅是表明耶和華品牌的專利權,而且同時也是希伯來人藉此雪洗屈辱感從而醫治心理創傷的強烈渴望。
弗洛伊德晚年寫過一部論著《摩西和一神教》。此著力圖論證摩西并非猶太人,而是埃及人;進而推斷,猶太教的一神教源于埃及歷史上的阿頓神教。弗洛伊德此說無疑極其大膽,甚至可以說,挑戰了猶太民族的心理底線。因為從《出埃及紀》所記載的希伯來歷史來看,埃及乃是猶太人的一個難解的心結,怎么可能接受摩西是埃及人的說法?當然,歷史事實有時并不以世人的好惡為轉移,但本筆的看法是,弗洛伊德斷言猶太教源自埃及的阿頓神教,未免有失輕率。僅就創世神話的溯源而言,希伯來人《創世紀》中的諸多元素,完全可以在蘇美爾神話里找到出處,卻沒有任何跡像可以證明與埃及神話有什么淵源。不僅如此,即便埃及人的創世神話,也都受到蘇美爾人的影響。比如,蘇美爾創世神話中的天地之分,是由天神之子風神吹開的。埃及創世神話中的天地之分,則是由太陽神拉吩咐空氣之神將天神努特與地神蓋伯強行分開的。應該說,埃及創世神話與希伯來創世神話全都受到蘇美爾創世神話影響是可能的,而希伯來創世神話是否受到過埃及創世神話影響,卻無從說起。至于弗洛伊德津津樂道的阿頓神教,乃是埃及歷史上轉瞬即逝的一神教插曲,阿頓神不過是由太陽神拉衍生出來的神明崇拜。相比之下,耶和華則是主宰一切的宇宙之主,其神力的涵蓋遠非太陽神拉可逮,更不用說從拉崇拜衍生出來的阿頓崇拜。對于一神教的猶太教來說,摩西的出身遠沒有耶和華的絕對意志意味或者說上帝意味,更為至關重要。就算摩西是個埃及人,也絕對是完全服膺了希伯來人心理需求的領袖人物,或者說完全符合希伯來人要求的引路人。相比之下,基督還是個猶太人呢,為什么會遭到法利賽人、尤其是猶太祭司那么強烈的反對,那么冷酷的拒絕?因為基督的言行不符合希伯來人的心理需求。同樣道理,假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政壇上崛起的不是希特勒那樣的人物,而是像基督那樣的慈悲為懷者,會被德國人接受么?遭受屈辱的民族需要強勁有力的領袖,一如希伯來人需要威震寰宇的上帝。
倘若將目光擴至整個人類文化歷史和人類精神視域,那么不難發現,后來的基督問世,乃是對耶和華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補充。基督不是神話人物,而是以道成肉身的凡世形象,出現在希伯來人賴以生存的那塊土地上。基督沒有冒犯耶和華的威嚴,也沒有觸犯摩西律法,基督只是幽幽然地補充了一道慈悲之光;以愛面世,以愛示人。從蘇美爾至巴比倫,再到希伯來,世代相繼的創世神話,因為基督的現身而變得空前的明媚。然而,先知在故鄉不遭待見的箴言,極其悲慘地落到了基督頭上。基督的悲劇并不在于面對羅馬總督,而是在于不得不面對希伯來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創傷。這份糾結,歷經千年而難以得解。其中的悲苦,惟基督自知,而已。
一個族群集體虛構的人物也罷,傳說也罷,都會成為該族群冥冥之中的主宰。所謂的絕對意志,就是這么的堅固,這么的難以突破,難以解困。同樣道理,倘若一個人物形象被整個族群所妖魔化,那么也很難洗清污名,很難平反昭雪。這里指的是,從蘇美爾神話落入希伯來神話的夜神莉莉斯。這位女神的身份地位變化,比中國歷史上的妲己還要悲慘。先是亞當的第一任妻子,然后被說成撒旦的情人,再后又變成夜之魔女,最后竟然成了女巫。更為荒誕的是,有關莉莉斯的傳說,變形到了極其魔幻的地步:莉莉斯夜魔竟然出現在男人的夢中,與他們性交吸取精液,并且,還有吞食嬰兒的癖好!據說,猶太男人出生后的割禮就是為了保護新生嬰兒免于遭到莉莉斯的戕害。僅從莉莉斯形象諸如此類的變幻,便可想見,基督所面對的,是多么沉重的世界。
一個族群的創世神話,既是該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也可以成為一個民族集體無意識創傷的映射。絕對意志可以讓一個族群堅韌頑強,但也會造成自我封閉的幽暗。但也不能反過來說,一個民族擁有平和溫婉的創世神話,就必定會通達明亮。對比希伯來民族有如石縫里的小草一般頑強,華夏民族始終掙扎在一種自暴自棄的淪喪之中。一個族群的命運,與其創世神話是否美麗,還真不是一回事。至于世界各地創世神話的能否得以進一步的還原,只能期待更多的考古發現。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寫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