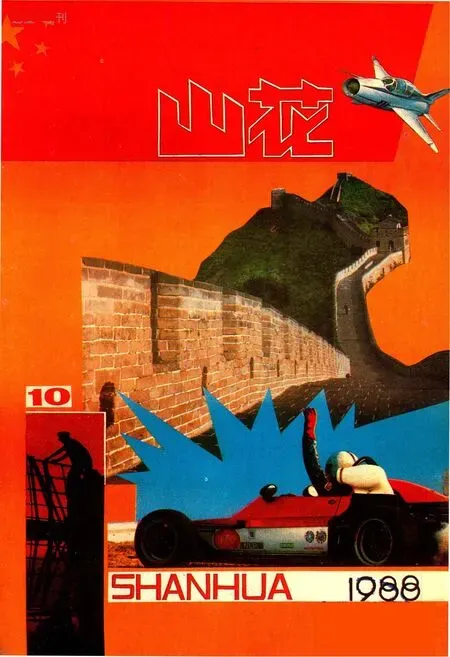揭示被藏匿的存在
龔云表
“瓶非瓶”,是盧治平近年來創(chuàng)作的一組絲網(wǎng)版畫系列作品的總標題,而其題目背后所蘊藉的審美內核和當代藝術思辨,卻可以涵蓋他幾乎所有作品的藝術觀念和創(chuàng)作訴求。諸如他的“水鄉(xiāng)”系列、“考古”系列等。這是因為他將一些歷史或現(xiàn)實的物像,通過刻意的顛覆、解構、整合、重組,賦予作品以具有當代審美意味的物化呈現(xiàn)。“瓶非瓶,非常瓶”。盧治平作品中的瓶,并非是我們通常所見到的青花玉壺春、磁州窯梅瓶、永樂花果紋執(zhí)壺、鈞窯出戟尊,而是將它們僅僅作為一種傳統(tǒng)構成元素和因子,融入到當代創(chuàng)作語境之中,尋找到與現(xiàn)代主義美學的結合點,創(chuàng)造出嶄新的構成邏輯,呈現(xiàn)出富有當代情致結合形制的藝術闡述范式。在這里,傳統(tǒng)構成因子已被突破,并且得到不斷的延伸與外拓,固有的審美內涵也被抽提和升華,在新的美學高度尋找到了依傍和歸納,從而“異化”為全新的、具有“形而上”哲思、包容了象征性隱喻的意象。
在盧治平的作品中,被有意識地植入了許多已然成為歷史的傳統(tǒng)藝術符號,諸如在“考古”和“水鄉(xiāng)”系列中的青銅器饕餮紋、龍鳳紋和曲折雷紋等,在“瓶非瓶”系列中的陶器的網(wǎng)紋、弦紋和垂幛紋等,瓷器的纏枝紋、折枝紋和蓮花紋等。而當這些符號被引用時就已經(jīng)納入被顛覆并重新建構的語境,嬗變成為一種嶄新的美學定位的現(xiàn)代主義符號。或許盧治平意識到,對于當下越來越傾向于物質的現(xiàn)代人,太需要為他們提供新的精神空間,于是,他用解構主義語言構建一種獨特的“可能世界”,而讓現(xiàn)實世界反而只是變成“可能世界”的一種物化形式。他就是用這種藝術方式來質疑現(xiàn)實,疏離物質,使人們置換到另一個空間,去尋覓別樣的依托,重新確定自己的審美價值判斷。
這不由讓我們想起蘇珊.朗格提出的“藝術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chuàng)造”這一揭示藝術本質的著名美學命題。藝術作為一種特殊的表象性符號,有著自己獨特的意蘊,這種意蘊就是人類情感。藝術家創(chuàng)作的過程,是一種藝術抽象、創(chuàng)造符號的過程,是一種將物質非物質化、對現(xiàn)實世界重新構造而營建超現(xiàn)實場景的表現(xiàn)性方式。盧治平的作品作為“有意味的形式”,已超越物象本身而以感覺空間的能動體積的意象,造成一種充滿玄妙機巧的藝術幻覺并因此獲得誘發(fā)想象的虛幻空間。他的這些作品是喚起人們想象的符號,它們所具有的內在認知和空間邏輯,將與人們固有的審美定勢和欣賞習慣產(chǎn)生沖突或者互動。對于我們觀看者來說,觀看的過程也便成為了一種充滿張力、奇妙無窮的視覺體驗。
細察盧治平作品中的空間邏輯,以及他對于空間的認識和處理,無疑具有一種強烈的超現(xiàn)實主義的特征,賦予了現(xiàn)實生活中一種觀察的距離,從而為我們提供了某種反思性的文化視野。在這些作品中,具象與抽象、現(xiàn)實與夢幻、局部真實與整體虛擬,總是被神奇而恰到好處地糅合在一起,使作品的內涵突破形象的束縛,讓人們似乎能看到第三度空間的幻像,看到被他的主觀意緒過濾后重新組合的非現(xiàn)實的意像。這種“非現(xiàn)實的意像”,盡管十分明顯地疏離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體驗,但卻與自己在苦苦尋找的某種情感正相吻合,因此便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藝術存在,盧治平只是把這種被“藏匿”的存在揭示出來而已。正如海德格爾在《詩歌、語言、思想》一文中所說:“自我藏匿的存在被照亮,這類光把它的光芒融入作品。被融進作品的光芒就是美的事物。美是一種方式,在其中,真理作為揭示產(chǎn)生了。”盧治平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美的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我們是能切切實實感到有一種能夠照亮被藏匿的存在的光芒的。
索緒爾曾經(jīng)說過:“在語言出現(xiàn)之前,一切都是混亂模糊的。”對藝術也應作如是觀。沒有完備的繪畫語言,任何圖式和形象都無法營造出美的意境。盧治平以他對于版畫語言的從容駕馭,通過對于絲網(wǎng)版和銅版特殊制作的精到認識和深刻理解,在刻痕、蝕印和線條的交織中,運用形象的符號化構成、強烈和單純的和諧對比、現(xiàn)實與虛幻的交互融合,以及對于物象的寫意性表達和淋漓盡致的情感抒發(fā),傳達出他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化審視和審美價值觀。盧治平通過他的作品正在試圖尋找和開拓更為寬闊的現(xiàn)代版畫之路,在整體上深入探索版畫藝術的內蘊,鍥而不舍地致力于版畫藝術的當代創(chuàng)作語境轉換,努力建立中國版畫的當代品格。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