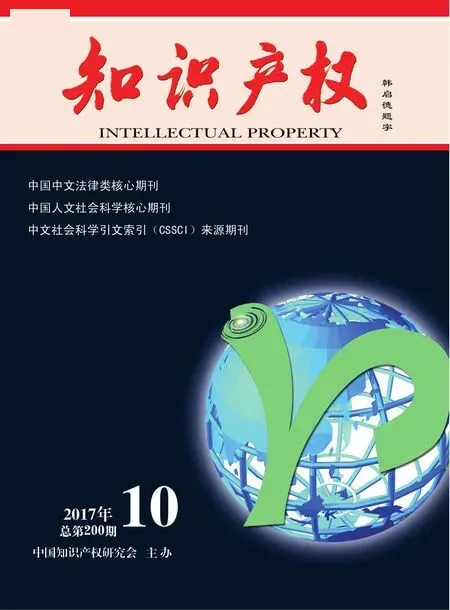侵犯著作權罪之復制發行的司法認定
霍文良 馮兆蕙
侵犯著作權罪之復制發行的司法認定
霍文良 馮兆蕙
當前形勢下一些新的復制發行行為給司法認定帶來了很多困惑。應當準確界定民事侵權行為與侵犯著作權罪的界限。相同與相似在屬性上具有本質的差別。網絡游戲軟件的盜版侵權,鑒定為實質性相似不能等同為相同,不能簡單地認定為復制發行。侵犯著作權罪之復制行為中“相同”的認定應當主要考慮兩點:是否改變作者署名、作品名稱;是否為作品內容的直接再現。
著作權 復制發行 實質性相似
復制發行是侵犯著作權罪客觀方面四種行為之一,也是侵犯著作權罪最常見的犯罪形式。然而近些年來,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一些新情況的出現,使我們對復制發行的認定產生了諸多爭議,出現了過去不曾遇到的新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復制發行行為進行準確的認定。
一、網絡游戲引發的復制、發行的新問題
隨著網絡的普及,我國可謂逐漸步入網絡時代,產生了新興的網絡游戲產業。但網絡游戲產業興起的同時也伴隨著侵犯著作權的私設服務器等違法活動的大量涌現,這一現象嚴重影響了網絡游戲產業的正常發展。面對這一局面,2003年新聞出版總署、信息產業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家版權局、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下發《關于開展對“私服”“外掛”專項治理的通知》。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于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依法嚴懲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的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審判職責,切實發揮刑事司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作用,打擊和遏制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活動,實現刑罰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的功能。要保持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活動的高壓態勢,依法從嚴懲處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犯罪分子。在此之后,司法機關加大了刑事打擊力度,各地人民法院作出了相當多的涉及網絡游戲的侵犯著作權罪的判決,具體情況見下表①相關判決都來自中國裁判文書網。這一點也進一步驗證了我國逐漸進入了網絡時代。。

涉及網絡游戲的侵犯著作權罪判決統計表
② 該判決如此,似乎關于游戲名稱有些混亂,沒有說明《熱血傳奇》與《傳奇世界》的關系。
這些司法判決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大都以鑒定機構的鑒定結論“實質性相似”作為構成復制發行(同一性是個別情況,具體差異后面將詳細分析)的依據,并沒有詳細論述理由,而是以此直接認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事判決中涉及剽竊、抄襲等侵權行為的認定時,人民法院同樣使用了“實質性相似”的判斷作為認定的標準。如莊羽訴郭敬明侵犯著作權案中,二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一審判決認定郭敬明未經許可,在其作品《夢里花落知多少》中剽竊了莊羽作品《圈里圈外》中具有獨創性的人物關系的內容及部分情節和語句,造成《夢里花落知多少》與《圈里圈外》整體上構成實質性相似,侵犯了莊羽的著作權,應當承擔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是正確的”。③參見法律博客網,http://lawyertiger.fyfz.cn/b/421594,2017年4月20日訪問。事實上,長期以來我國司法實踐中和理論研究中都是在民事侵權領域使用“實質性相似”規則,這個規則在知識產權各領域都有涉及,如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等侵權認定都涉及到“實質性相似”,而在著作權領域更是如此,特別是在抄襲、剽竊等侵權案的認定時屬于必用規則,一般堅持“接觸和實質性相似”的認定標準。對此規則在民事侵權領域的適用基本沒有異議,所以學者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實質性相似”認定的具體標準④參見梁志文:《版權法上實質性相似的判斷》,載《法學家》2015年第6期;吳漢東:《試論“實質性相似+接觸”的侵權認定規則》,載《法學》2015年第8期;孫松:《論著作權實質性相似規則的司法適用》,載《中國版權》2016年第1期。,而對于“實質性相似”在刑事審判中的適用還缺乏具體的研究。那么在這樣兩個不同領域中使用的“實質性相似”是否是同一含義,二者的區別是什么?司法判決中“實質性相似”的事實認定,能否作為侵犯著作權罪的復制發行行為來看待?這里的復制發行非法作品與原作品之間應當是相同還是相似?這些問題是以前研究探討侵犯著作權罪從未遇到的,目前尚未得到足夠關注。但是本文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問題,直接關系到侵犯著作權罪的罪與非罪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問題。
二、復制發行之相同還是相似
傳統作品的復制由于其方法手段的原因,一般都是原作品的簡單再現,所以認定起來相對容易,基本不會發生爭議,即所謂復制就是“復制”原作品,使之增加一份或多份。因此,不會涉及相同與相似的爭議,但是以計算機軟件為代表的新的作品形式,其再現作品的技術手段和方式發生了變化,不再只是簡單地原原本本地再現原作品,如前述中幾部門聯合下發的《關于開展對“私服”“外掛”專項治理的通知》對于“私服”“外掛”的界定對此就有體現;“私服、外掛違法行為是指未經許可或授權,破壞合法出版、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互聯網游戲作品的技術保護措施、修改作品數據、私自架設服務器、制作游戲充值卡(點卡),運營或掛接運營合法出版、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互聯網游戲作品,從而謀取利益、侵害他人利益。”這里強調了破壞游戲作品的技術保護措施、修改作品數據等行為,也就是說并非簡單地再現原作品游戲軟件,而是有修改行為,那么,這種行為是不是復制發行,對這些行為應如何定性?可見,何種情形下構成復制、何種情況下構成抄襲、何種情況下是合法創新需要一個合理的界定標準。
(一)“實質性相似”不等于相同
“實質性相似”的性質歸根結底仍是相似,而相同與相似在屬性上卻有著本質的區別。相同從字面意義上說是指某事或某事物完全一樣、一致,從本質上講是不能區分的、是無差異的;而相似是指某事或某事物有類似的地方,但其實是不完全一樣的、不完全一致的,從本質上講相似是不容易區分,容易混淆,但事實上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實質性相似”規則的提出其實也恰恰是由于侵權作品與原作品之間不完全相同,而提出的一個判定規則。抄襲、剽竊的侵權行為可以分為低級的抄襲、剽竊和“高級”的抄襲、剽竊,所謂低級的抄襲、剽竊,基本上是將他人作品原封不動地竊為己有而將之視為自己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對于這種低級的抄襲、剽竊認定是比較簡單的。而較為復雜的則是“高級”的抄襲、剽竊,將他人作品進行了一定的加工、甚至再創作,這時候對抄襲剽竊的認定就困難得多,因此引入了“接觸性+實質性相似”規則來判定。所以“實質性相似”規則的使用,其邏輯前提已經承認了兩個作品之間具有差異性、是不同的,因此以“實質性相似”作為相同的判定標準是行不通的。
(二)復制的本質是相同作品的再現而不是相似作品
復制的本質和特征在理論上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如有學者認為,復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作品內容再現性;第二,作品表達形式的重復性;第三,作品復制行為的非創造性。⑤吳漢東著:《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頁。還有學者認為復制具有四個基本特征:第一,形式再現性(即通過一定的物質形式再現原作);第二,非獨創性;第三,競爭性(復制件與原件的競爭、替代關系);第四,受眾與作品的非直接接觸性(強調的是原作與復制件所具有的沿襲傳承關系,而不直接表現為作品的傳播)⑥馮曉青、付繼存:《著作權法中的復制權研究》,載《法學家》2011年第3期,第99-112頁。。也有學者認為復制是“使用某種物質形式將作品一模一樣或者基本上一模一樣地再現出來,既包括靜態的文字、圖像,也包括將動態的聲音、圖像再現出來”。⑦湯宗舜著:《著作權法原理》,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頁。但也有不同的觀點,如有學者認為“并非所有再現作品的行為都是受復制權控制的復制行為,只有以特定方式對作品再現才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行為”。⑧王遷著:《著作權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本文認為研究探討著作權里的復制必須以著作權法為依托,從法律規定去分析復制的本質特征。根據《著作權法》第10條,復制是指以印刷、復印、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等方式將作品制成一份或多份的行為。《著作權法》第10條實際上采取了列舉式和概括式并行的模式定義復制,所以復制的具體方式并不限于第10條明確列舉的拓印、復印等七種情形,但是其他的復制方式應當是與這七種情形相類似、能達到相似效果的復制方式。因此著作權法雖沒有規定復制的本質特征,但通過對立法列舉的情形進行分析,可以初步判斷復制的構成條件。本文認為構成著作權法的復制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能夠再現作品內容,復制的核心是內容的復制,內容是作品的存在價值,所以復制首要的本質是內容的再現,這里內容的再現是非創造性的簡單再現,是不改變原作品獨創性的重復勞動,即可實現的再現。二是再現作品的載體是有形的物質性載體,在有形物質載體上再現作品,這是復制行為的目的之所在,復制一般是為發行、傳播而進行的。這也是復制行為與其他將作品再現行為,如表演行為等二次加工行為最本質的區別。三是再現的作品能夠相對持久穩定地固定在載體上,形成作品的有形復制件。
從復制的幾個條件來看復制是對作品的有形再現,因此復制品和原作品應當是“相同”而不是“實質性相似”,這是復制的應有之義。相同與相似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屬性,特別是在刑法領域,如假冒注冊商標罪刑法明確規定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構成犯罪,而使用近似、相似的商標只構成民事侵權,不構成犯罪。相同與相似有如此巨大的法律差異,這是因為相同與相似對權利人的權利侵害程度不同,從表面看來相同與相似差異不大,侵權行為人可能只是簡單地改變原作品,但是其實不然,相同會帶來混同,即消費者對合法的商品或作品與非法的商品或作品無法區分,而對權利人帶來巨大損害。相似則不然,相似雖也有較大可能使消費者發生誤認,但消費者只要注意區分還是能夠區分的,因此對權利人的損害相對要小一些,一般構成民事侵權而不是刑事犯罪。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行為人明知他人的合法權利是受法律保護的,而仍然赤裸裸地不加掩飾地實施侵害權利人權利的行為,其主觀惡性是極其嚴重的,而相似雖然可能只是稍加掩飾,但其性質已然不同,對他人的權利已然有了一定的認識,雖然仍然侵犯了他人的民事權利,但卻采取了相對委婉的、間接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種“擦邊”或者“占別人一點便宜”“沾點光”等思想,其主觀惡性相對地降低了。正如恩格斯所說“蔑視社會秩序的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行為人不加掩飾地復制發行和他人相同的作品,就是對他人權利的蔑視、對法律的蔑視,其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更大,理應作為犯罪處理。
相同與相似的區分還涉及到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區分,雖說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但是民法與刑法具體調整的范圍和保護的側重點并不一樣,所以民法與刑法所調整的行為范圍并不一樣。如刑法規定侵犯著作權罪有“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的內容、假冒注冊商標罪有“未經商標權人許可”的內容,這就涉及到民法與刑法調整范圍的不同。既然刑法規定未經權利人許可方構成犯罪,反之也就是說如果有權利人的許可則不構成犯罪,從這個角度來看,構成犯罪的行為必須是權利人有權許可的范圍內,是權利人的正當權利之內的。如假冒注冊商標罪中商標權人只有使用注冊商標的權利,未經注冊自己也不能使用與注冊商標相似的商標,更談不上授權他人使用,這是權利人的權利界限,但是可以禁止他人使用與自己注冊商標相似的商標,這就是主動權利范圍與被動保護禁止行為的范圍不一致,而刑法只保護主動權利范圍,只針對直接侵犯主動權利范圍的行為,從這個角度看,民法比刑法的保護范圍更廣,對權利的保護更周延、更嚴密,而刑法顯得更謹慎,范圍更小些。著作權領域同樣如此,著作權人只有許可他人復制發行自己作品的權利,沒有許可他人復制發行與自己作品相似的作品的權利,更沒有權利許可他人抄襲、剽竊自己的作品并發行,因此這些行為都是違反民法的侵權行為,但不構成犯罪,不屬于刑法所調整的范圍。
所以,刑法中侵犯著作權罪的“復制發行”行為,只能是再現與原作品相同的作品的行為才符合立法之本意。制作與原作品相似的作品之行為不能認定為“復制發行”行為,因此“實質性相似”規則不能簡單作為“復制發行”的認定標準。
三、復制發行之相同的認定標準
當然,相同并不是完全一致、絕對的相同,按照哲學的觀點,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事物,所謂“世界上不存在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所以這里的相同可以理解為“實質性相同”,即從一般觀念、感官上認為是相同的即可。如假冒注冊商標罪中相同的商標的認定,司法解釋基本上就是采用了這一標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刑法》第213條規定的“相同的商標”,是指與被假冒的注冊商標完全相同,或者與被假冒的注冊商標在視覺上基本無差別、足以對公眾產生誤導的商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進一步規定,關于《刑法》第213條規定的“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認定問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認定為“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一)改變注冊商標的字體、字母大小寫或者文字橫豎排列,與注冊商標之間僅有細微差別的;(二)改變注冊商標的文字、字母、數字等之間的間距,不影響體現注冊商標顯著特征的;(三)改變注冊商標顏色的;(四)其他與注冊商標在視覺上基本無差別、足以對公眾產生誤導的商標。這兩個解釋里都貫穿了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足以對公眾產生誤導而難以區分。本文認為,侵犯著作權罪的復制也應基本堅持這個標準,但由于注冊商標以平面商標為主,因而以視覺判斷為主,而著作權中的作品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所以其判斷標準也不一致,其最終區分標準應是,侵權作品是否對公眾產生誤導而使公眾在觀念上對二者不能加以區分。
具體而言,侵犯著作權罪中,復制行為中“相同”的認定應當主要考慮以下兩點;第一,是否改變作品的作者署名,是否改變作品名稱。對于傳統作品如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等而言作者是作品的第一標志。作者的知名度、對作者的認同,是我們通常選擇作品、了解作品的第一因素。作者是傳統作品的第一表征,公眾一般是由作者而關注作品。因此改變作品的作者署名后,再現的作品與原作品通常不會誤導公眾,二者將不會發生混同。如果將他人作品以據為己有為主觀目的,去掉原著作權人的署名而代之以自己的署名,將構成抄襲、剽竊。由于對抄襲、剽竊沒有比例限制,即使100%的完全照搬也可以認定為抄襲,因此抄襲、剽竊也具有再現他人作品的可能。抄襲與復制相比主要是侵犯了著作權人的著作人身權即署名權,其次才是著作財產權。二者對權利人的侵害很難說孰輕孰重,但刑法并沒有規定抄襲可以構成犯罪,所以改變署名的不構成犯罪。而對于網絡游戲軟件而言,名稱才是其對外表征,在網絡上一般沒人關注網絡游戲的作者是誰、著作權人是誰,游戲名稱通常是對作品區分的主要標志。也就是說,游戲名稱是決定玩家是否會對“私服”的非法游戲與著作權人合法游戲發生混同的關鍵因素。如前文表中涉及的案件1中行為人將《熱血傳奇》的游戲程序改為《神龍天下》網絡游戲,二者內容雖然基本相同,但公眾在觀念上一般不會產生二者是同一游戲的錯誤認識,更有可能認為是跟風游戲或者抄襲游戲,而并不會將其與著作權人的作品混同,因此只能說行為人構成民事侵權,而不能構成侵犯著作權罪的復制行為,不應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對于改變了網絡游戲的名稱而不會與合法游戲造成混同的行為,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只有不改變作品名稱直接導致與著作權人的合法作品產生混同,給著作權人帶來重大損失的行為,才能追究刑事責任。司法公正不是抽象的,不應僅僅將之作為司法目標或價值對待,而是體現在個案中的具體的、可感知的司法過程和司法結果。⑨梁平、陳燾:《基層司法公正實現路徑的微觀察——以發還改判案件講評機制為例》,載《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4期,第96-103頁。我們為了保護著作權人的權利而擴大了刑事打擊范圍,對違法者是不公平的、不正當的,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公平公正地處理每一個案件,既平等地對待每一個權利人,也要公正地對待每一個違法者。
第二,是否是作品內容的直接再現。復制本質是內容的再現,如果說作者署名是作品的外在表征,那么內容則是作品的內在表征,決定作品根本屬性的最終還是內容。如果行為人只是借用或者冒用著作權人的名字,利用著作權人的名聲、名氣來發行自己的作品,則不構成侵犯著作權罪的復制發行,當然美術作品是刑法有明確規定的特殊情況。前文表中案件的認定所謂“實質性相似”只是對作品內容的認定,其中判決2和4沒有詳細說明實質性相似的具體相似程度,判決4認定同一,只有判決3詳細說明了相似度。即該“私服”網絡游戲與《熱血傳奇》服務器端文件結構和應用功能的相同率達到86%,與《熱血傳奇》服務器端的內容相同率達到76%,與《熱血傳奇》的地圖文件相同率達到99%。如果“實質性相似”是專指內容的話,用在這里還是比較準確的,內容的再現,并不需要100%的相同,而是實質組成部分相同即認定為相同,所以實質性相似可以認定為內容相同。
因此,復制發行的相同的認定最終還是指復制發行的作品與權利人的作品無法區分,不管是從外在表征還是內在表征。以此為標準我們可以分析前些年爭議較大的珊瑚蟲QQ案,當時很多人對被告人表示同情,認為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按照這個標準我們認為人民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法院審理認為陳某以營利為目的,未經騰訊公司許可,擅自修改騰訊QQ軟件制作珊瑚蟲QQ軟件,其包含有騰訊QQ軟件95%以上的文件,且與騰訊QQ軟件的實質功能相同;同時,陳某還將珊瑚蟲QQ軟件上傳于其在互聯網上登記的網站“珊瑚蟲工作室”供他人下載,其行為已構成對騰訊QQ軟件的復制發行。這一論斷是正確的,從外部表征來看陳某對QQ軟件的發布雖增加了一定修飾語珊瑚蟲,但是并沒有能夠與QQ軟件相區分,很容易使人相信其是QQ軟件的不同功能的一個版本。從內部表征來看,其內容上含有QQ軟件95%上的文件,與QQ軟件的實質功能相同,特別是其與騰訊公司QQ軟件可以互聯互通,使公眾無法區分。因此構成侵犯著作權罪的復制發行,理所當然構成犯罪。
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保護創新首要的任務就是要保護知識產權。當前我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還存在很多問題,還遠遠不夠,但是這并不能成為擴大刑事懲罰的理由,并不是只有刑事司法才能發揮保護作用,并不是只有刑罰才能起到效果,民事責任、行政責任都是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途徑。法治秩序是人類社會的美好希冀,也是迄今為止能夠最大限度實現全民福祉的良好秩序。⑩梁平、馮兆蕙:《基層治理的法治秩序與生成路徑》,載《河北法學》2017年第6期,第123–131頁。但是法治秩序的實現是需要各個法律部門都發揮其應有作用,而不能只依靠刑法的懲罰。刑法應當是最后的手段,法治秩序的實現,民事責任、行政責任應發揮更大的作用。
Nowadays, the emergence of new methods of reproduction has brought many problems to judicial determination. The boundary between civil infringement and copyright crime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Being identical and being similar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infringing the online game copyright,substantially similar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identical by nature; it is therefore cannot simply regard similarity as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eing identical” in copyright crime should consider two major points: whether to change the author's signature and the title of the work; and whether the content of the work is reproduced straightforwardly.
copyright; copy and distribution; substantial similarity
霍文良,華北電力大學法政系教師,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地研究員
馮兆蕙,河北政法職業學院教授
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層司法改革研究(H B 1 4 F X 0 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