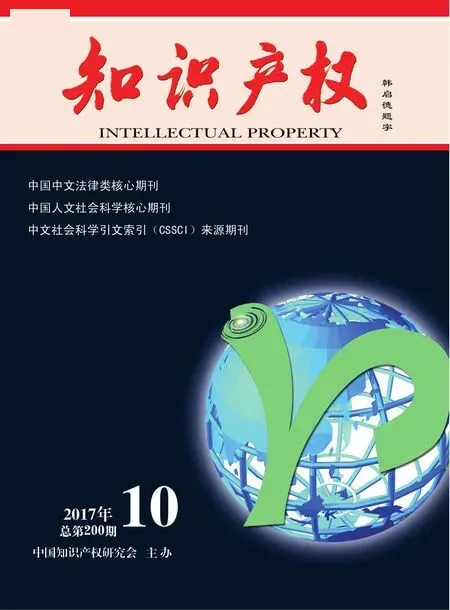知識產權的勞動價值論探析
梁心新
知識產權的勞動價值論探析
梁心新
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知識和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而知識產權在其中無疑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清晰地認識知識產權價值內涵,明確知識產權價值來源就顯得愈發重要。文章試圖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范疇內對知識產權價值問題進行討論,并分析知識產權價值與一般商品價值的異同。在此基礎上,對幾個重要概念進行辨析。
價值 使用價值 價值來源 勞動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他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①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頁。,“直接勞動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學勞動相比,同自然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相比……卻變成了一種從屬的要素”②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頁。。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即使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商品價值中來自直接勞動的部分已經降到很低的程度,而更多地來源于科學勞動。自從1996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知識經濟提出定義,“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③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機械工業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頁。,知識經濟更是蓬勃發展,知識和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而知識產權無疑在其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了將人的智力勞動成果從人的本身分離出來,并形成知識產權這一抽象物的過程,然后通過法律的方式將知識產權顯性地表達出來并予以確定。而這種分離的結果,使人的智力勞動成果(現在已經成為知識產權)能夠作為不依附于人的獨立物參與到生產交換過程中,并完全具備了商品的屬性,即使用價值和價值”。④梁心新:《知識產權制度未來發展試析——基于辯證唯物主義視角》,載《知識產權》2016年第1期,第123-124頁。“在客觀上,知識產權極大地擴展了商品的范圍,將抽象的人的智力勞動成果整合入商品的范疇”。⑤梁心新:《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的知識產權》,載《知識產權》2016年第9期,第73頁。因此,在當前發達的知識經濟和市場經濟環境下,研究知識產權價值問題愈發顯得重要。
一、知識產權價值的認識
價值的概念非常廣泛,既有哲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也有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價值概念。在實際使用中,價值概念是最容易混淆的。因此,為搞清楚知識產權價值是什么,我們不得不追溯一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理論中的價值問題。國內絕大多數教科書直接將價值定義為“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類勞動”,這無疑是對的,但我們有必要把價值概念展開。首先,價值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一切社會狀態下,勞動產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歷史上一定的發展時代,也就是使生產一個使用物所耗費的勞動表現為該物的‘對象性’屬性即它的價值的時代,才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⑥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77頁。“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么不言而喻,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⑦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61頁。因此,價值不是伴隨勞動產品而來的自然范疇,而是社會發展到商品交換社會以后才逐漸形成的概念,是商品經濟關系下特有的社會范疇。其次,價值是一個抽象概念。“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⑧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51頁。因此,價值是剔除掉具體勞動后人的抽象勞動的表達,只能有量的不同,而沒有質的分別。再次,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⑨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53頁。“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⑩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60頁。“對于價值本質的理解,不能從商品的物理屬性去探討,只能從人的本質和生產關系的角度去探討……”[11]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9頁。因此,價值的實體和唯一源泉只能是人的勞動,反映的是人的勞動在創造物質財富時的耗費。這里需要注意,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并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12]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57頁。。
通過對價值內涵的展開可知,知識產權作為商品,其價值的衡量依然不能超出勞動價值論的范疇,衡量的依據必然還是凝結在知識產權中的人的勞動耗費,而不包括任何的其它的內容和因素。我們在考察一個對象物是否具有價值時,需要看三個條件:一是要具備有用性,二是要用于交換,即滿足他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三是要包含人的勞動。我們以此標準來審視即可發現,知識產權的有用性和包含人的勞動是毋庸置疑的(這里的“毋庸置疑”是從總體而不是個別角度講),但是否用于交換卻要看具體情況。只有用于交換的知識產權才具有價值,而自用的則不具有價值。例如,一家高新技術企業生產了10個專利,其中5個通過交易的方式賣掉,則這些專利具有價值;剩余5個自用,則不具備價值。在這個問題上通常是比較容易混淆的,“……價值并不是物自身的價值,而是人的勞動在作為商品的物中的體現并經過交換而得以實現的”[13]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60頁。,價值是為了衡量人的勞動以便于交換的,而不是用來衡量物的有用性的。
二、知識產權價值的來源
從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知道,只有用于交換的知識產權才是商品,才具有價值,其價值來源只能是人的勞動,是人的抽象勞動的體現,反映的是人的勞動在創造物質財富時的耗費,這是由價值的定義所規定的。因此,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講,知識產權的價值,就是凝結在其中無差別的人的抽象勞動。知識產權價值量包括,生產知識產權轉移的物化勞動和消耗的活勞動的總和。但這只是從價值最一般的意義上講的,即簡單商品經濟背景下的個別商品價值。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重提價值問題,已經與第一卷當中的價值不是一回事情了。在這里,馬克思考慮了競爭和供求的因素,從價值決定到價值實現,完成了價值的兩次轉化。“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但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14]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201頁。這里明確提出了個別商品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繼而轉化為生產價格,即價值的兩次社會轉化。第一次轉化就是市場價值的形成,是部門內競爭形成的,“必須始終把市場價值——下面我們就要談到它——與不同生產者所生產的個別商品的個別價值區別開來”。“市場價值,一方面,應看作一個部門所生產的商品的平均價值……”[15]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199頁。。第二次轉化是生產價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不同部門間競爭從而影響供求關系,體現為比例關系。“如果某個部門花費的社會勞動時間量過大,那么,就只能按照應該花費的社會勞動時間量來支付等價。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總產品——即總產品的價值——就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勞動時間,而等于這個領域的總產品同其他領域的產品保持應有的比例時按比例應當花費的勞動時間。”此外,在分析價值轉化的同時,馬克思還解釋了資本追求增值的權利實現情況:“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的產品來交換。這些資本要求從剩余價值的總量中,分到和它們各自的量呈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們的量相等時,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16]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196頁。“資本作為一種社會權利,必然要求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要求按照其在社會總資本中占有的份額分享這種權利。”[17]《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十五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頁。
到這里,我們看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內涵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說最初的定義還有李嘉圖機械價值論的影子,好像價值是一種固定的東西存在于商品之中,那么到資本論第三卷時,在肯定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的前提下,價值已經轉化為一種價值形式,從而解決了為什么商品價值不能由耗費在它上面的直接的勞動量來進行衡量的問題。
我們可以用以下兩個過程式來簡單對照價值形式的轉化:
個別勞動時間(個別商品生產)——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部門內競爭)——另外一種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18]“必要勞動時間在這里包含著另一種意義。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只有這樣多的勞動時間才是必要的……社會在一定生產條件下,只能把它花費的社會勞動時間中這樣多的勞動時間用在這樣一種產品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第二卷,第545–546頁。(部門間競爭)。
個別價值(個別商品生產)——市場價值(部門內競爭)——生產價格(部門間競爭)。
在分析部門內競爭的時候,我們遇到了知識產權與一般商品(包括物質商品和服務商品)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知識產權個體的絕對唯一性,即每個知識產權在實質上都是完全不一樣的(是法律明確要求的,并經過法律的審查程序后確認的),而不僅是由于實際生產或服務過程造成的可以忽略的差別。因此,從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不存在馬克思當時所講的同種知識產權生產者的集合(即部門),或者說,每一個知識產權生產者即是自身生產者的集合,結果知識產權價值決定中的部門內部競爭消失了,決定知識產權價值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生產同種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的部門平均)與生產該知識產權的個別勞動時間唯一對應了,即第一必要勞動時間與個別勞動時間唯一對應了。
我們可以通過考察知識產權與服務類商品的區別來看清楚這個問題。我們講,知識產權之所以沒有部門內競爭(雖然只是理論上),不僅是因為每個知識產權本身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在服務業領域體現得也非常突出),而且從根本上來講,每個知識產權就是不同種類的商品。服務類商品雖然因為提供具體服務的人的差異而實際上使得每個具體的服務商品存在差異(應該說這是相當普遍的情況),但這些服務商品是可以建立統一標準的,不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就像金融服務,即使有統一的業務標準和服務內容,但實際上每一個銀行業務代表給每一個客戶提供的具體的金融服務總是不同的,但這種不同顯然不是本質上的不同。而知識產權,以發明專利為例,明確要求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具備新穎性和創造性。新穎性是指該發明不屬于現有技術,即現實不存在。創造性是指與現有技術相比,該發明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即實質不相同。因此,每一個知識產權在法律上均是現實中沒有的,且在實質上是不相同的,這與當時馬克思大工業時期所講的同種商品(主要是工業產品和服務產品)具有非常大的差別。
盡管如此,這也僅僅是依據知識產權的法律規定進行的理論討論,并且是從單個知識產權內部絕對差異來討論的,如果充分考慮知識產權之間存在的相當程度的替代性的話(相同的技術領域、相近的技術手段、相似的技術效果,等等),我們仍然可以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的知識產權的生產者集合會產生類似于部門內競爭的情況,即知識產權生產依然要經過第一次價值轉化的過程。而之所以要分析清楚知識產權與一般商品的區別,是為了便于我們更好理解知識產權價值的第一次轉化問題。
綜上,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作為商品的知識產權的價值,不能單純地由耗費在知識產權生產上的勞動來衡量(包括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活勞動新創造的價值),而必須充分考慮價值的兩次社會轉化,即在生產該知識產權的生產資料價值轉移和投入的活勞動消耗形成的價值基礎上,經過部門內競爭和部門間競爭兩次價值的社會轉化,完成社會總的剩余價值的再分配,從而從形式上最終確定知識產權的價值。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將上述文字歸攏一下:
設定一項知識產權的價值為V:

V1是生產知識產權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V2是知識產權生產者勞動創造的新價值,V3是經過部門內競爭增加或減少的價值,V4是經過部門間競爭增加或減少的價值。這里需要注意:本公式中的V3、V4代表的是社會范圍內價值轉移的增量或減量,不是轉移后的最終量;V3和V4可以增加,也是可以減少的,體現的是知識產權價值在社會范圍內的再分配情況。
這樣,我們也就容易理解為什么有些知識產權的價值比較高,有些卻很低。對于價值比較高的知識產權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首先,是知識產權生產使用的生產資料的價值(V1)比較高,包括高端的開發設備、實驗器材、研發環境,等等,因此轉移到知識產權中的價值也比較高;其次,是知識產權生產者所消耗的活勞動(V2)比表面看起來要多得多,設計、研究、開發等復雜勞動遠遠高于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再次,是由于通過市場價值和生產價格兩次價值的社會轉化,完成了勞動創造的價值總量在全社會(部門內和部門間)的再分配,知識產權價值量包括了在全社會的總剩余價值中多分配的利潤V3+V4。第二種情況,雖然知識產權生產的V1+V2比較低,但V3+V4的轉移價值比較高,因此知識產權的實際價值也比較高。這樣,在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知識產權“增值”了,這里的“增值”是相對于耗費在具體知識產權生產上的勞動(包括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活勞動新創造的價值)產生的價值而言的,它的來源是經過價值的兩次社會轉化完成的社會總的剩余價值的再分配,即V3+V4。而對于價值比較低的知識產權,也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雖然生產知識產權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V1+V2,但經過部門內競爭和部門間競爭,實際上V3+V4是減少的,抵消了部分甚至全部V1+V2,因此實際價值遠遠小于直接投入的價值。第二種情況,知識產權生產的V1+V2本身比較低,同時V3+V4也是減少的,導致知識產權的實際價值更低。
三、幾個重要概念的辨析
依照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我們需要對現在知識產權價值認識中存在的幾個誤區進行澄清。
(一)知識產權價值與知識產權使用價值
第一,“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19]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54頁。,使用價值是對對象有用性的表述,而價值是衡量人的勞動在社會中的交換關系。使用價值是具體勞動的產物,而價值是抽象勞動的衡量,價值只能有量的差別而沒有質的差別,因此,價值中不包含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第二,“隨著物質財富的量的增長,它的價值量可能同時下降。這種對立的運用來源于勞動的二重性”[20]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59頁。。價值只是表示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商品包含的價值不能作為使用價值的有用性大小的評估依據。我們絕不能拿知識產權的使用價值(有用性)來衡量知識產權的價值,因為二者并沒有必然的數量相關性。
(二)知識產權價值與知識產權價格
馬克思的價值規律認為,價值決定價格,價格因供求關系在價值上下波動,當平均利潤率趨勢形成后,價格就不再圍繞價值波動,而是圍繞生產價格波動。因此,雖然價值是價格的基礎,但價值和價格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而且在實際生產中,價值與價格甚至完全可以出現背離的情況,即“價格可以完全不是價值的表現”[21]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頁。。而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卻認為:“我們討論價值是由效用所決定、還是由生產成本所決定,和討論一塊紙是由剪刀的上邊裁還是由剪刀的下邊裁是同樣合理的。”[22]馬歇爾著:《經濟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版,第40頁。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需求和生產成本(供給)共同決定的,當供求雙方達到均衡時產生的均衡價格就是商品的價值,這就混淆了價值和價格概念,用價格代替了價值。而目前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中市場法經常采用的就是供求理論作為價值評估依據,混淆了價值和價格的概念,用價格評估取代了價值評估。
(三)知識產權創造價值與勞動創造價值
知識產權所包含的技術應用到生產過程,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在投入相同的人的勞動的情況下,能夠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物質財富),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要注意,是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而不是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勞動價值論的核心就在于,新的價值創造只能來源于人的勞動。知識產權作為人的智力勞動成果的商品存在,再投入到生產過程中時,只是作為生產資料轉移其自身價值,而不能創造新的價值。這絕沒有否認知識產權本身包含價值,甚至是極高的價值,也并不否認知識產權所包含的新技術應用到生產中能夠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在等量勞動下生產出更多更好的使用價值,因為這正是當今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重要原因所在。
我們正處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已經發生了很多重大變化,但是,目前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形態仍然主要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因此,勞動價值論就不會退出歷史舞臺,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正如恩格斯所講:“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提供這些研究使用的方法。”[23]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74–575頁。這就需要我們在繼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同時,也有必要結合時代發展的新特點,繼續發揚勞動價值論的內涵,以適應我們時代發展的需要。
With the rising of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re playing an ever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oubtedly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value and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scope of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value of general commodities. On the basis,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are clarified.
value; use value; source of value; labor
梁心新,國家知識產權局保護協調司處長
本文中的知識產權主要指由人的勞動創造生產的技術類知識產權,包括專利、集成電路布圖設計、計算機軟件著作權、植物新品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