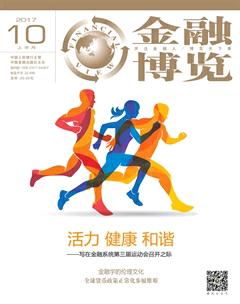德國經濟去杠桿的經驗之路
謝亞軒 高明
當前市場“新周期”之爭中有三個關鍵詞的關注度最高,一是供給出清,二是需求復蘇(尤其朱格拉周期),三是金融周期(涉及信貸與房地產)。三者之間的關系是,“新周期”應產生于需求復蘇,而供給出清是需求復蘇的前提,但杠桿率高企、金融周期向下,會在中長期之中抑制需求,非金融企業要在增速下降的情況下償債,因而會收縮投資,家庭部門要在房產財富減值的過程中償債,因而會收縮消費。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由于經濟下行失業增加,政府出手救助,德國的杠桿率也出現了加速上升的情況,但相比于其他經濟體,德國在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較為及時地實現了去杠桿,避免了債務依賴癥。德國的經驗表明,去杠桿和經濟穩定增長是可以兼得的,雖然這確實需要很多特定條件與特殊措施,但并非不可為之。因此,我們也不應該對金融周期向下所形成的經濟下行壓力過于悲觀,因為這種風險是可以通過努力緩解甚至消除的,這正是分析德國去杠桿經驗的意義之所在。
德國:去杠桿的“三好生”
2008年金融危機后,德國是G20國家中成功去杠桿的典范。G20整體非金融杠桿率在2009年、2015年都出現了中樞的躍升(幅度大約都是16個百分點)。歐元區杠桿率在金融危機之后加速上升,升幅最高時接近50個百分點,直至2015年后才出現觸頂跡象。美國在危機前快速上升,危機后逐漸穩定在250%左右。但德國的杠桿率一直處于相對低位,大致在175%~195%;而且就算在危機爆發時期因采取危機救助措施也出現過杠桿率快速上升,但在2012年就最早開始去杠桿化,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已實現16個百分點的降幅,完全回歸到了危機前的水平。
危機之前,正是美國家庭住房貸款及其證券化產品在2001~2007年的過度增長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進而引發債務減記、經濟增長降速、通脹收縮等一系列的不良反應。危機之后,為對沖家庭部門與非金融企業大幅度去杠桿的負面影響,發達經濟體(包括德國在內)的政府杠桿率普遍出現加速上升。在這一過程中,諸多經濟體都對政府債務產生了不同程度的依賴,但德國在2012年后就成功實現了政府去杠桿化,化解的政府債務約占名義GDP的12.7%。德國不僅在企業、家庭兩部門去杠桿,政府部門也成功實現去杠桿。根據定義“宏觀杠桿率=信貸存量/名義GDP”可得,影響杠桿率的上升可分解為兩部分,一是信貸加速增長(分子效應),二是名義GDP增速下行(分母效應)。結合這兩大影響因素,我們對德國杠桿率進行詳細分析。
分母效應:為何德國名義經濟增速在危機后不降反升?
首先,危機后德國的貿易順差仍能夠保持穩定增長。國際貿易順差的收窄或逆差的擴大,一方面會使經濟體內部出現資金缺口,增加信貸需求,通過分子效應提升杠桿率;另一方面會拖累經濟增長,通過分母效應提升杠桿率。
現實之中,首先是金融危機之前的美國、主權債務危機之前的歐元區(德國除外)與英國,在逆差占GDP比重持續擴大的過程中,總杠桿率也出現了加速上升。而德國的順差占比只是在危機爆發的當年出現了下降(從6.8%降至5.6%),這事實上也使德國總杠桿率從2008年第二季度的180%升至2010年第四季度的199%;此后開始企穩,并于2010之后重回上升路徑,從而助力了杠桿率的去化。同樣,危機后美國杠桿率年均增速從3.4%降至0.25%,歐元區杠桿率年均增速從1.54%降至0.93%,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貿易逆差收窄的支撐。
其次,德國的債務積壓問題較小,債務負擔輕。經驗分析顯示,非金融部門總杠桿率與其名義經濟增速之間存在負相關性,而德國的總杠桿率是發達經濟體中最低的之一。杠桿率高企不利于經濟增長或通脹目標的實現機制是:償債壓力過度,一方面債務人會減少開支,并低價出售產品與資產用于還債甚至選擇破產,另一方面債權人因風險上升而降低信貸供應,這會導致全社會信貸收縮、支出水平下降、通脹收縮,而通脹收縮又會進一步增加償債壓力,形成惡性循環。
分子效應:德國如何控制
非金融部門信貸的過度增長?
一是防止房價與住房貸款形成正反饋關系。金融危機之前,以美國為代表,發達經濟體的家庭部門大幅度加杠桿,其背景是房地產成為居民財富的主要類型,而房地產貸款成為新增貸款的主要部分。房地產等存量資產的交易會形成信貸規模與資產價格的上升循環,推升杠桿率,但對GDP增長的推動作用極其有限。
德國之所以能在金融危機之前控制住房價,在量化寬松與外資流入導致房價上升時期能控制住房貸,與其特定的住房管理制度與住房金融制度有密切關系,前者包括根據人口收入結構規劃住房供應、租賃市場發達、對房地產交易設定高稅率等,后者以住房儲蓄合同貸款模式(存款達到貸款金額的40%~50%才能申請貸款)為核心。
二是嚴格控制財政赤字。與總杠桿率一樣,降低政府杠桿率的途徑也有兩條,一是把赤字率控制在限度之內,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為3%;二是提升名義GDP增速,這既能通過分母效應降低杠桿率,也能提高財政收入,進而減小財政赤字。
金融危機之后的2到3年里,發達經濟體的名義GDP普遍負增長,但財政卻存在剛性支出,這使得財政赤字急劇擴大,也進一步導致政府部門債務加速累積。隨后在2010至2016年的恢復期中,德國嚴格執行財政紀律,有效收窄赤字,控制住了政府債務的積壓,成為危機后少數擺脫政府債務依賴的經濟體之一。歐元區整體的名義GDP恢復要弱于德國與美國,在財政赤字控制上雖然好于美國,但仍連續5年超過上限。直至2014年經過財政整肅,歐元區整體的赤字率終于收窄至3%的限度以內,才使得歐元區(德國除外)的政府杠桿率出現了收縮跡象。美國雖然名義GDP的復蘇好于歐元區,但由于財政赤字控制最差,導致政府杠桿率持續攀升,2012年到達峰值后居高不下。不過,與歐元區外圍國家相比,美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具有更高的融資地位,因而也能負擔更高比例的債務。endprint
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中國和德國最大的不同是杠桿率水平的差異。不過,杠桿率的直接對比并沒有實際意義,因為兩國經濟結構、信貸結構存在較大差異。
第一,加杠桿的用途不同。中國以非金融企業為加杠桿的主力,根源在于投資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而發達國家高杠桿的主要成因一是居民住房貸款,二是政府赤字,反映其已進入消費型社會的特征。兩種加杠桿模式的區別在于,中國加杠桿會形成生產性資產,有現金流入;而發達國家加杠桿大部分不會形成可以帶來收入的資產。
第二,儲蓄率水平不同。中國總儲蓄率高于發達經濟體,高儲蓄率能在一定程度上緩沖債務危機爆發的風險。
第三,宏觀調控理念不同。對于中國政府,短期要穩定經濟增速與保障就業,中期要確保“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標,長期要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以是積極主動的。對于德國,首先追求穩定反對通脹,這源于德國經歷過兩次惡性通脹;其次是秩序自由主義理念,這一理念與凱恩斯主義相反,不主張在衰退中使用擴張性政策,反而認為財政緊縮才是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基礎。
德國經驗的啟示。一是杠桿率高企不利于經濟增長或通脹目標的實現。而去杠桿要同時有利用分子效應(控制各部門債務過度擴張)和分母效應(提升名義經濟增速),既要防止刺激過度造成信貸激增,又要避免激進的去杠桿引發硬著陸的風險。支出的績效是實現兩個方面權衡的關鍵所在。
二是在全球貿易萎縮時期仍然保持貿易順差的擴大,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走制造業強國之路,憑借技術、勤勞上的競爭來獲取貿易順差,也是中國應該堅持的發展方向。
三是存量資產交易是資源重新分配的零和博弈。加杠桿意味著透支未來或剝削他人(通過加速通脹或違約風險等形式),以加杠桿的方式進行存量資源交易,是經濟資源的極大浪費。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與德國去杠桿相對成功的經驗表明,控制私人部門的信貸擴張與控制房地產等存量資產的價格上漲是密不可分的,需要建立雙層次的防控機制。
四是歐債危機的教訓表明,在衰退時期,財政空間有限的政府,將會面臨是否進行財政整肅的矛盾選擇。縮小赤字,則會進一步增加經濟下行壓力;放任赤字擴張或主動進行刺激,雖能托底增長與就業,卻會加劇政府債務問題。從德國經驗來看,財政整肅應在日常著力,留出政策空間;衰退時期的托底政策應該有效且快速,及時安排退出計劃,避免債務依賴。(謝亞軒為招商證券研發中心首席宏觀分析師,高明為招商證券研發中心博士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