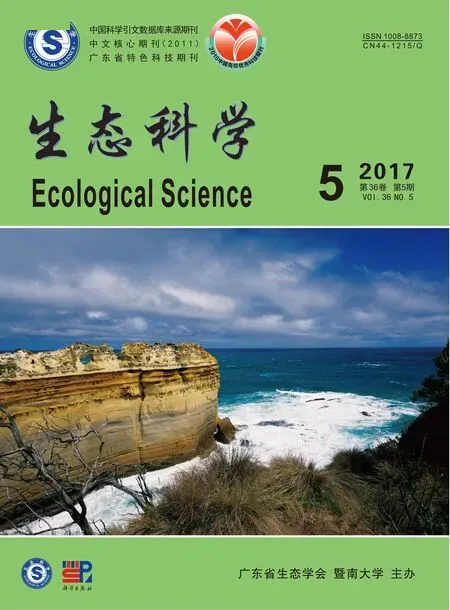貴陽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研究
2017-11-10 03:11:56蔡振饒李玉紅李旭東
生態科學
2017年5期
蔡振饒, 李玉紅, 李旭東
貴州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 貴陽 550001
貴陽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研究
蔡振饒, 李玉紅, 李旭東*
貴州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 貴陽 550001
隨著中國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快速推進, 生態脆弱城市的環境問題日益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通過構建貴陽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指標體系, 以綜合指數評價模型為基礎分析貴陽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發展趨勢, 并利用協調發展度模型揭示貴陽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的演化軌跡。結果表明, 貴陽市城市化綜合指數與生態環境綜合指數總體上呈上升趨勢, 兩大系統的發展均依賴于各子系統的共同進步, 不同子系統與指標對綜合評價體系具有不同的作用;協調度的演變明顯表現為不同的兩個階段, 而協調發展度演變表現為線形的上升趨勢, 由嚴重不協調階段逐漸步入高級協調階段。只有兩大系統共同發展, 二者的耦合關系才會逐漸增強。
城市化; 生態環境; 耦合; 協調; 貴陽
1 前言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中期階段, 快速的經濟增長與城市化進程對生態環境的脅迫作用日益突出[1]。目前, 國內學者對城市快速發展地區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交互關系已有大量的研究[2-4]。然而受較弱的技術、制度、城市文明與系統自身恢復力影響, 西部地區城市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與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具有明顯的脆弱性[5], 如何把握西部生態脆弱地區……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2022年3期)2022-05-23 13:46:54
中國核電(2021年3期)2021-08-13 08:56:36
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21年3期)2021-08-13 08:32:18
遼金歷史與考古(2021年0期)2021-07-29 01:06:54
科技傳播(2019年22期)2020-01-14 03:06:54
民用飛機設計與研究(2019年4期)2019-05-21 07:21:24
家庭影院技術(2018年11期)2019-01-21 02:20:52
華人時刊(2017年21期)2018-01-31 02:24:01
汽車工程學報(2017年2期)2017-07-05 08:13:02
北方交通(2016年12期)2017-01-15 13: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