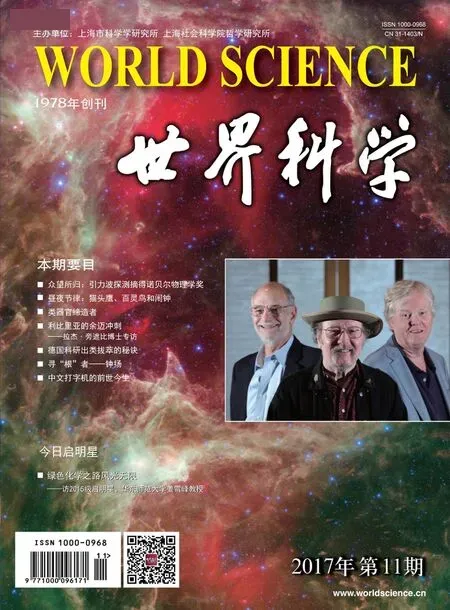德國科研出類拔萃的秘訣
胡德良/編譯
德國科研出類拔萃的秘訣
胡德良/編譯
無論問及哪位德國研究人員“為什么德國的科學基地正在繁榮發展”,他們一定會提到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他們會說,這位世界上最強大的女人并沒有忘記自己的根本——東德物理學家。
全球10年金融動蕩期間,默克爾政府的年度科研預算以典型的德國方式獲得了穩定的、可預測的增長,激發了大學之間的競爭,促進了公共資助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在默克爾的監督下,德國在可再生能源和氣候研究領域保持了世界領先地位,在保證對基礎研究大力支持的情況下,政府對其他領域的影響也在加大。
越來越多的外國研究人員選擇在德國發展事業,而不是選擇像美國或英國這樣的傳統人才吸引國。德國局勢安全,但發展緩慢,這一點是舉世聞名的,然而德國看起來開始呈現龜兔賽跑之勢。
德國慕尼黑馬普學會稅法和公共財政研究所所長、德國主要資助大學研究的機構——德國科學基金會(DFG)副會長沃爾夫岡·施恩(Wolfgang Sch?n)說:“德國是成功的,其背后的原因不僅僅是科學預算或某種‘默克爾效應’。像默克爾一樣,德國有著深厚的科學根基。”
在20世紀的動蕩形勢之前,德國的科技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其創建的慣例至今仍有許多國家在遵循。男性主導的等級制度和普遍的、死板的法規留下了一些殘余觀念,雖然德國一直在跟這些觀念做斗爭,但是德國的研究看起來一如既往,依然強大。特別是在全球似乎都對科學越來越無動于衷的階段,德國的這種勢頭難能可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肯尼斯·普雷維特(Kenneth Prewitt)說:“如果美國的科學政策制定者和預算決策者愿意再次從德國那里學習經驗,我會很高興。”
德國現代科學結構的基礎是兩個世紀前由普魯士教育家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的理念,他率先提出的諸多觀點在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影響力。例如,他提出建議——大學教授在從事教學的同時也要進行前沿領域的研究。
他的理念是:教育應該廣泛而深刻,學術生活應該不受政治和宗教的影響……這些對德國人而言仍然刻骨銘心。柏林高級研究院秘書長索斯藤·威廉米(Thorsten Wilhelmy)說:“洪堡體系是我們的DNA,即使在艱難時代,政治家也不想削減基礎研究,這就是其中的原因。”
這些理念經歷過劇烈的政治動蕩。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使科學走入歧途,使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1949年,德國被重建為兩個國家,兩國在相互對抗的政治制度下重新積累各自的科學實力。
西德民主立憲制仍然有效,該國宣稱:“藝術與科學、研究和教學應該是自由的。”為了確保中央集權和濫用權力的情況永遠不會再度發生,西德創建了一個高度聯邦化的國家,文化、科學和教育的責任由各州來承擔,這種特征注定對大學的發展產生正負雙面影響。
相比之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實施集中研究策略,研究受到嚴格的控制。東德科學家跟西德科學家是隔離開來的,隨著東德經濟的逐漸衰敗,其政治制度也變得越來越蒼白無力。默克爾是在這種體制中長大的。1978年,她畢業于萊比錫的卡爾·馬克思大學,獲得物理學學位,之后進入柏林的中央物理化學研究所——東德最負盛名的研究中心之一。在那里,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量子化學家喬基姆·索爾(Joachim Sauer),并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博士學位。
1990年,當兩個德國統一時,西德特別委員會評價了東德科學家的能力。許多人失去了工作,但索爾被接受,調入了柏林的洪堡大學。以前沒有公然表明政治立場的默克爾欣然參與了民主政治,很快就加入了中右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她頑強地爬到該政黨頂層領導的位置,并于2005年成為德國第一任女總理。2009年和2013年也分別贏得了聯邦選舉,而且看起來大有保住這一職位之勢。在德國,擔任政府首腦沒有任期的限制。3月份,她發表意見說:“我本人來自基礎研究領域,而且我也總是說,你不可能預測到這個領域的東西——但是你不得不為其發展留出空間。”
穩定的支持
德國公共資助的科學組織有五大支柱科研機構:大學及其四個獨特的研究機構,每個機構都是以德國歷史上的科學巨人命名的。
馬普學會成立于1948年,以諾貝爾獎得主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命名,目前管理著81家基礎研究所。這些研究所的所長都會得到額外的預算資金,他們擁有資金的支配權,可以用來開辟自己的研究方向。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通常每年可以獲得200萬歐元的基本運維資金來實施他們的研究計劃,其中不包括主要的設備采購資金。1949年弗勞恩霍夫協會成立,該協會致力于應用研究,是以巴伐利亞物理學家約瑟夫·馮·弗勞恩霍夫(Joseph von Fraunhofer)命名的,他是精密光學的先驅。國家研究中心根據政府優先事項實施大型戰略性研究計劃,目前該中心被收編于亥姆霍茲協會。亥姆霍茲協會是以開創性生理學家兼物理學家赫爾曼·馮·亥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命名的。一批其他的科研機構和設施被收編于由博學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命名的協會中。
早在1949年,一項協議規定:聯邦政府跟各州一起分擔這些研究機構的費用。但是一般說來,各州必須要為自己的大學提供財力支持。這樣的大學有大約110所,另外還有230所科技應用大學,這些大學主要是為產業界培養勞動力,不能授予博士學位。
米爾海姆市馬普學會煤炭研究所所長費爾迪·舒斯(Ferdi Schüth)說:“這種結構的清晰度和透明度迎合了德國人愛好井然有序的心態,這讓包括政壇官員在內的外界人士更加容易理解。”
西德在戰后經濟奇跡期間,對科學研究的支持迅速加強。盡管德國的統一使該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多年來政界人士一直對科研保持著穩定而強勢的支持。政府對所有研究機構和DFG的支持每年都保持增加5%。直到2015年,聯邦政府和各州之間簽訂的“研究和創新條約”規定,對科研支持的年增長幅度有所下降,這種下降態勢會持續到2020年,但是增幅仍然保持在令人羨慕的3%。
馬普學會主席、化學家馬丁·斯特拉特曼(Martin Stratmann)說:“未來的資助有保障,這真正地能夠使我們以長遠的目光對研究戰略進行規劃。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是其他國家幾乎不具備的優勢。”
支持資金流
20世紀70年代后期,免疫學家多洛雷斯·申德爾(Dolores Schendel)在慕尼黑大學做了兩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她深知在德國搞研究意味著什么。正是對長期資助充滿了信心,使得申德爾沒有返回自己的祖國——美國。她本想僅僅幫助慕尼黑大學的骨髓移植計劃建立一個小鼠實驗室,但是她發現實驗室的設備是富有吸引力的,而且隨著她的研究成果可轉化性越來越強,她的成果不再適合做成系列高端論文,她知道她可以依靠有保障的地方資助。后來,為了擴大研究規模,申德爾轉移到慕尼黑亥姆霍茲研究中心。她創建的一家新公司被收購時,她成為慕尼黑免疫治療企業——醫學基因公司(Medi gene)的執行總裁兼首席科學官。目前,她正在對候選的癌癥疫苗進行臨床試驗。申德爾說:“若是在美國,我不敢確定我是否能夠取得這些成就。在美國,資金的支持在穩定性上往往比較欠缺。”
1990年,國家統一造成了混亂局面,這迫使該國要解決某些制度問題,如各研究機構之間缺乏合作等問題。因此,政界人士開始鏟除合作道路上的諸多障礙。
1999年,默克爾之前的聯邦政府是社會民主黨和綠黨之間的一個聯盟政府,該政府修訂了一項法律,要求由各州政府為大學做出從分配預算資金到進行學術任命的所有決定。此后,各州逐個開始允許大學來管理自己的事務了。
所有大學在傳統上被認為是具有同等地位的。直到2005年,政府為大學提出一項重大改組行動,推出了“卓越計劃”。現在,該計劃已經很成熟,它鼓勵大學之間相互競爭,獲取聯邦資金,推動頂尖水平的研究,促進研究生院建設,而且最重要的是促進“卓越群體”建設——推動跟其他研究機構的科學家進行大規模合作。此外,在所有類別中勝出的大學也將獲得“精英大學”的稱號,還會獲取額外的資金支持。
2005年晚些時候,默克爾成為總理,她任命跟她志同道合的同事兼朋友安妮特·沙萬(Annette Schavan)擔任教育和研究部長,沙萬通過一系列巡查活動,推動了卓越計劃,從根本上改變了德國的大學。到目前為止,聯邦政府向該計劃投入了46億歐元,在各輪巡查中獲得精英稱號的大學共有14所。那些還沒有獲得這個稱號的大學,正在努力爭取獲得精英稱號,通過進行群體內部合作,增強了競爭力,開辟了其他的支持資金流。在德國科學領域,一度孤立的科研機構目前正在進行合作。
默克爾和沙萬捍衛了國家法律,允許聯邦政府直接資助大學的研究,允許大學拿出高薪來吸引或留住水平最高的科學家。作為公務員,德國大學教師的收入通常少于其他國家的科學家或產業界的科學家。
由于所有的這些變革,德國大學的世界排名已經攀升。2005年,只有9所德國大學出現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期刊排名前200位中。目前,有22所大學進入前200位。在絕大多數年份中,慕尼黑大學在德國大學排名中都是名列榜首,在每一輪卓越計劃中都能勝出,該校從2011年的世界排名第61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30位。
自從2005年以來,物理學家埃克塞爾·弗雷穆特(Axel Freimuth)一直擔任科隆大學的校長。他說:“科隆大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經變得難以辨認出來。”弗雷穆特看到了卓越計劃所帶來的巨大轉變和大學教學的轉型。在弗雷穆特成為校長的時候,德國開始從本國由來已久的特殊文憑制度轉變為歐洲標準的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制度。這樣,在3~5年的時間里能夠更加有效地培養學生。隨著大學自治的來臨,弗雷穆特創建了一個新的管理體系。他說:“對于一所大學來說,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從戰略上去行動,這其中有一種全新的精神。”
群體研究熱
與此同時,群體研究熱在德國已經蔚然成風。沙萬實施了幾項舉措,讓不同支柱領域的科學家一起搞研究,并與產業界合作。最引人矚目的是,她借助亥姆霍茲協會的影響力創建了一個國家衛生研究所網絡。在全國范圍內,亥姆霍茲協會將衛生研究機構的力量集中起來,這些研究機構中包括對神經退行性疾病或代謝性疾病等病變的研究。
柏林方面正在進行試驗,將查理特教學醫院和馬克斯-德爾布呂克分子醫學中心(亥姆霍茲協會下屬的一個中心)的研究力量匯集在一起,組成一個被稱為柏林健康研究院的轉化研究機構。巴登符騰堡州已經將數億歐元的資金投入到“網絡谷(Cyber Valley)”計劃中,該計劃于2016年12月推出,將所有區域性人工智能研究整合在一起,得到了寶馬、戴姆勒、保時捷、博世和臉書等大型公司的大力支持。
同時在海德堡大學和德國癌癥研究中心任職的神經科學家漢娜·莫耶(Hannah Monyer)說:“這種群體研究確實有很多優勢。”德國癌癥研究中心是亥姆霍茲協會下屬的一個中心,同樣位于海德堡市。盡管群體研究要求研究人員花更多的時間來進行交談和進行組織安排,但是莫耶說:“在當今,這是我們能夠采取的最佳行動。”在一輪卓越計劃中他們創建了一個研究群體,當她的研究工作暫時涉及不熟悉的領域——疼痛機制時,研究群體為她省去了大量的工作。她不必從頭開始學習一切,而是與當地的行為實驗室進行了密切協作,該實驗室為她提出了建議,提供了設備和技術支持。
大規模合作仍然處于測試階段。血管生物學家霍爾格·格哈特(Holger Gerhardt)在倫敦克里克研究院擁有一個固定的職位,2014年他離職加入了柏林健康研究所的一項計劃。他說:“我知道這是一項特大型的實驗,但是我覺得或許我真的能夠在這里創造出新的成果。”

在德國文化中,人們追求管理秩序和道德秩序。有時,研究人員目前所享受的條件改善會受到這些秩序的挑戰。格哈特說,他自己經常提醒群體合作伙伴不要創建不必要的組織結構。雖然對靈長類動物的研究是被允許的,但是這類研究特別難以進行。除了幾個較老的細胞系之外,人類胚胎干細胞的使用是被禁止的。在這一點上,默克爾仍然是堅定不移的。
有關德國的數字
總的來說,一些數據表明德國在科學上處于一種積極向上的狀態(見“德國數據”圖表)。在德國的大學中,外國學者的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9.3%躍升至2015年的12.9%。目前,在引用頻次指標中占前10%的公開發表論文中,德國的排名已經超過了美國。
但是,德國在科學上仍有需要追趕的領域,特別是在大學基礎設施方面。跟非大學研究機構的現代化相比,大學的設施看起來是極為破舊的。對于越來越多的學生,各州必須要承擔所需的費用,學生是免費上學的,結果樓房的修繕工作跟不上。
在德國,幾乎沒有科學家看到該國攀越到科學界的頂峰。一方面,德語可能仍然是令人反感的,盡管在當今德國的實驗室里通常講的都是英語;規章制度和填表要求也讓許多人望而生畏。因此克魯爾說:“在某種程度上,德國人是不愿承擔風險的。在這里,激進的、突破性的創新較為少見。”
此外,在提高女性代表在研究中的占比方面,德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研究機構中,2005年具有最高科技職位的女性所占比例為4.8%,少得可憐;2016年,這一比例上升到13.7%,仍然很少。在大學,擁有頂級學術職位的女性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10%上升至2014年的17.9%,仍然遠遠低于歐盟的平均水平。在產業界,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全國30強科技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有160名,申德爾是其中僅有的3名女董事之一。
但是,科學家們普遍相信,情況將會繼續得到穩步改善。在競選宣言中,默克爾承諾要繼續支持研究和創新,并將年度預算增加到4%。只要不出差,這位總理每天都會回到她在洪堡大學附近的公寓,利用余下的夜晚時光跟她的化學家丈夫待在一起。舒斯說:“歸根結底,這就是她的根。她知道作為科學家意味著什么,她清楚研究的價值,這種風氣是自上而下蔓延開來的。”

在安格拉·默克爾的監督下,德國在能源創新方面投入巨資
[資料來源:Nature][責任編輯:田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