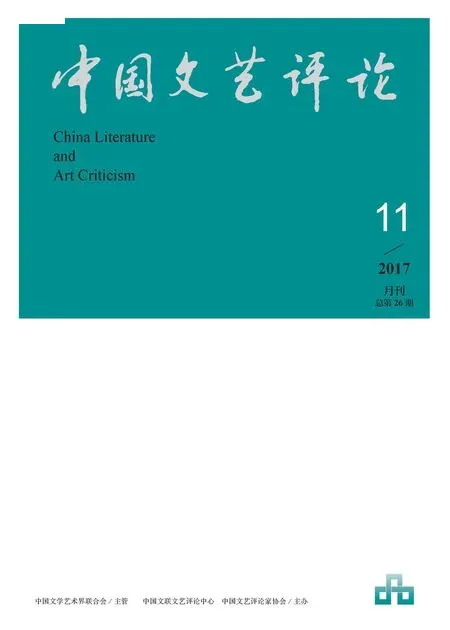警惕審美判斷與文藝評論的非本土化傾向
——從“黃賓虹的山水畫沒有造型”說開去
梅墨生
警惕審美判斷與文藝評論的非本土化傾向——從“黃賓虹的山水畫沒有造型”說開去
梅墨生
反傳統、輕視傳統的思潮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從未絕于耳。就文化藝術的審美領域言,“西化”與時勢意識形態化是數十年來的總傾向與常態。誠然在非本土化的傾向中每時每種表現都有不同,它糾纏于不同的政治背景與經濟、文化狀況。但有一點卻相同:批判本土化,抨擊傳統思想價值。就中國畫方面而言,即呈現一種文化達爾文主義思想方式,以陳舊論、過時論混淆抹滅中國哲學玄思的心靈自由與精神解放的審美品質與藝術表現。這是值得重視的傾向。
黃賓虹 中國山水畫 西方美學標準 西化 非本土化
文藝評論與審美判斷的分歧古今中外皆有,不足為奇。不過,就中國畫的審美價值論斷而言,理應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發言,筆者以為是毋庸置疑的。
前數年,筆者接到某高等美術院校教師同時為在讀中國畫專業博士生的電話,她稱:你一直說黃賓虹的畫好,我怎么覺得“黃賓虹的山水畫沒有造型”呢?看不出好來。我片刻啞然,然后回她說:因為你看畫的標準與我不同,所以才有如此判斷。看黃賓虹的畫不能用西畫“造型”的標準,中國畫有一套成熟的審美范疇與文化理念,我們更重視的是生命哲學意義的“氣化觀”,而不是西方范疇的創造模式——范型。
幾年過去,此一番電話對話帶給我的震撼余波猶在。依此邏輯,不僅黃賓虹的山水簡直一塌糊涂,由此上溯,王原祁、龔賢、石濤、八大山人、董其昌,以至王蒙、黃公望,再至米芾、米友仁、董源、巨然……由現代以至于五代時期千余年間的中國山水畫豈不是都價值黯淡——因為都缺少一種西方意義的“造型”啊!
欲辨“造型”之是非殊非易事。
簡單的道理是:造型是一切視覺藝術的基本概念,沒有“造型”怎么有繪畫?是的,作為視覺藝術的繪畫一定有造型。一個杯子、一只手、一朵花、一條狗、一塊石頭、一個院子、一條河、一座山乃至重巒疊嶂、千百群眾……
然而,進一步的道理是:作為鑄造范式的“型”字不足以牢籠界定中華文化體系概念里的“形”字——特別是與“形”相遞進的“象”。換句話說,西方意義的“造型”與中國傳統意義的“形象”并不對等,“型”是模范之式,“形”是意象之實,兩碼事兒。
自上個世紀初的“現代美術史”開始以來,隨著西方實證主義理念和科學至上思潮的深入國人之心,中國式思維或謂本土傳統式理念日漸邊緣乃至消亡。以《易經》為思維根底,以氣、意、象、境為審美概念的傳統美學標準日漸凌替而被“形式”“造型”“視覺”“圖像”類詞匯所取代。傳統的“天地意識”逐漸落地,具體化為一種造型之學。哲學玄化的世界與人天之際的意象審美被造型之學的幾何塊面與明暗光影切割得七零八落。于是,“新中國畫”以不同的表現形式紛呈,“嶺南派”的禁果初嘗、“徐蔣學派”的問鼎宗主、“新浙派人物畫”的一花獨放、“契斯恰科夫學派”的執中國畫壇牛耳、俄國“巡回畫派”的一統天下,傳統中國畫幾近美術領域的大家婢女角色而僅博得陪襯地位。
上述這種“西方美學標準”的價值確立當然是以“中華美學標準”的價值失落相映成趣的。“造型之學”的入中之勝利,也自然是以“意象之學”的失城之潰敗為結果的。百年來,中國畫的核心價值理念蕩然無存。我曾在一次小型學術會議上與著名油畫家、中國美協原主席靳尚誼先生開玩笑:若蒙上作者名款,縱齊白石、黃賓虹先生作投稿全國美展也會落選吧?靳先生笑答:很可能。問題不在于齊、黃該不該落選,而在于齊、黃所代表的傳統型中國畫的寫意表現在當代美術空間的全面失語,這是一個嚴重的藝術文化問題!不是嗎?當黃賓虹的山水畫被一個有相當知名度的畫家、教授、在讀博士視為“沒有造型”時,我的文化心理創傷難以言喻。
中華美學發源于“道”思想,先秦儒、道兩家乃為源頭活水。孔子之“志于道”與老子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莫不以“道”為尚。“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者也”(《中庸》),貫之以藝術中,則“一陰一陽之謂道”“執大象、天下往”!
莊子“游”觀,而“天下有大美而不言”。《千字文》開篇所言:“宇宙洪荒。”故山水畫之盛產于中國,乃根源于中國先民之俯仰于宇宙、游心于太玄、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之浪漫遐思。“不為物累”(莊子)的思想意識,乃在于“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超越時空的宇宙意識與心靈境界。因是而所創造之山水世界,不只是“畫”,尤重要在于由畫而“化”——“以一管筆擬太虛之體”(宋?王微《敘畫》)、“以一點墨攝山河大地”(明?李日華《畫媵》),所謂“一墨大千,一點塵劫”(明?沈灝《畫塵》)、“噓吸太空,牢籠萬有”(清?戴熙《習苦齋畫絮》),在山水林木、煙云變滅中體悟親證自然造化的奧妙偉力。一石一木、一山一水、一房一舍、一舟一橋固不可或缺,但終究不是畫旨所在,真正的山水畫旨趣在于“以蹊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絕不如畫”(董其昌)。
“筆奇造化”這是傳統山水畫勝于自然處。所謂來源生活而高于生活。
以創造范型為旨歸的西方美學,審美動機與思考方式終在“物”之實體。不唯古典寫實主義如此,便是現代派與后現代主義的表現亦不離于對實體世界的反向呈現而已。
中國畫則不然。就山水畫的美學呈現而言,由于玄思的“游”,而“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石濤畫語錄?變化章》)。“夫畫者從于心者也”(《石濤畫語錄?一畫章》)。山水林木是中國畫借用的東西,更重要的是表現藝術家的心境與情思。以傳統審美理念論,西方審美思想“為物所累”,中國審美思想乃“從心映現”。這一分歧,實是本質差別。所以說,雖同為繪畫這一付諸視覺的藝術形式,中國山水畫與西洋風景畫旨趣實在大大不同。
令人遺憾的是,時下的繪畫評論以及評獎入展等標準幾乎清一色地以西方標準為標準,把畫得像或把畫得完全不像作為取舍,拋棄了中華美學的“意象”與“境界”審美,過于關注摹仿自然或主觀臆造類山水畫,以致重大展覽呈現了比尺幅巨大、比畫面滿塞工細、比描繪再現逼真、比材料工藝制作、比形式新穎色彩鮮艷等傾向,愈來愈失卻了中國山水畫的意、象、氣、韻與趣味,寡然無味,意興索然。
黃賓虹山水畫是遙接五代兩宋以至元人精神的獨絕山水創造。有兩點十分突出而重要:
一、其畫就筆墨表現而言充分體現了唐代張彥遠“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歷代名畫論?論畫六法》)。其早年啟蒙師訓誡“作畫宜筆筆分明,如作字法”,成為其山水畫表現畢生恪守的金科玉律,而此一法理,正是與古代論家張彥遠一脈相承的。
二、其畫完美體現了清代惲格“氣韻藏于筆墨,筆墨都成氣韻”(《甌香館畫跋》)和清代石濤“筆與墨會是為氤氳,氤氳不分,是為混沌”(《石濤畫語錄?氤氳章》)之意旨,“執”了山川萬物之“大象”,故“近看不似物象,遠觀則景物燦然”(傅雷論黃畫語)。這不僅是黃賓虹的獨到特點,而且是中國山水畫親證自然神韻參至上一乘禪的活例子,衡諸千余年山水畫史,黃賓虹此一包孕陰陽功體造化之大境界、山水真境界代不數人,此正是黃賓虹高人一頭之偉大處!黃本人曾有言論:“山水乃圖自然之性,非剽竊其形。畫不寫萬物之貌,乃傳其內涵之神。若以形似為貴,則名山大川,觀覽不遑,真本俱在,何勞圖焉?”(見傅雷《觀畫答客問》)簡言之,黃作能“以有限示無限”,則豈可拘拘于形似輩可解之?質言之,黃作“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是一種登高望遠,“囊括萬殊、裁成一象”式的表現風格,意在表現不同山水精神,絕不以塑造一個模范形式為目的。知此,則知黃賓虹式的山水畫乃是“氣韻游心”“氣概成章”——不以形似、造型為理想。
無獨有偶,前些時又有名畫家著文發聲質疑黃賓虹繪畫之成就,且語多不屑……類似之批評亦常不絕于論者之口。
排除掉一些異論的某些難以言喻之心理動機,純從學術立場的否定黃畫,顯然與百年來的美術“西風壓倒東風”有關。反傳統、輕視傳統的思潮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從未絕于耳。就文化藝術的審美領域言,“西化”與時勢意識形態化是數十年來的總傾向與常態。誠然在非本土化的傾向中每時每種表現都有不同,它糾纏于不同的政治背景與經濟、文化狀況。但有一點卻相同:批判本土化,抨擊傳統思想價值。就中國畫方面而言,即呈現一種文化達爾文主義思想方式,以陳舊論、過時論混淆抹滅中國哲學玄思的心靈自由與精神解放的審美品質與藝術表現。這是值得重視的傾向。
梅墨生: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程陽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