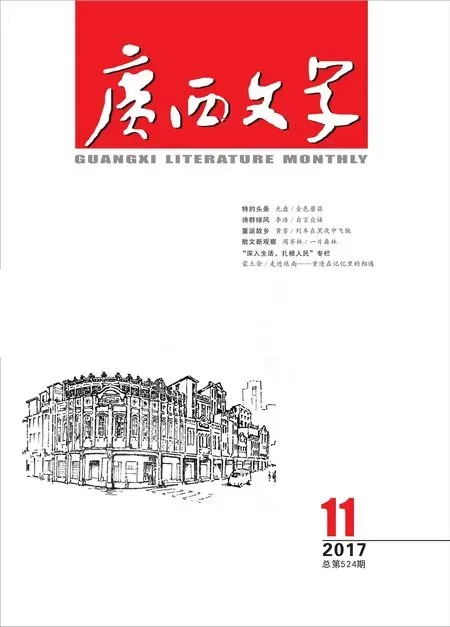散文新觀察之周齊林篇
劉 軍/著
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白話文學初期形成一股否定“父權”的潮流,“父親”形象作為腐朽、專制的封建性符號遭遇了批判性的審視,逐漸從儒家人倫秩序設定的神壇上落下。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種文學新思潮興起之際,對“父親”形象的解構從制度、人倫層面轉向了人性層面,更加暗黑的涂抹方式漸次發生。方方中篇小說《風景》中的父親是一個浸泡于碼頭文化中的惡棍形象,《在細雨中呼喊》中余華的刀鋒更加鋒利,作為一個父親,孫廣才本質上就是一個蠻橫殘暴的流氓無賴。他虐待父親,迫害兒子,侮辱兒媳。在他身上我們看不到任何作為父親本應承擔的責任,父親的形象、尊嚴、權威在此轟然倒塌。當孫光平憤怒地拿刀追趕父親時,一個忍無可忍的兒子,最終走向了弒父的道路,傳統的父權神話在此也被徹底顛覆。除了方方、余華之外,蘇童、朱文的小說中,皆有弒父主題的集中處理。盡管在后來,相關“父親”形象的建構各自有所回歸,但觀念的洗禮業已發生,作為神權符號的父親形象無疑遭受剝落,回到人本的立場上來。作為比照,散文中的父親、母親形象幾乎巋然不動。作為親情的維系與情感投射的鏡像載體,父愛與母愛的主題盡管在處理上由一味地抒情走向了豐富和駁雜,但是,“愛”的情感主題則恒定如初。考察新時期以來的散文寫作,母愛因其如一性和單向性,如同寬厚的大地,如同平靜的川流,在處理上往往沒有父愛的主題出彩,畢竟,父子之間更像是落差極大的山河,其中有飛濺,有對抗,還有特定階段發生的和解。一句話來總結,在現實關系上父子之間要比母子之間多出更多的戲劇性要素。也因此,散文中的父親形象更容易趨于厚度、深度與寬度。汪曾祺的《父子多年成兄弟》,北島的《父親》,賈平凹的《酒》,玄武的《父子多年》,龐余亮的《半個父親在痛》,李穎的《父親的三個可疑身份》,皆是書寫父親的佳作。
周齊林的《一片森林》延續了父親形象的慣性處理方式,這里出現的父親是隱忍的、沉默的,也是富于自我犧牲精神的。他的身上有兩大特性,一方面,父親作為農耕時代鄉土中國最后一抹微紅而存在,其生活歷程與精神特性具備了某種象征性。就個體而言,作品中的父親與其說是一種本我形象,不如說是一種位置和角色,是經過長期人倫規訓下群體意識的符號載體。父親始終生活在各種關系之中,而非現代性所強調的自我指向。面對當下社會的結構性劇變,父親身后崛起的新一代人,城市化、城鎮化成為必然的潮流,無論農民的身份是否得以改變,自我意識的突出以及實利主義的價值準則,必將取代人倫準則至上的信條,也將取代群體意識下的自我犧牲精神。因此,最后一抹晚霞的定義并非夸張之言。這篇散文在塑造父親形象之際,也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關系而展開,比如一以貫之的誠實守信準則,對待鄉鄰,對待父親與母親,對待兒女,父親皆是表里如一,恪守倫理要求,不越雷池,也不退后一步。另一方面,盡管有多年的外地打工經歷,但父親始終如同河南作家李佩甫筆下的人物,是一株頂著泥土在城市行走的植物,在遭遇了意外受傷、暴力脅迫、身份歧視之后,總是一個人悄悄地吸納、融化諸種傷害,回到樸素、老實本分的人生本色上來。在父親這里,苦與痛如同被咽進腸胃的食物,就是活著本身。因此,忍耐就構成了植物的某種根性,也構成了父親形象的基本文化屬性。